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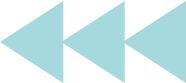
人们在使用晚期资本主义(Spätkapitalismus)这个术语时,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设:即使是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充满了矛盾”(Widerspruch)或危机(Krise)。 [1] 因此,我想先来解释一下危机概念。
危机概念在被当作科学术语使用之前是一个医学用语。在医学上,危机是指疾病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将决定身体的自我康复能力是否足以使人恢复健康。危机过程就是疾病,似乎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传染病是由外界感染身体而引发的;受到感染的身体则偏离了其正常的健康状态(Sollstand),这点可以观察出来,并能够用经验参数加以衡量。病人的意识在这里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他感觉如何,他觉得自己的病情如何,不过是他本人所遭遇的一个事件的某种症状而已,对于这个事件,他本人无能为力。尽管如此,当医学上涉及生死问题的时候,如果这仅仅是一种外在观察出来的客观过程,且如果病人在主观上并没有完全卷入这一过程,我们也就不会说这是一场危机。危机不能脱离陷于危机中的人的内心体会:面对客观的疾病,病人之所以感到无能为力,只因为他是一个陷于被动的主体,被暂时剥夺了作为一个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主体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以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当我从危机的医学概念转向戏剧概念时,这一点就变得更为清楚。在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古典美学中,危机意味着一种命定过程的转折点。尽管它具有十足的客观性,但它决不是简单地从外部强加于人身上,也不是始终外在于陷于危机的人本身。戏剧冲突的灾难性高潮中所体现出来的矛盾,是情节系统结构与主角个性系统中所固有的。如果剧中人物自身无法通过树立一种新的认同,来破除命运的神秘力量,进而重新获得自由,那么,命运也就占据了上风。命运具体表现为对打破剧中人物个性并且相互冲突的规范的揭示。
古典悲剧中所形成的危机概念和救赎历史(Heilsgeschichte)中的危机概念是一致的。 [2] 这种思维方式经过18世纪的历史哲学,渗透到了19世纪的社会进化理论。 [3] 因此,马克思首次提出了一种社会科学的系统危机(Systemkrise)概念。 [4] 我们今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讨论社会危机或经济危机的。例如,我们每每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那场全球经济危机,就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但是,我不想用另一种对马克思危机学说的阐释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救赎历史。 [5] 我的目的是要全面引入一种社会科学的危机概念。
今天的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系统论的危机概念。 [6] 根据这种系统理论,当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存所必需的限度时,就会产生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就是 系统整合 (Systemintegration)的持续失调。人们可能会否定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价值,认为它没有考虑到造成系统容纳不下(或是结构解决不了)控制能力的 内在 原因。社会系统的危机不是由于环境的突变,而是由于结构固有的系统命令(Systemimperativ)彼此不能相容,不能按等级整合所造成的。当然,只有在我们能够确定对于维持生存十分重要的结构时,才能确定结构固有的矛盾。这种结构与其他的系统因素必须区别开来。系统因素可以改变,但系统本身必须保持不变。由于很难用系统理论的语言来明确界定社会系统的界限与实存,因此,人们对系统论的社会危机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7]
人的机体具有明确的时空界限;它们维持其存在具有理想价值(Sollwerte),而这种理想价值只能在经验确定的承受限度内有所变化。相反,社会系统能够在一种高度复杂的环境中维持其存在,具体途径表现为:不是改变系统因素或理想价值,就是同时改变二者,以便把自己维持在一个新的控制水平上。但是,如果系统通过改变其界限和实存来维持其存在,那么,它们的认同就会变得模糊起来。同样的系统发生改变,既可以说是系统的学习过程和转型过程,也可以说是系统的瓦解过程和崩溃过程。究竟是有一种新的系统在形成,还是只有旧系统在更生,这是无法明确判定的。当然,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并不是所有的结构变化都会带来危机。很显然,如果社会系统的理想价值发生变化,而没有从根本上危及其实存,或没有丧失其认同,那么,就无法从系统论的客观主义立场出发,去把握这种情况的承受限度。系统不能说是主体;根据前科学概念的定义,只有主体才会被卷入危机。在社会成员感觉到结构变化影响到了继续生存,感觉到他们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我们才会说出现了危机。系统整合的失调只有在使 社会整合 岌岌可危时,即在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变得失范时,才会危及继续生存。危机状态表现为社会制度的瓦解。 [8]
社会系统也有其同一性,而且也可能会失去这种同一性;因为历史学家完全能够把国家的革命或帝国的崩溃与单纯的结构变化区分开来。他们在进行这种区分时,参照了系统成员的解释,依靠这种解释,系统成员获得了其自我认同,认为自己属于某个群体;进而用这种集体认同来捍卫其自我认同。在历史叙述中,传统断裂导致了确保认同的解释系统丧失了其社会整合的力量,因此,传统断裂是社会系统崩溃的一个标志。从这一点看,一旦后代在传统结构中再也无法确认自己,社会便失去了其认同。当然,这种唯心论的危机概念也有其弱点。起码传统的断裂不是一个精确的标准,因为传统的中介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形式本身都随历史而变化。此外,当代的危机意识往往会让后人误解。社会成员说到危机的时候,并不一定或并不总是就意味着社会陷入了危机。如果社会危机只能用意识现象来加以确定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才能把危机意识形态与实实在在的危机经验区分开来呢?
危机过程的客观性在于:危机是从无法解决的控制问题中产生出来的。认同危机与控制问题紧密相关。虽然行为主体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没有意识到控制问题的重要性,但这些控制问题造成了一些后果,对主体的意识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以至于危及到了社会整合。关键在于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控制问题。因此,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之间的联系。“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这两个概念,分别来自于不同的理论传统。我们所谓的社会整合,涉及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 [9] 我们所说的系统整合,涉及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能力。这里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它们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 生活世界 (Lebenswelt)和 系统 (System)这两个范式都很重要,问题在于如何把它们联系起来。 [10] 就生活世界而言,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是社会的规范结构(价值和制度)。我们依靠社会整合的功能(用帕森斯的话说就是:整合与模式维持),来分析事件和现状,此时,系统的非规范因素是制约条件。从系统的角度来看,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是控制机制和偶然性范围的扩张。我们依靠系统整合功能,用帕森斯(T.Parsons)的话说就是:适应与目标达成,来分析事件和现状,此时,理想价值是数据。如果我们把社会系统理解为生活世界,就会忽略控制问题;如果我们把社会理解为系统,就不会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的现实性在于虽然得到公认,但往往是虚拟的有效性要求是实际存在的。
系统论的概念策略的确也把规范结构包容在自己的语言中。但是,它是从每一种社会系统的控制中心来定义各种社会系统的。因此,在已经发生分化的社会中,政治系统(作为分化出来的控制中心),其地位高于社会文化系统
 和经济系统。图1取自一份研究材料。
[11]
和经济系统。图1取自一份研究材料。
[11]

图1 规范系统的前政治因素
社会进化表现为三个层面,即生产力的提高,系统自主性(权力)的增强以及规范结构的变化。系统论在它的分析框架内通过降低环境的复杂性,而把社会进化限制在权力增长这个唯一的层面上。卢曼对社会学基本概念的重新定义就表现出这样一种趋势。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尝试过指出
 ,如果把生活中文化再生产结构中的有效性要求,诸如真实性、正确性等,理解为控制媒介,并且把它们和权力、金钱、信任以及影响等放到同一个层面上,它们就会失去其通过话语而能够得到兑现的意义。系统论只会承认经验实践以及经验状态属于它的对象领域,因而必定会把
有效性问题
(Geltungsprobleme)转化为
行为问题
(Verhaltensprobleme)。因此,卢曼主张要对诸如认识与话语、行为与规范、统治与意识形态证明等概念重新加以定义;抛开这些概念,有机系统中的劳动与社会系统中的劳动才能区分开来(正如我所认为的,卢曼甚至想把意义和否定用作区分的基本概念)。一旦控制方面被独立出来,社会科学的对象领域也被局限于选择的潜能,那么,一种理解性的概念策略就会变成概念帝国主义,其长处也就变成了短处。
,如果把生活中文化再生产结构中的有效性要求,诸如真实性、正确性等,理解为控制媒介,并且把它们和权力、金钱、信任以及影响等放到同一个层面上,它们就会失去其通过话语而能够得到兑现的意义。系统论只会承认经验实践以及经验状态属于它的对象领域,因而必定会把
有效性问题
(Geltungsprobleme)转化为
行为问题
(Verhaltensprobleme)。因此,卢曼主张要对诸如认识与话语、行为与规范、统治与意识形态证明等概念重新加以定义;抛开这些概念,有机系统中的劳动与社会系统中的劳动才能区分开来(正如我所认为的,卢曼甚至想把意义和否定用作区分的基本概念)。一旦控制方面被独立出来,社会科学的对象领域也被局限于选择的潜能,那么,一种理解性的概念策略就会变成概念帝国主义,其长处也就变成了短处。
行为理论的概念策略尽量避免这些短处,但它还是造成了规范结构与有限的物质条件之间的背离。 [12] 在分析层面上,社会文化系统、政治系统以及经济系统等社会亚系统之间尽管存在着一种等级秩序,但是,在任何一种系统中,规范结构都必须和有限的物质基础区别开来(表1)。
表1

这种抽象的要求用对具有控制意义的限制和潜力的分析,来补充对规范结构的分析。当然,对于危机分析来说,“补充”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我在对社会系统的历史分析当中发现了这个层面;对社会系统的历史分析,使得我们能够确定一种宽容领域,从而允许一种确定的系统的理想价值有活动的空间,而又不会使该系统的持续存在受到严重威胁。这种活动空间的界限就是历史连续性的界限。 [13] 当然,规范结构的弹性,即既能有所变化,又不至于引起传统断裂的限度,并不只是依赖,或者说主要不是依赖规范结构自身的坚决要求。因为,社会系统的理想价值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价值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系统整合非规范要求的产物:在理想价值中,社会生活的文化定义与系统论对于生存命令的重构是相互联系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可靠的概念和方法来分析这种联系。
显然,我们只有在社会进化理论的框架范围内,才能为结构转型提供各种变化空间。
 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概念是很有帮助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由基本的组织原则所决定的,而这种组织原则为社会状况的改变提供了抽象的可能性。我所说的组织原则,是一些高度抽象的原则,是在巨大的进化动力中表现出来的自然特性,标志着不同阶段上的新的发展水平。组织原则限定了一个社会在不失去其认同条件下的学习能力。根据这一定义,控制问题如果在社会组织原则所允许的活动范围内得到解决,就会产生危机效应。这种组织原则首先确定的是生产力的提高所依赖的学习机制;其次,它们决定着保障认同的解释系统的活动范围;最后,它们还设定了控制能力扩张的制度界限。在用一些例子说明这一组织原则概念之前,我想用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来阐明选用这个概念的正当性。
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概念是很有帮助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由基本的组织原则所决定的,而这种组织原则为社会状况的改变提供了抽象的可能性。我所说的组织原则,是一些高度抽象的原则,是在巨大的进化动力中表现出来的自然特性,标志着不同阶段上的新的发展水平。组织原则限定了一个社会在不失去其认同条件下的学习能力。根据这一定义,控制问题如果在社会组织原则所允许的活动范围内得到解决,就会产生危机效应。这种组织原则首先确定的是生产力的提高所依赖的学习机制;其次,它们决定着保障认同的解释系统的活动范围;最后,它们还设定了控制能力扩张的制度界限。在用一些例子说明这一组织原则概念之前,我想用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来阐明选用这个概念的正当性。
[1] 奥佛(Claus Offe):“晚期资本主义——尝试对一个概念的定义”(Spätkapitalismus——Versuch einer Begriffsbestimmung),载《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问题》( Strukturprobleme des kapitalistischen Staates ),Frankfurt am Main,1972,第7页及以下诸页。
[2] 洛维特(Karl Löwith):《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 Weltgeschichte und Heilsgeschehen ),Stuttgart,1953。
[3] 德雷泽尔(H.P.Dreitzel):《社会转型》( Sozialer Wandel ),Neuwied,1967;斯克莱尔(L.Sklair):《进步社会学》( The Sociology of Progress ),London,1970。
[4] 科瑟勒克(R.Koselleck):《批判与危机》( Kritik und Krise ),Freiburg,1961;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 Theorie und Praxis ),1971,第244页及以下诸页。
[5] 策莱尼(J.Zeleny):《科学逻辑与资本》( Die Wissenschaftslogik und das Kapital ),Frankfurt,1968;赖希特(H.Reichelt):《论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 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sbegriffs bei K . Marx ),Frankfurt am Main,1970;古德里尔(M.Godelier):《〈资本论〉中的系统、结构和矛盾》( System , Struktur und Wiederspruch im Kapital ),Berlin 1970;毛克(M.Mauke):《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理论》( Die Klassentheorie von Marx und Engels ),Frankfurt am Main,1970。
[6] 耶尼克(M.Jänicke):《统治与危机》( Herrschaft und Krise ),Opaladen,1973;其中刊载有耶尼克、多伊奇(K.W.Deutsch)以及瓦格纳(W.Wagner)的文章。
[7] 哈贝马斯、卢曼:《社会理论还是社会技术学?》(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Frankfurt am Main,1971,第147页及以下诸页。
[8] 从涂尔干到默顿(Merton)的社会科学文献,以及默顿之后对于失范行为,特别是犯罪行为的研究,都阐述了这种失范(Anomie)概念。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请参阅莫泽尔(T.Moser):《少年犯罪与社会结构》( Jugendkriminalität und Gesellschaftsstruktur ),Frankfurt,1970。
[9] 伯格(P.Berger)和卢克曼(Th.Luckmann):《现实的社会结构》( Die gesellschaftliche Konstruktion der Wirklichkeit ),Frankfurt am Main,1969。
[10] 舒茨(A.Schütz)的现象学和社会控制论所表明的概念策略分别把这两个方面揭示了出来。社会科学功能论已经开始尝试关注社会的双重结构,并把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帕森斯(T.Parsons)在其《草稿》( Working Papers )中从范畴的高度把系统理论和行为理论联系起来;埃齐奥尼(Etzioni)把控制能力和共识结构看作是系统的两个方面;卢曼从系统理论的角度对现象学的基本概念“意义”(Sinn)重新进行了阐释。所有这些尝试对于如何恰当地把社会系统问题揭示出来是有启发的,但它们并没有解决社会系统问题,因为主体间性结构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也没有得到准确的把握。
[11] 奥佛:《危机与危机的控制》( Krise und Krisemanagement ),载耶尼克:《统治与危机》,第197页及以下诸页。
[12] 洛克伍德(D.Lockwood):“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载佐尔山(G.Zollschan)和赫希(W.Hirsch):《社会转型探索》( Explorations in Social Change ),London,1964。布兰特(Gerhard Brandt)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点。
[13] 鲍姆伽特纳(H.M.Baumgartner):《连续性与历史》( Kontinuität und Geschichte ),Frankfurt,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