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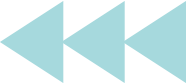
合法化危机的概念是仿照经济危机的概念而形成的。根据这一概念,相互矛盾的控制命令是通过行政人员而非市场参与者的目的理性行为而表现出来的。它们表现为不同的矛盾,直接威胁着系统整合,并从而危及社会整合。
我们已经看到,只有当政治争端(阶级斗争)维护而不是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条件时[如宪章运动(Chartistenbe wegung)和制定标准工作日],才能说是发生了一种经济系统的危机。由于阶级关系本身被重新政治化,国家既承担补充市场的任务,又承担着取代市场的任务,并造成了更加富有弹性的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因此,阶级统治可以不再采用价值规律这种匿名形式。相反,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否或如何能通过公共部门而获得保护,阶级妥协的条件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所有这些现在都要取决于实际的权力格局。由于这种变化,危机倾向尽管从经济系统转移到了政治系统,但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交换过程的自足性被破坏了。在自由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Warenfetisch)被打破,以及所有的参与者都或多或少变为价值学说的熟练实践者之后,自发的经济发展过程至少可以以次要形式在政治系统中重新确立起来,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必须保留某种自发性残余,以便使自己的计划功能不再新添任何责任,因为要承担这些责任,就必须透支财政。因此,经济危机倾向继续上升,而且继续以目的理性的方式耗费基本的财政资源。但是,如果我们不想回到各种经济原理那里,那么,国家行为也就只能在可以获得的合法性中找到必要的界限。只要动机依然依赖于需要证明的规范,把合法权力引入再生产过程就意味着:在怀疑行政行为并带来诸多实际后果的时候,“基本矛盾”(Grundwiderspruch)永远都会冲破基本的规范。如果已经成型的先验决定不能容忍相应的主题、问题和论据,那么,这种基本的规范还会继续被冲破。由于经济危机已经得到遏止,并且转化为公共预算系统的沉重包袱,因此,它也就脱掉了作为社会固有命运的外衣。如果国家对危机的控制失败了,那么它就落后于它自身所提出的一整套要求。对于这种失败的惩罚,就是合法性被撤销了。因此,行动范围正好在它急需膨胀的时候萎缩了。
这种危机原理的基础是一种一般性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社会认同是通过旨在维护系统整合的能力而间接确定下来的,在阶级结构基础上,这种社会认同往往是很脆弱的。正如奥康纳(O'Connor)所力图证明的,非普遍性利益的社会生产的基本矛盾,经过加工和转化,所产生的有争议的后果,集中表现为分层征税和对有限税收的特殊使用,因为一种避免危机的政策会耗尽和透支有限的税收。一方面,经济危机倾向经过行政和财政的过滤,使得越来越零碎化的阶级对立阵线不那么一目了然;阶级妥协削弱了潜在的阶级的组织能力。另一方面,零散的次要冲突也变得明显可见了,因为它们不是作为客观的系统危机而出现的,而是直接引起合法性问题。这就可以解释使行政系统尽可能独立于合法性系统为何在功能上具有必要性。
为了这一目的,人们把行政机关的工具功能同能够释放出一般顺从意愿的表现符号区分开来。在这方面,人们所熟悉的策略包括实际问题的人格化、象征性地听证、专家裁决、司法解释,以及从寡头垄断竞争中模仿来的广告技巧等等。这些广告技巧既肯定又利用现有的偏见结构,通过打动情感和刺激起无意识的动机等,从正面或反面来肯定某些内容,贬低另外一些内容。 [1] 为实现有效的合法化而建立起来的公共领域,其首要功能在于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定的主题上面,也就是说,把其他主题、问题和争论都排挤到一边,从而避免有关舆论的形成。政治系统承担起规划意识形态的任务(卢曼的观点)。可以肯定,这样做的时候,机动的余地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文化系统特别能抵制行政控制:意义从来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创造出来的。对符号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消耗掉虚拟的有效性规范力量。获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对合法化的追求就会不战自败。
文化传统具有自己脆弱的再生产条件。只要它们是以自发的方式形成,或者带有解释学意识(解释学作为对传统的学术解释和学术应用,具有自己的特性,它能够打破传统的自发性,并把它们保持在一种反思水平上 [2] ),它们就依然具有“活力”。对传统的批判占有,破坏了话语媒介中的自发性。因为批判的特点就在于它有双重功能 [3] :一方面,通过分析或意识形态批判,来消解无法用话语兑现的有效性要求,另一方面,它能够把传统中的语义学潜能释放出来。 [4] 就此而言,批判和解释学一样,也是一种占有传统的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被占有的文化内容都保持着其作为命令的力量。也就是说,它们保障着历史的连续性,有了这种历史的连续性,个人和群体就能够确认自身和彼此的认同。如果文化传统是以客观主义形式提供出来的,并被当作策略加以使用,那么,它就会丧失这种力量。在这两种情况下,文化传统的再生产条件就会受到破坏,传统也会受到破坏。在乐观的历史主义的展览效应中,以及在为了行政和市场目的而剥夺文化内容所产生的破坏效果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很显然,只有当传统还没有脱离保障连续性与认同的解释系统时,传统才能保持其提供合法性的力量。
因此,行政行为领域与文化传统领域之间的结构差异就构成了一种系统界限,限制着通过有意识的操纵来弥补合法性欠缺的努力。当然,如果想由此而提出危机的论据,就必须和另一个角度联系起来考虑,即国家行为的膨胀会造成对合法性需求超比例增长的这一副作用。我认为,超比例增长是有可能的,原因不仅在于行政事务的膨胀使得国家行为的新功能需要得到大众的支持,而且还在于这种膨胀导致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的界限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原来被视为理所当然并且作为政治系统条件的文化事务,便落入到行政计划领域。这样,一直避免成为社会争端,尤其是避免成为实践话语主题的传统,也就成为了议题。行政直接处理文化系统的一个例子便是教育计划,尤其是课程安排。过去,学校的行政管理只需要将自发形成的一系列规则整理成法规,而现在的课程安排的前提在于,传统模式可能是大相径庭的:在这个曾经正好具有自我合法化力量的领域,行政计划造成了一种合法化的普遍压力。 [5] 间接干扰文化自我特性的例子是地区规划和城市规划(土地的私人占有)、卫生系统的规划(“无阶级差别的医院”),以及计划生育和婚姻法(放宽了性禁忌,扩大了家庭解放的界限)等等。最终,不仅传统内涵具有了一种偶然性意识,传统的技术,即社会化的技术也具有了一种偶然性意识。早在学龄前阶段,正规学校教育就与家庭培养开始竞争。教育常识成为疑难问题,这一点在学校提高家长权力的机制化和个别咨询而承担的普及教育知识的任务中,以及在有关该问题的教育心理学的报刊文章中都可以看到。 [6]
在各种层次上,行政计划都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干扰作用和宣传效果。这些效果削弱了传统自发形成的辩护潜能。一旦传统受到破坏,而变得不再是毫无问题,有效性要求就只有通过话语才能保持稳定。因此,对文化自我特性的干扰,促进了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生活领域变得政治化。这就意味着,通过公共领域的结构而得到非正式保护的公民私人性受到威胁。积极参与的努力以及可选择模式的涌现,尤其是在学校(中小学和大学)、新闻、教会、剧院、出版社等文化领域中,正如公民请愿的数量越来越多一样,都显示了这种威胁。 [7]
由此也就可以解释人们为何要求和尝试参与到计划当中。由于行政计划越来越触及文化系统,即触及深层的规范观念与价值观念,并且使传统的立场变得摇曳不定,因此,人们的接受能力也就有了大大的提高。为了在计划过程中推行革新,行政机构试着让那些相关者参与这个过程。当然,参与政府计划的功能是模棱两可的。 [8] 于是便出现了灰色领域。在这些灰色领域里,控制冲突的需求究竟是增大了还是减小了,从一开始就是不清晰的。计划者们在计划过程中越是把自己置于共识形成的压力之下,就越可能产生一种具有相反动机的负担:一方面是谋求合法性而引起的过分要求,而行政机构在一种不对称的阶级妥协条件下是无法满足这些要求的;另一方面是对计划的保守抗拒,这就缩小了计划的范围,降低了创新的程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动机可以归入同一种对立的解释模式,因此,通过分析可以区分开来的反抗立场是由同一个派别所代表的。为了这个理由,(纳肖尔德所说的)“创造性的参与”(Produktivkraft Partizipation)是一种弥补合法化欠缺的极端手段,对于行政机构来说也是一种冒险手段。
以上所援引的这些论据都证明了一个观点,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合法化困境。然而,它们是否足以表明合法化问题不可解决,或者说,它们是否能够对预见合法化危机进行证实呢?即使国家机器能够以确保无危机但并非无干扰的经济增长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分配生产力成果,经济增长的实现依然要受制于某种优先权。这种优先权不是为了全民的普遍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利润极大化的私人目标。加尔布雷思(Galbraith)曾经从“私人财富与公共事业贫困的对立”当中来分析这种优先模式。 [9] 而这种优先模式是从一种通常处于隐蔽状态的阶级结构中产生出来的。总而言之,这种阶级结构是合法化欠缺的根源。至此,我们看到,国家不能简单地接管文化系统,国家计划领域的膨胀实际上使得文化的自主性成为了问题。“意义”是一种稀有资源,而现在变得更加稀有。因此,以使用价值为趋向的期望,即追求成功的期望,正在公众中兴起。这种要求的上涨程度是与合法化需求的增长同步进行的。财政所吮吸的“价值”资源,必然要取代有限的“意义”资源。失去的合法化必须要根据系统的要求来加以弥补。只要对这种弥补的要求比可获得价值量增长得快,或者用这种弥补无法满足新出现的期望,就会出现合法化危机。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需求水准保持在政治—经济系统运作能力的范围之内呢?需求的上升速度是可以把现存生产方式范围内的适应和学习过程完全强加给控制系统和维持系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持续的发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0] 只要社会福利国家纲领与广泛传播的专家治国论的共同意识结合在一起,并把公民的私人性维持在一个必要的水平上,对合法化的需求就不一定会导致危机;专家治国论的共同意识在遭到怀疑的情况下能够把责任推给没有受到影响的系统压力。
但是,奥佛及其合作者怀疑,这种谋求合法化的形式是否会使相互竞争的政党在其纲领中竞相抬价,从而不断地提高民众的胃口。而这可能导致在许诺与结果之间产生不可避免的鸿沟,从而引起选民的失望情绪。
 这样,民主竞争型的合法化就会产生无法负担的代价。即使这种论点具有足够的经验论据,也还需要解释为什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终究还必须保持着形式民主。如果仅仅从行政系统的功能条件来考虑,形式民主也可以被其他的民主形式所取代,比如能够把公民的政治参与减少到无损害程度的保守权威主义的社会福利国家,或者法西斯主义的极权国家。法西斯主义的极权国家无须像社会福利国家那样去透支财政,就可以把民众保持在一个较高程度的持续动员水平上。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两种国家形式显然都不如具有政党民主特征的大众民主体制那样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因为社会文化系统所提出的要求是极权主义制度所无法满足的。
这样,民主竞争型的合法化就会产生无法负担的代价。即使这种论点具有足够的经验论据,也还需要解释为什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终究还必须保持着形式民主。如果仅仅从行政系统的功能条件来考虑,形式民主也可以被其他的民主形式所取代,比如能够把公民的政治参与减少到无损害程度的保守权威主义的社会福利国家,或者法西斯主义的极权国家。法西斯主义的极权国家无须像社会福利国家那样去透支财政,就可以把民众保持在一个较高程度的持续动员水平上。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两种国家形式显然都不如具有政党民主特征的大众民主体制那样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因为社会文化系统所提出的要求是极权主义制度所无法满足的。
奥佛他们的思考支持了我的观点,即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只有当无法用现有的价值量,或一般来说,用符合系统要求的补偿来满足的期望大量而全面地出现时,才能够对合法化危机作出预测。因此,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与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1] 埃德尔曼(M.Edelmann):《政治的符号意义》(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Chicago,1964;《作为符号行为的政治》( Politics as Symbolic Action ),Chicago,1971。
[2] 伽达默尔(Gadamer):《真理与方法》( Wahrheit und Methode ),Tübingen,1969。
[3] 维尔默(A.Wellmer):《社会批判理论与实证主义》( Kritische Gesellschaftstheorie und Positivismus ),Frankfurt am Main,1969,第42页及以下诸页。
[4] 哈贝马斯:“启蒙批判还是拯救批判”(Bewusstmachende oder rettende Kritik),载:《论本雅明的现实意义》( Zur Aktualit ät Walter Benjamins ),Frankfurt am Main,1972,第173页及以下诸页。
[5] 联邦德国的讨论主要是由罗宾索恩(S.B.Robinsohn)的《作为教学理论修正方案的教育改革》( Bildungsreform als Revision des Curriculum ,Neuwied,1967)一书引起的。
[6] 奥佛曼(U.Oevermann)在他的《教育研究所研究计划》( Institut für Bildungsforschung ,Berlin,1970)中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论据。
[7] 巴尔(H.E.Bahr)编:《日常生活的政治化》( Politisierung des Alltags ),Neuwied,1972;奥佛:“公民的创造性”(Bürgerinitiativen),载:《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问题》,第153页及以下诸页。
[8] 美茵茨(R.Mayntz):“参与公共计划的功能”(Funktionen der Beteiligung bei öffentlichen Planung),载:《民主与管理》( Demokratie und Verwaltung ),Berlin,1972,第341页及以下诸页。
[9] 请参阅魏德迈耶尔(H.P.Widmaier):《社会福利国家的权力结构:雷根斯堡经济学论集》( Machtstrukturen im Wohlfahrtsstaat . Regensburger Diskussions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1973。
[10] 肖恩菲尔德(Shonfield):《现代资本主义》( Modern Capit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