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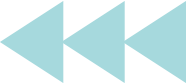
无论是把国家看作自发经济规律的无意识的执行机构,还是把国家视为联合起来的垄断资本家的计划代理人,都不足以说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由于国家已经卷入生产过程,因此,它就改变了资本实现过程本身的决定因素。在阶级妥协的基础上,行政系统获得了一种有限的计划能力。这种计划能力可以在通过形式民主获得合法性的架构内,用于被动地避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维护集体资本主义的利益一方面与个别资本集团的利益发生矛盾和竞争,另一方面与各种大众集团以使用价值为取向的普遍利益发生竞争。通货膨胀和公共财政的持续危机,取代了原来的危机循环,使之在时间上分散开来,并减少了社会后果。这种取代现象究竟标志着对经济危机的成功控制,还是标志着经济危机只是暂时转移到了政治系统中,则是一个经验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终要看间接的生产投资是否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生产率的增长,按照该系统的功能要求分布,是否足以保证大众的忠诚以及同时确保积累过程的顺利进行。政府的预算负担着越来越社会化生产的公共费用:比如,它负担着帝国主义市场策略的费用和非生产性商品需求的费用(如军备和航天事业等);它负担着与生产直接有关的基础设施的费用(如交通系统、科技进步以及职业培训等);它负担着与生产间接有关的社会消费费用(如住宅建设、交通、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它负担着社会福利,尤其是失业的费用;最后,它还负担着私人生产造成的环境恶化的外部费用。归根到底,这些开销都只能通过税收来维持。因此,国家机器同时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方面,它必须从利润和个人收入中来征集必要的税收,并合理地使用可供支配的税收,以此来避免经济成长过程中的危机。另一方面,有选择的征税,税收使用的明显次序以及行政运作本身,都应该满足随时会出现的合法性需求。如果国家不能完成前一项任务,那么,就会出现行政合理性的欠缺;如果不能完成后一项任务,就会出现合法性的欠缺(请参阅下文第六章)。
由于相互矛盾的控制命令会导致自发的商品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并且使增长充满危机,而这些控制命令又是在行政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因此就会出现合理性欠缺。关于这种改良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赫希(Hirsch)等人用科学的行政管理作为例子来加以证明。
 这种观点具有某种描述价值,因为它能够证明,权力机构几乎毫无信息能力和计划能力,彼此也不能很好地协调一致,因此它们要依赖于其服务对象所给予的信息。这样也就无法保证它们和服务对象会保持必要的距离,以作出独立的决策。个别经济部门似乎能够将某些公共行政部门据为己有,从而把个别社会利益之间的竞争转移到国家机器内部。这种危机原理目前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上,即由于一直具有私人目的的生产日益社会化,这就给国家机器带来了无法满足的矛盾要求。一方面,国家必须发挥集体资本家的功能,另一方面,只要不消灭投资自由,相互竞争的个别资本就不能形成或贯彻集体意志。这样就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命令,一方面要求扩大国家的计划能力,旨在推行一种集体资本主义的规划,另一方面却又要求阻止这种能力的扩大,因为这会危及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于是,国家机器就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一方面是人们期待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是被迫放弃干预;一方面是独立于自己的服务对象,但这样会危及系统,另一方面则是屈从于服务对象的特殊利益。合理性欠缺是晚期资本主义所陷入的关系罗网的必然后果。在这个关系罗网中,晚期资本主义自相矛盾的行为必然会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这种观点具有某种描述价值,因为它能够证明,权力机构几乎毫无信息能力和计划能力,彼此也不能很好地协调一致,因此它们要依赖于其服务对象所给予的信息。这样也就无法保证它们和服务对象会保持必要的距离,以作出独立的决策。个别经济部门似乎能够将某些公共行政部门据为己有,从而把个别社会利益之间的竞争转移到国家机器内部。这种危机原理目前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上,即由于一直具有私人目的的生产日益社会化,这就给国家机器带来了无法满足的矛盾要求。一方面,国家必须发挥集体资本家的功能,另一方面,只要不消灭投资自由,相互竞争的个别资本就不能形成或贯彻集体意志。这样就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命令,一方面要求扩大国家的计划能力,旨在推行一种集体资本主义的规划,另一方面却又要求阻止这种能力的扩大,因为这会危及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于是,国家机器就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一方面是人们期待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是被迫放弃干预;一方面是独立于自己的服务对象,但这样会危及系统,另一方面则是屈从于服务对象的特殊利益。合理性欠缺是晚期资本主义所陷入的关系罗网的必然后果。在这个关系罗网中,晚期资本主义自相矛盾的行为必然会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下面我想列举针对这种论点所出现的三种反对意见:
(1)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经济系统转移到了行政系统,有可能解决这些矛盾的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在经济系统中,矛盾直接表现为价值量之间的关系,间接表现为由资本损失(破产)和剥夺生存手段(失业)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在行政系统中,矛盾表现为不合理的决策和行政失误所导致的社会后果,即生活领域的瓦解。破产和失业说明未完成功能所带来的风险到了一个极限。相反,生活领域的瓦解则是一个连续过程,而且很难说出什么是忍耐的界限,也很难判断对于能够忍耐以及已经觉得无法忍耐的情况的感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应越来越无序的环境。
(2)更重要的是,在经济系统中,策略行为的规划同得失的尺度一样,是已经确定的。交换媒介不允许通过经常调整行为来使冲突得到解决。收益最大化的控制原则是不可动摇的。相反,行政系统则以妥协为原则,与它所依赖的环境进行协商。“讨价还价”(bargaining)的目的是强行让双方互相适应期待结构和价值系统。实行躲避政策的回应方式,体现了国家机器机动能力的有限性。国家能够使其谈判伙伴认识到,大众的普遍利益是如何有别于有组织的个人利益,以及如何有别于集体资本主义在维持系统存在方面的利益。但是,使用合法权力就必须考虑不同利益领域之间的合法性差异。而这种差异是已经完全合法化的交换系统所没有的。
(3)最后,危机倾向可以通过个体市场参与者的特殊行为表现出来,但无法以同样的方式,通过无意识的集体行政行为表现出来。因为,对于权力行使这一中介来说,自发的过程和计划之间的区别不再那么鲜明,正如在策略博弈中,有意识地遵守规则可能会带来意料以外的副效应。相反,避免危机被概括为行为目标。由于决策过程处于自发性与计划性之间,因此,行政系统及其谈判伙伴所遵循的就是这种独特的证明方式:每一次,人们所要求或所希望的行政行为,都是用一种从行为角度提出的系统合理性来加以证明。
 也就是说,是用系统功能的控制行为来加以证明;控制行为所发挥的是一种虚构的功能,由于没有一个参与者驾驭了系统,因此也就没有谁能够履行这种功能。政治妥协与市场支配系统中的经济决策一样,不能构成一个用目的理性的个人行为所编制起来的近乎自然的环境。因此,在集体资本主义计划与投资自由之间,在需要计划与拒绝干预之间,在国家机器的独立自主与国家对私人利益的依附之间,逻辑上都没有什么必然的利益冲突。逻辑上根本就不排除有下述可能性的存在,即行政系统可能会为相互竞争的要求找到一条妥协的路子,从而使得组织永远都有充分的合理性。
也就是说,是用系统功能的控制行为来加以证明;控制行为所发挥的是一种虚构的功能,由于没有一个参与者驾驭了系统,因此也就没有谁能够履行这种功能。政治妥协与市场支配系统中的经济决策一样,不能构成一个用目的理性的个人行为所编制起来的近乎自然的环境。因此,在集体资本主义计划与投资自由之间,在需要计划与拒绝干预之间,在国家机器的独立自主与国家对私人利益的依附之间,逻辑上都没有什么必然的利益冲突。逻辑上根本就不排除有下述可能性的存在,即行政系统可能会为相互竞争的要求找到一条妥协的路子,从而使得组织永远都有充分的合理性。
鉴于这些反对意见,人们当然会试着为行政系统建立另一个层次上的自发性。就不可逆料的后果问题而言,官僚机构独自推行的各种资本主义计划与根据话语意志形成的民主计划形式之间是有区别的。 [1] 这些不可逆料的问题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加以处理,而且它们也有可能会集中到一起,以至于最终即使靠“时间”也无法解决。这种危机原理或许可以转述如下:这种次要形式的自发性(Bewusstlosigkeit)造成一种表象,国家机器必须退缩在这种表象背后,以便最小限度地削弱用于补偿积累过程中被剥削的受害者所需要的开支。即使在今天,资本主义的增长也是靠企业的集中以及资产的集中与转移来实现的。 [2] 这就使得剥夺和重新分配资本成为一种常规现象。正是这种常规性成为了问题,因为国家提出要求承担计划权威的角色,而那些受害者便能把自己的损失转嫁到国家头上,并且向国家提出预防和补偿的要求。这种机制的有效性就反映在诸如结构政策中。由于经济资源不足以充分弥补资本主义的增长对资本家的损害,因此就产生了进退维谷的困境,要么使国家不再承担这种角色,要么阻碍成长过程。第一种方法会产生新的难题。为了保证积累过程顺利进行,国家必须承担越来越明显的计划功能。但是这些功能不应被公开视为国家所应有的行政行为,否则国家就负有补偿的责任,而这将妨碍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合理性危机原理依然依赖于关于资本主义增长的经济瓶颈的经验假设。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急剧上升的计划需求会造成新的瓶颈,而这并非是系统所特有的。复杂社会中的长期计划使得每一个行政系统,不仅仅是晚期资本主义的行政系统,都面临着结构困境;对于这种结构困境,沙普夫(F.W.Scharpf)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作出了深刻的阐述。 [3] 我倾向于认为,并非每一种渐进主义(Inkrementalismus)本身都反映负担过重的行政机构缺少合理性。所谓渐进主义,是一种着眼于中期目标的计划,对外部的影响非常敏感。必要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为下面这种躲避行为的合理性界限提供合乎逻辑的证明:这种躲避行为必然要研究各种利益的相容性(Kompromissfähigkeit),但不能预先让公众讨论这些利益的普遍性(Verallgemeinerungsfähigkeit)。晚期资本主义对合理性的限制在于,有一种计划类型在结构上是不被接受的。这就是按照芬克(R.Funke)所说的民主渐进主义。 [4]
行政计划缺少合理性是一种必然会发生的趋势,对此,奥佛提出了另一种更有创见的论据。奥佛认为,有三种倾向可以证明,系统异质因素的扩散是系统本身所不可避免的。这些倾向所涉及的是价值趋向模式的扩散,这就使得符合系统要求的行为控制难以为继。

(1)制定商业策略的有效条件在由公共部门和垄断部门组织起来的市场中发生了变化。大公司在进行决策时,在时间上和物质上都有极大的选择余地,这就使得投资政策——这种投资政策需求有更多的条件作为论证基础——取代了由外部因素所决定的理性选择。因此,高级管理阶层必须采用评估和决策的政治模式,而不是采用预先规定确定的行为策略。
(2)与公共部门功能紧密相关,出现了一些职业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具体劳动,即以使用价值为趋向的劳动,越来越取代抽象劳动;这点同样也适用于官僚机构中负责计划任务的雇员,适用于公共服务部门(如交通、医疗、住宅建设以及休闲等),适用于科学和教育系统,适用于研究和技术发展部门。极端的专业主义(Radical Professionalism)表明,这些领域中的职业劳动可以脱离私人的奋斗模式和市场机制,而具有一定的目标。
(3)非就业人口不是由劳动市场再造出来的,他们与有职业的人口一起在增长。非就业人口包括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失业者、靠养老金生活的人、社会救济对象、无专长的家庭主妇、病人以及犯人等。这些群体同那些在具体劳动条件下兴起的群体一样,也会形成一定的价值取向模式。
随着生产的不断社会化,资本主义就业系统中的这些“异物”(Fremdkörper)对行政计划产生了一种限制作用。为了照顾到私人企业的投资自由,资本主义的计划采取的是一种宏观调控手段,通过改变外部条件来影响其对象的行为。资本主义计划根据系统要求所能改变的参数,如利润率、税收、津贴、商业佣金、收入的二次分配等等,通常都是表现为货币量。正是这些货币量失去了其控制作用,于是,交换价值也就越来越丧失其抽象的指导作用。国家干预加快了生产的社会化,它所带来的后果于是也破坏了国家干预本身的重要手段所得以施展的条件。当然,这不是什么逻辑上的矛盾。
上述三种倾向说明,积累过程是通过交换之外的媒介而实现的。但是,曾经具有市场合理性的决策现在所具有的政治特性,某些职业的政治化以及那些无收入者与市场无关联的社会化等等,所有这些并非必然会缩小行政机构的活动空间。在某些前提下,甚至参与也能比由外部刺激所引起的行为反应更有助于贯彻行政计划。 [5] 只要这些发展在实际上造成了与危机相关的瓶颈,那么,关键就不在于计划缺少合理性,而在于动机机制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也就是说,行政机构没有能够动员其合伙人一起合作。概要来说,当外部刺激的控制手段在原来能行之有效的行为领域中遭到失败时,晚期资本主义不一定会受到损害。但是,当行政系统不再能够承担维持生存的重要计划功能时,晚期资本主义就会陷入困境。行政系统之所以不再能够承担重要的计划功能,原因在于,不管采用何种手段,它都无法控制对于计划有重要意义的行为领域。但是,这种诊断不能根据行政合理性的减弱来加以推导,而至多只能从系统所必需的动机机制的衰弱中得出。(请参阅第二部分第七章)
[1] 科恩(St.Cohen):《现代资本主义计划》( Modern Capitalist Planing ),Cambridge,1969。
[2] 阿恩特(H.Arndt):《西德经济的集中趋势》( Die Konzentration der westdeutschen Wirtschaft ),Pfulligen,1966;胡夫施密特(J.Hufschmid):《资本政策》( Die Politik des Kapitals ),Frankfurt,1970;科尔科(G.Kolko):《美国的财富与权力》( Besitz und Macht ),Frankfurt am Main,1967。
[3] 沙普夫(F.W.Scharpf):“作为政治过程的计划”(Planung als Politischer Prozess),载:《论管理》( Die Verwaltung ),1971;“作为政治计划限制的复杂性”(Komplexität als Schranke der Politischen Planung),载:《政治季刊》( PVJ ),1972,第168页及以下诸页。
[4] 芬克(R.Funke):《论计划的合理性》( Exkurs über Planungsrationalität ),手稿,MPIL,和《计划管理的组织结构》( Organisationsstrukturen planender Verwaltung ),Darmstadt,1973。
[5] 纳肖尔德(F.Naschold):《组织与民主》( Organisation und Demokratie ),Stuttgart,1969;“复杂性与民主”(Komplexität und Demokratie),载:《政治季刊》,1968,第494页及以下诸页。请参阅卢曼的批评,载:《政治季刊》,1969,第324页及以下诸页,以及纳肖尔德的回应,同上,第326—327页。此外还可参阅S.斯特里克(Sylvia Streeck)和W.斯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政党制度及其现状》( Parteisystem und Status quo ),Frankfurt am Main,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