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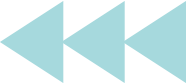
即使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市场也没有独立承担起社会整合的功能。只有在国家能够满足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前提之后,阶级关系才会表现为非政治性的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只有当国家具有补充市场机制而非从属于市场机制的功能时,才有可能通过私人对社会生产剩余价值的占有造成非政治统治。资本是在个别资本(最初)无限竞争过程中形成的。但是,维持这种竞争的条件或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基础本身的再生产却不可能用资本手段来实现。它们需要一种与个别资本相对应的非资本家的国家发挥强制性作用,充当代理角色,贯彻竞争领域所无法形成的“集体资本主义意志”。就其非资本主义手段而言,国家限制着资本主义生产;就其功能而言,国家又维持着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当国家对经济进行补充的时候,国家才可以说是经济的工具。 [1]
这种观点也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 [2] 当然,根据这个观点,今天的国家不可能仅限于满足生产的一般条件。它还必须对再生产过程本身进行干预,也就是说,它必须为闲置的资本创造利用的条件,提高资本的使用价值,控制资本主义生产的后果和代价,调整阻碍增长的比例失调,通过社会政策、税收政策和商业政策等来调节整个经济循环过程等等;但是,国家干预所发挥的始终还是一种非资本家的工具作用,它所承担的是代理角色,从而推行集体资本主义的意志。
根据这种正统观念(orthodoxe Position),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也一直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恩格斯语),因为它无法终止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它能够限制资本主义生产,但它不可能像集体资本主义的计划权威那样控制着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干预主义的国家确实是进入了再生产过程;因此,它不仅保障着生产的一般条件,而且本身也变成了价值规律的一种执行机构。国家行为没有终止价值规律的能动作用,而是听从于价值规律。因此,从长远角度看,行政行为必然会强化经济危机。
 正如马克思以当代英国劳动保护法为例所指出的那样,阶级斗争虽然能够导致符合雇佣工人利益的法规,但也依然是“资本运动的要素”
正如马克思以当代英国劳动保护法为例所指出的那样,阶级斗争虽然能够导致符合雇佣工人利益的法规,但也依然是“资本运动的要素”
 。
。
由此看来,政府功能取代市场功能,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整个经济过程的无意识特性。这点可以从政府调控活动空间的有限性中看出来。国家不能对产权结构进行实质性干预,否则就会引起“投资中断”。从长远看,它也不能消除积累过程的周期性紊乱,即内生的停滞(萧条)倾向。它甚至也不能有效地控制住替代性危机,如经常性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
反对这种观点的人一般都认为,阶级结构是否已经改变,以及是如何改变的,这一问题只能用经验来回答,而不能预先在分析层次上加以确定。把价值学说的概念策略绝对化,就使得经济危机理论无法接受经验的检验。马克思希望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形成的运动规律加以分析,由此来掌握整个社会系统的危机发展模式(包括政治斗争和国家机器功能),但他在论证时也只能指出,阶级统治的实现是采取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非政治形式。然而,自从维持合法统治的社会整合功能不再通过市场的系统整合功能和前资本主义传统的腐朽残余来实现,而是再次被纳入政治系统,这种难以置信的格局就发生了变化。由于政府现在极力实现控制系统的明确目标,以避免危机,从而使阶级关系丧失了其非政治形式。因此,阶级结构必然是通过围绕着如何使用行政手段对社会产品的增值部分进行分配的斗争来加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阶级结构就会直接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于是,经济过程不能再被认为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经济系统的内部运动。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统治差不多已经具有非政治形式。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价值规律才能把交换过程的二元性(控制过程和剥削过程)表现出来。但是,经济过程如何行使权力,行使到什么程度,如何确保剥削,确保到什么程度等,这些问题今天则要看具体的权力格局来决定了,具体的权力格局已不再是由劳动市场的自发机制所预先决定的。今天,国家必须承担一些功能。这些功能既不能用维持生产方式的必要前提来加以解释,也无法从资本的内部运动中推导出来。资本的这种内部运动不再是通过可以用价值学说来把握的市场机制而实现的,而是一直发挥作用的经济动力和政治反向控制的产物;政治反向控制体现的是生产关系的位移。
为了更准确地理解生产关系的位移,我认为有必要根据与经济系统的要求之间的关系,把国家行为分为以下四类,以便加以分析:
1. 要想建构和维持生产方式,就必须实现确保存在的前提条件:国家保护民法系统及财产和契约自由等核心制度;国家保护市场系统,消除其自我毁灭的副作用(比如,实行标准工作日、制定反托拉斯法、稳定货币系统等);国家满足整个经济生产的前提条件(比如教育、运输和交通等);国家大力发展本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能力(比如,贸易政策和关税政策等);国家对外使用军事力量来维护国家的完整统一,对内则对制度的敌对力量进行军事镇压,以此来实现自身的再生产。
2. 资本的积累过程要求法律系统适应产业组织、竞争、融资等新形式(比如,在银行法和商业法中制订新的法律内容,调节税收制度等)。在此过程中,国家应当把自己限定在通过补充市场而适应发展过程,国家不能直接推动发展过程,只有这样,社会的组织原则和阶级结构才会保持不受影响。
3. 国家补充市场行为应当与国家取代市场的行为区别开来。国家取代市场的行为并没有从法律的角度考虑到独立发生的经济态势,而是在对经济动力的弱点作出反应时,使得依靠自身的动力无法再自发前进的积累过程持续发展下去,由此创造新的经济态势,其方式或者是创造和改善投资机会(如政府对非生产性商品的需求),或者是改变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如科技进步的政府组织、劳动力的职业培训等)。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的组织原则都受到了触动,这点我们在系统之外的公共部门的兴起中看得清清楚楚。
4. 最后,国家对积累过程的功能失调所带来的后果作出补偿,因为这些后果在个别资本团体、有组织的劳工或其他有组织的团体之中引起了政治反应。因此,一方面,国家承担私人企业所导致的外部损失(如环境破坏),或通过结构性政策措施保障受到威胁部门的生存能力(如采矿业和农业)。另一方面,国家根据工会和改良主义政党的要求进行调节和干预,以改善工人的社会依附状况。从历史上看,这种调节和干预始于工人争取结社权利,后来扩大到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社会福利,乃至制定教育政策、卫生政策和交通政策。今天被划入“社会费用”(social expenses)和“社会消费”(social consumption)项目的国家开支
 ,其起源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工人组织要求在政治上实现其使用价值。
,其起源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工人组织要求在政治上实现其使用价值。

后两类国家行为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以上所提出的区分在很多情况下很难从经验中得出,原因在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也承担着前两类任务,而且它是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承担着这两类任务,当然,它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新添的任务。譬如,货币政策在今天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核心部分,尽管确保货币和资本的国际流通以及对这种流通的反应都属于建构生产方式的行为。区分的标准不是国家行为的范围和手段,而是它的功能。如果我们的模型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说,自由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行动,是保障生产方式继续存在所必需的前提,而且通过补充市场机制,来满足由市场控制的积累过程的需求。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也这么做,甚至在范围上要更大一些,手段上也更有效一些。但是,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要想完成这些任务,就必须同时填补市场的功能空缺,干预积累过程,并对其政治上的沉重后果加以补偿。在这些行为中,阶级结构的变化引起了注意,也就是说,形成了另一种权力格局。其结果是,从根本上要依赖无组织的劳动市场制度化的社会组织原则也受到了影响。
总之,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出以下三种特征:
(1)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发生了变化,这就影响到了社会组织原则;
(2)出现了一种准政治性的雇佣结构,这就表现出了一种阶级妥协;
(3)政治系统的合法性需求有所增加,这就使得以使用价值为取向的需求起了作用,这种需求可能会与实现资本的需求产生竞争。
关于(1):公共部门的兴起也表明,国家开始关注集体消费的商品的生产。国家以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基础设施形式,把这些集体消费的商品提供给私人使用,以达到节约的目的。
[3]
在履行这种职能时,国家提高了个人资本的使用价值,因为集体消费的商品主要是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价值学说角度来看,这种情况表现为不变资本发生贬值,剩余价值率则有所提高。
[4]
国家对教育系统的组织,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而提高了人类劳动的生产率,也取得了同样的效果。
[5]
这样,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就发生了变化。
[6]
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提高绝对剩余价值主要靠榨取体力,延长劳动时间,雇佣廉价劳动力(妇女和儿童)等。这些做法有一个自然极限,标准工作日的规定就表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相对剩余价值,主要采取的形式包括:利用现有的或外部的发明和信息,来发展技术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力。只有在政府有组织的发展科技事业,以及不断扩大教育系统的情况下,能够提高生产力的信息、技术、组织和职业素质等因素才会成为生产过程本身的因素。反思性劳动(reflexive Arbeit),即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施加于劳动的劳动,第一次能够被视为一种集体的自然商品。今天,它已经融入经济循环当中。因为国家(或私人企业)现在已经投资购买科学家、工程师和教师等间接生产性劳动力,把他们的劳动成果转变为上述范畴下的节约成本的商品。
 如果我们恪守教条主义概念方针,把反思性劳动视为(马克思所说的)非生产性劳动,那么,我们就会忽略这种劳动对于资本实现过程的特殊功能。从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角度来看,反思性劳动不具有生产性。但是,它也并非没有生产能力,否则,它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不会产生任何重大影响。马克思准确地看到:即使执行职能的资本量已给定,资本所合并的劳动力、科学和土地(经济学上所说的土地是指独立于人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条件),也会成为资本之有伸缩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定限度内使资本具有一个不依赖于它本身的量的作用范围。但是,他把“科学”看作是像“土地”一样,是一种无偿的集体商品,而没有把在其生产中所耗用的反思性劳动视为一种真正的生产要素。作为支付反思性劳动工资的可变资本,是一种间接的生产性投资,因为它全面改变了从生产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的条件。因此也就间接促进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思考一方面说明,古典价值学说的基本范畴已不能满足对国家的教育政策以及科技政策进行分析的需要。另一方面还说明,新的剩余价值生产形式是否能够补偿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也就是说,是否能制止住经济危机,是一个经验性问题。
如果我们恪守教条主义概念方针,把反思性劳动视为(马克思所说的)非生产性劳动,那么,我们就会忽略这种劳动对于资本实现过程的特殊功能。从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角度来看,反思性劳动不具有生产性。但是,它也并非没有生产能力,否则,它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不会产生任何重大影响。马克思准确地看到:即使执行职能的资本量已给定,资本所合并的劳动力、科学和土地(经济学上所说的土地是指独立于人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条件),也会成为资本之有伸缩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定限度内使资本具有一个不依赖于它本身的量的作用范围。但是,他把“科学”看作是像“土地”一样,是一种无偿的集体商品,而没有把在其生产中所耗用的反思性劳动视为一种真正的生产要素。作为支付反思性劳动工资的可变资本,是一种间接的生产性投资,因为它全面改变了从生产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的条件。因此也就间接促进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思考一方面说明,古典价值学说的基本范畴已不能满足对国家的教育政策以及科技政策进行分析的需要。另一方面还说明,新的剩余价值生产形式是否能够补偿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也就是说,是否能制止住经济危机,是一个经验性问题。

关于(2):在垄断部门中,企业组织与工会实现了合作,这就导致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是经过准政治谈判确定的:在这些“劳动市场”上,竞争机制被国家赋予合法权力的组织之间的妥协所取代了。这种对劳动市场机制的侵蚀自然带来了经济后果(如把某些成本的增高转嫁到价格上)。但是,这些后果实际上是一种非政治性的阶级关系被终止所带来的。由于“政治性”工资
 是劳资双方经过协商而确定的,因此,主要在资本密集和成长迅速的经济部门中,人们能够缓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造成局部的阶级妥协。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原则上是可以在价值学说的框架内,来分析有组织的市场上的权力价格形式,因为商品可以按高于其本身价值的价格来出售。但是在这里,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是价值计算的单位尺度。因此,不能用类似的方式来对待劳动市场上的准政治性的价格形式;因为就其本身而言,它是通过平均工资水平来决定价值量的,劳动力高于价值出售的偏离量必须根据这种价值量来加以衡量。我们还不知道劳动力再生产独立于文化规范之外的成本标准,马克思也没有从这种脱离文化规范的标准为出发点。
是劳资双方经过协商而确定的,因此,主要在资本密集和成长迅速的经济部门中,人们能够缓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造成局部的阶级妥协。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原则上是可以在价值学说的框架内,来分析有组织的市场上的权力价格形式,因为商品可以按高于其本身价值的价格来出售。但是在这里,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是价值计算的单位尺度。因此,不能用类似的方式来对待劳动市场上的准政治性的价格形式;因为就其本身而言,它是通过平均工资水平来决定价值量的,劳动力高于价值出售的偏离量必须根据这种价值量来加以衡量。我们还不知道劳动力再生产独立于文化规范之外的成本标准,马克思也没有从这种脱离文化规范的标准为出发点。
 当然,人们可以恪守一种教条的概念方针,通过确定平均工资,来计算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但是,这种做法会使人们在分析层面上对主要是经验性的问题带有偏见。这个经验性的问题就是,政治和工会组织起来的阶级斗争是否仅仅由于在某种经济学意义上取得成功,并且明显地改变了剥削率而使工人阶级中最有组织的部分获得好处,从而对系统产生一种稳定效果。
当然,人们可以恪守一种教条的概念方针,通过确定平均工资,来计算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但是,这种做法会使人们在分析层面上对主要是经验性的问题带有偏见。这个经验性的问题就是,政治和工会组织起来的阶级斗争是否仅仅由于在某种经济学意义上取得成功,并且明显地改变了剥削率而使工人阶级中最有组织的部分获得好处,从而对系统产生一种稳定效果。
关于(3):最后,生产关系之所以也发生了变化,是由于交换关系为行政权力所取代是和下列条件相关的,即合法权力必须用于制定行政计划。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增添了功能,用行政手段处理的社会事务也增多了,这就增加了对合法化的需求。这点毫无神秘之处。对合法化的需求是从填补市场空缺的行政系统明显的功能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自由资本主义是以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建构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说明这一点。因此,今天有必要用(基于普选权基础之上的)政治民主来满足对合法化的需求。反之,那种完全把资产阶级民主视为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上层建筑的教条主义观念,也就忽略了这个特殊问题。由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单纯是非政治性阶级关系的上层建筑,因此,获取合法性的形式民主手段也就的确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系统被迫使用现成的控制手段,来满足以使用价值为取向的需求。只要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自身还能够产生一种有生命力的意识形态,就不会出现相应的合法性问题,这种问题为解决资本实现问题设下了限制性条件。新的合法化问题不能被归入过于一般化的自我维持的命令,因为如果不考虑对合法的要求,即对使用价值的分配的满足,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对资本实现的兴趣正是禁止人们考虑这一点。合法化问题不能归结为资本实现问题,因为阶级妥协一直被当作再生产的基础,所以,国家机器必须在下述限制性的条件中完成自己在经济系统中的任务,即必须同时保证形式民主架构内的大众忠诚,并使之与普遍主义有效的价值系统相一致。这种对合法化的压力只有通过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各种结构才能得到缓和。由结构所保障的公民私人性,成为维持继续生存的必要条件,因为没有其他功能能够取而代之。因此,就出现了一种用正统观点无法把握的新型的危机。
关于经济危机理论,民主德国(DDR)的知名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种修正主义观点。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 [7] 没有受到上述观点的反驳,因为它假设,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自发性已经被国家垄断计划所取代;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被中央对生产机构的控制所取代。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导致了大公司的个别利益与维持该系统的资本主义整体利益趋于一致。由于该系统的继续生存受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和超越系统的内部力量双方面的威胁,因此,这种趋向还在继续发展。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的整体利益。垄断集团联合起来,依靠国家机器,有意识地追求这种整体利益。与这种新的意识相对应的应当是资本主义的计划。资本主义的计划使投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市场机制”,从而保障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有一种代理理论(Agenturtheorie)所阐述的就是垄断集团权力与国家机器权力之间的形式结合。据说整个社会的控制中心置于资本主义整体利益之下,具体途径是一种控制生产的组织形式(本身还在循序渐进)依然与资本实现这一目标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阶级关系公开地重新政治化,使得国家垄断统治容易受到(按照人民阵线模式组织起来的)民主力量所施加的政治压力的影响。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其前提同样也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新的组织形式中并没有被克服,而是被加剧了。不过,经济危机此时采取了一种直接的政治形式。
针对这一理论,出现了两种反驳意见。 [8] 第一种意见认为,不管代表何种利益,国家机器都能够积极地制定计划,提出和贯彻一种集中的经济策略;这是无法用经验来加以证明的。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和西方的专家治国论一样,没有能够正确地认识到,晚期资本主义的行政计划是有界限的。负责计划的官僚机构的举措只是为了消极地避免危机。而且,不同的官僚机构之间也不完全协调一致。由于缺乏敏感度和计划能力,它们受到了其主顾的左右。 [9] 正好是由于政府行政缺乏足够的合理性,才使得有组织的特殊利益集团会获得成功。这样,资本主义局部利益之间的利益,资本主义局部利益与资本主义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系统所特有的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矛盾等等,都转移到了国家机器当中。
第二种意见认为,所谓国家是联合起来的垄断集团的代理人的观点,也是没有经验依据的。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与西方精英理论一样,高估了个人交往以及行为彻底规范化的意义。对于各种权力精英集团的来源、构成以及互动的研究,不足以解释经济系统与行政系统之间的功能联系。
 在我看来,奥佛及其合作者所提出的系统论模型似乎更有说服力一些。这个系统论模型将行政系统的结构同解决冲突和形成共识的过程、决策及其执行过程区分开来。奥佛认为,“结构”是一组积淀而成的选择规则。这些规则能够预先决定,什么是公认需要调控的。什么是应该考虑的主题,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管理渠道,什么是应该优先加以考虑的以及通过何种渠道优先加以考虑等等。行政行为模式能够相对稳定地有所取舍,这客观上对资本的运作是有影响的,所谓客观,是说这些行为模式与行政部门公开承认的意图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它们可以用选择规则(Selektionsregeln)来加以解释,因为选择规则预先决定了对于问题、主题、论证以及利益是予以考虑还是加以压制。
在我看来,奥佛及其合作者所提出的系统论模型似乎更有说服力一些。这个系统论模型将行政系统的结构同解决冲突和形成共识的过程、决策及其执行过程区分开来。奥佛认为,“结构”是一组积淀而成的选择规则。这些规则能够预先决定,什么是公认需要调控的。什么是应该考虑的主题,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管理渠道,什么是应该优先加以考虑的以及通过何种渠道优先加以考虑等等。行政行为模式能够相对稳定地有所取舍,这客观上对资本的运作是有影响的,所谓客观,是说这些行为模式与行政部门公开承认的意图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它们可以用选择规则(Selektionsregeln)来加以解释,因为选择规则预先决定了对于问题、主题、论证以及利益是予以考虑还是加以压制。

[1]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阐述了这一概念。也可参阅普兰查斯(N.Poulantzas):“资本主义国家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载:《新左派评论》( New Left Review ),1969,第67页及以下诸页。
[2] 穆勒(W.Müller)、钮苏斯(Ch.Neusüss):“社会福利国家的幻觉”(Die Sozialstaatsillusion),载 SoPo ,1970,第4页及以下诸页;阿尔特瓦特(E.Altvater):“关于国家干预主义的若干问题”(Zu einigen Problemen des Staatsinterventionismus),载耶尼克:《统治与危机》,第170页及以下诸页。
[3] 马蒂克(P.Mattick):《马克思与凯恩斯》( Marx und Keynes ),Boston,1969,第128页及以下诸页,第188页及以下诸页;罗德尔(V. Rödel):《研究的优先性与技术的发展》( Forschungsprioritäten und technologische Entwicklung ),Frankfurt am Main,1972,第32页及以下诸页。
[4] 霍兰德(H.Holländer):《利润率下降的规律》( Das Gesetz des tendenziellen Falls der Profitrate ),Regensburg,1972,经济学论丛。
[5] 阿尔特瓦特、徽斯肯斯(F.Huiskens):《教育部门的政治经济学论集》( Materialien zu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s Ausbildungssektors ),Erlangen,1971。
[6] 松莱特(A.Sohn-Rethel):《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二元性》( Die ökonomische Doppelnatur des Spätkapitalismus ),Neuwied,1972。
[7] 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中央委员会编:《当代帝国主义》( Imperialismus heute ),Berlin,1965;京德尔(R.Gündel)、海宁格(H.Heininger)、赫斯(P.Hess)、齐尚(K.Zieschang):《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 Zur Theorie des staatsmonopolitischen Kapitalismus ),Berlin,1967。
[8] 沃特(M.Wirth):《民主德国的资本主义理论》( Kapitalismustheorie in DDR ),Frankfurt am Main,1972。
[9] 赫希(J.Hirsch):“晚期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国家管理功能的改变”(Funktionsveränderungen der Staatsverwaltung in spätkapitalistischen Industriegesellschaften),载:《德国政治与国际政治集刊》(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1969,第150页及以下诸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