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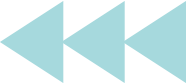
晚期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给国际社会(Weltgesellschaft)带来了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不能说是系统所特有的危机现象,但是,解决这些危机的可能性却受到系统的特殊限制。这里我所说的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人格系统一贯要求的损害(异化),以及对国际关系所造成的巨大压力。由于国际社会系统变得愈益复杂,其边界范围已经远远地推进到了其周围环境之中,以至于外部自然和内在自然都达到了承受的极限。生态平衡为增长规定了一个绝对的界限;不那么明显的人类学平衡则规定了另一个界限,如果逾越后一个界限,就会付出改变社会系统的社会文化认同的代价。最后,国际平衡中自我毁灭的危机是一个能够带来破坏力的生产力发展的后果。
如果说,经济增长在抽象层面上可以归结为:为了提高人类劳动的生产率,通过技术而越来越多地利用能源,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特点就在于,它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解决比较突出。当然,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增长自发地获得了制度化,以至于根本不存在任何自觉控制该过程的可能性。通过系统竞争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资本主义首先追逐的经济增长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开来,尽管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中存在着停滞甚至衰退的倾向。 [1]
已经建立起来的增长机制造成世界范围内人口和生产的增加。经济增长,就要求人口增多,要求更多地开发和掠夺自然,这样就遇到了两个物质限制:一是不可再生资源,如可开发和居住的土地资源、淡水资源、食品,此外还有不可再生的能源,如矿物、燃料等;二是不可替代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主要是消化污染物,如放射性废料、二氧化碳、废热等。诚然,福里斯特(For rester)和另一些人对于人口、工业生产、掠夺自然资源等的急剧增长的极限以及环境污染的极限的估计没有充分的经验依据。 [2] 我们对人口增长机制同对地球消化主要污染物能力的界限一样,都是不甚了了。而且,我们无法准确地预测技术发展的前景,不知道未来在技术上可以使何种能源被取代或更新。
但是,根据乐观的假定,也能指出一种增长的绝对限制,即使暂时还不能作出明确的判断,比如环境消化能源消耗所释放出来的热量极限。 [3] 如果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更多的能源消耗,如果所有的自然能源都转换为具有经济用途的能源,并最终释放出来成为热能(这是指全部能量,而不仅仅指在传导和转化时所丧失的部分),那么,越来越多的能源消耗最终必然会导致全球气温的升高。当然,从经验上确定危机阶段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必须根据经济增长以及能源消耗对气候的影响来决定能源消耗(根据现有的知识,这种危机间隔大约是在75到150年之间)。但这些思考起码表明了一点,这就是人口和生产的急剧增长,即对外部自然进行控制的扩张,总有一天会达到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
这点对于所有复杂的社会系统都是有效的,但是,各个社会系统可能采用的避免生态危机的手段则各不相同。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抛弃自己的组织原则,就不可能遵循增长限度的律令,因为,从自发的资本主义增长转变为注重品质的增长,就要求根据使用价值来对生产作出规划。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脱离了交换价值生产的要求,就不可能不触犯到该系统的逻辑。
与外部自然的社会化过程不同,内在自然的整合没有极限。如果说,对生态平衡的破坏标志着掠夺自然资源的程度,那么,人格系统则没有明确的承受界限。我怀疑是否有可能确定人性中那些限制着内在社会化过程的心理恒定因素。但是,我在社会化过程中看到了一种限制。迄今为止,社会系统就是通过社会化产生出自己的行为动机的。社会化过程贯穿着语言主体间性的结构,决定了一种依靠尚需证明的规范和确保认同的解释系统建立起来的行为组织。这种交往行为组织能够成为复杂决策系统的障碍。和在个别组织中一样,当决策机构在功能上独立于组织成员的动机之外时,社会系统层次上的控制能力同样也会有所增强。在极其复杂的系统中,组织目标的选择与实现必须独立于聚集起来的各种狭隘动机;其目的是要实现一种普遍的赞同意愿。这种意愿在政治系统中表现为大众忠诚(Massenloyalität)。只要我们被迫面对在交往行为组织中约束着内在自然的社会化形式,我们就无法想象会有对任何行为规范的合法化能够保证人们会不假思索地接受某种决定。人们之所以准备服从一种内容尚未确定的决策权力,是因为人们期待这种权力会按照合法的行为规范运作(参阅本书第三部分第五章)。人们准备服从的“根本”动机是一种信念,从而使自己在发生疑问的时候能够得到话语的说服。
由于规范需要合法化,动机则依赖于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样就确定了一个界限。要想打破这个界限,就必须把动机与交往行为结构脱离开来:社会化形式以及社会文化系统的认同也就必然会随着发生变化。如果行为动机不再依靠需要加以证明的规范,如果人格系统不必再到确保认同的解释系统中去寻找自身的统一性,那么,不假思索地接受决定就会变成一种无需责备的机械习惯, [4] 绝对服从的意愿就会达到随意的程度(我在第三部分将回过头来探讨以下问题,即目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达到的内在复杂程度是否已经迫使交往行为组织发生瓦解)。
世界体系(Weltsystem)由于人们使用核武器而面临着自我毁灭的危险。这种危险属于另一种层面上的问题。毁灭能力的积累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由于生产力的技术基础是中性的,因此生产力也有可能变成一种破坏力。由于国际交往处于自发状态,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发生。在军事行为系统中,各方之间针锋相对,都视对方为外部自然的一个部分;在有组织的殊死战斗中,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敌人也就成为了最终目的(ultima ratio)。今天,这种系统第一次掌握了一种能够从根本上摧毁世界自然基础的技术能力。因此,国际交往也就要求必须自我克制,而这是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 [5] 虽然所有高度军事化的社会系统都做到这一点,它们各自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却有所不同。而且,如果我们注意到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阶级社会背后的动力,就会发现真正的裁军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只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成功地在国家对非生产性用品的需求和增加资本使用价值之间取得平衡,军备竞赛的控制本身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之间也就并非水火不相容。
[1] 加尔通(J.Galtung):“帝国主义的结构理论”(Eine strukturelle Theorie des Imperialismus),载桑哈斯编:《帝国主义与结构权力》;弗洛贝尔(F.Fröbel)、亨利希(J.Heinrichs)、克列耶(O.Kreye)、森克尔(O.Sunkel):《劳动和资本的国际化:发展与低度发展》( Internationaliserung von Arbeit und Kapital: Entwicklung und Unterentwicklung ),手稿,MPIL。
[2] 米多斯(D.Meadows):《增长的极限》( Grenzen des Wachstums ),Stuttgart,1972。
[3] 迈耶尔—阿比希(K.M.Meyer-Abich):“经济增长的生态极限”(Die ökologische Grenze des Wirtschaftswachstums),载《环视》( Umschau ),1972,第72卷,第20期,第645页及以下诸页。
[4] 卢曼:“政治系统的社会学”(Soziologie des politischen Systems),载《社会学启蒙》(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Opladen,1970,第170页。
[5] 魏茨泽克(C.F.v.Weizsäcker):《战果与战备》( Kriegsfolgen und Kriegsverhütung ),München,1971,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