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燕市书春 奇才惊客过
朱门忆旧 热泪向人弹
人生的岁月,如流水的一般过去。记得满街小摊子上,摆着泥塑的兔儿爷,忙着过中秋,好像是昨日的事。可是一走上街去,花爆摊,花灯架,宜春帖子,又一样一样地陈设出来,原来要过旧历年了。到了过年,由小孩子到老人家,都应得忙一忙。
在我们这样一年忙到头的人,倒不算什么,除了焦着几笔柴米大账,没法交代而外,一律和平常一样。到了除夕前四五日,一部分的工作已停,反觉清闲些啦。
这日是废历的二十六日,是西城白塔寺庙会的日子。下半天没有什么事情,便想到庙里去买点梅花水仙,也点缀点缀年景。一起这个念头,便不由得坐车上街去。
到了西四牌楼,只见由西而来,往西而去的,比平常多了。有些人手上提着大包小件的东西,中间带上一个小孩玩的红纸灯笼,这就知道是办年货的。
再往西走,卖历书的,卖月份牌的,卖杂拌年果子的,渐渐接触眼帘,给人要过年的印象,那就深了。快到白塔寺,街边的墙壁上,一簇一簇的红纸对联挂在那里,红对联下面,大概总摆着一张小桌,桌上一个大砚池,几只糊满了墨汁的碗,四五支大小笔。桌子边,照例站一两个穿破旧衣服的男子。
这种人叫做书春的。就是趁着新年,写几副春联,让人家买去贴,虽然不外乎卖字,买卖行名却不差,叫做书春。但是这种书春的,却不一定都是文人。有些不大读书的人,因为字写得还像样些,也做这行买卖。所以一班人对于书春的也只看他为算命看相之流,不十分注意。就是在下落拓京华,对于风尘中人物,每引为同病,而对于书春的,却也是不大注意。
这时我到了庙门口,下了车子,正要进庙,一眼看见东南角上,围着一大群人在那里推推拥拥。当时我的好奇心动,丢了庙不进去走过街,且向那边看看。
我站在一群人的背后,由人家肩膀上伸着头,向里看去,只见一个三十附近的中年妇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在那里写春联。旁边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妇人,却在那里收钱,向看的人说话。
原来这个妇人书春,和别人不同——别人都是写好了,挂在那里卖;她却是人家要买,她再写。人家说是要贴在大门口的,她就写一副合于大门的口气的;人家说要贴在客堂里的,她就写一副合于客堂的口气的。
我心里想,这也罢了,无非卖弄她能写字而已。至于联文,自然是对联书上抄下来的。但是也难为她记得。我这样想时,猛抬头,只见墙上贴着一张红纸,行书一张广告。上面是:
诸公赐顾,言明是贴在何处者,当面便写。文用旧联,小副钱费二角,中副三角,大副四角。命题每联一元,嵌字加倍。
这时候我的好奇心动,心想,她真有这个能耐?再看看她,那广告上,直截了当,一字是一字,倒没有什么江湖话。也许她真是个读书种子,贫而出此。但是那“飘茵阁”三字,明明是飘茵坠溷的意思,难道她是浔阳江上的一流人物?
我在一边这样想时,她已经给人写起一副小对联,笔姿很是秀逸。对联写完,她用两只手撑着桌子,抬起头来,微微嘘了一口气。
我看她的脸色,虽然十分憔悴,但是手脸洗得干净,头发理得齐整,一望而知,她年轻时也是一个美妇人了。我一面张望,一面由人丛中挤了上前。那个桌子一边的老妇人,早对着我笑面相迎,问道:“先生要买对联吗?”
我被她一问,却不好意思说并不要对联。只得说道:“要一副,但是要嵌字呢,立刻也就有吗?”
那个写字的妇人,对我浑身上下看了一看,似乎知道我也是个识字的人。便带着笑容插嘴道:“这个可不敢说。因为字有容易嵌上的,有不容易嵌的,不能一概而论。若是眼面前的熟字眼儿,勉强总可以试一试。”
我听她这话,虽然很谦逊,言外却是很有把握似的。我既有心当面试她一试,又不免有同是沦落之感,要周济周济她。于是我便顺手在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这些围着在那里看的人,看见我将名片拿出来,都不由得把眼睛射到我身上。
我拿着名片,递给那个老妇人。那个老妇人看了一看,又转递给那书春的妇人。我便说道:“我倒不要什么春联,请你把我的职业,作上一副对联就行,用不着什么颂扬的口气。”
那妇人一看我的名片,是个业新闻记者的,署名却是文丐。笑道:“这位先生如何太谦?我就把尊名和贵业做十四个字,行么?”
我道:“那更好了。”
她又笑道:“写得本来不像个东西,做得又不好,先生不要笑话。”
我道:“很愿意请教,不必客气。”
她在裁好了的一叠纸中,抽出两张来,用手指甲略微画了一点痕迹,大概分出七个格子。于是分了一张,铺在桌上,用一个铜镇纸将纸压住了。然后将一支大笔,伸到砚池里去蘸墨。一面蘸墨,一面偏着头想。
不到两三分钟的工夫,她脸上微露一点笑容,于是提起笔来,就在纸上写了下去。七个字写完,原来是:文章直至饥臣朔。我一看,早吃了一大惊,不料她居然能此。这分明是切“文丐”
两个字做的。用东方朔的典来咏文丐,那是再冠冕没有的了。而且“直至”两个字衬托得极好。“饥”字更是活用了。她将这一联写好,和那老妇人牵着,慢慢地铺在地下。从从容容,又来写下联。那七个字是:斧钺终难屈董狐。
这下一联,虽然是个现成的典。但是她在“董狐”上面,加了“终难屈”三个字,用的是活对法,便觉生动而不呆板。这种的活对法,不是在词章一道下过一番苦功夫的人,绝不能措之裕如。
到了这时,不由得我不十二分佩服。叫我当着众人递两块钱给她,我觉得过于唐突了。虽然这些买对联的人,拿出三毛五毛,拿一副对联就走。可是我认她也是读书识字的,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样藐视文人的事,我总是不肯做的。
我便笑着和老妇人道:“这对联没有干,暂时我不能拿走。我还有一点小事要到别处去,回头我的事情完了,再来拿。如是晏些,收了摊子,到你府上去拿,也可以吗?”
那老妇人还犹豫未决,书春的妇人,一口便答应道:“可以可以!舍下就住在这庙后一个小胡同里。门口有两株槐树,白板门上有一张红纸,写‘冷宅’两个字,那就是舍下。”
我见她说得这样详细,一定是欢迎我去的了,点了一下头,和她作别,便退出了人丛。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事,不过是一句遁词。我在西城两个朋友家里,各坐谈了一阵,日已西下,估计收了摊子了,便照着那妇人所说,去寻她家所在。
果然,那个小胡同里,有两株大槐树,槐树下面,有两扇小白门。我正在敲门问时,只见那两个妇人提着篮子,背着零碎东西,由胡同那头走了过来。我正打算打招呼,那个老妇人早看见了我,便喊着道:“那位先生,这就是我们家里。”
他们一面招呼,一面已走上前,便让我进里面去坐。我走进大门一看,是个极小的院子,仅仅只有北房两间,厢房一间。她让进了北屋,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带着一个上十岁的男孩子,在那里围着白泥炉子向火。见了我进来,起身让座。
这屋子像是一间正屋,却横七竖八摆了四五张桌椅,又仿佛是个小小的私塾。那个老妇人,自去收拾拿回来的东西。那书春的妇人,却和那个老头子,来陪我说话。我便先问那老人姓名,他说他叫韩观久。我道:“这是不是府上一家住吗?”
韩观久道:“也可以说是一家,也可以说是两家。”
便指着那妇人道:“这是我家姑奶奶,她姓冷,所以两家也是一家。”
我听了这话不懂,越发摸不着头脑。那妇人知道我的意思,便道:“不瞒你先生说,我是一个六亲无靠的人。刚才那个老太太,我就是她喂大的,这是我妈妈爹呢。”
我这才明白了,那老妇人是她乳母,这老人是乳母的丈夫呢。这时我可为难起来,要和这个妇人谈话了,我称她为太太呢,称她为女士呢?且先含糊着问道:“贵姓是冷?”
对道:“姓金,姓冷是娘家的姓呢。”
我这才敢断定她是一位妇人。便道:“金太太的才学,我实在佩服。蒙你写的一副对联,实在好。”
金太太叹了一口气,说道:“这实在也是不得已才去这样抛头露面。稍微有点学问有志气的人,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沿街鼓板一样的生活,哪里谈到好坏?本来呢,我自己可以不必出面,因为托我妈妈爹去卖了一天,连纸钱都没有卖出来;所以我想了一个下策,亲自出去。以为人家看见是妇人书春,好奇心动,必定能买一两副的。”说着脸一红。又道:“这是多么惭愧的事!”
我说:“现在潮流所趋,男女都讲究经济独立,自谋生活,这有什么做不得?”
金太太道:“我也只是把这话来安慰自己,不过一个人什么事不能做,何必落到这步田地呢?”
我道:“卖字也是读书人本色,这又何妨?我看这屋子里有许多小书桌,平常金太太也教几个学生吗?”
金太太指着那个男孩子道:“一来为教他,二来借此混几个学费;其实也是有限得很,还靠着晚上做手工来补救。”
我说:“这位是令郎吗?”
金太太凄然道:“正是。不为他,我何必还受这种苦,早一闭眼睛去了。”
便对那孩子道:“客来了,也不懂一点礼节,只躲到一边去,还不过来鞠躬。”
那孩子听说,果然过来和我一鞠躬。我执着那孩子的手,一看他五官端正,白白净净的。手指甲剪得短短的,身上穿的蓝布棉袍,袖口却是干净,并没有墨迹和积垢。只看这种小小的习惯,就知道金太太是个贤淑的人,更可钦佩。但是学问如此,道德又如彼,何至于此呢?
只是我和人家初交,这是人家的秘密,是不便于过问的,也只好放在心里。不过我替她惋惜的观念,就越发深了。我本来愁着要酬报她的两块钱,无法出手。
这时我便在身上掏出皮夹来,看一看里面,只有三张五元的钞票。我一想,像我文丐,当这岁暮天寒的时候,决计没有三元五元接济别人的力量。但是退一步想,她的境遇,总不如我,便多送她三元,念在斯文一脉,也分所应当。
一刹那间,我的恻隐心,战胜了我的悭吝心,便拿了一张五元钞票,放在那小孩子手里。说道:“快过年了,这个拿去逛厂甸买花爆放吧。”
金太太看见,连忙站起来,将手一拦那小孩。笑着说道:“这个断乎不敢受!”
我说:“金太太你不必客气。我文丐朝不保夕,决不能像慷慨好施的人随便。我既然拿出来了,我自有十二分的诚意,我决计是不能收回的。”
金太太见我执意如此,谅是辞不了的,便叫小孩子对我道谢,将款收了。那个老妇人,已用两只洋瓷杯子斟上两杯茶来。两只杯子虽然擦得甚是干净,可是外面一层珐琅瓷,十落五六,成了半只铁碗。杯子里的茶叶,也就带着半寸长的茶叶棍儿,浮在水面上。
我由此推想他们平常的日子,都是最简陋的了。我和他们谈了一会儿,将她对联取了,自回家去,把这事也就扔下了。
过了几天,已是新年,我把那副对联贴在书房门口。我的朋友来了,看见那字并不是我的笔迹,便问是哪个写的?
我抱着逢人说项的意思,只要人家一问,我就把金太太的身世,对人说了,大家都不免叹息一番。
也是事有凑巧,新正初七日,我预备了几样家乡菜,邀了七八个朋友,在家里尽一日之乐。大家正谈得高兴的时候,金太太那个儿子,忽然到我这里来拜年,并且送了我一部木版的《唐宋诗醇》。那小孩子说:“这是家里藏的旧书,还没有残破,请先生留下。”
他说完,就去了。我送到大门口,只见他母亲的妈妈爹在门口等着呢。我回头和大家一讨论,大家都说:“这位金太太,虽然穷,很是介介,所以她多收你三四块钱,就送你一部书。而且她很懂礼,你看她叫妈妈爹送爱子来拜年,却不是以寻常人相待呢。”
我就说:“既然大家都很钦佩金太太,何不帮她一个忙?”
大家都说:“忙要怎样帮法?”
我说:“若是送她钱,她是不要的,最好是给她找一个馆地。一面介绍她到书局里去,让她卖些稿子。”
大家说:“也只有如此。”
又过了几天,居然给她找到一所馆地。
我便亲自到金太太家里去,把话告诉她。她听了我这话,自然是感激,便问:“东家在哪里?”
我说:“这家姓王,主人翁是一个大实业家,只教他家两位小姐。”
金太太说:“是江苏人吗?”
我道:“是江苏人。”
金太太紧接着说:“他是住在东城太阳胡同吗?”
我道:“是的。”
金太太听说,脸色就变了。她顿了一顿,然后正色对我道:“多谢先生帮我的忙,但是这地方,我不能去。”
我道:“他家虽是有钱,据一般人说,也是一个文明人家。据我说,不至于轻慢金太太的。”
金太太道:“你先生有所不知,这是我一家熟人,我不好意思去。”
她口里这样说,那难堪之色,已经现于脸上。我一想,这里面一定有难言之隐,我一定要追着向前问,有刺探人家秘密之嫌。便道:“既然如此,不去也好,慢慢再想法子吧。”
金太太道:“这王家,你先生认识吗?”
我说:“不认识,不过我托敝友辗转介绍的。”
金太太低头想了一想,说道:“你先生是个热心人,有话实说不妨。老实告诉先生,我一样的有个大家庭,和这王家就是亲戚啦。我落到这步田地……”说到这里,那头越发低下去了,半晌,不能抬起来。早有两点眼泪,落在她的衣襟上。
这时,那个老妇人端了茶来。金太太搭讪着和那老妇人说话,背过脸去,抽出手绢,将眼睛擦了一擦。我捧着茶杯微微呷了一口茶,又呷二口茶,心里却有一句话要问她,那么,你家庭里那些人,哪里去了呢?
“但是我总怕说了出来,冲犯了人家,如此话到了舌尖,又吞了下去。这时,她似乎知道我看破了她伤心,于是勉强笑了一笑,说道:“先生不要见怪,我不是万分为难,先生给我介绍馆地,我决不会拒绝的。”
我道:“这个我很明了,不必介意。”说完了这两句话,她无甚可说了,我也无甚可说了。
屋子里沉寂寂的,倒是胡同外面卖水果糖食的小贩,敲着那铜碟儿声音,一阵阵送来,我又呷了几口茶,便起身告辞,约了过日再会。
我心里想,这样一个人,我猜她有些来历,果然不错。只是她所说的大家庭,究竟是怎样一个家庭呢?后来我把她的话,告诉了给她找馆的那个朋友。那朋友很惊讶,说道:“难道是她吗?她怎样还在北平?”
我问道:“你所说的她,指的是谁?”
我那朋友摇摇头道:“这话太长,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若真是她,我一定要去见见。”
我道:“她究竟是谁?你说给我听听看。”
我的朋友道:“现在且不必告诉你,让我见了她以后,那一天晚上你扇一炉子大火,沏一壶好茶,我们联床夜话,我来慢慢地告诉你,可当一部鼓儿词听呢。”
他这样说,我也不能勉强。但是我急于要打破这个哑谜,到了次日,我便带他到金太太家里去,作为三次拜访。不料到了那里,那冷宅的一张纸条,已经撕去了。门口另换了一张招租的帖子。
我和我的朋友都大失所望。我的朋友道:“不用说,这一定是她无疑了。她所以搬家,正是怕我来找她呀。既然到此,看不见人,进去看看屋子,也许在里面找到一点什么东西,更可以证明是她。”
我觉得这话有理,便和他向前敲门。里面看守房子的人,以为我们是赁房的,便打开门引我二人进去。我们一面和看守屋子的人说话,一面把眼睛四围逡巡,但是房子里空空的,一点什么痕迹都没有。
我的朋友望着我,我望着他,彼此微笑了一笑,只好走出来。走到院子里,我的朋友,看见墙的犄角边,堆着一堆字纸。便故意对着看屋子的人道:“你们把字纸堆在这里,不怕造孽吗?”说时,走上前便将脚拨那字纸。
我早已知道他的命意,于是两个人四道眼光,像四盏折光灯似的,射在字纸堆里。他用脚拨了几下,一弯腰便捡起一小卷字纸在手上。我看时,原来是一个纸抄小本子,烧了大半本,书面上也烧去了半截,只有“零草”两个字。
这又用不着猜的,一定是诗词稿本之类了。我本想也在字纸堆里再寻一点东西,但是故意寻找,又恐怕看屋子的人多心,也就算了。我的朋友得了那个破本子,似乎很满意的,便对我说道:“走吧。”
我两人到了家里,什么事也不问,且先把那本残破本子,摊在桌上,赶紧地翻着看。但是书页经火烧了,业已枯焦。又经人手一盘,打开更是粉碎。只有那两页书的夹缝,不曾被火熏着,零零碎碎,还看得出一些字迹,大概这里面,也有小诗,也有小词。但是无论发现几个字,都是极悲哀的。
一首落真韵的诗,有一大半看得出,是:……莫当真,浪花风絮总无因。灯前闲理如来忏,两字伤心……我不禁大惊道:“难道这底下是押‘身’字?”
我的朋友点点头道:“大概是吧?”
我们轻轻翻了几页,居然翻到一首整诗,我的朋友道:“证据在这里了。你听,”
他便念道:铜沟流水出东墙,一叶芭蕉篆字香,不道水空消息断,只从鸦背看斜阳。我说道:“胎息浑成,自是老手。只是这里面的话,在可解不可解之间。”
我的朋友道:“你看这里有两句词,越发明了。”
我看时,是:……说也解人难。几番向银灯背立,热泪偷弹。除是……这几句词之后,又有两句相同的,比这更好。是:……想当年,一番一回肠断。只泪珠向人……我道:“诗词差不多都是可供吟咏的,可惜烧了。”
我的朋友道:“岂但她的著作如此,就是她半生的事,也就够人可歌可泣呢。”
我道:“你证明这个金太太,就是你说的那个她吗?”
我的朋友道:“一点不错。”
我说道:“这个她究竟是谁?你能够告诉我吗?”
我的朋友道:“告是可以告诉你。只是这话太长了,好像一部二十四史,难道我还从三皇五帝说起,说到民国纪元为止吗?”
我想他这话也是,便道:“好了,有了一个主意了。这回过年,过的我精穷,我正想作一两篇小说,卖几个钱来买米。既然这事可歌可泣,索性放长了日子干,你缓缓地告诉我,我缓缓地写出来,可以作一本小说。倘若其中有伤忠厚的,不妨将姓名地点一律隐去,也就不要紧了。”
朋友道:“那倒不必,我怎样告诉你,你怎样写得了。须知我告诉你时,已是把姓名地点隐去了哩。再者我谈到人家的事,虽重繁华一方面,人家不是严东楼,我劝你也不要学王凤洲。”
我微笑道:“你太高比,凭我也不会作出一部《金瓶梅》来,你只要把她现成的事迹告诉我,省我勾心斗角、布置局面,也就很乐意了。”
我的朋友笑道:“设若我造一篇谣言哩?”
我笑道:“当然我也写上。作小说又不是编历史,只要能自圆其说,管他什么来历?你替我搜罗好了材料,不强似我自造自写吗?”
我的朋友见我如此说,自然不便推辞。而且看我文丐穷得太厉害了,也乐得赞助我作一篇小说,免得我逢人借贷。自这天起,我们不会面则已,一见面就谈金太太的小史。我的朋友一天所谈,足够我十天半个月的投稿。
有时我的朋友不来,我还去找他谈话。所幸我这朋友,是个救急而又救穷的朋友,立意成就我这部小说,不嫌其烦地替我搜罗许多材料,供我铺张。
自春至夏,自秋至冬,经一个年头,我这小说居然作完了。至于小说内容,是否可歌可泣,我也不知道。因为事实虽是够那样的,但是我的笔笨写不出来,就不能令人可歌可泣了。好在下面就是小说的正文,请看官慢慢去研究吧。
陌上闲游 坠鞭惊素女
阶前小谑 策杖戏娇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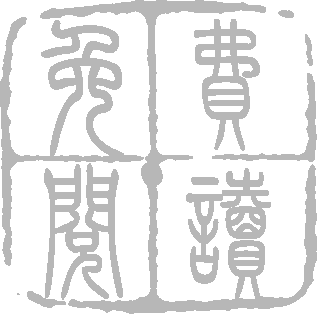
却说北京西直门外的颐和园,为逊清一代留下来的胜迹。相传那个园子的建筑费,原是办理海军的款项。用办海军的款子,来盖一个园子,自然显得伟大了。
在前清的时候,只是供皇帝、皇太后一两个人在那里快乐。到了现在,不过是刘石故宫,所谓亡国莺花。不但是大家可以去游玩,而且去游览的人,夕阳芳草,还少不得有一番凭吊呢。
北地春迟,榆杨晚叶,到三月之尾,四月之初,百花方才盛开。那个时候,万寿山是重嶂叠翠,昆明湖是春水绿波,颐和园和邻近的西山,便都入了黄金时代。
北京人从来是讲究老三点的,所谓吃一点,喝一点,乐一点,像这种地方,岂能不去游览?所以到了三四月间,每值风和日丽,那西直门外,香山和八大处去的两条大路,真个车水马龙,说不尽的衣香鬓影。
这一年三月下旬,正值天气晴和,每日出西直门的游人,络绎于途。什么汽车马车人力车驴子,来来往往,极是热闹。但是有些阔公子,马车人力车当然是不爱坐。汽车又坐得腻了。驴子呢,嫌它瘦小。
先有一项不愿受的,就是驴夫送来的那条鞭子太脏,教人不敢接着。有班公子哥儿,家里喂了几头好马,偶然高兴出城来跑上一趟马。在这种春光明媚的时候,轻衫侧帽,扬鞭花间柳下,目击马嘶芳草的景况,那是多么快活呢!
在这班公子哥儿里头,有位姓金的少爷,却是极出风头。他单名一个华字,取号燕西,现在只有一十八岁。兄弟排行,他是老四,若是姐妹兄弟一齐论起来,他又排行是第七,因此他的仆从,都称呼他一声七爷。
他的父亲,是现任国务总理,而且还是一家银行里的总董。家里的银钱,每天像流水般的进来出去。所以他除了读书而外,没有一桩事是不顺心的。这天他因天气很好,起了一个早,九点多钟就起来了。
在家中吃了一些点心,叫了李福、张顺、金荣、金贵四个听差,备了五匹马,主仆五人,簇拥着出了西直门,向颐和园而来。
燕西将身上堆花青缎马褂脱下,扔给了听差,身上单穿一件宝蓝色细丝驼绒长袍,将两只衫袖,微微卷起一点,露出里面豆绿春绸的短夹袄。右手勒着马缰绳,左手拿着一根湘竹湖丝洒雪鞭。两只漆皮鞋,踏着马镫子,将马肚皮一夹,一扬鞭子,骑下的那匹玉龙白马,在大道之上,掀开四蹄,飞也似的往西驰去。
后面的金荣,打着马赶了上来,口里嚷道:“我的小爷,别跑了。这一摔下来,可不是玩的。”说时,那后面的三匹马,也都追了上来。
路上尘土,被马蹄掀起来,卷过人头去。燕西这一跑,足有五里路。自己觉得也有些吃力,便把马勒住。那四匹马已是抄过马头,回转身来,挡了去路。燕西在驼绒袍子底下,抽出一条雪花绸手绢,揩着脸上的汗,笑道:“你们这是做什么?”
金荣道:“今天路上人多,实在跑不得。摔了自己不好,碰了别人也不好,你看是不是?”
燕西笑道:“你们都是好人?前天你学着开汽车,差一点把巡警都碰了。”
金荣笑道:“可不是!你骑马的本领,和我开车的本领差不多,还是小心点吧。高高兴兴出来玩一趟,若是惹了事,就是不怕,也扫兴得很啦。”
燕西道:“这倒像句话。”
李福道:“那么,我们在头里走。”说着,他们四匹马,掉转头,在前面走去。燕西松着马缰绳,慢慢在后面跟着。
这里正是两三丈宽的大道,两旁的柳树,垂着长条,直披到人身上马背上来。燕西跑马跑得正有些热,柳树底下吹来一两阵东风,带些清香,吹到脸上,不由得浑身爽快一阵。他们的马,正是在下风头走,清香之间,又觉得上风头时有一阵兰麝之香送来。
燕西在马背上目睹陌头春色,就不住领略这种香味。燕西很是奇怪,心想,这倒不像是到了野外,好像是进了人家梳头室里去了呢。一面骑着马慢慢走,一面在马上出神。第一阵香气,却越发地浓厚了。
偶然一回头,只见上风头,一列四辆胶皮车,坐着四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追了上来。燕西恍然大悟,原来这脂粉浓香,就是她们那里散出来的。在这一刹那间,四辆胶皮车已经有三辆跑过马头去。最后一辆,正与燕西的马并排走着。
燕西的眼光,不知不觉地就向那边看去。只见那女子挽着如意双髻,髻发里面,盘着一根鹅黄绒绳,越发显得发光可鉴。身上穿着一套青色的衣裙,用细条白辫周身来滚了。项脖上披着一条西湖水色的蒙头纱,被风吹得翩翩飞舞。
燕西生长金粉丛中,虽然把倚红偎翠的事情看惯了,但是这样素净的妆饰,却是百无一有。他不看犹可,这看了之后,不觉得又看了过去。只见那雪白的面孔上,微微放出红色,疏疏的一道黑刘海披到眉尖,配着一双灵活的眼睛,一望而知,是个玉雪聪明的女郎。
燕西看了又看,又怕人家知觉,把那马催着走快几步,又走慢几步,前前后后,总不让车子离得太远了。车子快快地走,马儿慢慢行,这样左右不离,燕西也忘记到了哪里。
前面的车子,因为让汽车过去,忽然停住,后面跟的车子,也都停住了。燕西见人家车子停住,他的马也不知不觉地停住。那个漂亮女子,偏着头,正看这边的风景。她猛然间低头一笑,也来不及抽着手绢了,就用临风飘飘的蒙头纱,捂着嘴。
在这一笑时,她那一双电光也似的眼睛,又向这边瞧了一瞧。燕西一路之上,追看人家,人家都不知觉。这时人家看他,他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忽然低头一看,这才醒悟过来。原来自己手上拿的那条马鞭子,不知何时脱手而去,已经落在地下了。大概人家之所以笑,就是为了这个。
自己要下去拾起马鞭子来吧,真有些不好意思。不捡起来吧,那条马鞭子又是自己心爱之物,实在舍不得丢了。不免在马上踌躇起来。
金荣一行四匹马,在他前面,哪里知道,只管走去。金荣一回头,不见了燕西,倒吓了一跳,勒转马头,脚踏着马镫,昂首一看,只见他勒住马,停在一棵柳树荫下。金荣加起一马鞭,连忙催着马跑回来。便问道:“七爷,你这是做什么?”
燕西笑了一笑,说道:“你来了很好,我马鞭子掉在地下,你替我捡起来吧。”
金荣当真跳下马去,将马鞭捡了起来交给燕西。他一接马鞭子,好像想起一桩事似的,也不等金荣上马,打了马当先就跑。
金荣在后面追了上来,口里叫道:“我的七爷,你这是做什么?疯了吗?”
燕西的马,约摸跑了小半里路,便停住了,又慢慢地走起来。
金荣跟在后面,伸起手来搔着头发。心里想道:这事有些怪,不知道他真是出了什么毛病了?自己又不敢追问燕西一个究竟,只得糊里糊涂在后跟着。又走了一些路,只见后面几辆人力车追了上来,车上却是几个水葱儿似的女子。
金荣恍然大悟,想道:我这爷,又在打糊涂主意呢!怪不得前前后后,老离不开这几辆车子。我且看他,注意的是谁。这样想时,眼睛也就向那几辆车子上看去。他看燕西的眼光不住地盯住那穿青衣的女子,就知道了。
但是自己一群人有五匹马,老是苍蝇见血似的盯着人家几辆车子,这一种神情,未免难看。便故意赶上一鞭,和燕西的马并排走着,和燕西丢了一个眼色。只这一刹那的工夫,马已上了前。燕西会意,便追上来。
金荣打着马,只管向前跑,燕西在后面喊道:“金荣,要我骂你吗?好好的,又耍什么滑头?”
金荣回头一看,见离那人力车远了,便笑道:“七爷,你还骂我耍滑头吗?”
金燕西笑道:“我怎样不能骂你耍滑头?”
金荣道:“我的爷,你还要我说出来,上下盯着人家,也真不像个样子。”复又笑道:“真要看她,三百六十天天天都可以看得到,何必在这大路上追着人家?”
燕西笑道:“我看谁?你信口胡说,仔细我拿鞭子抽你!”
金荣道:“我倒是好意。七爷这样说,我就不说了。”
燕西见他话里有话,把马往前一拍,两马紧紧地并排,笑道:“你说怎样是好意?”
金荣道:“七爷要拿鞭子抽我呢,我还说什么,没事要找打挨吗?”
金贵三人听见这话,大家都在马上笑起来。燕西道:“你本是冤我的,我还不知道?”
金荣道:“我怎敢冤你?我天天上街,总碰见那个人儿,她住的地方,我都知道。”
燕西笑道:“这就可见你是胡说了。你又不认识她,她又不认识你,凭空没事的,你怎样会注意人家的行动?”
金荣笑道:“我问爷,你看人家,不是凭空无事,又是凭空有事吗?好看的人儿,人人爱看。那样一位鲜花般似的小姐在街上走着,狗看见,也要摆摆尾呢,何况我还是个人。”
燕西笑道:“别嚼蛆了,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金荣道:“爷别忙,听我说。这一晌,七爷不是出了一个花样,要吃蟹壳黄烧饼吗?我总怕别人买的不合你意,总是自己去买。每日早上,一趟西单牌楼,是你挑剔金荣的一桩好差事。”
燕西道:“说吧,别胡扯了。”
金荣道:“在我天天去买烧饼的时候,总碰到她从学校里回来。差不多时刻都不移。有一天她回来早些,我在一个地方,看见她走进一个人家去,我猜那就是她的家了。”
燕西道:“她进去了,不见得就是她的家,不许是她的亲戚朋友家里吗?”
金荣道:“我也是这样说,可是以后我又碰到两次哩。”
燕西道:“在什么地方?”
金荣笑道:“反正离我们家里不远。”
燕西道:“北京城里,离我们家都不远,你这话说得太靠不住了。”
金荣道:“我决不敢冤你,回去的时候,我带你到她家门口去一趟,包你一定欢喜。先说出来,反没有趣了。”
燕西道:“那倒也使得,那时你要不带我去,我再和你算账!”
金荣笑道:“我也有个条件呢,可不能在大路上盯着人家,要是再盯着,我就不敢说了。”
燕西看他说的一老一实,也就笑着答应了。
主仆一路说着,不觉已过了海淀。
张顺道:“七爷,颐和园我们是前天去的,今天又去吗?”
燕西在马上踌躇着,还没有说出来。李福笑道:“你这个人说话,也是不会看风色的,今天是非进去逛逛不可呢。”
张顺笑道:“那么,我们全在外面等着,让七爷一个人在里面,慢慢地逛吧。”
燕西笑骂道:“你这一群混蛋,拿我开心。”
金贵道:“七爷,你别整群地骂呀,我可没敢说什么哩。”
主仆五人,谈笑风生地到了颐和园,将马在树下拴了,五人买票进门。燕西心里想着,那几个女学生,一定是来逛颐和园的。所以预先进来,在这里等着。
不料等了大半天,一点影子也没有,恐怕是一直往香山去了。无精打采,带着四个仆人,一直回家。
刚一到大门口,只见停着一辆汽车,他的大嫂吴佩芳、三嫂王玉芬和着第三个姨妈翠姨,都从车子上下来。
翠姨一见燕西下马,便笑道:“闲着没事,又到城外跑马去了吗?你瞧,把脸晒得这样红红的,又算什么?回头让你那白妹妹瞧见,又要抱怨半天。”
燕西将马鞭子递给金荣,便和他们一路进去,问道:“一伙儿的,又在哪里来?”
佩芳笑道:“翠姨昨晚上打扑克赢了钱,我们要她做东呢。”
燕西道:“吃馆子吗?”
佩芳道:“不!在春明舞台包了两个厢,听了两出戏呢。”
燕西道:“统共不过三个人,倒包了两个厢。”
翠姨道:“这是他们把我赢来的钱当瓦片儿使呢。我说包一个厢得了,他们说:有好多人要去呢。后来,厢包好了,东找也没有人,西找也没有人。”
燕西一顿脚,正要说话,在他前面的王玉芬哎哟一声,回头红着脸要埋怨他。然后又忍不住笑了,说道:“老七,你瞧,我今天新上身的一件哔叽斗篷,你给人家踩脏了。”说时,两只手抄着她那件玫瑰紫斗篷的前方,扭转头只望脚后跟。
燕西一看,在那一路水钻青丝辫滚边的地方,可不是踏了一个脚印,燕西看了,老大不过意,连忙蹲下身子去,要给他三嫂拍灰。
王玉芬一扭身子,往前一闪,笑道:“不敢当!”
大家笑着一路走进上房。各人房里的老妈子,早已迎上前来,替他们接过斗篷提囊去。
燕西正要回自己的书房,翠姨一把扯住,说道:“我有桩事和你商量。”
燕西道:“什么事?”
翠姨道:“听说大舞台义务戏的包厢票,你已经得了一张,出让给我,成不成?”
燕西道:“我道是什么要紧的事,就是为了这个?出什么让,我奉送得了。”
翠姨道:“先放在你那里,我自己来拿,若是一转手,我又没份了。”
燕西答应着,自己出去了。一回书房,金荣正在给他清理书桌。
金荣一看,并没有人在屋子里,笑道:“七爷,你不看书也罢,看了满处丢,设若有人到这里来看见了,大家都不好。”
燕西道:“要什么紧?在外面摆的,不过是几本不相干的小说。那几份小报送来没有送来?我两天没瞧哩。”
金荣道:“怎样没有送来,我都收着呢,回头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再拿出来瞧吧。”
燕西笑了一笑,说道:“你说认得那个女孩子家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
金荣道:“我不敢说。”
燕西道:“为什么不敢说?”
金荣笑道:“将来白小姐知道了,我担当不起。”
燕西道:“我们做的事,怎样会让他们知道?你只管说,保没有什么事。”
金荣笑了一笑,踌躇着说道:“对你不住。在路上说的那些话,全是瞎说的。”说着,对燕西请了一个安。
燕西十分不快,板着脸道:“你为什么冤我?”
金荣道:“你不知道,在路上你瞧着人家车子的时候,人家已经生气了。我怕再跟下去,要闹出乱子来呢。”
燕西道:“我不管,你非得把她的家找到不可。找不到,你别见我了。”说毕,在桌上抽了一本杂志自看,不理金荣。
金荣见燕西真生了气,不敢说什么,做毕了事,自退出了。他和几个听差一商量,说道:“这岂不是一桩难事,北京这么大的地方,教我在哪里去找这一个人?”
大家都说道:“谁叫你撒谎撒得那样圆,像真的一样。”
金荣也觉差事交代不了,吓得两三天不敢见燕西的面。好在燕西玩的地方很多,两三天以后,也就把这事淡下来了。
金荣见他把这事忘了,心里才落下一块石头。
偏是事有凑巧,这一天金荣到护国寺花厂子里去买花,顶头碰见那个女学生买了几盆花,在街上雇车,讲的地方,却是落花胡同西头。金荣这一番,比当学生的做出了几个难题目还要快活。让她车子走了,自己也雇了一辆车子跟了去。到了那地方,那女学生的车子停住,在一个小黑门外敲门。
金荣的车子,一直拉过西口,他才付了车钱下来。假装着找人家似的,挨着门牌一路数来。数到那个小黑门那儿,门牌是十二号,只见门上有块白木板,写着“冷寓”两个字。那门恰好半掩着,在门外张望,看里面倒是一个小院子。只是那院子后面,一带树木森森,似乎是人家一个园子。
金荣正在这里张望,又见那女学生在院子里一闪,这可以断定,她是住在这里了。
金荣看在眼里,回得家去,在上房找着燕西,给他丢了一个眼色。
燕西会意,一路和他到书房里来。
金荣笑道:“七爷,你要找的那个人,给你找到了。”
燕西道:“我要找谁?”
金荣笑道:“七爷很挂心的一个人。”
燕西道:“我挂心的是谁?我越发不明白你这话了。”
金荣道:“七爷就全忘了吗?那天在海淀看到的那个人呢。”
燕西笑道:“哦!我说你说的是谁,原来说的是她,你在哪里找到的?又是瞎说吧?”
金荣道:“除非吃了豹子胆,还敢撒谎吗?”
他就把在护国寺遇到那女学生的话说了一遍,又笑道:“不但打听得了人家的地方,还知道她姓冷呢。”
金荣这一片话,兜动了燕西的心事。想到那天柳树荫下,车上那个素妆少女飘飘欲仙的样子,宛在目前,不由得微笑了一笑。然后对金荣道:“你这话真不真我还不敢信,让我调查证实了再说。”
金荣笑道:“若是调查属实,也有赏吗?”
金燕西道:“有赏,赏你一只火腿。”
金燕西口里虽这般说,心里自是欢喜。他也等不到次日,马上换了一套西装,配上一个大红的领结,又拣了一双乌亮的皮鞋穿了。手上拿着一根柔软藤条手杖,正要往外走,忽然记起来还没戴帽子。身上穿的是一套墨绿色的衣服,应该也戴一顶墨绿色的帽子。
记得这顶帽子,前两天和他们看跑马回来,就丢在上房里了,也不知丢在哪个嫂子屋里呢。便先走到吴佩芳这边来。刚要到月亮门下,只见他大嫂子的丫头小怜搬了几盆兰花,在长廊外石阶上晒太阳,拿了条湿手巾,在擦瓷盆。她一抬头,见燕西探出半截身子,一伸一缩,不由得笑了。
燕西和她点一点头,招一招手,叫她过来。
小怜丢了手巾,跑了过来,反过一只手去,摸着辫子梢,笑道:“有话就说吧,这个样子做什么?”
金燕西见她穿一身灰布衣服,外面紧紧地套上一件六成旧青缎子小坎肩,厚厚地梳着一层黑刘海,越发显得小脸儿白净,便笑道:“这件坎肩很漂亮呀。”
小怜道:“漂亮什么?这是六小姐赏给我的,是两三年前时兴的东西,现在都成了老古董了。”
金燕西道:“可是你穿了很合身。”
小怜道:“你叫我来,就是说这个话吗?”
金燕西笑道:“大少奶奶说,让你伺候我,你听见说吗?”
小怜对他微微地啐了一下,扭转身就跑了。
燕西用手杖敲着月亮门,吟吟地笑。吴佩芳隔着玻璃窗子便叫道:“那不是老七吗?”
燕西便走进月亮门说道:“大嫂,是我。”
佩芳道:“你又什么事,鬼鬼祟祟的?”说时,佩芳已走了出来。
小怜低着头在那里擦花盆,耳朵边都是红的。
佩芳在长廊上,燕西站在长廊下,佩芳掩嘴笑了一笑,燕西也勉强笑了。便道:“我头回戴着的墨绿的呢帽子,丢在这里吗?”
佩芳笑道:“趁早别这样说了。年轻轻儿的哥儿们,戴个什么绿帽子呀?”
金燕西道:“现在戴绿帽子的,多着呢。”
佩芳明知他把话说愣了,故意呕着他道:“因为戴绿帽子的多,你就也要戴上头顶吗?”
燕西笑道:“你这是戴了眼镜锔碗——没碴儿找碴儿啦。”
佩芳笑道:“你听听,自己说话说错了,还说我找碴儿啦。”
燕西道:“得了,你告诉我一声吧,帽子在这里不在这里?我等着要出去呢。”
佩芳道:“你总是这样,东西乱丢,丢了十天半月也不问,到了要用的时候,就乱抓了。这个毛病,有个小媳妇儿管着,就好了。”说到这里笑了一笑,又道:“我看你待小怜很好,要不,我对母亲说一声,先让她去伺候你,给你收拾收拾衣服鞋袜吧?”
小怜一撒手道:“大少奶奶也是的!”说着,一掉辫子就跑了。
燕西道:“人家也是十六七岁的孩子了,你就这样当面锣对面鼓地开玩笑,也不怕人害臊。”
佩芳笑道:“害什么臊?她还不愿意吗?”
燕西道:“到底帽子在这里不在这里?”
佩芳道:“帽子没有,马褂倒是有一件扔在我这里,你别处找吧。”
燕西想着,二嫂那里是没有的。不在翠姨那里,或者就在三嫂那里,因此由长廊下转到后重屋子里来。
一转弯,只见小怜拿了一根小棍子,挑那矮柏树上的蛛丝网。这柏树一列成行,栽着像篱笆似的。金燕西在这边,小怜在那边。
小怜看见金燕西来了,说道:“你找什么帽子?”
金燕西道:“刚才不是说了,你没听见吗?你又想我说一句找绿帽子吧?”
小怜笑说:“我才不占你的便宜哩。”说时,用棍子指着金燕西衣服,问道:“是和这个颜色一样的吗?”
金燕西道:“是的。你看见没有?”
小怜道:“你的记性太不好了,不是那天你穿了衣服要走,白小姐留你打扑克,把帽子收起来了吗?”
金燕西道:“哦!不错不错,是白小姐拿去了。她放在哪里,你知道吗?”
小怜道:“她放在哪里呢?就扔在椅子上。我知道是你买的,而且听说是二十多块钱买的,我怕弄掉了,巴巴地捡起来,送到你屋子里去了。”
燕西道:“是真的吗?”
小怜道:“怎样不真?在你房背后,洗澡屋子里第二个帽架子上,你去看看。”
金燕西笑道:“劳驾得很!”
小怜将那手上的小棍子,对燕西身上戳了一下,笑道:“你这一张嘴,最不好,乱七八糟,喜欢瞎说。”
燕西笑道:“我说你什么?”说着,燕西就往前走一步,要捉住她的手,抢她的棍子。小怜往后一缩,隔着一排小柏树,燕西就没有法子捉住她。
小怜顿着脚,扬着眉,撅着嘴道:“别闹!人家看见了笑话。”
燕西见捉她不到,沿着小柏树篱笆,就要走那小门跑过来,去扭小怜。小怜看见,掉转身子就跑,当燕西跑到柏树那边时,小怜已经跑过长廊,遥遥地对着金燕西点点头笑道:“你来你来!”
金燕西笑着,就跑上前来。小怜身后,正是一个过堂门,她手扶着门,身子往后一缩,把门就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