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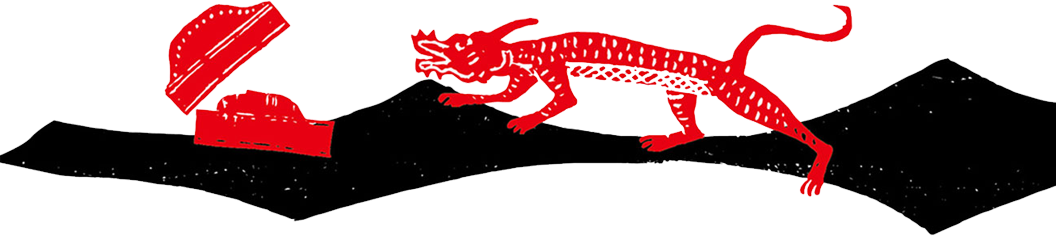
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在任何一个“当下”的种种热点问题之中,哪些才是新问题,哪些却是老问题,嗯,这是一个问题。
而且,还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比如这两年,年轻人中流行“请笔仙”,把笔仙当真的大有人在,结果搞得电视台请出专家来做解释,从心理学等等科学角度来破除笔仙迷信,但结果依然是信者自信、疑者自疑。其实这问题早有人做过极其深入的研究——许地山在几十年前就曾写过一部《扶箕迷信的研究》,论之极详,商务印书馆在1997年把这书印了区区三千册,使之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在小范围流传,其实如果趁着笔仙热把它重新包装一下,比如配些插图,找个中学生把许前辈的文字做一些生动的点评,书名改成《许地山谈笔仙》之类,封面文案再点明许地山就是《落花生》的作者,想来发行量无论如何也不止三千册吧?(我把好人做到底,再透露一个重要信息:许地山死于1941年,作品已经过了版权保护期了。)
笔仙这个新问题原来却是老问题,也早有人妥帖地解决了。眼睛再看看别处:近年又有人争论法国大革命的是是非非,好像以前我们所认为的那一场绚烂光辉的运动其实血腥得很。这是一个颠覆我们常识的问题,自然免不了许多辩论。但是,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有人把法国大革命的内容详详细细、残残酷酷地展现给我们了——他就是康有为,那时他游历法国,写下了一部《法兰西游记》,这部书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就在国内出版了,其中讲到大革命的“盛况”,除了各式各样的“屠”简直就找不到别的东西了——“异党屠尽,则同党相屠;疏者屠尽,则亲者相屠”,种种场面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或许正所谓“实现正义的热情,会使我们忘记慈悲为怀;对公正的热望,使许多人成了铁石心肠。”(奥克肖特《巴别塔》)
康有为还点了一句:“合数十百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一罗伯卑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君主。”看来他从激进派转为保守派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一百年啊!一百年前的这部《法兰西游记》也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读过?
和这些个问题一样,很多新问题其实都是老问题,下面我就再来说几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