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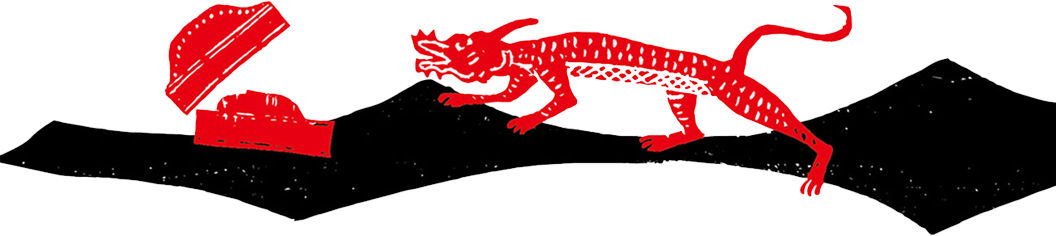
我们已经大略看过了儒学于汉、唐两代在政治运作中的实用意义,看来儒家典籍既可以在审案的时候被援引为法律判例,更可以在国家大政上发挥纲领性的指导作用。嗯,儒学并不像现在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什么讲做人、讲伦理的——不是的,儒学的核心是在政治,而且,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并不是很多现代人认为的那样主要体现在《论语》当中,而是体现在《春秋》里的。
钱穆曾经很清晰地梳理过这个脉络:“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
 ……此下魏晋南北朝以迄于隋唐,《春秋》列于经,仍非《论语》所能比。”后来直到宋朝,《论语》才和《春秋》平起平坐了,二程和朱熹则抬高《论语》超过了《春秋》,到清代乾嘉以后,《春秋》又超过了《论语》,“只有最近几十年,一般人意见,似乎较接近两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论语》,而忽略了《春秋》”。
……此下魏晋南北朝以迄于隋唐,《春秋》列于经,仍非《论语》所能比。”后来直到宋朝,《论语》才和《春秋》平起平坐了,二程和朱熹则抬高《论语》超过了《春秋》,到清代乾嘉以后,《春秋》又超过了《论语》,“只有最近几十年,一般人意见,似乎较接近两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论语》,而忽略了《春秋》”。

其实,要说这“最近几十年”,《春秋》也发出过不小的声音——晚清时代公羊学独胜,维新派拿它讲变法,革命家拿它讲“华夷之辨”和“易姓革命”,即如一向给人以埋头训诂之印象的杨树达前辈,也在1943年出版的《春秋大义述》自序当中倡明“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切复仇之志,明义利之辨,知治己之方”。他所指明的这几条“春秋大义”在当时是实有所指的。而如果以我们现在为坐标,这“最近几十年”的特色则更是明显——要知道,“《春秋》学”比“《论语》学”可复杂和深奥多了,所以,偌大文化断层边缘上的人们借助于《论语》来给断层搭桥显然要比借助于《春秋》容易得多。不过悲观地说,现在再怎么熟读《论语》和《春秋》,乃至其他种种儒家经典,都不会恢复当年的风光了——看看人家汉朝,儒者之学居然切切实实地施展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当中,影响着内政与外交,掌握着生杀大权,真是威风八面啊。
汉代的儒家政治传统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
不太较真地说,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首倡之人是董仲舒。
 董仲舒治学非常刻苦,“目不窥园”这个成语就是从他这儿来的。董仲舒是当时治公羊学首屈一指的专家——所谓“治公羊学的专家”,也就是研究《公羊传》的专家。在当时,因为《春秋经》号称是孔子所修,所以地位崇高,据说孔子他老人家还曾亲口说过,“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董仲舒治学非常刻苦,“目不窥园”这个成语就是从他这儿来的。董仲舒是当时治公羊学首屈一指的专家——所谓“治公羊学的专家”,也就是研究《公羊传》的专家。在当时,因为《春秋经》号称是孔子所修,所以地位崇高,据说孔子他老人家还曾亲口说过,“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更显得《春秋经》意义之无比重大。而如果说《春秋经》是一部权威教材,那么,为《春秋经》编写教辅的人也不在少数。在这里,《春秋》作为教材被称为“经”,那些教辅则被称为“传”。我们一直都说“《春秋》三传”,就是《春秋经》加上《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是谓“一经三传”。《春秋经》据说是孔子根据鲁国国史亲手编订的,其意义正如孟子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孔子一直都是“述而不作”的,只搞古籍整理,却从来不去原创,所以,《春秋经》作为他老人家唯一的“作品”,地位自然无比尊崇——比如清代桐城派名人方苞在《春秋直解》自序中说:“夫他书犹孔子所删述,而是经则手定也”——这是两千年来很主流的一种观点。但此事是否可靠,后人聚讼纷纭,我这里就不细表了。
,更显得《春秋经》意义之无比重大。而如果说《春秋经》是一部权威教材,那么,为《春秋经》编写教辅的人也不在少数。在这里,《春秋》作为教材被称为“经”,那些教辅则被称为“传”。我们一直都说“《春秋》三传”,就是《春秋经》加上《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是谓“一经三传”。《春秋经》据说是孔子根据鲁国国史亲手编订的,其意义正如孟子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孔子一直都是“述而不作”的,只搞古籍整理,却从来不去原创,所以,《春秋经》作为他老人家唯一的“作品”,地位自然无比尊崇——比如清代桐城派名人方苞在《春秋直解》自序中说:“夫他书犹孔子所删述,而是经则手定也”——这是两千年来很主流的一种观点。但此事是否可靠,后人聚讼纷纭,我这里就不细表了。
据说原本是孔子的学生子夏得了孔子《春秋》亲传,又传授给公羊高和榖梁赤,而后分别一代代口传心授,到汉初才形成文字,就是《公羊传》和《榖梁传》——这里边有没有猫腻,专家们也是一大堆意见,但我们先不去理会,就当这说法是真的好了。不过,即便承认此说为真,这么长篇大论的东西被几代人口头传承下来是否已经多多少少走了样,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左传》,号称左丘明所著,而这位左丘明据说还和孔子同时,甚至两人还有过交往,所以他对孔子时的史料知之甚详,对孔子作《春秋》的意图也领会得最深。至于这些说法是否属实,古往今来的专家做过数不清的考证——这在任何一本思想史著作或者“一经三传”注释本的前言里都能了解到,况且也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所以就不多说了。
“一经三传”,其实原本该说“《春秋》五传”的,另外两传是《邹氏传》和《夹氏传》,
 可惜都失传了。不过,韩愈有诗“《春秋》五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很让后人纳闷了一番:难道他那时候还能凑齐“《春秋》五传”吗?
可惜都失传了。不过,韩愈有诗“《春秋》五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很让后人纳闷了一番:难道他那时候还能凑齐“《春秋》五传”吗?

后来,继续为《春秋经》作传的大有其人,
 但名声能和“《春秋》三传”媲美的却只有一部,这就是南宋大儒胡安国写的《春秋传》(也可以称之为《胡氏传》或《康侯传》,胡安国字康侯),这部《春秋胡氏传》在元、明两代影响很大,甚至和那“三传”一同被列为“《春秋》四传”。
但名声能和“《春秋》三传”媲美的却只有一部,这就是南宋大儒胡安国写的《春秋传》(也可以称之为《胡氏传》或《康侯传》,胡安国字康侯),这部《春秋胡氏传》在元、明两代影响很大,甚至和那“三传”一同被列为“《春秋》四传”。
 更有甚者,胡安国这部书还曾被官方独尊,俨然居“三传”之上,甚或高居《春秋经》之上。
更有甚者,胡安国这部书还曾被官方独尊,俨然居“三传”之上,甚或高居《春秋经》之上。
 当然,学术的荣辱兴废无不是和政治有关的,胡安国这部书重点就在“尊王攘夷”和“复仇大义”上边,正是南宋偏安背景之下的应时激愤之语,乃至清人尤侗批评说:胡安国一门心思扑在复仇上,曲解经文来附会己意,他这部《春秋胡氏传》完全可以说是一本新书,和原本的《春秋经》没有一点儿关系。
当然,学术的荣辱兴废无不是和政治有关的,胡安国这部书重点就在“尊王攘夷”和“复仇大义”上边,正是南宋偏安背景之下的应时激愤之语,乃至清人尤侗批评说:胡安国一门心思扑在复仇上,曲解经文来附会己意,他这部《春秋胡氏传》完全可以说是一本新书,和原本的《春秋经》没有一点儿关系。

明代姜宝为徐浦《春秋四传私考》作序,把这“四传”的关系做过一个有趣的比喻:《春秋》就像老天,《左传》负责“照临、沾濡、焦杀、摧击之用”,《公羊传》和《榖梁传》就是日月、雨露、霜雪、雷霆,《胡氏传》则把大家伙儿的工作给统一调理起来,以成就一个大丰收的年景。

及至清初,有儒臣奏请废除科举考试中的脱经题,据毛奇龄说:“于是三百年来专取《胡传》阅卷之陋习为之稍轻”
 ,这也可见胡安国的《春秋传》曾经专擅科场三百年之久!不过,胡安国的这部《春秋传》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不论它再怎么出色,也确实没能一劳永逸地附列于“三传”之下,就好像赵云的加入始终没成就“桃园四结义”一样。
,这也可见胡安国的《春秋传》曾经专擅科场三百年之久!不过,胡安国的这部《春秋传》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不论它再怎么出色,也确实没能一劳永逸地附列于“三传”之下,就好像赵云的加入始终没成就“桃园四结义”一样。
清朝贬斥《春秋胡氏传》也是顺理成章的,那个恐怖的年头哪里还能再谈什么“尊王攘夷”呢,这正是统治者最大的忌讳呀。于是,“四传”又变回了“三传”。

在这“三传”当中,现在大家都比较清楚《左传》是怎么回事,不大熟悉《公羊传》和《榖梁传》,其实在最初的汉朝时候情况恰恰相反,大家不大重视《左传》,觉得《左传》虽然内容非常丰富,文学性也很强,但说到底无非就是一本史书,仅仅记载历史而已,而《公羊传》和《榖梁传》大为不同,这两部书是着重阐发孔圣人《春秋经》里边的“微言大义”的,所以应该归入意识形态领域,归入政治哲学类。——如果你是位现代社会的图书馆管理员,会把“《春秋》三传”分到一类,比如,既可以分在“中国古典哲学”类,也可以分在“中国历史”类,但你如果是位汉朝的图书馆管理员,就应该把这四部书分开来放:《春秋经》和《公羊传》《榖梁传》要归入“经典著作”,《左传》要单独归入“历史”类。当然,我说的这只是总体情况,在细节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公羊学”是最早成为官学的,兴于董仲舒,立于汉武帝。汉武帝的时代,正是汉代官学“破旧立新”的时代,哪家学术如果被立为官学,日后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于是,正如权力是专制政治这个“市场”上的稀缺资源一样,学术地位也变成了官学“市场”上的稀缺资源,以后会发生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学术地位是稀缺的,是稀缺就要有竞争,汉武帝还算公平,给大家设了一个擂台,让各大学派的掌门人公开过招,汉武帝亲自来当裁判。——这个裁判意义重大,开了风气之先,要知道,后世著名的石渠阁擂台和白虎观擂台也都是由皇帝来为学术争议做最高裁判的。但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一个问题:难道皇帝的学术水平还能高过在擂台上过招的那些学术专家吗,那些人可都是全国范围内最顶尖的高手哎!
但这时候高手不高手的看来并不重要,权力永远要凌驾于学术之上:一方面来说,皇帝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最伟大的统治者,同时还是最伟大的导师和最高的大祭司;另一方面,只有符合权力要求的学术才能在擂台获胜——反过来说,学术为了获胜,除了碰巧之外,就必须改造自己以迎合权力的需要。
一旦某种学术被立了官学、设了博士,荣华富贵也就随之而来了。当然了,专家学者们都是些饱读诗书的高尚人士,想来在打擂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庸俗念头的。现在,《易》学、《尚书》学等等我们暂且不谈,就单说这个“公羊学”。——事情是这样的:《春秋》学要立博士,《公羊传》和《榖梁传》都是解释《春秋经》的,见解有同有异,那时候人们的脑瓜还不够开通,觉得这两者只能立一家,于是,公羊派第一高手董仲舒和榖梁派第一高手瑕丘江公登上擂台,比武过招。
这位榖梁派的瑕丘江公,单听名字就知道是个高手,但可惜的是,他老人家肚子里存货虽多,却笨嘴拙舌,辩不过董仲舒。这就好比请陈寅恪上“百家讲坛”和易中天“争鸣”,陈老前辈恐怕输面居多。再加上当时的丞相公孙弘本身就是位公羊学专家,哪能让榖梁派讨了好去。结果瑕丘江公败北而归,汉武帝尊崇公羊学,安排太子学习《公羊传》,公羊学从此大兴。

公羊学之兴,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孙弘,他这位公羊专家以草民百姓的身份却不但当了丞相,还封了侯,这对天下读书人的刺激实在太大了,于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
。
但是,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太子虽然听了皇帝爸爸的话,开始学习公羊学,可学完之后却悄悄喜欢起《榖梁传》来了,于是找了位老师来辅导学业,而这位老师正是当年擂台败北的那位瑕丘江公。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人们很容易推测出来:汉武帝早晚是要驾崩的,等太子即位之后,公羊学必定失宠,榖梁学则要卷土重来。
这确实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但是,中途却出事了——出的还是件大事,这就是武帝朝极为著名的那场“巫蛊之祸”,太子被迫逃亡,而太子的亲娘、老婆、儿女,在这场动乱中全部死光。

太子的亲娘就是著名的卫子夫,所以,这位不幸的太子通常被人称为卫太子,前文提到隽不疑本着“春秋大义”毅然抓获一个在宫门外自称卫太子的人,起因就在这里。
卫太子事件是一起轰动朝野的冤案,而卫太子不幸中的大幸是,他有一个襁褓之中的孙子被人偷偷救了下来,抚养在民间,后来又阴差阳错地做了皇帝,是为汉宣帝。汉宣帝自幼在民间就听说祖父当年爱读《榖梁传》,于是自己也勤于诵习,待到即位之后,便以皇帝之尊公开贬斥公羊学、尊崇榖梁学,这其中所蕴含的恐怕并非什么政治考虑,而是对祖父的怀念和对曾祖父的报复吧。这段史事,是《汉书》当中极为感人的一幕。
自此之后,《公羊传》和《榖梁传》各有浮沉命运,暂不细表,而“三传”中的《左传》却终西汉之世始终未被列入官学,后来在新莽之际受到官方大学者刘歆的推崇,其后又在刘秀时代昙花一现,及至魏晋以后才渐重于世,至于真正升格为“经”而与《公羊传》《榖梁传》并列(甚至超过公、榖)则要晚到唐代。这段历史,伴随着长达两千年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脉络过于复杂,还是留到以后再说吧。
《公羊传》和《榖梁传》早为官学,地位崇高。既然是官学,就有相应的官办研究院,院里也有专业的研究员,但我们千万不能把它们和现代的大学做类比——如果要做个类比的话,大体可以说:汉朝的官办研究院近似于现代的党校,院里的博士近似于现代的党校老师。——即便不谈笼统的儒学,单就《春秋》学而言,通经致用之风历数朝而不衰,比如牟润孙讲宋代经学,说:“宋人之治经学,谈义理者则言《易》;谈政治者则说春秋大义。”
 所以说,当年的儒学(或仅仅是春秋学)绝对不像后来那样只是象牙塔里的皓首穷经,搞得个“人谁载酒问奇字,我欲携经坐古龛”那般的冷板凳,相反倒是热火得很,经义学问被广泛应用在现实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说,当年的儒学(或仅仅是春秋学)绝对不像后来那样只是象牙塔里的皓首穷经,搞得个“人谁载酒问奇字,我欲携经坐古龛”那般的冷板凳,相反倒是热火得很,经义学问被广泛应用在现实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公羊学,更要坐到实用政治学的第一把交椅。但这实在是件太有趣的事情,傅斯年所谓:“就释经而论,乃是望文生义,无孔不凿;就作用而论,乃是一部甚超越的政治哲学,支配汉世儒家思想无过此学者。”
 ——如果说得难听一些,傅斯年的话可以这样理解:一部胡说八道的经典和一门穿凿附会的学问竟然天长地久地被尊奉为官方政治学的圭臬,并且当真在指导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果说得难听一些,傅斯年的话可以这样理解:一部胡说八道的经典和一门穿凿附会的学问竟然天长地久地被尊奉为官方政治学的圭臬,并且当真在指导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无论如何,这一“通经致用”的确就是中国历史上主流的学术风气,好听点儿说,为学是要“有补于世”,当然,文字狱的时代又另当别论。这个“致用”,或者“有补于世”,大多和数理化没有关系,着眼点主要在政治上面。当年傅斯年议论这个问题,说了另一段很不中听的话:“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学术之用,非必施于有政,然后谓之用……”
 这话如果倒推,正说明了前人学术之用,是“必施于有政”的。
这话如果倒推,正说明了前人学术之用,是“必施于有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