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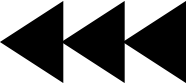
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在他们的一阶需求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买了那件我想要的夹克衫,就不能买那张我也想要的CD了”)。然而,一个形成了伦理偏好的个体,将会产生新的冲突。例如,假设我看了一部电视纪录片,片中讲述了巴基斯坦的一些小孩因为要完成缝制足球的工作而未能接受学校教育的事,我因此决定人们应该为杜绝此种情况发生做些事。两周后,我来到了一个运动用品商店,发现自己本能的选择是不想买更昂贵的工厂制作的足球。而基于我刚刚产生的伦理偏好(应当买较贵的工厂制作的足球),选择上的新冲突就此产生了。要解决这个冲突,我可以试图艰难地重新构建自己的一阶需求(例如,尝试不要自动偏好较便宜的产品),否则我就必须忽略这种新产生的伦理偏好(应当买较贵的工厂制作的足球)。人们的其他一些含有政治、道德或者社会承诺意义的反常举动,同样也会导致不一致的情况发生。由这个例子可见,人们新产生的价值和承诺造成选择中出现了新的不一致情况。如果人们不在乎价值和承诺,只关注计划好的能够有效地完成自己的一阶需求的行动,这些不一致的情况就不会出现。
简而言之,我们的价值观是用来启动对需求进行评价的一个主要诱因。行动/价值的不一致表明:我们需要对一阶需求和它们的价值进行规范化的批判和评价。价值因此为需求结构可能需要进行的重新建构提供了一种动力,它们使得人类理性成为一种广义的理性,其中个体需求的内容也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与大猩猩和其他动物的狭义理性特征有所不同。
对个体自身需求结构的批判有更正式的定义。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1971)在他的一篇引用率很高的文章中,将对个体自身需求结构的批判称为二阶需求——想要具有某种需求的需求。用经济学家和决策理论家通常使用的语言来说(Jeffrey,1974),这种更高水平的状态可以称为二阶偏好:对一系列特定一阶偏好的偏好。法兰克福猜测,只有人类才拥有二阶需求。并且,他将没有二阶需求的生物(其他的动物、人类婴儿)用一个能唤起人们相似感情的词命名为“荒唐者”(wantons)。我们说荒唐者不形成二阶需求,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身的一阶需求是不留意或不认真的。在狭义的、纯粹的工具性理性层面,荒唐者可以是理性的。荒唐者可能在它们的环境中表现良好,能够以最佳的效率实现它们的目标,只是不能对自身的目标进行反思;荒唐者是有需求的,但它们不在意自身的需求是什么。
法兰克福(1971)用三种类型的成瘾者,举例说明了这一概念。三种类型分别是:荒唐的成瘾者、不情愿的成瘾者和自愿的成瘾者。荒唐的成瘾者只是想得到毒品,这就是此种类型成瘾者的全部想法。荒唐者的其他认知器官都让位于找到满足需求的最好方式了(即荒唐的成瘾者完全可以被称为是工具性理性的)。荒唐的成瘾者不会反思这种需求,不会考虑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下这是不是一件好事,仅仅有需求就够了。相比之下,不情愿的成瘾者同荒唐的成瘾者有相同的一阶需求,但同时又产生了不想拥有这种需求的二阶需求。不情愿的成瘾者希望自己并不想吸毒,但是这种“希望自己不想吸毒的需求”没有“想要吸毒的需求”强烈。因此,不情愿的成瘾者最后也会和荒唐者一样继续吸毒。但是,不情愿的吸毒者和他们行为间的关系和荒唐者是不同的,不情愿的成瘾者的感受或需求同他们吸毒的行为间是分离的,而荒唐者不是。不情愿的吸毒者在吸毒时可能还会体验到一种对自我概念的背离,而荒唐者在吸毒行为中永远不会感受到。
最后是自愿的成瘾者(也是人类中存在的一种可能性)。自愿的成瘾者思考他们对吸毒的需求,并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这种成瘾者事实上希望自己吸毒。法兰克福(1971)为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类型,指出这样一种情况:当对毒品的渴求开始衰减时,自愿的成瘾者会想要采取措施增强成瘾度。自愿的成瘾者同不情愿的成瘾者一样,都对成瘾进行了思考,但在自愿成瘾的情况下,他们决定鼓励自身的一阶需求。
法兰克福(1971)描述的三种成瘾者虽然表现出了相同的行为,但是他们在需求阶层的认知结构上存在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虽然没有在现在的行为中得到体现,却可能对未来的成瘾性产生很大影响。不情愿的成瘾者(从统计上说)是最有可能发生行为改变的,这种成瘾者是三种中唯一有内在认知挣扎的类型。我们可以就此认为,这种挣扎至少可能会使一阶需求动摇或变弱。荒唐的成瘾者并没有这种内在挣扎,因而一阶需求有较少的可能性会被扰乱。然而,要意识到荒唐的成瘾者其实比自愿的成瘾者更有可能戒掉毒瘾,后者有一种内在的管理体系保证其成瘾性的存在,即需要成瘾的二阶需求。自愿的成瘾者会采取方法阻止成瘾性的自然衰减,而成瘾性的自然衰减在荒唐的成瘾者中并不会受到阻碍,他们会进而从事其他一些在其一阶目标等级中有较高位置的活动。如果荒唐的成瘾者戒掉了毒瘾,他们并不会感到伤心,同时也不会感到开心,因为此种情形下,成瘾者不会反思他们需求的产生和消失。
个体对自身需求结构所进行的批判这一概念,可以用在经济学家、决策理论家、认知心理学家中使用的更普遍的一个术语来进行更正式的解释(见Jeffrey,1974;Kahneman&Tversky,2000;Slovic,1995;Tversky,Slovic&Kahneman,1990),即二阶偏好(对一系列特定一阶偏好的偏好)。例如,想象一下约翰喜欢抽烟(他对抽烟的偏好大于不抽烟)。那么使用效用理论正式公理化的基础——偏好关系,我们可以有如下表示
S偏好~S
然而,似乎只有人类能够表现出一种具有理想化偏好结构的模型。例如,一个基于对长期生命年限考虑的高阶判断模型(或者是Gauthier,1986,称为考虑过的偏好)。因此,一个人可以说,相比于“偏好抽烟”,我偏好于自己“不偏好抽烟”。而且,只有人类能够从一阶的需求中脱离。用偏好的记法表示是
(~S偏好S)偏好(S偏好~S)
这种二阶偏好成为一阶偏好的激励性对手。在二阶偏好的水平上,约翰偏好于自己能偏好不抽烟;然而,他的一阶偏好却是偏好于抽烟。偏好结果的冲突表明,约翰缺乏诺齐克(1993)所说的对偏好结构理性整合的能力。这种不匹配的一阶/二阶偏好结构,是人类在公理化层面上的理性不如其他动物的原因之一(Stanovich,2004)。这是因为获得理性整合的挣扎会动摇一阶偏好,使其更易受到环境效应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对效用理论基本公理的违背。
为获得理性整合所做的挣扎,也造成身处现代社会的人在沉思自己的选择后,经常会感受到一种分离感。当人们的高阶偏好同他们实际做出的选择相矛盾时,他们很容易察觉到这一情况。
可以被构建的高阶需求层次数目是没有限制的,但是人类的表现能力却可能会对此产生一些限制——在非社会化的领域,对大多数人来说三个水平显然是一个合理的限制(Dworkin,1988)。不过,可以通过三阶判断来帮助个体获得对低阶偏好的理性整合。因此,比如说,前文提到的抽烟者约翰,可以通过对感觉的这种比较来实现整合:
他对他偏好于偏好不抽烟的偏好高于对抽烟的偏好。
这一关系可以用符号如下表示
[(~S偏好S)偏好(S偏好~S)偏好[S偏好~S]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说,约翰的三阶判断认同了他的二阶评价。可以假定,对他二阶判断的这种批准会增加他改变一阶偏好的认知压力,使其采取一些行为措施来让改变更可能发生(参加一个戒烟项目,和医生咨询,不去烟雾缭绕的酒吧等)。另一方面,三阶的判断也可能会对二阶偏好产生削弱的作用,比如在不批准它的情况下:
约翰可能对抽烟的偏好高于他对偏好不抽烟的偏好。
[S偏好~S]偏好[(~S偏好S)偏好(S偏好~S)]
在这个例子中,虽然约翰希望他不想抽烟,但对这种偏好的偏好并没有对抽烟的偏好强。我们可以想象,这种三阶的偏好不仅可能会阻止约翰采取有效的戒烟行为,并且长期下来可能还会侵蚀他对二阶偏好的信念,进而产生对三个水平的理性整合。
典型的是,哲学家会倾向于将他们的分析侧重在构建出的最高水平需求上——在对更高阶进行回归时给予其最高的权重,用最高阶作为分析的基础,并将其定义为真实自我。现代认知科学取代这种观点,提出了一种不特别赋予某一水平特权的诺伊拉特项目。哲学家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1932/1933;Quine,1960)使用了一个船身有一些腐烂木板的船只的比喻,来形象地说明这一问题。修理木板的最好方法是把船拖上岸,让其待在坚硬的土地上,然后再更换木板。但如果船只不能被带上岸呢?实际上,我们仍能修理船只,但是要冒一定的风险。我们可以在海上修理木板,在修理时踩在其他木板上。这项工程能够开展——我们可以不站在坚硬的土地上来修理船只。然而,诺伊拉特项目并不能受到完全的保证,因为我们可能选择站在了腐烂的木板上,这样就会发生危险。在法兰克福(1971)对高阶需求的阐述中,并没有任何地方能够保证,高阶的判断不会受到有损个人想法的影响(Blackmore,1990,2005;Dawkins,1993;Dennett,1991,2006;Distin,2005;Laland&Brown,2002;Mesoudi,Whiten&Laland,2006)。
理性整合的达成,不能总是通过简单地把分析水平中的少数偏好进行翻转来实现,而赋予最高水平特权这种简单的规则,也不能总达到最佳的效果。对于类似马克·吐温小说中人物哈克贝利·费恩矛盾思想的例子,有专门的哲学文献对其进行研究(如Bennett,1974;McIntyre,1990)。哈克出于最基本的友谊和同情心,帮助他的奴隶朋友吉姆逃跑。然而,当哈克开始对奴隶逃跑和白人对此的帮助这些事的道德错误进行明确的推理时,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行动是否正确。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希望哈克认同他的1型情感加工,而抛弃他所接受的明确道德教育。
哲学家曾经认为,除非我们有一个基础性的认知分析水平(最好是最高阶的),否则我们自身所珍视的一些东西(哲学文献中提到的例子如人格、自主性、身份和自由意志)就会受到威胁。相反,赫尔利(Hurley,1989)则赞成诺伊拉特式的观点,认为在需求的连锁关系之外,不存在一个“最高阶的平台”或所谓的真实自我。她主张“对自主性的练习,需要依靠我们一些特定的价值观作为评判和修正其他观念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和所有其他观念的脱离;并且,自主性并不依赖于向越来越高阶态度的回归,而应该从第一步起就需要开始重视”。简而言之,自我定义的这项人类独特工程始于第一步,此时个体开始攀爬有阶层的价值观阶梯,这也是个体第一次面对理性整合的问题。但我们如何知道个体已经深深陷入这种自我定义和理性整合的过程中了呢?有趣的是,或许对此最好的指示是,当我们探测到个体的一阶和二阶需求不匹配时,个体将在这两者中挣扎:其会承认一套特定的价值观,认为他应当偏好去做一些不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简而言之,人们期望能从广义上对理性进行设想,而不仅是从工具性理性出发。人们想要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但是他们也关心其所持有的需求是否正确。因为人们期望理性是从广义上而非狭义上定义,所以就需要对他们的理性进行一种包含两层(行为及需求本身)的评价。我们达成的工具性理性,必须通过考虑我们所追求目标的复杂性,以及我们认知批判动态性的分析来进行评价。换一种说法,狭义和广义的理性都需要被评价。检验工具性理性的标准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阐释。而评价广义理性的标准却更加复杂,并存在争议[见诺齐克(1993)对偏好评价的23条标准的讨论],但这些标准一定会包括以下内容:进行评价的强烈程度,个体对缺乏理性整合的厌恶程度和想要采取办法进行纠正的意愿,个体能否对所有的二阶需求给出原因,个体的需求是否会引发导致非理性信念的行动,个体是否会避免形成难以实现的需求,以及其他的标准等(Nozick,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