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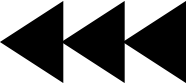
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2001)在其关于理性的一本著作的开始部分,提到了特内里费岛上著名的大猩猩问题[最早由心理学家沃尔夫冈·科勒(Wolfgang Kohler,1927)研究过],以及大猩猩所展示出的许多卓越的问题解决能力(这些已被纳入教科书中)。其中一个实验情境是:给大猩猩一个盒子、一根棍子,还有一串挂得高到它够不着的香蕉。在此情况下,大猩猩能够想出解决办法,将盒子放到香蕉下面,自己爬到盒子上,然后用棍子把香蕉弄下来。塞尔(2001)指出,大猩猩的行为达到了工具性理性的所有标准,它使用了有效的方式来完成自身的目标。通过采取合适的行动,大猩猩获得香蕉的首要需求得到了满足(见Jensen,Call&Tomasello,2007)。
塞尔根据柯勒研究的大猩猩所表现出的工具性理性,提出了一个挑衅性的问题:人类的理性是否仅仅是大猩猩表现出理性的一种延伸?依照艾尔斯特(1983)对理性的狭义和广义理论的区分,我们可以给出答案。作为人类,如果我们追求的仅仅是工具性理性的狭义理论,那么人类理性确实就如同大猩猩的理性一样。无论人还是大猩猩,他们对理性选择的评价都会按照同样的方式实行。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只需要明确:这一系列行动是否遵循了选择的公理?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大多数人不会满足于狭义的理论。大多数人对他们做出的选择和追求的目标都会持有一个立场。选择和目标经常会受到外部标准的评价,对选择的评价是依据它们给选择者带来的意义而做出的,而对目标的评价则是根据它们是否与人们所持有的价值观相一致做出的。
在一系列有关决策所具有的一致性内涵的文章中,梅丁和他的同事们(Medin&Bazerman,1999;Medin,Schwartz,Block&Birnbaum,1999)强调:决策不仅会对个体传递效用,同时也会对环境中的其他行动者发出富有意义的信号,象征性地增强了个体的自我概念。决策者经常会从事象征性的行动,(向自己或其他人)发送表明他们是哪种人的信号。梅丁和巴泽曼对许多实验进行分析,发现被试在自己认为需要保护的价值物受到威胁时,不愿进行交易或物品的比较(Baron&Leshner,2000;Baron&Spranca,1997)。例如,人们不想对自己的宠物狗、家族已拥有多年的土地,或者他们的结婚戒指进行市场交易。在梅丁和巴泽曼的被试中,人们会把对这种交易的请求视作一种侮辱,代表人们这种想法的一种典型性观念就是“这关乎意义,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1993)很好地阐述了这种能够帮助人们维持人格中价值观念的象征性动作的理性之处,尽管这种行为与人们体验到的效用之间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人们可能完全明白,做出某种特定行为只是某种类型人的一个特征,并不能直接使他们成为这类人。但是,在将这种类型的人象征化为一个模式后,做出该种行动可能会使个体得以维持自身的形象。对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投票行为就具有这种象征意义。许多人都清楚,我们在政治系统中进行投票,这种影响所能带来的直接效用(百万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的分量,取决于选举规模),还抵不上参与投票所要花费的努力(Baron,1998;Quattrone&Tversky,1984)。然而,很多人却仍旧不会错过每一次选举!投票对我们来说,就具有象征性的效用。它代表了我们是哪种人——我们是严肃对待投票的“这类人”。可以看出,我们使用了一种价值观念来评价投票的行动,而并不是仅仅根据体验到的效用对此进行评定。
另一个例子是买书,这对于许多热爱知识的人来说也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但通常情况下,买书的象征性效用,与消费效用或使用效用完全分离了。在这点上,我和很多人都一样,会买很多自己从来不会阅读的书(我完全明白自己所说的“退休后会有时间读书的”完全是白日梦)。然而,我从购买大量这类图书的行动中获得了象征性效用,尽管这些图书永远不会作为消费的商品产生效用。
森(1977)指出,我们会依据选择是否与自己的价值观相一致,来评判自己选择的倾向。然而,这种评判方式对传统经济学狭义理性的假设是一种威胁,因为它在选择和个人福利之间产生了分裂。基于价值的选择可能实际上会降低个体的私人福利(按照经济学家的测量方式),例如,当我们给一个政治候选人投票时,他可能会实施违背我们物质利益的行动,但同时又会表现出其他一些我们看重的社会价值。伦理偏好这一概念(Anderson,1993;Hirschman,1986;Hollis,1992)也有相同的作用,它会割断观察到的选择同经济文献中提到的工具性理性最大化假设之间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非工会葡萄的联合抵制,80年代对南非产品的联合抵制,90年代对新出现的公平贸易产品的兴趣,都是伦理偏好的例子。它影响了人们的选择,并且割断了对标准的经济学分析至关重要的、选择和个体福利最大化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