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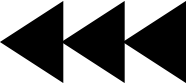
在本章中,我们一定程度上反驳了第2、3章中主导性的观点。
在前几章中我们看到,启发式和偏见研究者以多种方式表明了,工具性和认识性理性的描述模型与规范模型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这些研究者认为,这种差距是真实存在的,它显示了人类认知特征中存在的一种非理性反应模式。不过,作为社会改良主义者,他们认为这种差距是可以补救的。通过对恰当的理性思维策略以及概率思维和科学推断领域必要知识的训练,人们能够以更好的方式思考和做出反应。社会改良主义者认为,人们在总体上虽然不是完全理性的,但可以变得更理性。
然而,在本章中我们看到,许多相同任务上人们的普遍表现,似乎可以被重新解读为看起来更加理性的行为,这就是过度乐观主义理论者所采取的方法。如果我们接受本章中讨论的对任务的另一种解读,那么这些任务中很多被试的反应模式都会变得更符合理性。社会改良主义者和过分乐观派的观点有时也被称为元理论(metatheoretical)的视角,因为它们并不是针对某个特定任务的理论,而是一种会使我们的总体结论偏向一边或相反一边的广泛性的框架。两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和互补的优点以及缺点。
在一篇微妙地平衡了两者所持论点的文章中,阿德勒(Adler,1991)主张,最好将一个面对推理任务的个体看成在不同的目标体系中进行平衡,他需要牺牲自己的回答在某一方面的准确性来换取其他方面的提升。阿德勒指出,许多经典问题都要求人们在预测准确性和解释一致性之间做出权衡。比如在琳达问题中,如果被试表现出合取谬误的话,就失去了预测准确性——认为琳达是一名女性主义银行柜员的概率要高于琳达是一名银行柜员的概率,显然是押错了赌注。为避免做出错误的预测,个体必须忽略对琳达的性格描述。但另一方面,如果个体的关注点是建立起一个对琳达的描述在整体上具一致性的观点(一种能够帮助建立起对她未来行为期望的观点)的话,那么仅就这一点,密切关注对琳达的性格描述并且赋予其更高的权重就有意义了。因此,对解释一致性的关注会导致错误的预测,而关注预测准确性又会牺牲掉解释一致性。
阿德勒(1991)警告社会改良主义者,如果像实验者设定的问题那样,目光短浅地关注静止性的、一次性的目标,就会无意中忽视掉被试可能赋予实验任务的长期目标的合理性。同样,他也警告过分乐观派,“人们可以对一系列目标的看重程度高于另一系列,这种做法是合理的,但这并没有消除他们为此而牺牲了另一些正当目标的事实”。因此,尽管有类似本章前面提到的研究结果,如发现以频率形式表示的问题,经常会带来比单个事件版本的概率问题更好表现的现象,也并不能否认,如果人们必须要处理单个事件版本的概率问题,就会产生不准确的结果这个事实。阿德勒(1991)给出的平衡性观点同时囊括了对两个阵营的警告:
即使被试的回答是错误的,也不能排除这些回答在其他一些相关的评价维度上却很合适的可能性。同样,如果有一种能够适用于被试的合理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他们的回答被证明是正当的,这也并不能使他们的决策免于被批评。对决策和推理的研究要综合考虑多个评价维度,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理解。
阿德勒认为,试图仅使用一种评价维度来缓和社会改良主义者和过分乐观派的对立,是一种根本的不足。
因此,在这场争论中另一种有建设性的观点应当认识到,理性大争论中每一个阵营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盲点,每一种立场的提出都使得对人类理性的理论和实践争议更进一步:过分乐观派表明了从进化上进行解释的力量,以及把刺激的展示方式同进化所塑造的认知维度互相匹配的必要性(Cosmides&Tooby,1996);社会改良主义者则拥护了认知改变的可能性,并警示了人们,人类认知倾向与科技社会所要求的思维不匹配时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
然而,与之对应,社会改良主义者经常草率地宣称人们的推理过程具有瑕疵,因此可能会错失人类认知中存在的一些真正优势,而这些优势可以在改进人们的行为时加以利用。过分乐观派有时则不能承认,当科技社会以一种人们尚未在进化上适应的方式呈献在人们的认知器官面前时,就会产生真正的认知障碍;他们有时也未能强调,展示灵活性可以通过任务指示得以来提高,过分乐观派也经常忽视修复可以改正的认知错误的机会。
争论的两大阵营都承认了研究发现人们行为具有的相同事实,但他们对关注点的前景和背景的选取却不相同。社会改良主义者看到了一个似乎充满惊人讨厌事件的世界——金字塔销售计划面临“破产”并引发了财政困境,大屠杀否认者引起媒体关注,每年有100亿美元花在医疗骗术中,受尊敬的物理学家宣布他们相信创世论,金融机构似乎在自我毁灭并耗费了纳税人数以亿计的钱财——他们认为人类认知中一定存在一些基本的错误,才能解释这一切的大混乱。当然,社会改良主义者忽视的背景正代表了过分乐观派阵营关注的前景——所有人类具有惊人优异表现的认知特长。对后一阵营来说,以下这些人类的表现都是奇迹:人类是精巧的频率探测者,他们可以几乎超自然地轻松推测出他人的意图,他们从稀少的输入中就掌握了复杂的语言密码,以及他们能够以难以置信的精准度来理解三维结构(见Levinson,1995;Pinker,1994,1997)。
显然,两个阵营都意识到他们的立场有好处也有代价,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计算了付出代价和收获好处的可能性。例如,两个阵营对进化适应机制同科技社会中许多现实情况所要求的表现方式不相匹配的可能性,就有强烈的争论。社会改良主义者认为会有许多这类情况,因而被告知我们所拥有的这种不合适的机制,在一些其他表现方式下或许能够非常有效地工作,并不能起安慰作用。过分乐观派则认为,这种情况是很少的,我们为此做准备的能力被社会改良主义者对非理性归因的关注而降低了。简而言之,两个阵营对大脑中存储的认知表现与生态所匹配的程度,有着不同的假设。
启发式和偏见研究中的两派,内部都存在的一些先于理论的与认知修复有关的偏见,也有可能部分支持了社会改良主义者的立场,以及他们在过分乐观派阵营中的批评者的立场。促使先于理论的这种偏见产生的原因,也是由于两大阵营对人类理性本质不同假设的相对代价和益处赋予了不同的权重。例如,如果恰巧过分乐观派在他们的假设上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可能错失改善推理功能的机会。同样,不正当的社会改良主义也有其代价。对认知修复的努力可能是无用的,我们可能没能感受到并感激这种不需辅助的人类认知的惊人准确性。过度的改良主义可能导致一种倾向,忽略改变环境与改变认知相比,可能是一条更易改善人们表现的道路。
这些争议中的一些评论者感到,像社会改良主义者一样,认为人类的非理性属性非常广泛可能是对人们的一种侮辱。这种情感表现出了一种值得肯定的、对民间心理学以及研究发现的解读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的忧虑。但其他的评论者则怀疑,我们对此的直接反应——认为对人类非理性的归因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本身可能就表现出了自身的轻率。世界充满了由人类行动引发的灾难。社会改良主义者认为,这其中的一部分灾难,或许可以通过教会人们较少地受非理性的决策和行动的诱导来加以避免。
在社会改良主义者的立场之外,还有哪些解释存在?假设社会改良主义者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周围的战争、经济衰退、技术意外、金字塔销售计划、电话传销诈骗、宗教狂热、算命骗局、环境恶化、婚姻破裂、抵押贷款丑闻,这些混乱的事件都不是出于可改善的非理性思维,这难道不是更令人不安吗?如果这些混乱的发生不是由于人类的非理性,那么又是什么东西出错了呢?实际上,对此确实还有别的解释存在。一种解释就是,这些灾难的原因是一些更难处理的社会困境,比如著名的囚徒困境(Colman,1995;Hardin,1968;Komorita&Parks,1994),我们将会在第6章中对此进行讨论。
如果难处理的社会困境也不是原因所在,那么事实上对此还有一种解释,但这种解释就更令人不愉悦了。回忆一下,工具性理性意味着通过最有效的方式达成目标,但并不在意这些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世界看起来充满了灾难性事件,而每个人又被假定(按照过分乐观派的观点)在理性地追求他们的目标,并且这也不涉及社会困境,那似乎就只剩下一种最痛苦的解释了,即世界上一大批人一定是在追求一些真正邪恶的人类需求。第1章中讨论过狭义理性的问题,并提到这种狭义理性理论可能会认为希特勒是理性的。因此,设想世界上存在很多“理性的希特勒”,是一种能够使得过分乐观派对人类理性的假设,同观察到的每天发生无数人为灾难的现象相一致的方式。面对这样一种令人震惊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认为人类具有一定的非理性,反而并不像我们曾经想象的那么令人担忧。而讽刺的是,过分乐观派对完美人类理性的假设,也并不像它开始看起来的那么令人温暖舒适。如果我们对侮辱人类感到反感,那么似乎说他们是非理性的,比起说他们是邪恶的或者自私得可鄙,要好得多。
以上这些讨论,就是引发了人类理性大争论的元理论关注点中涉及的一些问题。看到这里,我们可能会问,是否有更多的实证方法能够裁决这些争议?或者,在解决这些争议之外,有没有可能有一种融合两种观点(社会改良主义者和过分乐观派的框架)的方式?第5章展示了一种进行了此种尝试的理论。在我们仔细叙述这项理论之前,需要先讨论一个重要的证据类别,是这类证据引发了第5章中对提出理论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