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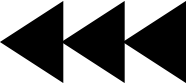
考虑第3章中讨论过的沃森(1966)的四卡片选取任务。被试面对桌上放着的四张卡片,两张上写着字母两张写着数字(K、A、8、5)。他们被告知,每张卡片都是一面数字一面字母,实验者对这四张卡片有如下一个规则(以“如果P,那么Q”的形式):“如果卡片的一面是元音,那么另一面就是偶数。”通常,只有小于10%的被试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卡片A(P)和卡片5(非Q)——这是要证伪这条规则所需的唯一两张卡片。被试做出的最普遍的错误选择是——卡片A和卡片8(P和Q),或者只选择了卡片A(P)。
对人们在这一任务上不佳表现的最早解释是,人们广泛存在一种在检验假设时不能顾及相反立场的倾向。然而,奥克斯福特和蔡特(Oaksford&Chater,1994)对人们在这个任务上的表现却有另一种解释,他们提出,被试所表现出的典型反应可能以一种更理性的方式对假设进行了检验。只是这需要我们认同一个关键性的假设,即被试读出了比字面上含义更深的指示内容。奥克斯福特和蔡特对选择任务的分析,假设被试是按照一种数据选择的归纳任务来理解任务的,他们有对多种类型卡片(元音、偶数)的相对稀缺性的假设。也就是说,尽管指示中只提到了四张卡片,被试却认为他们在从四组卡片(一组元音、一组辅音等)中进行抽样。现在想象你需要在现实生活中确认这条叙述,“如果你吃了牛肚你就会生病”。当然你会从“吃了牛肚的人”这个群体中抽样来证实或证伪这一叙述。然而,你会从“没有生病的人”这个群体中抽样吗?很有可能你并不会这么做,因为这个类别太大了。但你也可能从“生病的人”这个类别中抽样,去看是否他们中有人吃过了牛肚。
这种对待任务的方式在任务的指示中并无依据。指示中并未提及任何有关类别的信息——指示只是针对四张卡片。而奥克斯福特和蔡特(1994)的这种解释则假设被试认为自己在从四类卡片中进行抽样。基于奥克斯福特和蔡特所推举的表现模型,被试甚至对这四类卡片的相对稀缺性有暗含的假设,被试认为规则中提到的类别是较稀少的。而且,按照奥克斯福特和蔡特的观点,尽管指示中用到的表述是让被试确定真伪,大多数被试仍会忽略这个,而是按照归纳性概率的方式来思考。不论这种对指示的另一种解读是否有充足的依据,奥克斯福特和蔡特表明,一旦这种解读方式被允许,那么之后对P和Q的选择也就会更加符合理性。
关于奥克斯福特和蔡特(1994)对人们在这一任务上表现的解释是否正确,争论还在持续中(Evans,2007;Johnson-Laird,1999,2006;Klauer et al.,2007;Stenning&van Lambalgen,2004)。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允许了对这个任务指示所进行的这种另外解读,那么人们的表现就会变得更加理性。
进化心理学家已经说明,许多人们感到困难的抽象性问题如果被情境化,就容易处理得多,尤其是把问题以一种与特定进化适应模块所使用的表示法更符合的方式,进行情境化后。他们的一些工作也与四卡片选取任务有关。例如,在对这项任务的早期研究中,研究者最早想到,可能是由于元音/数字规则的抽象内容使得问题对于人们变得复杂,更偏向实际生活或者“主题化的”、不抽象的问题可能会极大地改善人们的表现。研究者因而尝试了类似如下目的地规则的例子:“如果‘巴尔的摩’在车票的一面,那么‘飞机’就在车票的另一面。”被试面临如下分别呈现的四张卡片:
目的地:巴尔的摩
目的地:华盛顿
旅行方式:飞机
旅行方式:火车
这四张卡片依次对应于“如果P,那么Q”规则中的P、非P、Q以及非Q选项。令人惊异的是,这种类型的任务内容一点也未能改善人们的表现(Cummins,1996;Manktelow&Evans,1979;Newstead&Evans,1995)。大多数人仍然选择了P和Q,或者只选了P卡片。正确的P(巴尔的摩)、非Q(火车)选择并未被大多数人所发觉。
格里格斯和考克斯(Griggs&Cox,1982)是第一个使用主题化版本的任务类型发现被试在实验中的表现有明显提高的,之后的研究者也多次证实了这一情况(Cummins,1996;Dominowski,1995;Newstead&Evans,1995;Pollard&Evans,1987)。下面是格里格斯和考克斯(1982)的规则中一种比较简单的版本,本书作者的研究队伍也曾使用过这一版本进行研究(Stanovich&West,1998a)。请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体会这道题目是否更加容易。
想象你是一名执勤的警官,在一个当地的酒吧内巡逻。你的工作是确保饮酒法令在这间酒吧得到执行。当你看到某人在酒吧进行某种特定活动时,你必须确保他首先符合规定该种情形发生的法令,其中的一条法令即“如果一个人在酒吧里喝酒,那么其必须年满21岁”。桌上有四张卡片,每张卡片上有关于一个人的两条信息。一个人是否在喝酒的信息在卡片的一面,而这个人的年龄则在卡片的另一面。有两个人,你能看到他们的年龄,但不能看到他们在喝什么;而另外的两个人,你能看到他们在喝什么,但不能看到他们的年龄。你的任务是确定是否有人违反了法令。请选择要确定法令是否被违背,你必须要翻开的卡片。你可以选择卡片中的任意一张或是全部。
四张卡片面向被试的信息依次是:
年龄:22
年龄:18
饮品:啤酒
饮品:可乐
大多数人都正确回答了饮酒年龄这个问题,包括很多在抽象版本中回答错误的人。虽然这两道题目的背后逻辑看起来是一样的,但事实就是如此。两者的答案都是选择P和非Q——在这个问题中,即啤酒和18岁。
随着饮酒问题的出现,研究者终于在15年来的研究后(以格里格斯和考克斯报告这项研究的时间1982年来计算),找到了一种能够让被试对沃森的四卡片选取任务给出正确答案的方法。然而,这种兴奋并未持续太久,因为研究者很快就开始怀疑,能够带来对抽象版本进行正确反应的推理过程,是否与饮酒年龄版本中引起正确反应的推理过程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尽管两条规则在表面上具有相似性,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它们事实上触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推理机制。例如,目的地规则,被称为指示性规则(indicative rule)的一种——一种有关对世界的陈述是否符合真实状态的规则。与此相比,饮酒年龄规则就是所谓的义务性规则(deontic rule)。义务性推理涉及考虑用来指导人们行为的规则——关于什么是“应该”或者“必须”完成的。卡明斯(Cummins,1996)将义务性规则定义为,“什么是个体在给定的一系列条件下可能、应该或者必须不能做的事”(p.161;又见Manktelow,1999;Manktelow&Over,1991)。大量的理论家都论证了义务性规则和指示性规则涉及的不同思想机制。
这些提议中最著名的一个是科斯米德斯(Cosmides,1989)的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她是为心理学打好进化理论基础的领头人物之一,这一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传遍心理学(Cosmides&Tooby,1992,1994)。她提出,进化过程让我们对有关人类互动的社会交换系统建立起专门的处理系统(她称为“达尔文算法”)。这些算法包含了基本的规则,“如果你得到一个好处,那么就必须付出一个代价”,并且是极端敏感的“作弊探测器”——它们对个体没有付出代价就得到好处的情况反应异常强烈。在饮酒年龄规则中,一个在规定年龄之下就喝酒的个体正是一名作弊者。因此,在这种规则下,一个18岁的人喝啤酒的可能性(P和非Q情况)就显得非常突出了,因为规则自动引发的进化算法正好与决定卡片选取的正确选项有关,人们碰巧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指示性的规则当然并不会引发这种达尔文算法,进化并没有为我们在大脑中提供解决指示性问题的特殊模块。解决这种问题的工具大都是文化的产物,并且由于这类问题需要较多的计算容量,支持它们的大脑过程也相对薄弱(Dennett,1991;Evans,2007;Stanovich,2004,2009)。
科斯米德斯(1989)的假设并不是对人们在饮酒年龄问题上优异表现的唯一解释(见Evans&Over,1996;Manktelow,1999;Manktelow&Over,1991)。其他的理论家对她观点的某些部分还有所争议,例如,过分强调调控社会交换的领域特异性模块和信息封装模块。然而,其他的解释与科斯米德斯(1989)的解释的确也有一定的相关性。他们倾向于将饮酒年龄问题看成工具性理性的一个问题,而非认识性理性的问题。指示性选择任务触及认识性理性:探测了人们如何检验有关世界本质的假设。相反,义务性任务则触及工具性理性:涉及了行动应当如何被调控,以及人们在特定情况下应当如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