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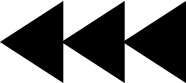
好的决策能够尽可能有效地满足个体目标,这是对工具性理性或者说行动理性的定义。认知科学家又进一步把对这种理性的定义,改进为主观期望效用的最大化这个定量概念。对期望效用的公理化方法,使我们能够不须进行效用的直接测量就可以评定理性。我们能够证明,如果人们遵循了一些特定的理性原则,那么不须直接测量效用值,就可以确定他们确实是在最大化自身效用。
公理化方法的所有原则,都不允许各种各样的无关情境来影响选择。倘若公理认定的情境因素影响了我们的选择,那我们所做的决策就是缺乏理性的。在这一章中,我们看到,人们会受一系列的情境效应所支配,而这种情况本不应发生在一个具备了工具性理性的个体身上。人们是否是理性的,这是一件我们需要切实关注的事,它并不仅仅是哲学课里要讨论的一个抽象问题,得出人们的行动是缺乏理性的这个结论有许多深远的影响。
本章所描述的思维偏见有很实际的含义:它们会导致一些严重的社会及个人问题。由于我们的这种理性思维能力未能适当建立,特别是由于本章前面所描述的一些情境化错误,导致了如下种种后果的产生:医生选择了不太有效的治疗措施;人们不能够准确地评估环境中的风险;司法过程中的信息被滥用;政府和私人企业将数百万的钱财投入不需要的项目;父母未能给子女接种疫苗;不必要的手术被实施;动物被猎杀以至灭绝;数以亿计的资金被浪费在无用的医疗方法上;耗费巨大的财政误判(Baron et al.,2006;Camerer,2000;Gilovich,1991;Groopman,2007;Hilton,2003;Sunstein,2002;Thaler&Sunstein,2008)。
然而,比这些实际影响更为重要的问题可能是理性和个体自主性间关系的本质。理性的表现意味着,我们的决策不会受到自身认为对决策无关的情境因素的影响。如果这些情境因素影响了我们的决策,就说明我们的自主权会被能够控制这些情境因素的人所掌握。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思维而去听从能够操纵我们环境的人;我们让自己的行动被那些能够创造刺激来触发我们肤浅的自动加工倾向的人所决定。我们使自己生活的前进方向,很容易受到能够控制我们所处符号环境的人的扭转。这些能够控制我们所处符号环境的人,包括控制展示给我们何种选择框架的人、控制选项中内容和展示顺序的人,以及控制我们的默认现状如何的人。
埃普利、马克和陈爱生(Epley,Mak&Chen Idson,2006)讲述了一个说明我们的行为是如何被控制框架的人所操纵的例子。他们进行了一个研究,受测者在实验室受到接待,并收到每人50美元的支票。在解释为什么他们会拿到支票的时候,一组受测者听到的描述是“奖金”,另一组受测者听到的描述则是“学费退款”。埃普利和他的同事推测,奖金会被编码成一种对现状的正向改变,而退款则被编码成回到原先的富裕状态。他们认为,由于从现状中花钱会更易被编码成一种损失,因而奖金的框架比退款的框架会导致受测者更快地花完这笔钱。事实也正是如此,当一周后再联系受测者时,奖金组已经花掉了较多的钱。在另一个实验中,受测者被允许从学校的书店中以很低的折扣买东西(包括零食)。又一次,奖金组的受测者在实验指定的折扣商店中消费了更多的钱。
埃普利在2008年1月31日《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里阐明了这些发现与现实的相关性。在2007~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议会和总统都在思索能够刺激当前衰退经济的机制。作为刺激人们消费的一种可能方法,退税这一手段正在被政府考虑(这种退税手段在2001年就被使用过,同样作为一种刺激机制)。埃普利在他的专栏文章里指出,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人们花钱,那么这个钱最好被冠以税费奖励的名义而非退还税款。“退还”这个术语意味着本来就是你的钱被退还给你,你重新回到了原先的某种现状。根据前景理论的预测,你不太会愿意取出现状下的钱进行消费。然而,把支票描述成税费奖励则意味着钱是“额外的”,是相对于现状的一种增加。人们会更愿意消费这种“奖励”。有关2001年使用的退税项目的研究指出,只有28%的钱被人们消费了,出现这种低比例的部分原因,很可能就是由于它不幸被描述为“退款”了。
埃普利的观点说明,政策分析家需要对措辞效用有更多的了解。相比之下,广告商就对这种措辞的重要性了若指掌。我们经常可以预见,一个产品一定会被广告宣传为“95%脱脂”,而非“5%含脂”,这些措辞的提出者非常清楚它们的意义。问题是,我们作为这些措辞的消费者,是否能够理解措辞的重要性,并将自己转变成一个更加自主的决策者。
对于选择是如何被以另一种方式措辞化及情境化问题,如果决策者不敏感的话,他们的选择就会被其所处世界中任何有权决定这些事情的人所决定。基于这样的描述,现状可能对我们很不利,但或许这里还有有利的一面存在。的确,一个对我们所处环境恶意的控制者很可能想利用我们。但一个对我们环境仁慈的控制者或许会愿意帮助我们——能够在不改变我们认知基本成分的情况下,将我们从不理性的行为中解救出来。因此,这个有利的一面就是,对于一些特定的认知问题,改变环境可能比改变人类认知更容易。因为,在一个民主制度下我们可以部分控制自己的环境,那么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我们就可以决定把世界重建成能够帮助人们表现得更理性的样子。
例如,在一个关于器官捐献率的跨国研究中,约翰逊和戈德斯坦(Johnson&Goldstein,2006)发现,在瑞典,85.9%的人都同意成为器官捐献者。然而,这个比例在英国却只有17.2%;在美国,这个比例是28%,相比瑞典要更接近英国的水平。瑞典、英国和美国之间器官捐献率的差别,同人们对器官捐献的态度间并无任何关系。这些差异的原因是,各国对成为器官捐献者的国家政策不同。在瑞典,正如比利时、法国、波兰和匈牙利这些器官捐献同意率高达95%以上的国家,对人们器官捐献态度的默认情况是赞同。在采取这种政策的国家,人们被默认允许自己的器官被使用,但可以通过一个行动来退出(通常是在他们的驾照上做一个标注)。与此相比,美国和英国,与德国、丹麦和挪威类似,器官捐献同意率都低于30%,默认的情况则是不捐献,要成为器官捐献者有着明确的行动要求。
所有这些国家公民的行为都受到了当地环境现状的极大影响。不同的表现,只是因为在一些例子中,当地环境的情况比其他例子被设定得更优。约翰逊和戈德斯坦(2006)判断,当人们在没有默认项的情况下真正思考这个问题时,大约会有80%的人(更接近瑞典和其他退出型国家的比例)倾向于成为器官捐赠者。自从1995年以来,美国有超过4.5万名病人在等待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死亡。对捐赠者决策环境的一点无害的改变(因为在所有假定人们同意捐献的国家,退出的选项都是被允许的),就可以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类似这类器官捐献的例子使得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和法律理论家凯斯·桑斯坦(Thaler&Sunstein,2008)支持一种他们称为“自由意志家长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政策。在他们的理论中,家长制的部分就是认为政府应当操纵人们的选择朝向对他们自身有利的行动;而自由主义的部分,则是为了保证政策的改变而保存了选择的完全自由性。如何能够在不干扰人们选择自由的情况下操纵人们的选择?答案就是,利用决策者对情境的极度敏感性。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要控制环境中(间接)影响决策者行为的方方面面,即默认值、框架、选择集合、指定的现状、选择的过程以及选择的描述等。我们作为人类的天然倾向,就是会受到选择环境中无关方面的影响,这导致了我们做出缺乏理性的选择。但是,利用集体智慧,一种被塞勒和桑斯坦(2008)称为“选择体系”的民主决策的形式,可以帮助我们设计出一种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环境,也使我们能够采取更多的理性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