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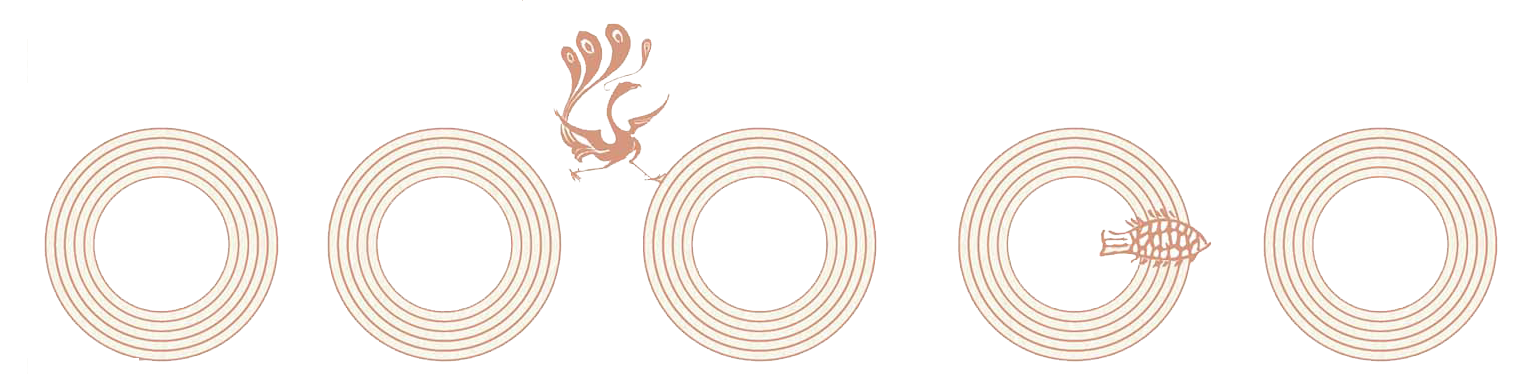
祭祀之礼的重要性,可从《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语看出来。但如果我们追问一句:在祭祀这个“国之大事”的问题上,是祭祀的对象重要,抑或是祭祀者在祭祀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和怀抱的精神重要?
以常情论,照说应该是祭祀对象重要,所祭之对象如不重要,祭又何为?然而在中国文化的话语里,是又不然。的的确确是祭祀者所具有的“敬”的精神,比祭祀对象还要重要。《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具列出如何对民须施以“十二教”,其第一教便是:“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礼记·少仪》也说:“宾客主恭,祭祀主敬。”此处的“祭祀主敬”一语,可以说是对“祀”与“敬”的关系的最精要的概括。
敬和诚一样,都是需要“无为”的,其大忌是刻意地操持饰作。《礼记·祭统》说得好:“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礼,安之以乐,参之以时,明荐之而已矣,不求其为。”忠敬和诚信是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信仰,其最高的致祭境界,是本乎自然,“不求其为”。如果祭祀者故意在那里经营操持,就失去了本身应有的真正的“诚敬”。故《礼记·祭统》说:“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然则祭道之“敬”,以诚信之“尽”来标识,说明“敬”这个价值理念已经超乎语词环境,具有了绝对的性质。
《礼记·檀弓》还有一句话,更道出了此一题义的全部谜底。这句话是:“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几乎将“敬”视为祭礼的全部义涵。“祭礼”之礼,本来是有祭祀对象,然后才有祭祀的礼仪。可是《礼记》此篇却说,“礼”不足尚不能算是祭礼的大问题,但如果“敬”不足,就是祭礼所绝对无法容忍者。这句话,子路说是“闻诸夫子”。《礼记》诸篇借孔子现身说法的事例多有,此处的引述是否即为孔子话语之所原出,似不好确指。
但《论语·八佾》篇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一语,则真真切切地是出自孔子之口。此处,孔子等于对祭祀对象做了一个假设,即在祭祀的时候,要假设“神”是存在的,或者说是“在场”的。因为只有祭祀时相信“神”是“在场”的,祭祀的人才可能守持得住纯洁的诚敬之心。反之一面祭祀,一面心里却在怀疑“神”到底“在”还是不“在”,敬的精神便难以树立了。显然孔子强调的是“敬”这个价值理念在祭祀现场的发用。至于非祭祀情况下“神”是否依然存在的问题,孔子没有回答,似乎也不想回答。
应该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一是不“在”。事实上孔子对“神”的存在与否,并不特别关心,这有他的众多相关言论可证。《论语·述而》篇辑录孔子的说话,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记载。同一书的另一条,还记载孔子说过:“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而当有一次,弟子直接向他请教如何事“鬼神”的时候,孔子近乎抬杠似的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口气显得很不耐烦。
口气显得很不耐烦。
祭祀的时候,假定“神”存在,不祭祀的时候,“神”存在不存在不在探寻范围,这应该是孔子对待“神”的本然的态度。因此“神”在孔子眼里并没有成为信仰的对象。但对于祭祀者必须具有的敬的精神,孔子却一点都不马虎。他认为祭祀者的“敬”的主体价值,远比对祭祀对象的斟详要重要得多。这里不妨以《红楼梦》的男主人公贾宝玉对祭祀所持的态度,来补充、参证、领悟孔子的祭祀论。
第一个例证,是《红楼梦》第五十八回,回目作:“杏子阴假凤泣虚凰,茜纱窗真情揆痴理。”写贾府专事演戏的十二个女伶中的藕官,在大观园烧纸钱去祭死去的菂官。原因是两个人经常饰演夫妻,所以存了一份同性相爱之情。宝玉得知个中缘由,不禁视为同调,“又是欢喜,又是悲叹,又称奇道绝”。但又特地请芳官带话给那个烧纸钱的藕官:
以后断不可烧纸钱。这纸钱原是后人异端,不是孔子遗训。以后逢时按节,只备一个炉,到日随便焚香,一心诚虔,就可感格了。愚人原不知,无论神佛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例的。殊不知只一诚心二字为主。即值仓皇流离之日,虽连香亦无,随便有土有草,只以洁净,便可为祭,不独死者享祭,便是神鬼也来享的。你瞧瞧我那案上,只设一炉,不论日期,时常焚香。他们皆不知原故,我心里却各有所因。随便有清茶便供一钟茶,有新水就供一盏水,或有鲜花,或有鲜果,甚至荤羹腥菜,只要心诚意洁,便是佛也都可来享。所以说,只在敬,不在虚名。以后快命他不可再烧纸。
贾宝玉虽然平时有“毁僧谤道”的言动,但对祭祀的事情却极为严肃认真。他此番言论的核心题旨,是关于祭者所应秉持的“诚心二字”,以及“心诚意洁”的态度,认为“一心诚虔,就可感格”。贾宝玉还说:“只在敬,不在虚名。”反复强调的祭祀态度,无非是诚敬而已。
第二个例证,是《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贾宝玉在晴雯蒙冤而死之后,撰写了一篇《芙蓉诔》并为之祭奠。这一情节,书中是这样写的:
独有宝玉一心凄楚,回至园中,猛然见池上芙蓉,想起小丫鬟说晴雯作了芙蓉之神,不觉又喜欢起来,乃看着芙蓉嗟叹了一会。忽又想起死后并未到灵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岂不尽了礼,比俗人去灵前祭吊又更觉别致。想毕,便欲行礼。忽又止住道:“虽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也须得衣冠整齐,奠仪周备,方为诚敬。”想了一想,“如今若学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况且古人有云:“潢污行潦,蘋蘩蕴藻之贱,可以羞王公,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
贾宝玉这段关于祭奠的心理独白,也都是围绕“诚敬”二字。而且对祭者如何诚敬有所提示,比如“衣冠整齐,奠仪周备,方为诚敬”等等。而提出祭奠之物,不在贵贱,是为祭礼勿奢之意,也是孔子的思想。
向被认为具有“反儒”思想的贾宝玉,却在祭祀之道上为孔子提倡的思想正名背书,简直是在宣讲孔子的祭祀之道了。是呵!贾宝玉在第一个例证中不是同时还说,烧纸钱不是孔子遗训,而是后人不明祭祀之理而走入的“异端”吗?一向被认为是“异端”的怡红公子,也在反对“异端”了。当然,问题不在于异端不异端,而是究竟何者为异端,何者是正理?《红楼梦》作者一定充满自信地认为,他所阐释的才是孔子的至理真道。
要之,连作为经典名著的稗史说部都可以出来证明,在孔子那里,“敬”已经具有了可以超离对象的独立的精神本体价值,实即绝对的义理价值,也可以称之为人类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