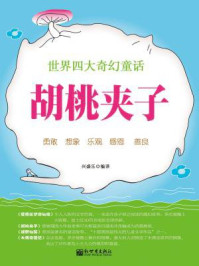玛丽睡了很久,醒来时,天色变得非常昏暗。火车停靠在一个站台,而莫德劳克太太正在摇醒她。
“你已经睡得够久了!”她说,“该睁开眼睛啦!到斯韦特站了,接下来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赶呢!”
玛丽站起来,尽力睁开眼睛,莫德劳克太太正在收拾着她的行李,但玛丽没有一点儿想要帮忙的意思,在印度时,拿东西、搬东西永远是印度仆人的工作,对玛丽而言,让别人伺候自己是很理所当然的事。
车站很小,除了她们之外没有其他人下车。在小站台的外边,停着一辆四轮马车。玛丽看着时髦的车厢,就连扶她进车厢的车夫打扮得也挺时髦的,他身上的长雨衣、雨帽都滴着雨水,反着光。
车站站长关上门,和车夫一起堆好行李箱子后,他们便开车了。玛丽发现自己坐的角落有垫枕,不过她不准备再睡了。她眼睛望着窗外。马车灯在他们前面投下一束束的光线,她匆匆瞥过光线照耀之处。离站后,他们驶过一个极小的村庄,她看到墙面粉白的农舍,农舍里有灯光,农舍里橱窗模样的小窗里有玩具、糖果和其他小东西出售。接着他们经过了一座教堂的牧师的房子,然后他们上了公路,她看到灌木篱笆和树木。接下来的景色则没有任何变化。
终于,马车开始慢下来,好像在上坡,现在没有灌木篱笆和树木了。除了一片漆黑,她看不见任何东西。突然,马车大大颠簸了一下,她身体猛然前倾,脸也跟着压到了玻璃窗上。
“嗯!现在可以肯定我们到荒泽上了。”莫德劳克太太说。
马车灯的一道黄光照着粗糙不平的路面,这条路看来是从灌木和低矮植物中穿过,那些植物被沉沉的黑暗笼罩着。一道风起,传来一阵单调、低沉、急促的声音。
“那是不是海?是不是?”玛丽问,转过去看着莫德劳克太太。
“不,不是。”莫德劳克太太回答,“也不是田野和山脉,那只是一块无边无际的荒地,什么也不长,只有石楠、荆豆和金雀花;什么也不生,只有野马和绵羊。”

马车在黑暗中疾驰着,尽管雨停了,风仍急急掠过,呼啸着发出怪声。路面时高时低,马车过了几座小桥,桥下水流很急,发出巨大的声响。玛丽觉得这段路似乎永远走不完,那宽广、荒凉的荒泽是一片茫茫的海洋,她正沿着一条小路穿过它。
“我不喜欢这儿,”她心想,“我不喜欢这儿。”她的嘴唇抿得更紧了。
马车正行驶在一段上坡路的时候,玛丽看到了亮光。莫德劳克太太舒了一口长气。
“啊,看到那点灯光我心里就踏实了,”她说,“那是庄园门房的灯。等一下我们无论如何得先好好喝杯茶。”
他们的车从圆顶拱廊驶进一片开阔场地,停在一栋很宽阔但不是很高的房子前面,房子似乎松散地围着一个石头院子。起初玛丽以为那些窗户里没有灯,但是她下马车后看见楼上一角有暗淡的红光。
入口的巨门用厚重的橡木壁板做成,壁板形状新奇,装饰着大铁钉,镶着大铁棍。它开向一间巨大的厅堂,灯光昏暗,墙上画像的脸、穿铠甲的人,这些都让玛丽好奇地多看一眼。她站在石头地上面,形成了一个渺小、奇怪的黑影。她脸上显露的表情和心里的感觉一样,都是那么的微小、迷惘、古怪。
一个瘦巴巴的老人站在为她们开门的男仆旁边。

“你带她去她的房间,”他的声音沙哑,“他不想见她。他明天早上要去伦敦。”
“好的,皮切尔先生,”莫德劳克太太回答,“只要告诉我要我做什么,我就会照办。”
“你要做的,莫德劳克太太,”皮切尔先生说,“是保证他不被打扰,不让他见到他不想见的东西。”
然后玛丽·伦诺克斯被领去了她的房间,她爬上一段楼梯,沿着一段长走廊下去,又登上一小截台阶,穿过两条走廊,来到墙上一道被打开的门里,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有炉火的房间,晚饭正摆在桌上。
莫德劳克太太冷冰冰地说:“行了,你到了!这个房间和隔壁的那间归你住,你只能在这两个房间里活动。不要忘了!”
就这样,玛丽来到了米瑟斯韦特庄园,她这辈子恐怕都没有比现在更不开心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