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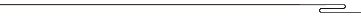
我建议将下列问题暂置一旁,因为尚需更进一步的探讨。这些问题是,儿童的原始自恋遇到的障碍,儿童为保护自我对付障碍的反应及其不得不采取的方式。不过,最重要的问题可归结为“阉割情结”(男孩对阴茎的焦虑及女孩对阴茎的嫉羡),并将它视为性活动早期受阻的结果予以分析。
精神分析的研究使我们能够追溯到,从自我本能中分化出来的力比多本能的变化。但在阉割情结的特殊情形下,我们可以推断存在着一种“纪元”(epoch)和一种心理情境,在它们的存在中,这两种本能依然相互融合地联合活动,以自恋兴趣的形式表现出来。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阿德勒发展了他的 “男性抗议” (mastuline protest)概念,他几乎将它视为性格及神经症形成的唯一动机力量(motive force)。不过,这不是建立在自恋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社会价值的基础上,并且仍然具有力比多倾向。精神分析的研究从一开始便确定了“男性抗议”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与阿德勒的看法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它本质上是自恋的,并源于阉割情结。在性格形成方面,“男性抗议”与其他许多因素共同起作用,根本不适于对神经症问题的解释,而阿德勒仅考虑了它服务于自我本能的方式。我发现,将神经症的形成建立在阉割情结这狭窄的基础之上是根本不可能的,虽然在抵抗神经症的医治方面它力量十足。在我遇到的几例神经症中,“男性抗议”,或我们视作的阉割情结,根本不是致病的原因,甚至压根儿就未出现过。
对正常成人的观察表明,他们早先的妄自尊大已经消除,而我们欲从其心理特征中引申的婴儿自恋也不复存在。他们的自我力比多变成了什么呢?我们可以设想它均变成了对象贯注吗?显然,这种可能性与我们论证的总趋势背道而驰。但在对压抑的心理分析中我们也许会找到回答这一问题的其他思路。
我们知道,如果力比多本能冲动与一个人的文化和伦理观念发生冲突,那么,这些冲动便会出现病理性的压抑变化。就此而言,我们绝无意认为个体具有这些观念存在的知识,而是认为个体能将这些观念作为自己的标准,并服从于这种标准的要求。
我们说过,压抑来自自我,不过更确切地讲, 压抑来自自我中心的自尊 。同样的印象、经验、冲动和欲望,一个人可以沉溺其中难以自拔或至少能通过意识的检验,另一个人则可能由于强烈的自尊而拒绝接受,甚至在未进入意识前就被扼杀了。两者压抑条件的不同可以用力比多理论加以描述。可以说,后者为自己确立了一种理想(ideal),他以理想检验自己实际的自我;而前者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理想。 对自我而言,理想的形成可称为压抑的形成因素 。
理想自我 此时成了自爱的目标,即便童年时曾为真实的自我所陶醉,个体的自恋会将自身展示给新的理想自我。理想自我就像 早期自我 (infantile ego)一样,发现自己最有价值的部分。
就力比多的经常表现而言,个体在此表现出不能放弃曾经有过的满足,他不愿弃绝童年的自恋完美性(narcissistic perfection),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为别人的告诫及自己评判力的唤醒而烦恼,于是,他再也不能保持原来的满足感,并寻求自我理想的新形式而将其恢复。个体为自己树立的理想不过是童年失却的自恋的替代,在那种自恋中他就是自己的理想。

自然地,又到了该检验理想的形成与升华的关系的时候。 升华是一个与对象力比多有关的过程,它将本能指向远离于性满足的其他目标。 在这一过程中,重点强调的是性的转移。理想化是一个关系到“对象”的过程,通过理想化,个体在不改变对象的条件下,在心目中将对象聚集和夸大。理想化既可产生于对象力比多中,也可产生于自我力比多中,比如,对某一对象性的高估便是对它的理想化。既然我们一直将升华与本能相联系,将理想化与对象相联系,这两个概念当然是相互区别的。
将自我理想的形成与本能升华的混淆会有损我们对事实的理解。一个将自恋敬献给很高的自我理想的人未必导致本能的升华。升华是一种特殊的过程,理想也许能促动它,但其过程却是完全独立于这种促动的。正是在神经症患者中,我们发现了在自我理想的发展与原始本能的升华量之间存在着潜能的最大区别:要说服一个理想家力比多的不明智分布,远比说服一个虚荣心保持更适当的一般人更为困难。
此外,在神经症的病因方面,自我理想的形成与升华也是极其不同的。正如我们所知,理想的形成增强了自我的要求,是导致压抑的最强大因素;升华则是一种出路,可以在无压抑的条件下满足自我的这些要求。
如果我们能发现一种特殊的心理器官,它负责观察自我理想怎样实现自恋满足,并为了这一目标用理想检验真实的自我,那么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如果这样的器官真的存在,那我们遇见它就不是“发现”的结果——我们只能确认它,因为我们所称的“道德心”(conscience)具有我们所要求的特征。对这一器官的确认使我们能够理解“被视妄想”(delusions of being noticed),或者说是“被观察”(being watched)。这是偏执狂疾病的显著症状,或作为一种独立的疾病出现,或在移情性神经症中夹带出现。这类病患抱怨他们所有的思想都为别人所知,他们的行为被别人所观察和监视,好像有第三个人告诉了他们这一器官的功能(“现在他又想那个了”,“现在他走了”)。这一抱怨是被证实了的,它描述了真实观察、发现和批评我们所有意图的力量确实存在,在我们每个人的正常生活中都确实存在。
由于“被视妄想”以退行(regressive)的形式展示了其能量,所以病人试图抵抗它的过程与原因也便显露了出来。比如,是什么促成了病人自我理想的形成?监视其行为的道德心是代表谁的?是父母的批评性影响(通过声音的传递),还是随着时间的进展增加了训练者、教育者及环境中无法计量的人的影响(同伴及舆论)?
通过这种方式,同性恋力比多的大部分便形成了自恋的自我理想,并找到了保持该理想的途径及获得该理想的满足。道德心的建立基本上是一个体现外在影响的过程——首先是父母的批评,其次便是社会的批评。这一过程会重复出现在下列情形中:来自外界的禁止或阻碍使个体出现了压抑的趋势。于是疾病便将无法确定的人群、声音带到了跟前,道德心以退行的方式重新构建。然而,患者对“稽查器”(censoring agency)的反叛源于自身的愿望(与病症的基本特征相适应):免受所有这些影响的束缚,从父母开始,将同性恋力比多从他们身上撤回。这样,患者的道德心便进入了外界的敌对影响下的退行状态。
偏执狂患者的抱怨还表明,道德心的自我批评与建立在此之上的自我观察基本上是共生的。这样,具有道德心功能的心理活动还负责“内心探索”(internal research),从而在物质上增强了其智慧活动能力,这也许有助于偏执狂患者的特征趋向构建思辨系统。
如果这种富有批评性的观察器活动(变成了道德心和哲学性内省)可在其他领域中被发现,那对我们来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在此我将提到西尔伯瑞(Herbert Silberer)所称的“功能现象”(functional phenomenon),这是对梦理论少有的无可争辩的有价值的补充。
众所周知,西尔伯瑞认为,在睡眠与清醒之间的状态,我们可直接观察思想向视觉表象的转化。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见的表征(representation)却不是思想内容的,而是反抗睡眠的人的实际状态(愿望、疲劳等)。西尔伯瑞同样指出,梦的结论或某些片断的内容不过是梦者对自己睡眠与清醒知觉的象征而已。这样,西尔伯瑞便明确了观察在梦的形成中的作用(从偏执狂病人被视妄想的意义上讲)。这一作用并不是持久不变的。我所以忽视它,也许因为在我自己的梦中它从未起过任何重要作用,对于天才的哲学家或习惯于内省的人,观察的作用也许是非常显然的。
在此我们可以回忆已经发现的事实,梦形成于“稽查”主导之时(强迫对梦的思想进行歪曲)。然而,我们并没有将这种稽查描述为一种特殊力量,而是用该术语表明控制自我的压抑倾向的一个方面,即指向梦的思想的方面。如果更进一步地探讨自我的结构,我们就会发现,在自我理想及良心的动力学言辞之中还有“梦稽查”(dream-censor)。即使在睡眠中这种稽查警觉到一定程度,我们也会理解自我观察和自我批评何以会有这样的活动。比如,“他困得实在不能思考了”,“他现在已经醒了”。这些活动为梦的内容做出了贡献。
说到此我们便可以讨论正常人与神经症者的自尊问题了。首先,在我们看来。自尊是 自我规格 (size of ego)的一种表达,而决定规格的因素是什么倒是无关紧要的。一个人占有的任何方面,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他的经验所确定的任何原始全能感(primitive feeling of omnipotence)的残余,都可以增强他的自尊。
在注意到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的区别时,我们必须明确,自尊对自恋力比多有特殊的依赖性。有两个基本事实可支持这一点:精神偏执症的自尊是增强的,而移情性神经症的自尊却降低了。在爱情关系中,不被爱降低了自尊,而被爱则增强了自尊。如我们已指出的,自恋对象选择的目的与满足恰恰在于被爱。
此外,很容易观察到,力比多的对象贯注并不会增强自尊,对所爱对象的依赖反而会降低自尊感:恋爱中的人是低劣的。也就是说,爱别人者失去了自恋的一部分,只有被爱才能将其替代。在所有的条件下, 自尊似乎总与爱的自恋因素有关。
由于心理或生理障碍而不能爱的人,一旦意识到丧失了爱的能力,其自尊便遭到强烈地挫伤。以我之见,我们必须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移情性神经症者随时都告知于人的 自卑感 (feelings of inferiority)。最主要的恐怕就是自我的剥夺,它源于大量的力比多贯注从自我中撤出。也就是说,由于自我的性趋向再也不被控制而使自我受到伤害。
阿德勒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即当一个人活跃的心理生活使他意识到自己某一器官的缺陷时,他就会产生一种动力,产生一种更高水平的活动,以实现过度补偿 (over compensation)。然而,如果我们遵照阿德勒的例证,将任何成功的成就都归结为器官的原始缺陷,那无疑是言过其实的。
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视力不好,所有的演说家也并非先天的口吃者。倒是有足够的例子证明,杰出成就的取得源于“优越”(superior)的器质性天资。神经症的病因学研究表明,器官缺陷及不完善的发展并不起什么作用,正像当前主动感觉到的物质对梦的形成不起作用一样。神经症者倒是以缺陷为借口,这如同用任何其他适宜的因素做借口一样。我们或许可以相信一个女神经症病人的话,她说她肯定会得病,只因为她长相丑陋,缺乏魅力,于是没有人会爱她。但她的神经症会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她会坚持其神经症及对性的厌恶,尽管与一般的女性相比,她的欲望更强或更为别人所爱。大部分歇斯底里症女性患者都是富有吸引力,甚至是漂亮的,而在社会较低的阶层中,女性的丑陋、器官缺陷及疾病(体弱)却并未导致神经症的增加。
自尊与性欲的关系,也即自尊与力比多对象贯注的关系可用下列方式清晰地予以表达。有两种情形必须分清,即 性欲贯注 (erotic cathexes)是自我和谐的(ego-syntonic)还是受到压制的。
在第一种情形下(力比多的活动表现为自我和谐),对爱的估价像对待自我中的其他活动一样,因为爱本身总与渴求和剥夺相联,故降低了自尊。但若被爱,这时候爱被归还,主体占有所爱的对象,自尊则会再度增强。力比多一旦受压抑,性欲贯注使自我严重枯竭,爱的满足毫无希望,自我的重新丰满只有通过力比多从对象上撤回才能实现。对象力比多对自我的重归及向自恋的转移,标志着(本应该的)幸福之爱的重现。当然,从另一方面看,真正的幸福之爱与原始条件是相符的:对象力比多与自我力比多根本无法区分。
为证实该主题的重要性及广泛性,我还必须再强调几点,因为在此之前这些方面总是松散地拼在一块的。
自我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以离开原始自恋为始然后再拼命地恢复。这种分离是由外力之下的力比多移置于自我理想造成的,而满足则源于理想的实现。
与此同时,自我又使力比多进行对象贯注。由于这些贯注而使自我贫乏不堪,如同它为了实现自我理想一样。同样,自我的丰满还必须再通过对象贯注的满足,如同它通过理想的实现一样。
自尊的一部分是原始的,即婴儿自恋的残余,另一部分源于个体经验证实现的“全能”(自我理想的实现),还有一部分来自对象力比多的满足。
自我理想通过对象对力比多满足施加了严格限制,因为它使某些不相容的力比多通过稽查遭到拒绝。若这种自我理想没有形成,那么性趋向将以性倒错的人格形式表现出来。相对于其他趋向,性趋向再次成为他们的理想,如同在童年期一样:这就是人们极力争取的幸福。
爱包括自我力比多向对象的移动,它具有驱除压抑和改变性倒错的能量,它可以使性对象升级为性理想。既然对“对象型”(或依恋型)而言,爱产生于婴儿期爱的实现条件之下,那么我们可以说,不管是什么满足了这一条件,都是理想的。
性理想可以从一种有趣的从属关系进入自我理想(ego ideal)。当自恋满足遇到真正的障碍时,性理想可以成为替代满足。如果一个人的爱与其对象选择的自恋型相一致,就会爱过去之我(尽管现在已不复存在),或爱自己从不曾有过的任何优秀品质。与此平行的公理可表述为:凡能成为理想而自我又缺乏的优秀品质均可以爱。这种权宜之计对神经症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神经症者的过分对象贯注导致了自我的贫瘠,以致无法实现自我理想,于是,他们便通过性理想的选择(作为自恋型者不可能具备这些优秀品质),将力比多指向对象的挥霍过程拉回至自恋。这便是爱的治疗(cure by love),一种他们通常偏爱的分析性治疗。
的确,他们无法信任治疗的任何其他机制。他们通常带着这种期望对待治疗,并将这种期望指向医生、病人由于过分压抑而导致的不能爱,实际上阻碍了这样的治疗计划。在治疗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是,病人部分地解除了压抑:为了得到所爱对象,病人拒绝继续治疗,以一种爱着某人的生活持续了原来的治疗。如果病人未曾留下对帮助他的人的极有害的依赖,我们对这样的结果当然应满意。
自我理想为理解 群体心理学 (group psychology)打开了一条重要渠道。这种理想除了具有个体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它同时还是一个家庭、一个阶层或一个民族的共同理想。它不仅限制了个人的自恋力比多,而且在很大程度了约束了同性恋力比多,从而使力比多返回至自我。若这种理想不能实现,便会产生试图满足的愿望,从而解放了同性恋力比多,使之转化为罪恶感(社会焦虑)。这种罪恶感起初是害怕父母的惩罚,或更确切地讲,是害怕失去父母的爱。此后父母将被无数的同伴所替代。这样,在自我理想的范围内,对自我的伤害、满足的受挫,便成了精神偏执症的常见原因。并且这种原因也变得更加明白易懂,既同于理想形成和自我理想升华的汇聚,又同于精神偏执症中升华与理想可能转变的复归(in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