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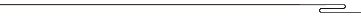
在原始人类的性生活中,他们对处女,即女性童贞的态度,大概是最让我们震撼的事情之一。在今天,男性关心自己所追求的女子是否为处女,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以至于如果有人被问及这么做的理由,反而不知所云了。
我们这个社会要求女子在与一个男子步入婚姻的殿堂前,不得有与其他男子发生性行为的经历,这么做其实是为了保证男子对自己妻子的排他性占有权,同时使他们得以垄断妻子的过去,而这恰恰是一夫一妻制的实质。
从这一点出发分析女人的性生活,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人们对处女有着这样的态度了。众所周知,教育和环境迫使少女要尽量压制内心对爱欲的渴望,到处小心翼翼,不会轻易和男子发生关系,而当她一旦冲破外界的压力,选择了一个男人来满足她的爱欲时,内心深处就已经将自己交付给了这个男人,对他一心一意,不再对别的男人产生感情。女人的这种“臣服”态度使她能够抗击婚后各种外来的新诱惑,这正是由于结婚前长时间的孤独和寂寞导致的,男人从此可以永远地占有她。
1892年,克拉夫特·艾宾首创 “性臣服” (sexual bondage)这一概念,用来形容一个人在与另一个人发生性关系后,对其产生高度的依赖性和顺从心理的这一事实现象。有时候,这种归属感十分强烈,以至于使一个人彻底丧失主见,甚至不惜承受最为残酷的自我利益牺牲。
同时,他也指出,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十分必要,有助于性关系的维持”。事实上,一定程度的“性臣服”奠定了文明婚姻的基础,保护其免受多配偶倾向的影响,对于我们的社会人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艾宾看来,“性臣服”形成于这样的组合:“一个极为感性和性格软弱的人”狂热地爱上了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其后果就是前者对后者的臣服。但具体的案例分析表明,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们不难发现,完成性行为所要克服的阻力大小,才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此外,性行为的专注度和初夜的独一无二性,也对性臣服的诞生有着相当大的意义。由此可见,性臣服在男性和女性身上出现的频繁程度是不一致的,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彻底委身他人,但与古代相比,今天的男性也更易臣服在他人的石榴裙下。
在男性性臣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多是这样引起的:一个男子在某个特定的女子身上成功克服了自己的心理性阳痿,从此就跟定了她。许多奇异的婚配和悲剧事件似乎都可以根据这一根源予以解释。
现在,让我们转向原始人对女人贞操的态度问题。如果我们认为,原始人类不重视童贞,并把当时许多女孩都在第一次婚内性行为前就破处了当作证据,这其实是不恰当的。相反,破处对于原始人类来说是一种有着重要意义的行为,只不过他们将它当成了一种禁忌,甚至是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禁制。根据习俗的要求,处女之身不应留给女孩的夫君,后者甚至应该刻意回避破处。
在此,我无意一一列举能够证实此言不虚的文献证据,也不想强调这一现象地理分布的广泛性及其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我只想指出一点:即使是在今天,在那些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未开化的人群中间,婚前移除处女膜的行为也是十分普遍的。诚如克劳雷所说:“这种由丈夫以外的人穿破处女膜的婚姻仪式,在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部族或社会阶段是很普遍的,尤其在澳大利亚。”
既然失贞不是婚姻中第一次性交的结果,那么它一定发生在婚前——不管方式如何,也不管由谁操作。接下来,我将引用克劳雷书中的几处言论,并附上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在《神秘的玫瑰》(Mystic Rose)一书中,克劳雷对此用了很大篇幅来描述,以下我们引用几段。
第191页:在澳大利亚的狄里及一些邻近部落,女孩进入青春期时弄破处女膜是普遍的习俗,在波特兰和格里尼格部落,通常由一位老妇人为新娘子做,有时则请白种男人让新娘失贞。
第307页:通常,人们会在少女进入青春期后弄破她的处女膜,偶尔这也会发生在她的婴儿期……在澳大利亚,人们常常会为此组织一次正式的交配行为。
第348页:(Spencer&Gillen,1899)在澳大利亚的一些部落,人们会人为地捅破处女膜,那些受命执行这一“手术”的人,要像出席仪式一样庄重地排成一排,与少女进行性交……整个过程分为两部分:捣破处女膜和性交。
第349页:在马萨(赤道非洲的一个地方),婚前的一个重要仪式便是对女孩施行手术。在萨克斯、贝勒斯及西里伯思岛的阿福尔斯部落,女孩的处女膜往往由父亲在其做新娘前弄破。在菲律宾,假如女孩在童年期没有老妇人将其处女膜弄破,那么请某些职业的男人去做。在一些爱斯基摩人部落,通常由巫师或牧师来操作让女孩失贞。
以上所引的内容有两点是很关键的:
首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报道未能将“无性交而简单地弄破处女膜”与“通过性交弄破处女膜”区别开来。只有一处说到将这一过程分为两部分:弄破处女膜(用手或其他工具)及紧接着性交。
有的材料尽管很丰富但对我们却无助益,因为它们对破处的描述仅仅对于解剖学有意义,而根本不谈其心理学意义。
其次,我们大概都很想知道所谓“仪式化”的性交与普通的性交之间有什么区别。在我手头的这些资料中,作者要么是对这一话题羞于启齿,要么就是低估了这些性交细节的心理学意义,对此大都语焉不详。
我真希望旅行家及传教士能为我们提供更加完整而明确的第一手资料。然而,由于这类材料大部分是国外的,眼下我们还得不到,所以我还不能对这个问题做更多的定论。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仪式化的性交象征了普通性交,人们去繁从简,在仪式中对早期完整的性交行为进行了简化。这样一来,我的第二点疑问或许就可以忽略了。
对于处女的禁忌,人们有着不同的解释,以下我将对其做大致的介绍。 通常来说,少女在破处的过程中都会流血;一些原始人群将血液视作生命之源,对血液存在畏惧,这就是对于处女禁忌的第一种解释。
流血的禁忌也存在于性行为之外,它显然与谋杀的禁忌息息相关。要知道,人类的祖先曾经嗜血如命,甚至以杀人为乐,人们将流血视为禁忌,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原始的欲望死灰复燃。这样看来,处女禁忌大概也与无处不在的月经禁忌类似。原始人类对于每月一次的神秘流血现象感到颇为不安,他们认为月经,尤其初潮,是被某种精灵鬼怪撕咬所致,也许就是少女与这些幽灵发生性行为的标志。偶尔也会有人认为,这些幽灵就是人们的某个祖先。于是就有一些观点认为,处于月经期的少女是祖先灵魂的所有物,绝对不容许他人染指。

另一方面,有人也提醒我们不要高估了流血恐惧的影响力。因为在保留处女禁忌的同一个民族中,我们还看到以下一些现象:割掉男孩的包皮,更有甚至,切除女孩的阴蒂和阴唇……这些现象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些民族的一种习俗。还有其他一些以流血为目的的仪式,岂不都与这样的解释相抵触吗?因此,有些女子在第一次性交后为了满足丈夫,便不再遵守月经禁忌,这当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种解释同样与性无关,相较第一种也更具有普遍性。如同精神分析理论所研究的焦虑性神经症一样,这种解释认为原始人长期陷入一种“潜伏的焦虑”当中,这种焦虑型神经症在一些不同寻常的情形下都表现得异常强烈。比如,每当遇到新奇、神秘、怪诞的事情,遇到不可理解或无能为力的事情时,这种情绪就会在原始部族的人群中表现出来。
为了缓解这种焦虑,原始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祭奠仪式,并被保留下来,在一些重要仪式中广泛采用。比如,在新店开业,人生面临重大转折,人或动物刚生育下一代,庄稼喜获丰收之际,人们都会举行形式不同的仪式。在这些珍贵的历史时刻,人们难免心存期望,希望借助某种仪式来得到神秘力量的加持。
同理,婚姻中的第一次性交是非常重要的,所有人都必须谨慎对待,那么举办一场仪式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流血禁忌和对新生事物的恐惧这两种解释并不矛盾,相反,两者还能互为补充。 初次性交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何况还会因此而流血,原始人对此当然惧之更甚了。
第三种解释认为,处女禁忌这个问题应该联系性生活的大背景来理解,这也是克劳雷所推崇的。这种观点认为,不仅与女性的第一次性交是禁忌,性交本身其实就是禁忌;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女人都是禁忌。这不仅是因为女人要来月经,要怀孕、生产、坐月子,即使是在这段时间之外,与女性的交合也会受到重重限制,有时我们甚至要怀疑,野蛮人的性交自由是否真的存在。
诚然,在某些条件下,原始人的性行为会突破所有阻碍,但通常来说,他们的性行为其实比处于更高文明阶段的我们受到更多的约束。男子在做一些大事,如出行、打猎、作战之前,往往要远离妇女,尤其要避免与她们发生性行为;否则,他们的精力就会受到影响,从而不得善终。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有远离异性的趋势,女人与女人住在一起,男人与男人住在一起。许多原始部落根本不存在我们文明人所享有的正常的家庭生活。这种分离有时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以至于他们都被禁止称呼异性的名字。于是,女人便发明了自己的词汇。当然,性的需要会不时地冲破这种分居的樊篱,以至于在一些部落中,丈夫与妻子的性交也要在室外秘密地进行。
但凡原始人设立一项禁忌,就表明此处存在着他们所害怕的危险。 在所有的这些禁忌背后,是男人内心中对女性的无比恐惧之情,这一点是我们所无法否认的。 这也许是因为女性的生理结构与男性不同,他们永远像谜一样神秘而陌生,这不免会让人觉得她们有些不怀好意。男人们害怕女人会削弱他们的力量,他们怕被女性同化,从而丧失自己应有的功能。
性交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性交过后的一段时间里,男人往往会四肢乏力,疲惫不堪,这恰恰让他们充分感受到了女人的可怕。他们越是对此顾忌重重,内心就越是惶恐不安。即便是在今天的社会中,不少男人心中也存在类似的想法。
许多人对现存的原始民族进行观察后指出,他们的情欲冲动比较微弱,从未达到文明人的强烈程度。当然,另外的观察者会有相反的说法,无论如何,我们所描述的每一种禁忌都证明,他们当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反对爱的力量,他们把女人当作奇怪而有敌意的对象来看待。
克劳雷的说法和精神分析学说的通行术语几乎无异。他认为,个体间的分离源于 “个人隔离禁忌” (taboo of personal isolation),更确切地说,别人和自我大体相似,只存在着细微差别,但这些差异却带来了人和人之间陌生和隔阂。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其实源于每个人对于细微差别的自恋。对于自己与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每个人都会感到骄傲不已,这就使得人们无法相亲相爱,也很难做到宽以待人。精神分析学相信,男性之所以自视颇高,却对女性不屑一顾,是因为 “阉割情结” 影响了他们对女性的判断。
然而,第三种解释已经远离了我们的主题,对于女人的广泛禁忌并不能使我们更加了解,为什么要对处女的初次性交加以特殊的限制。就此而言,我们还是只能引用前面两种解释,惧血及害怕所有的“第一次”。即使如此,也没有触及对处女禁忌的核心。显然,人们设置处女的禁忌是要为少女未来的丈夫省去一些不必要的烦恼,而这必然与第一次性行为有关。而此前我们却说过,少女会对其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的男子产生一种特殊的依赖。
在此,我不想再去研究禁忌的来源和真实意义。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我已经就此做过论述,并指出禁忌必然包含着矛盾的情感,它起源于一些史前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则直接导致了家庭的诞生。
但在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原始人群的禁忌中,这种原始含义已经不复存在。即便是当今最不开化的人群,他们的文化也已经与史前相去甚远,尽管他们的文明没有我们发达,但从时间跨度看,他们的发展历程并不逊色于我们。而这一点却常常被我们给忘记了。
今天原始族群的那些禁忌,早已经发展成一套高明的系统,旧的动机逐渐被新的、更有利于和谐共生的动机所取代,其复杂程度堪比一些神经症患者在恐惧症中所表现的那样。
如果不考虑起源问题,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原始人群害怕什么,就为此设置一个禁忌。总的说来,危险其实停留在心理层面上,因为原始人不像我们这样重视区分实际的危险与心理的危险。他们的世界属于泛灵论,在他们看来,来自同类的威胁,在本质上与来自自然和动物的危险并没有什么两样。另一方面,他们也擅长将自己内心的敌意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去,从而对那些他们不喜欢或陌生的对象表现出敌意。所以,既然女性被看作是危险的来源,那与她们的第一次性交就显得尤为危险了。
写到这里,原始部族所感受的异常强烈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它又为何只威胁着女人的未婚夫,我想已经可以弄明白了。只要我们对今天文明社会里的女人的性生活做更深入的研究,就会找到答案。我可以预先告知各位,研究的结果显示,这种危险的确是存在的,因此原始部族的人们对处女的禁忌并不是空穴来风,这一禁忌的确能够帮助他们排除心理上的危机。
一般情况下,女性在性交中达到高潮后会情不自禁地用手紧紧地拥抱丈夫,将其重重地压在自己身上,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反应,可将此视为女人对男人的感激并永远服从男人的一种表现。但我们也知道,上述过程通常不会在初夜发生,大多数女性都会对初夜感到失望。通常来说,只有在一段时间的反复摸索后,女性才能体会到性爱的乐趣。
当然,不同的女人情形也未必相同。有的女人性冷淡仅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消失;有的女人却是永久的、顽固的性冷淡,无论丈夫如何温柔都无济于事。据我所知,人们对女人的这种性冷淡仍缺乏足够的重视,如果女人的这种性冷淡不是由于丈夫的性能力不足造成的,那就需要综合性的研究给予解释了。
许多女人会害怕和逃避第一次性交,但我对此不想做深入的研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最主要的观点认为,这是一般的女性防御倾向的表现。与此相反,我相信从一些病态的案例研究入手,或许可以更容易地解释女人性冷淡背后的原因。
有些女性在第一次性交后,突然对自己的丈夫产生了敌意,在他们面前骂骂咧咧,甚至举手打他。我就曾碰到过一个这样的典型案例,并对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事实上,这位女性深爱自己的丈夫,主动要求与其做爱,但是在获得充分的满足之后却仍对她的丈夫恨意十足。
我认为,这种奇怪的、矛盾的反应是同一冲动的结果,只不过它通常表现为性冷淡。这种冲动使温情反应受到抑制而无法有效地表达出来。在这种病态状态下,正像我们早已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所发现的 “双相症状” (dipbasic symtoms)一样,这种感情分成了两部分,而在经常出现的性冷淡中,两者联合起来产生了抑制效果。女人失贞所导致的后果之一便是对使她失贞的人产生敌意,所以,作为丈夫当然有足够的理由避免这种敌意。
经过分析,我们已经知道这种矛盾行为是由女人的冲动引起的。我想,它可以用来解释女人的性冷淡问题。第一次性交使许多冲动超出了女性的本性范围,其中有些冲动在以后的性交中不会再出现。
在这里,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处女在破处的过程中所要承受的痛苦。但我们没有必要夸大这一痛苦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将矛盾行为完全归咎于初夜的痛苦。处女膜的撕裂,也对女性的自恋人格造成了创伤。她们失去童贞后的哀怨之情,就是具体的表现。但是,原始族群的婚俗已经在警告我们不要高估童贞的价值。上文提到,有些地方的婚礼仪式由两部分组成:先是(用手或工具)戳破处女膜,再是正式的性交或简易性交,而性交的对象则不是丈夫本人,而是他的替身。
由此可见,处女禁忌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避免解剖学意义上破处行为的发生。丈夫所要回避的,不只是破处带给妻子的伤害,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初夜常常令生活在文明世界中的女子大失所望,因为现实和她们的期望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结婚前,性交行为是被严厉禁止的,因此,即便是性交终于合法化,成了被允许的行为,她们也无法放开手脚。许多新娘在陌生人面前对自己新的情感生活讳莫如深,甚至对自己的父母也不愿吐露半个字,这固然没有必要,但却也是人之常情,是性压抑对女性造成重重束缚的表现。
女孩们常说,如果其他人对此有所知晓,那她们的爱情就失去了意义。有时候,这种情感过于强烈,甚至可能会影响婚姻中的爱欲。只有在不被允许的秘密关系中,她的温情体验才能被激发,热情无限。
然而,这种说法也还不够深入,毕竟这是以文化对女性造成性压抑为先决条件的,在原始人群身上其实并不适用。因此,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建立在力比多的发展之上。通过之前的分析,我们已经明白力比多对于最初的性对象有着强烈的依附心理。这些性对象大多来自孩提时期的性愿望,对于女性来说,她们的力比多大多聚焦在自己的父亲或兄长身上。这并不是说她们一定想与父兄性交,而只是一个模糊知觉到的目标。丈夫总是一位替代者,而不是正宗的人选,父亲才是女人第一个性爱对象,丈夫充其量只是第二人选。
如果这种聚焦作用十分强烈,童年的性愿望一直挥之不去,那她们就不能从作为替身的丈夫身上获得满足,也就不甘委身于他。因此,女人的性冷淡便成了神经症的病源因素。女人在性生活中的心理因素越强烈,力比多对第一次性行为的抵抗力就越强大,她们对丈夫对自己身体的占有就越无法忍受。性冷淡甚至会变成一种固定了的神经性抑制,为其他神经症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而男人轻度的性能力下降又会大大加剧女人性冷淡的过程。
原始人的习俗似乎考虑到了女人的这种早期性愿望动机,于是请长者、巫师或贤人作为父亲的替代者,来实行破处这项仪式。在我看来,中世纪极为烦人的领主“初夜权”似乎直接由此沿袭而来。斯托夫(A.J.Storfer)有过类似的见解,而荣格在他之前就对广泛流传的“多比亚司之夜”(Tobiasehe,指在婚后的头三个晚上节欲的风俗)现象中,父辈对新娘享有初夜的特权做过解释。
如同我们所期望的一样,只要父亲的替代者带有“神祇”的意象,就可委以破处的重任。在印度的一些地区,女人的初夜被迫献给木制的男性生殖器像。据奥古斯丁(S.Angustine)所言,这一习俗也存在于罗马的婚礼之中(是否指在他那个时代),只不过做了些改变,新娘只需在石制的普里阿普斯(Priapus)的巨大阳具上象征性地坐一下就行了。
此外,另一个动机也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着女性对男性的矛盾反应,在我看来,这也是导致女性性冷淡的主要原因。这便是初次性交激起了女人的其他冲动(以上描述的及长期存在的),这些冲动与女人的角色与功能是完全相悖的。
通过对许多女性神经症患者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早期,她们曾嫉妒亲兄弟的男性生殖器并因为自己不具有它而感到自卑与羞耻。我们将这种“阴茎嫉羡”视为“阉割情结”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所理解的 “男性特征” (masculine)包含着想成为男人的意思,那么这种行为就可以被称为 “男性抗议” (masculine protest)了,这一说法由阿德勒(Adler)首创,并认为它可以解释所有神经症的起因。
在这个阶段,女孩子们出于嫉妒,往往会对自己的兄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他们也会尝试着像自己的兄弟一样站立着小便,想要以此实现两性的平等。前面我们说到过,有一个女子在性交后就对自己的丈夫百般动粗,从这个例子我可以断定,阴茎嫉羡出现在对象选择期之前。在那以后,小女孩的力比多转移到了父亲身上,她们不再想要长一个阴茎,而开始想要生一个孩子。
如果在其他情形中,这些冲动以相反的顺序出现,“阉割情结”在对象选择期之后出现,我也不会感到奇怪。但通常来说,女人羡慕男孩阴茎的雄性期要出现得较早一些,它跟自恋期的关系要比对象选择期更近一些。
不久前,我有机会对一位新婚少妇的梦进行了分析。这个梦是对其贞操丧失的反映,它同时暴露了这个女人的愿望:阉割年轻的丈夫,并把他的阴茎安在自己身上。当然,这个梦可以解释为她在幼儿期欲望的延续和重复。然而,梦的一些细节却不符合这一解释。这位少妇此后的行为与性格表明它有更严肃的意义。在阴茎嫉羡的背后,是女性对男性的敌视和怨念,这也是两性关系中永恒的主题之一,许多女权主义者的诉求和文学创作都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弗伦茨从古生物学的角度追溯了女人的这一敌意的起源(我并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做的第一人),认为它产生于性别分化期。在他看来,性交产生在两个相似的个体之间,而后一方变得强盛起来并迫使弱者臣服于这种两性关系。这种臣服的痛苦体验依然存在于今日女性的天性之中。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过分强调它的价值,这样的假设也没有什么不好。
针对女性性冷淡以及在被破处后矛盾表现的成因,我们列举了数种可能性。现在,我们可以总结说:女性不成熟的性心理,都会一股脑儿地发泄到第一个与她发生性关系的男子身上。
这样一来,处女的禁忌就好理解了,人们之所以设置这样的规定,就是为了使今后要与妻子朝夕共处的丈夫避免这种危险。而在较高级的文明中,出于种种其他的诱惑,同时也考虑到破处对性从属的促进作用,人们开始忽视这种危险,而将贞操视作一笔任何男子都不愿错过的财富。
然而,关于婚姻问题的研究告诉我们,促使女人对破贞进行报复的动机即使在文明的女人的心理活动中也未完全消失。细心的观察者肯定能注意到,许多女子在第一次婚姻中有性冷淡,而且感到不幸福,而在离婚之后,她们往往能和第二个丈夫恩爱有加,相处得其乐融融。可以说,她们对男人天生的敌意已经在第一任丈夫身上消耗殆尽了。
不过,撇开这一点不论,对处女的禁忌在文明社会也并未彻底消亡。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作家不时地以此为素材进行创作。安泽鲁波(Anzengruber)曾写过一部喜剧,述说一个单纯的农村青年因担心自己的生命将被吞噬掉而不与所爱的人结婚,但他倒是同意她嫁给别人,只有到她成为寡妇不再有危险时才娶她。这部喜剧的名字是《处女之毒》,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驯蛇者:他们会先诱使毒蛇去咬一块布,待其毒性散尽后,就任由他们摆布了。
在赫贝尔(Hebbel)的悲剧《朱迪丝和霍洛芬斯》中,对处女的禁忌及其动机做了最有说服力的描述。朱迪丝是一位受到禁忌保护的处女,她的丈夫在新婚之夜被一股神秘的恐惧感困扰,从此不敢再触碰她的身体。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的美丽有如颠茄
 ,享有我的人,非疯即死。”当亚述国的将军进攻她的城市时,她下定决心用自己的美色去诱惑他,从而置他于死地。
,享有我的人,非疯即死。”当亚述国的将军进攻她的城市时,她下定决心用自己的美色去诱惑他,从而置他于死地。
在这里,作家用爱国的主题很好地将性这一主题掩盖了起来。在被骄傲自负的将军粗暴地破身之后,朱迪丝从自己的愤怒中获得了力量,一举砍下了将军的脑袋,也由此成了自己国家人民的救星。
我们知道,砍头是阉割的一种象征,所以朱迪丝阉割了夺取她贞操的男人,这种做法与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女子的梦境不谋而合。赫贝尔巧妙地将这个爱国的故事渲染上了性的色彩,在原文中,朱迪丝回家后还四处辩说自己并没有遭到玷污,也没有任何关于那个恐怖的新婚之夜的记载。当然,也许正是作家的细腻情感,使得赫贝尔觉察到了这个颇有倾向性的故事背后隐藏着的古老命题,从而使得这段素材回归到性的本色。
萨德格(Sadger)曾对赫贝尔做过深入的分析,认为他之所以选择这一素材,乃是恋亲情结所致,而且他在两性的不断斗争中站到女人这一边,用自己的方式体验女人心理的隐蔽冲动。萨德格还引用了诗人自述的动机,说明为何对这一故事做了改编。他发现,这些动机是人为的,不过是在表层上对外展示一下作者的潜意识,深层上却是将其掩蔽的。

对于作家将故事中的寡妇朱迪丝描绘成处女寡妇的用意,萨德格也进行了解释,我不在此赘述。总的来说,这大概与孩子们的幻想有关;他们总是想向父母隐瞒自己的性行为,并把自己的母亲想象成不可侵犯的处女。但我要说的是:当作家将自己的主人公确定为贞洁的处女之后,他自然就联想到了贞操被破之后朱迪丝的愤怒回应。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文明的结果,女人破贞不仅意味着永久地屈从于一个男人,而且还产生了对男人的原始敌视反应。这种敌意常常演变成一种病态,对夫妻双方的性生活造成阻碍,这也是许多女性的第二次婚姻会比第一次更加美满的原因。
原始族群的处女禁忌要求丈夫不得参与自己妻子的破身过程,这尽管有些奇怪,但考虑到破处引发的敌意,其实也不无道理。
有趣的是,精神分析学者竟遇到了这样的女人,在她们当中存在着屈从与敌视这两种反应,而且能保持两者的密切关系。
有一些女人对自己的丈夫已经毫无感情可言,却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他们。每当她们想要尝试与其他的男人相爱,第一任丈夫的影子就会出现在她们眼前。尽管她们已经不爱对方,有些画面就是挥之不去。分析表明,这类女性尽管已经对自己的丈夫柔情不再,却依然在心底依附于对方。她们之所以无法离开自己的丈夫,是因为她们的报复行为尚未完成。在某些典型案例中,她们的报复欲隐藏得很深,甚至连她们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