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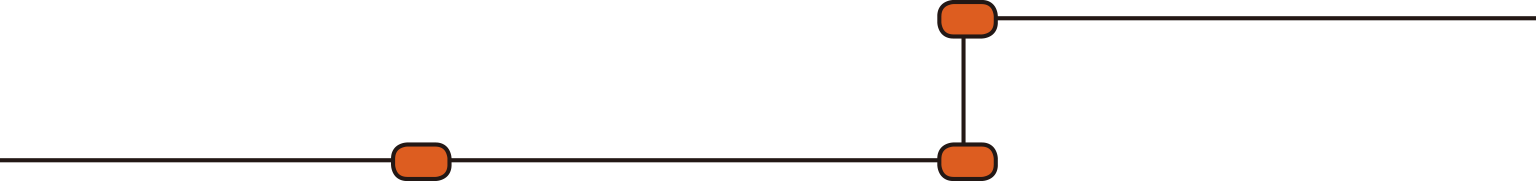
狩野浩之(一九六三年生)
生于东京,但很快搬到郊县,在那里送走了少年时代。弟妹各有一个。上大学时弄坏了身体,开始去奥姆真理教主办的瑜伽道场。仅仅二十天后麻原彰晃便劝他出家,五个月后出家。他是老资格萨马纳(出家者),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时属科学技术省,在那里主要从事电脑操作。对他来说,六年时间的教团生活是一片晴朗的、美好的,一直持续到地铁沙林事件毁坏那种平稳为止。在教团中也遇到了许多朋友。
如今虽然还没有退出奥姆真理教团,但已从集体生活中脱离出来,同其他成员之间总的说来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东京都内一个人生活,同时继续单独修行。对佛教怀有兴趣,理想是将佛教理论化。他说“经济上不想给教团添麻烦”。同伴中也有很多人离开教团。才三十二岁,往后走怎样的道路,心情想必摇摆不定。
采访时间很长,但一次也没从他口中说出“麻原彰晃”四个字。不仅名字,甚至教祖、GURU
 这样的外围性称呼也未出口。始终回避称呼。大概很难将麻原彰晃式的存在作为语言顺利说出口来。只有一次使用了“那个人”这一表达方式。这点我记得尤其清楚。
这样的外围性称呼也未出口。始终回避称呼。大概很难将麻原彰晃式的存在作为语言顺利说出口来。只有一次使用了“那个人”这一表达方式。这点我记得尤其清楚。
看上去像是在道理上循规蹈矩思考问题那样性格的人。无论什么都要自行予以理论化才能接受和理解。要想从长年累月渗入骨髓的铁杆逻辑=教养中挣脱出来而转入“自己本身的活的逻辑”,可能要多少花些时间。
总的说来,小时候是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小学时代身高就超过了一米六,比周围同学高出了二十厘米。体育也喜欢,很多运动都做得入迷。但上初中以后个子一点儿不再长了,如今比一般人还矮一些。怎么说好呢?肉体成长有时候也跟精神性的东西相呼应,开始一点点走下坡路。健康状态好像也是。
学习成绩不差,但起伏相当大。尤其上初中以后,自己想做的和不想做的,变得非常明显。学习本身倒不头痛,但对用功总好像有非常强烈的抵触感。就是说,自己想学的和学校教的,相差太大了……
对自己来说,学习意味着变聪明。可是在学校做的是死背硬记,如“澳大利亚有多少只羊”什么的。我想,那玩艺儿做多少也不可能变聪明。聪明那东西,以小孩时的印象来说,好比《姆米一家》
 中出现的司那夫金的那个东西。对我来说,长大就是那么回事,就是具有那样的沉着啦知性啦智慧啦什么的。
中出现的司那夫金的那个东西。对我来说,长大就是那么回事,就是具有那样的沉着啦知性啦智慧啦什么的。
——您父亲是怎样一位人士呢?
工薪族,开印刷机的。手巧,但讲不出道理。倒是没有动手打过我,但说是工匠气质也好什么也好,反正脾气暴躁,好生气。我一问什么就大发雷霆。学校的老师也半斤八两,我有什么疑问刚一深问,就马上火蹿头顶,不肯讲解。莫名其妙啊!那么大一个人,却因这么一点点事就脸红脖粗气急败坏。我心目中的大人印象和现实中的大人之间,差距实在太大了。
使得这个差距变得无可救药的,是我没考上大学复习期间在电视上看的《致星期五的妻子们》。看得我大失所望,心想就算成了大人也好像什么也没长大。
——就是说,看电视剧时发现剧中人全都一塌糊涂,所以大失所望?
是的。我心目中的大人图像彻底土崩瓦解。心想即使知识啦经验啦增加了,实质上也根本没出息什么。换掉那种外表,去掉表面性知识,剩下的岂不和小孩差不多?
另外,对恋爱那个东西也有很大疑问。十八九岁的时候,我这个那个归纳一番,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单纯爱一个人和所谓恋爱是两码事。就是说,单纯爱一个人,其中不会有为了自己利用人家这样的事情介入。但恋爱不是这样,里边混杂着希望对方喜欢自己这样的东西。不用说,如果单纯爱对方就心满意足,那么单相思也完全不至于痛苦。只要对方没变得不幸,就算自己不被对方爱,自己也用不着为此闷闷不乐。最后所以变得闷闷不乐,总之是因为那里有希望对方喜欢自己这样的欲望。所以我认为恋爱那东西同单纯爱一个人是两码事。单相思的苦恼也会因此大大减少。
——是够认死理的了!就算是单相思,一般人也绝不至于想到那个地步。
的确是的。一天天我总是想这类东西。从十二三岁我就这个那个拼凑那类哲理性结论。一旦开始想什么,就一个人呆呆思考五六个钟头。对我来说,“学习”总之就是这么回事。在这方面,学校里教的只是分数赛跑发令枪那样的玩艺儿。
偶尔也跟同学讲起这个,但讲不下去。跟学习好的同学讲这种话,对方只是感叹:“嗬,你居然想这样的东西,厉害厉害!”但交谈没办法推进。根本遇不上能够就自己最感兴趣的事开怀畅谈的对象。
——一般情况下,思春期每当为这种本质性问题感到苦恼的时候,人都是要专心看书的,以便从书中找到有益的建议。
看书无论如何看不来,一看就看出各种各样的漏洞。尤其哲学书,虽然只看过几本,就怎么也看不下去。这是因为,对于我的哲学是用来寻找“改善措施”的东西,通过深刻的认识来找。具体说来,就是深刻理解人生意义等本质性价值,以此增加欣喜和充实感,或弄清楚眼下该做什么。“改善措施”是最终目的,其中间阶段终究不过是阶段罢了。不料,我看的书是了不起的先生为了炫耀自己写的书,挥舞语言技术告诉大家他的智性多么多么高。这种东西看在眼里,就怎么也看不成了。这么着,我就对哲学那东西本身失望了。
还有一点,我想起小学六年级时的一件事,当时我看见自己面前有一把剪刀,就忽然心想:这剪刀虽说是大人们拼命制造出来的,但总有一天要坏掉。有形的东西迟早必然坏掉。人也同样,最后肯定有死到来。所有东西都朝毁灭勇往直前,倒退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毁灭才是宇宙的规律。这样的结论一下子浮上脑海后,看东西的眼光就变得相当消极起来。
比方说,如果自己人生的结论在于毁灭,那么,总理大臣也好流浪汉也好,下场岂不一个样?果真如此,就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努力奋斗有什么用呢!假如人生的苦恼多过欢喜,那么岂不早早自杀更为明智?
如果只有一条通道,那就是“死后世界”。那是唯一的可能性。最初听得这种话时,心想那是多么无聊!尽管如此,我还是看了丹波哲郎
 的书。是以否定性心情看的,想看他说了怎样的傻话。那是一本《死了会怎么样》的书。
的书。是以否定性心情看的,想看他说了怎样的傻话。那是一本《死了会怎么样》的书。
我这人的性格,反正一旦开始想什么,就要不管三七二十一想个究竟。不会心想“算了吧,车到山前必有路”。非把脑袋里的东西明确分成两类不可:“这个明白”、“这个不明白”。学功课也是这样。老师教一个新的,我就会冒出十个新的疑问。必须全部弄懂之后才能往下进行。
——看来是要给老师讨厌啊(笑)!
非常讨厌我。例如什么“青春的绿色”啦,一碰上这样的句子就忍无可忍。还有什么“七跌八起
 ”之类,爬起的次数岂不是比跌倒多了一次?可是,每次拿出这样的疑问逼问大人,都被大人一笑置之。谁也不理睬我,谁也不好好解释。一看见那样的人,就觉得他们实在太马虎了。对不明白的东西就那么稀里糊涂放过去。那样合适么?作为自己是有抵触情绪的。
”之类,爬起的次数岂不是比跌倒多了一次?可是,每次拿出这样的疑问逼问大人,都被大人一笑置之。谁也不理睬我,谁也不好好解释。一看见那样的人,就觉得他们实在太马虎了。对不明白的东西就那么稀里糊涂放过去。那样合适么?作为自己是有抵触情绪的。
——我偶尔是两方面都可以解释的(笑)。不过身边是没有人耐心回答这样的疑问。可另一方面,一般世人正因为对细小地方适当敷衍了事,也才得以活下去啊!
那是的。可是自己不能那样,觉得不能这样顺水推舟地活下去。
所以我认为丹波哲郎的书本身无聊透顶。不过其中介绍了斯维登堡
 的书,那本书看得我吃了一惊。斯维登堡是个有名的学者,即使拿诺贝尔物理学奖也无足为奇,可是五十岁刚过忽然成了特异功能者,留下了数量庞大的关于死后世界的记述。看了那种书,不由得对书中敏锐的逻辑性佩服得五体投地。和其他这方面的书不同,给我的印象是逻辑上无懈可击。对我来说,理由和结论的关系非常容易理解。所以产生了信赖感。
的书,那本书看得我吃了一惊。斯维登堡是个有名的学者,即使拿诺贝尔物理学奖也无足为奇,可是五十岁刚过忽然成了特异功能者,留下了数量庞大的关于死后世界的记述。看了那种书,不由得对书中敏锐的逻辑性佩服得五体投地。和其他这方面的书不同,给我的印象是逻辑上无懈可击。对我来说,理由和结论的关系非常容易理解。所以产生了信赖感。
这么着,我想查一下资料,弄清死后世界是怎么一个东西。临死体验方面的资料这个那个看了好多,受到的震动相当大。日本也好外国也好,人们的证言惊人地相似。而且都是真名实姓带照片的证言——那些人异口同声一齐说谎的概率是几乎没有的。得知“karma
 法则”是后来的事。得知后,从小怀有的疑问一下子迎刃而解。
法则”是后来的事。得知后,从小怀有的疑问一下子迎刃而解。
还有,佛教的根本性无常观和我所考虑的宇宙毁灭法则是同一回事。我对那种东西的认识是消极的,但由于那样的关系,我非常顺利地进入了佛教。
——读了与佛教相关的书?
太正规的佛教书我没有读。内容好像不直接,找不到改善措施。经文什么的出现好多好多,怎么也找不见中心点。感觉上好像没办法检索到自己想知道的部分。相比之下,直接的经验之谈对我想知道的东西写的直接得多。当然,不能完全信赖的部分相应也是有的。
但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确信,确信自己能够区分那个人的话哪部分可以信赖、哪部分不可信赖,自信在经验上或直觉上具有加以取舍选择的能力。
——听你这么说,好像你一直排斥同自己拥有的理论啦感觉啦相对立的要素。就是说,作为对抗价值,你身上有许许多多复杂的东西促使你从相反的立场挑战世人怀有的理论和感觉。不过,想积极参与的念头却不强烈,是吧?
从上小学开始,跟大人争论就很少败过。这样一来,周围的大人们在我眼里就全都显得很蠢,尽管实际上不蠢。现在很后悔,后悔当时不该那么看待大人。当然还不成熟啊!每当要争论什么,自己心里明白什么东西自己不是对手,就巧妙回避了。这样,剩下的这方面就百战百胜。从小学开始跟老师争论就没败过阵。以致变得过于自信,我想。
不过跟身边同学相处得很好。说话内容也适当迎合对方。什么地方怎么说对方容易接受——对此非常清楚。因了这种感觉,朋友也相当不少。让朋友开心,自己看着开心,这样的生活差不多持续了十年。回到家后,就自己一个人沉思:这么活下去到底会怎么样呢?归根结底,能够跟自己一起做自己想做的事的人一个也没有。
我没有拼命准备高考,进了电气方面的大学。在学校学的是工科,我想做的和这东西多少有所不同。我真想做的是真正有智慧的学问。比如把东方思想加以理学化什么的,就理想来说。
例如生物光量子(photon),能从生命发光。再如病症方面的,我预想,如果详细统计,说不定那里会有物理性法则。而且,从生命发出的微弱的光和心的作用的关系之间,也必然有物理性法则。这是我从瑜伽体验中得到的想法。
——对你来说,将那样的力进行量化计测,或在视觉上加以显现——这种事是非常重要的吧?
是的。那样一来,就可以做出大家都能认同的体系。现代科学那东西想得非常充分,是个好东西。所以,如果用那个在理论上进行数学组合,我想可以得到水平相当精巧的体系。奥姆里面也有极具价值的部分。作为我,想把那种成为血肉的部分保留下去。用宗教那一形式是不成的,我个人觉得。必须作为自然科学加以理论化才行。
对于不能进行科学测定的东西,我没多少兴趣。说没有兴趣也好什么也好,因为那没有说服力,也可能给周围的人还原成利益。如果不能测定的东西有了力量,结果就有可能成为奥姆那样的东西。测定可能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那种危险性,我想。
——可是,测定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这点,由于立场和看法不同,因而结论不同的时候也是有的。一来必须判断那个程度的测定是不是充分,二来还有测定仪器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赖的问题。
那类统计学构筑方式,我想可以和普通医学差不多——出现如此症状这么解释啦,对如此症状这么处理如何啦等等。
——你不看小说的吧?
嗯,小说看不来。看三四页,忍耐力就到了极限。
——我因为是小说家,所以看法和你相反,认为不能测定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不否定你的活法和想法,是以既不否定又不肯定的所谓中立立场倾听你的话。但是,世人送走的人生的大部分都是由不能测定的庞杂的东西构成的。把那些彻头彻尾变成可以测定的东西,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吧?
嗯。倒不是认为那些庞杂的东西没有价值,只是,观察如今世上的情况,我觉得多余的痛苦实在太多了。社会使得痛苦的原因越来越多,使得无法控制欲望的人感到痛苦,例如食欲啦性欲啦什么的。
奥姆做的,就是迅速减轻那种精神压力,增加每个人本身的力量。在信徒看来,奥姆真理教的百分之九十九都属于这个:对于精神现象和物理现象的思考方式,相应的改善措施、解决方案。从内侧来看,奥姆就是这些的组合。至于组织上怎么样,末世思想如何如何,那是媒体描绘的奥姆。在我周围,没有什么人认真思考诺斯特拉达穆斯
 的预言。那个层面的事情谁也不懂。
的预言。那个层面的事情谁也不懂。
我想做的是把轮回啦karma(业障)啦等东方思想在理学上一个个体系化,哪怕体系化一点点也好。比如说,去了印度那里,就有很多人在生活中彻头彻尾相信那个。可是发达国家的人要理解和接受那样的东西,就需要相应加以理论化——我想已经到了这样的时代。
——例如战前一部分日本人相信天皇是神,为此宁愿去死。这是对的吗?信了就可以的吗?
就那样结束了也就罢了。但想到下一个生,恐怕还是佛教式的生活好些。
——可那不外乎是信天皇还是信佛教轮回,也就是所信对象的区别吧?
只是结果不同。信天皇死后得到的东西和信佛教死后得到的东西,结果是不一样的。
——但那是信佛教的人说的吧。对于信天皇和相信为天皇死了灵魂可以进靖国神社安息的人来说,结果恐怕就是那样也未尝不可。不是吗?
所以我在考虑用数值证明佛教的方法。正因为还没有那个方法,才会有这样的议论。更多的我什么也不能说。
——这就是说,假如出现把天皇从理论上加以测定的方法,那么那样就可以的了?
是的。如果因此在死后结果上对那个人有利,那样也是可以的。
——我想说的是,从历史上看,科学这个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为政治和宗教所利用。例如纳粹就是这样。所以后来有了不少似是而非的伪科学,它给社会留下了巨大创伤。你也许是一再进行严密验证的人,问题是世上很多人一听大人物说“这是科学、这是结论”,就会全盘接受,一下子拥去那边。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
我认为现在的状态可怕。如今世上的人品尝了很多本来不该品尝的痛苦,所以我在考虑能够避免的方法。
——对了,你是因为什么契机成为奥姆真理教信徒的呢?
看了一本“在家里可以轻易冥想”那样的书。一做,精神上陷入了异常状态。倒也不是做得多么认真,硬要净化cakra
 来着,以致气的运行一下子变弱了。本来净化cakra要同时加强气功才行,可我没那么做,结果cakra状态失去了平衡。痛苦得不得了。一会儿热得不行,一会儿冷得不行,冷热交替袭来。精力变差了,总是贫血。很危险的,那个!东西也吃不下去,体重降到四十六公斤。现在倒是有六十三公斤。在大学听课也难受,学习根本谈不上。
来着,以致气的运行一下子变弱了。本来净化cakra要同时加强气功才行,可我没那么做,结果cakra状态失去了平衡。痛苦得不得了。一会儿热得不行,一会儿冷得不行,冷热交替袭来。精力变差了,总是贫血。很危险的,那个!东西也吃不下去,体重降到四十六公斤。现在倒是有六十三公斤。在大学听课也难受,学习根本谈不上。
这样,我就去了奥姆的世田谷道场。在那里介绍自己处于什么什么状态,对方三下五除二当场教给了办法。照着一做,仅仅简单做了个呼吸法就恢复了,简直难以置信。
往下两个月时间没怎么去道场,后来开始经常去。折叠传单的志愿服务做了二十来天。之后马上有能够同教祖直接面谈的“秘密瑜伽”。面谈时直接问了(问麻原彰晃)怎么对待身体的不适,结果让我出家,就像一眼看穿资质了似的。周围人也对我说:“还没有人得到过这样的指点,好厉害啊!”于是横竖退学离校,出了家。二十二岁时的事。
一开始就出家的人没有多少,我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我想。不过作为我,身体已经衰弱到连十分钟都走不了的地步,觉得自己怕是活不成了。他(麻原彰晃)说“你跟现世太不合拍了”,不用他说,实际也是那样。并没有正经谈什么,就这么劈头一句。平时根本没说过话,一见面就被说中了很多,简直像无所不知似的。所以全都信了。
——我猜想见面之前他大概已经准备好了那些数据,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
作为可能性那怕也是有的,不过当时没有看出来。我出家是八九年,那时的出家者数量不是很多。实际我想也就二百人多一点点。最终倒是有了三千人左右,我想。
那个人(麻原彰晃)亲切的时候,是我人生中见到的最亲切的人;那个人可怕的时候,又成了我人生中见到的最可怕的人。那种反差大得惊人,所以光说话就深切感到有一种神灵附体那样的东西。
叫我出家时,实在难受得很。一来不想让父母担心,二来对新兴宗教也非常讨厌。跟父母倒是一五一十说了,父母哭得够呛,我心里难受得不得了。与其说是吵架,不如说父母是哭了又哭。那以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那也让我不好受。母亲当时精神上就这个那个有很多苦恼,但形式上我就像火上浇油似的。估计父亲以为是我害死了母亲,百分之百。
(当了信徒后不久就有众议院选举。奥姆教团中也出了不少候选人。狩野君说选举因为运动做得扎实,相信麻原彰晃肯定当选。关于几乎没有选票进来这点,至今仍一副完全难以置信的样子。这就是说,多数信徒认为选举存在某种操作。那以后他被分配到教团的建筑班,参与熊本县波野村教团设施的建设。)
波野村去了五个月左右,在那里一直当长途卡车的司机。跑遍全国搜集预制房屋材料,装在载重四吨的卡车上拉回来。啊,也没什么吃不消的,施工现场的人专门干累人的土方,相比之下,卡车司机算是舒服的了。
同现世生活相比,教团生活当时苦得不得了。不过苦是苦,但极有充实感,自己内心的痛苦减轻了,从中找到了感谢之情。同伴也认识了不少。无论大人小孩,无论男女,哪怕老婆婆,也都很快成了朋友。奥姆里面,因为大家都在生活中把提高精神水平放在首位,所以心情上基本合得来。在那以前,为了与人交往很多时候要勉强(改变自己),那种必要性消失了。
也没有疑问。什么疑问都有答案,全都能解决,比如这样就会这样等等。无论提什么样的问题都马上有答案回来。所以一拍即合(笑)。媒体不报道这个,综合节目那东西,只顾收视率。至于正确报道真相什么的,根本就不做。
从波野村返回富士山本部,那以后一直做电脑方面的工作。上边有村井(秀夫),交谈偶尔也是有的。我说想个人研究点什么,他说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好了——就是这种感觉(好像不怎么来劲儿)。反正那个人对上面交代的事尽心尽力。
——“上面”就是指麻原彰晃吧?
是的。所以,那个人给人的感觉实在是一再削减自己的个人欲望。根本就不考虑由下而上提出(新方案)。不过,如果自己有想做的事,他的态度是那么做也不碍事。
我的地位是“师补”那个东西。不是干部的人,最高就是“师补”。拿公司来说,大概类似股长吧。不是多么风光的东西。即使当了“师补”,部下也一个都没有。感觉上就是自己一人独立做事,约束什么的,一概没有。处于这种立场的人我周围有很多。媒体报道什么的,说我们全都被管得死死的,其实那里面自由行动的人是相当不少的。出入当然也是自由的。倒不是专用车,但能随便用的车也是提供的。
——可是到了后来,例如坂本律师事件啦殴打致死啦松本沙林事件等等,接连不断发生了这种有组织的暴力犯罪吧?对这个没有感觉到什么吗?
怎么说呢,兵荒马乱的气氛是有的。有的形迹可疑,秘密主义那样的地方也出来了。不过,不管看到什么,或许也还是很顽固的(相信自己这些人做的事是不错的),毕竟摆在自己眼前的利益那样的东西实在太大了。即使看见媒体的报道,也还是绝对不能相信,认为是媒体的信息操作。但大约从前年(九六年)开始,终于开始认为那种情况有也说不定。
就拿坂本事件来说吧,原以为奥姆不是一连几年都巧妙封锁消息那样的团体,以为不会做那种事。不管怎么说,作为组织,计划都太恶劣了。无论出怎样的差错都不解雇。而且,虽说是工作,但根本没有工资。与其说是不负责任,不如说完全没有“每个人的责任”这样的观念,说about
 也好什么也好,反正马虎得不得了。以为只要精神上提高了,往下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无所谓,就是这样一种意识。社会上一般人因为有太太有家庭,所以大体都很负责,拼命干。奥姆完全不同。
也好什么也好,反正马虎得不得了。以为只要精神上提高了,往下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无所谓,就是这样一种意识。社会上一般人因为有太太有家庭,所以大体都很负责,拼命干。奥姆完全不同。
例如,说明天以前必须把钢筋送到施工现场,但没有送来。负责这个的人只要说一声“啊忘了”就算完事。倒是有人多少说他一句,可说他,他也全然不动。全都到了不火烧眉毛就无动于衷那样一种状态。比如就算发生了什么糟糕事,也只是说:“啊,karma(业障)掉了。”全都欢天喜地。即使出错挨训,也认为这一来自己的污秽掉了(笑),顽固不化。对什么都苦恼不起来。所以教团的人不知不觉地看不起现世的人:啊,大家都这个那个苦恼不堪,只有自己超然物外,就是这样。
——就你来说,从八九年到九五年在教团待了六年,那期间完全没有问题啦疑问啦什么的?
同问题相比,感觉到的更是感谢啦或大有好处啦充实什么的,只是这些。就算有难受的事,也有人一一详细解释它的含义。倒是没有我个人特别景仰的人、尊敬的人,没有那样的人。能给出那种回答的能力,教团中“师”以上的人谁都有。大凡萨马纳(出家信徒),即便不是“师”,在日常教学中也都理解的。只是,层次越高越厉害。看上祐君就能看出,那么能言善辩的人教团里横躺竖卧。他们身上明显具有和世人(水平)不同的东西。就拿睡眠时间来说,厉害了,一天只睡三个小时,这样的人到处都是。例如村井秀夫等人。精神力、判断力,无论干什么都同样厉害。
——直接见麻原彰晃交谈过吗?
这个么,过去人数还少的时候,可以凑得很近说话,“最近困得不得了”这样无谓的问题都不管不顾提出问他。但教团大了以后,这种情况就慢慢变少了。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这样做。
类似仪式(initiation)那样的东西也这个那个做过好几回,有的很难受。尤其“温热”那种,受不了的。也有用药物的,当时倒是不知道,后来得知是LSD
 。做这个,状态就只剩下心了。身体感觉没有了,可以从正面看清那时自己的深层意识里有怎样的要素。那时的体验确实让人吃不消。说一塌糊涂也好什么也好,得知自己死后大概就是这么一种状态。虽然不知道那是药物,但认为单纯深入自己内侧的药物是有利于修行的。
。做这个,状态就只剩下心了。身体感觉没有了,可以从正面看清那时自己的深层意识里有怎样的要素。那时的体验确实让人吃不消。说一塌糊涂也好什么也好,得知自己死后大概就是这么一种状态。虽然不知道那是药物,但认为单纯深入自己内侧的药物是有利于修行的。
——但是,由于使用药物而出现相当严重的幻觉而致使心灵遭受深度创伤的例子好像也是有的……
我想那是因为用量偏多或方法不当的关系。有个地方叫治疗省,林郁夫负责的,但那地方也马虎得很。要是那里再做得多少科学些正规些,应该没有问题……还有,教团里常常胡作非为,让人勉为其难的事有很多的。这方面多少为别人着想些就好了。
——发生地铁沙林事件的九五年三月你在哪里做什么来着?
闷在上九一色的房间里,一直一个人鼓捣电脑来着。我在的地方有电脑能够进行电脑通讯,就用来仔细看新闻。本来是不该做那种事的,但还是稀里糊涂地做了。也时不时去外面买报纸回来,大家轮流看。倒是有人提醒小心别让人发现,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么着,在电脑通讯上看到报社的速报,知道了东京地铁事件。但根本没以为那种事是奥姆真理教干的。谁干的不知道,反正认为不至于是教团干的。
地铁事件后,上九一色受到了全面搜查。因为科学技术省成员很可能由于冤罪而被连窝抓走,感觉上好像还是外出为好,我也开车去外面游逛了一阵子,所以全面搜查时我不在那里。不管怎样,作为我,完全没有怀疑教团参与事件的心情。
(麻原)被逮捕也完全没感到愤怒什么的。不外乎认为那怕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奥姆信徒来说,感情上愤怒之类是低层次的事,而认为较之愤怒,多少深一些看穿那里的情况才是美德。这样,我就考虑该采取怎样的行动。认为重要的是继续做现在能做的有价值的事情。
大家商量往下如何是好。结论大体是应该做的只有修行。那里没有千钧一发的悲壮感。教团里面就好像是台风眼,平静得很。周围吵吵嚷嚷,可只要迈进一步,一个风平浪静的世界就在那里展开。
说不定真是奥姆干的——开始这么认为是在现行犯被捕并且招供之后。他们几乎全是早有交往的熟人。既然有了那些人的话,这些人都说干了,那么就有可能是真的。
不过么,以奥姆人的感觉说来,相比之下,自己是不是修行了才是问题,这和干了还是没干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怎么进行内侧开发,即使同奥姆干还是没干相比。
——可是,奥姆真理教团所推行的教义朝某个方向发展的结果,引起了那样的犯罪,很多人被夺去生命或者受伤。这样的要素原本就包含在教义之中的吧?关于这点是怎么考虑的?
那部分明显分开,作为真言秘密金刚乘
 。做真言秘密金刚乘部分的人只限于层次特别高的人。只有大乘修完的人才能做那个,这点平时被一再强调。所以我们做的是离那儿很远的事。所以对我们自己一直做的修行或活动(即使事件发生后)根本没产生疑问。
。做真言秘密金刚乘部分的人只限于层次特别高的人。只有大乘修完的人才能做那个,这点平时被一再强调。所以我们做的是离那儿很远的事。所以对我们自己一直做的修行或活动(即使事件发生后)根本没产生疑问。
——不过,层次高低姑且不论,真言秘密金刚乘在奥姆教义中作为重要一环是有很大意义的吧?
说重要也好什么也好,在我们看来那不过是画上画的饼罢了。同平时做的事、平时想的事简直不相干,离得实在太远了。去那里之前必须做的事要好几万年才能做完。
——所以你说无关。可是,假如你的层次一下子提高了,开始涉及真言秘密金刚乘部分,因而作为到达涅槃(nirvana)的途径而叫你杀人,你会杀吗?
我认为不具有真正看透轮回转生能力的人是不能做那种事的,不能参与那种事。问题是,奥姆里面,到达那里的人一个也没有,想必。
——可那五个人做了。
我不做。那个区别是有的。因为,对那种行为自己还不具有负起责任的能力。所以怕得无论如何也做不来。那种地方是暧昧不得的。不能看透他人转生的人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资格。
——麻原彰晃有那个?
我想那时是有的。
——那能测定吗?客观上能证明吗?
不能,现阶段不能。
——那么,受到现世法律制裁,无论出来怎样的判决都是没办法的,是吧?
是的。所以我不是说奥姆的本质都是对的。只是,那里面实在有些有价值的东西。作为我,心情上总想把它处理一下,想把好处给普通人。
——说句非常常识性的话吧,在把那种好处给普通人之前出现了那样的犯罪行为,把普通人杀害了。不从内侧好好总结,却提出好处来,说“也有好地方”——这样子,谁也不会认可吧?
所以我想再不能用奥姆这一形式提出了。我还留在奥姆里面,那是因为过去给的好处实在太大了。对那个还没整理好,从个人角度。我觉得那里好像还有可能性。比如有没有内里招数(某种理论上的颠覆性),有没有前景什么的。所以现在想把明白的部分和不明白的部分区别开来,一个个弄清楚。
等两年左右。如果奥姆还是眼下这个状态,我就打算退出。但退出前有各种事情非考虑不可。不过,就不执著这点上,奥姆真理教团绝对世界第一。无论人家说什么,说没听见也好,说没传进耳朵也好,反正一点儿也不受影响。悲壮感那样的东西也没有,完全没有。即使对地铁沙林事件,感觉上也是“那是别的什么人的事,跟自己的工作无关”。
我不一样,我认为地铁沙林事件是坏透顶的事,是不能干的事。所以,“坏透顶的事”和自己一直体验的“好上天的事”在自己心中剧烈碰撞。简单说来,结果会是这样的:“坏透顶的事”这一认识占上风的人退出教团,“好上天的事”这一认识占上风的人留下不动。我还处于中间。也就是说要看看情况。
现行犯那些人,这以前一直对教祖说的话言听计从,因此获得了很大好处。在此前的阶段是没有犯罪要素的。所以我猜想恐怕是脱离了类似连续性那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