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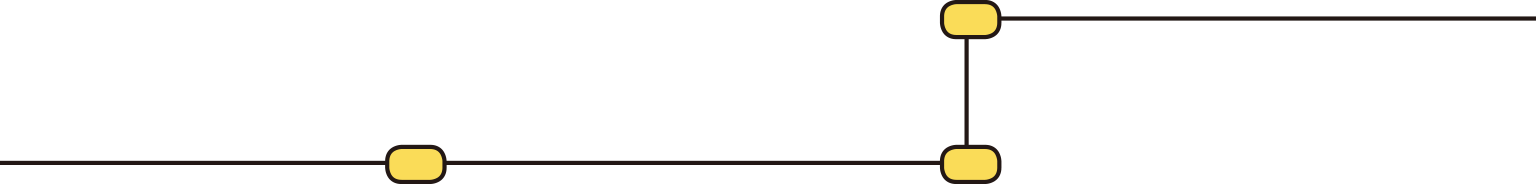
村上春树
一天下午,我偶然拿起餐桌上那本杂志,啪啦啪啦翻看。浏览了几则报道,而后目光逐一扫过投稿专栏刊登的读者来信。至于何以如此,原因已记不清楚了。估计是一时兴之所至,也可能特有时间。因为,无论拿起女性杂志还是阅读投稿专栏,对我都是相当少有的事。
信是一位女性写的,她丈夫因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失去了工作。她丈夫在去公司上班途中不幸遭遇沙林毒气事件,昏倒后被送去医院。几天后倒是出院了,却不幸留下后遗症,无法正常工作。最初阶段还好,但时间一长,上司和同事就开始说三道四。丈夫忍受不了那种冷冰冰的环境,遂辞职回家——实际上是几乎被赶出来的。
杂志现在不在手头,准确表述记不起来了,但内容大体不会有错。
记忆中,写得并不那么“痛切”,也不特别恼怒。总的说来算是心平气和的,或许莫如说约略近乎“牢骚”。也好像为之困惑:“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似乎仍未能理解命运何以急转直下。
读完信,我吃了一惊。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不用说,那对夫妇心中的创伤是很严重的,我打心眼里觉得不忍。同时我也明白,对她本人来说,可就不仅仅是“不忍”就能了结的了。
虽然如此,自己现在却又不能在此做什么。我——大多数人想必也如此——叹口气合上杂志,返回自己本身一如往常的生活和工作中。
可是,那以后我每每想起那封信,“为什么?”这一疑问从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是个很大的“question mark”(问号)。
非常不幸的是,遭遇沙林事件的纯粹的“受害者”不仅仅忍受事件本身造成的伤痛,还必须遭受那种冷酷的“次生灾害”(换句话说,即我们周围无处不在的 平常社会所产生的暴力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周围任何人都不能制止?
不久我转而这样认为:对于那位可怜的年轻职员所遭受的双重剧烈暴力,即使身边的人能明确区别那是来自异常世界还是来自正常世界,而对于当事人想必也不具有任何说服力。对他来说,不可能将两种暴力分成 这边与那边 。作为我,越想越觉得二者性质相同——肉眼看得见的外形固然不同,但都是地下同一条根长出来的。
我想了解写那封信的女性(们),想了解她的丈夫(们),作为个人。并且想深入了解产生如此双重剧烈伤痛的我们这个社会的构成方式,了解事实真相。
具体下定采访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的决心,是那以后不久的事。
当然,杂志上的那封读者来信不是写这本书的惟一理由。那好比现实性点火栓。当时我心中已经存在关于写这本书的若干大的个人动机。不过,这点我想在最后部分慢慢讲述。姑且先请大家看这本书好了。
※
这些采访,从一九九六年一月初至同年十二月底,做了整整一年时间。直接面见同意做证的人士,倾听大约一个到一个半小时,把音录进磁带。当然这终究是平均数,也有时采访长达四个小时。
录音带径直转到专家手里进行所谓“录音带处理”。即把明显与采访目的不相关的部分除掉,其余原封不动地变成文字处理机中的字。无须说,有的相当冗长。而且,一如我们的日常交谈,大部分话题这里那里跳来跳去,抑或离题万里,后来突然出现。这就需要就内容加以筛选,置换前后顺序,删除重复部分,调整文节,使之大体容易阅读,且长度基本适中。仅靠阅读录音处理稿有时候很难把握细微语感,因此屡屡重放录音带确认。有三次由于某种原因而直接依录音带照写下来。
不过,在如此成稿过程中,当时的个人“印象”和“记忆”往往起很大作用。无论谈话细节拾取得多么认真,也无论录音带反复听多少遍,而若把握不住当时气氛的整体流程,有时也会丢失类似谈话核心的部分。这样一来,证词本身势必失去力量。所以,听对方讲述的时间里我尽可能集中全副精力,把每句话都打入脑海。
录音被拒只有一次。电话中本来已跟对方讲明要录音,但实际去那里从手提包里掏出录音机时,对方说没有讲过要录音的事。结果只好一边倾听一边时不时记录数字和地名什么的,差不多听了两个小时。回到家马上伏案写稿,依据简单的记录和记忆再现当时的谈话,我自己也不由得感叹:人的记忆这东西关键时候还是蛮靠得住的嘛!对于平日从事采访工作的人来说,这倒有可能是家常便饭。不料,由于成稿后对方拒绝发表,致使这种努力也前功尽弃。
这里容我倾听谈话(以下称采访)的人士,是为此书做调查的押川节生和高桥秀实两位找到的。作为具体手段,采取以下两种:
(1)依据报纸或各种大众传媒报道,从迄今作为“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发表的人名中挑选;
(2)向周围人打听是否知道谁是地铁沙林事件的受害者。或者通过其他种类(因故难以公开具体方法)如“小道消息”等方法查找。
老实说,做起来困难比预想的大。最初阶段简单以为东京一带有那么大数量的事件受害者,搜集事件证言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事情没那么轻而易举。
这是因为,只有法院或检察院等司法机关才有“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的正式名册。理所当然,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尊重,局外人不能查阅名册。各医院住院者的名册也是同样。我们勉强弄明白的只是住院之人的姓名,这是事件发生当天报纸等媒体报道的。然而这仅仅是姓名,至于住址、电话号码则无从知晓。
姑且把知道姓名的七百人做成名册,由此开展工作,但得以明确“身份”的仅为其中百分之二十左右。对于如“中村一郎”这样常见的姓名,仅凭姓名锁定对象是非常困难的。不过,经过如此程序,总算同一百四十多人取得了联系。可是很多人以种种理由拒绝接受采访,不是说“不愿意再回忆那个事件”就是说“不想和奥姆发生关系”或者“媒体不可信赖”等等。尤其对媒体采访的反感和不信任感强烈得超乎意料,刚说出出版社名字对方就挂断电话那样的情形举不胜举。接受采访请求的,一百四十多人之中归终仅四成多一点点。
对于奥姆的恐惧,大部分人伴随时间的推移和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被捕而逐渐淡薄。但仍有不少人拒绝接受采访:“自己症状算是轻的,不值一提”(也可能是出于拒绝接受采访目的托词,无从确认)。此外也有几个这样的例子:本人愿意介绍事件,但身边家人十分不情愿“进一步卷入其中”,以致无法取得证词。以职业种类来说,各种公务员和从事金融方面工作的人的证词极难得到。
女性受害者的访谈所以少,主要原因是很难根据姓名实际弄清身份。而且——终究是我个人的推测——未婚女性之中大概也有人对这类采访有抵触情绪。也有几人虽然口说“家人反对”而接受了采访。
因此,尽管正式发表的受害者达三千八百人之多,但找出六十人左右“肯做证的事件受害者”却是极花时间极费精力的劳作。
作为方法,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公开征求愿意为本书提供证言的受害者:“我正在写这样一本书,请为此接受采访。”这样,我想结果上可能得到更多的证言。实际上当采访在某个地方卡住的时候也受到了这样的诱惑,但同调查人员和编辑几次商议的结果,最终决定不采用那种方法。理由是:
(1)首先,我们并无有效手段确认对方主动提供的证言的真伪。与此相比,我们主动时候的风险要小得多。
(2)有自己主动想谈的人出现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由于那种积极接受采访者的比例的增加,有可能导致书整体印象的改变。相比之下,作为笔者(村上)宁愿重视随意抽取式的平衡。
(3)在调查性质上,如果可能,打算尽量不引起世人的注意,进行秘密调查。否则,对媒体采访怀有的不信任感会更加强烈。而且,笔者想最大限度地避免在其中出现。
避免“公开征求证言人”,事后想来,带来了另一个好的结果——由于排除较为简单的手段而使得笔者同调查人及编辑之间更有向心力了,产生一种类似“达成感”的感觉。“这是大家一个一个凑起来的”——这种实实在在的质感得以从中产生。紧密配合成为制作这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珍惜每一位证言人的心情也更强了。
访谈稿出来后,首先送到被采访者那里请其确认。每次都附有这样一封信:“作为我们诚然希望尽量以真名实姓发表证言,可以么?如是不愿意,我们可以匿名,由您选择。”——约有四成希望匿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测,书中没有一一注明何为真名何为匿名。因为若注明匿名,反而有可能刺激某种好奇心。
而且,请对方确认成稿后的访谈是否属实时,若有“这个不想写出来”那样的部分,我们就请其先告知是希望删除还是如何更改。差不多所有人——尽管程度多少有别——都希望更改或删除。
笔者按照采访对象的指示,对指定地方加以更改或删除。删除或更改的部分往往含有能让人真切感到采访对象的人品或生活场景的内容,作为作家的我个人是相当遗憾的。但除了删除或更改后致使前后不连贯的情况,我都完全照做。难以照做的时候由我提出替代方案,求得对方同意。
如果改正或删除较多,出于准确性的需求,就把新稿送过去请其再次确认。若仍有希望改动的地方,只要时间允许,便按同样顺序重复一遍。有的访谈如此反复五次。
作为我们,一来不想给欣然接受采访的人添麻烦,二来想极力避免使得对方不快。即使为了消除对于大众传媒的普遍的不信任感,也不想让对方感到后悔或觉得一番好心被利用了。为此尽最大可能对访谈稿加以认真删改。
采访对象总数达六十二人。但前面也说了,成稿后有两例拒绝公开证言,而且都是内容深入的关键证言。老实说,舍弃已完成的稿件感觉上有切肤之痛,但既然采访对象说“No”,那么只能放弃。我们自始至终都坚持尊重证言人本人的自发性,这一姿态贯彻采访整个过程。当然,有时也做一定程度的解释或说服,但若仍然说“No”,我们随即撤下。
反过来说,收在这本书里的证言,完全属于本人自发的、积极的。没有文字性润色,没有诱导,没有勉强。我的写作能力(我是说如果我多少有那东西的话)只集中于一点:如何原封不动地采用对方的话语而又能使其容易阅读。
对于部分愿意用真名实姓发表证言的人,我们曾再次确认:“以真名出现,有可能出现一定的社会反响,那也不要紧吗?”如果对方说“不要紧”,才将其真名用在这里。对此深表感谢。将证言收进这本书的时候,以真名讲述所具有的现实性冲击力往往强烈得多,愤怒也好、诉求也好、悲伤也好、其他什么也好……
不过,这当然不意味轻视选择匿名方式的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由,我也很理解这点。莫如说我要对尽管有那样的情由而仍能接受采访这点再次表示感谢。
采访时笔者最先问的是每位采访对象的个人背景:在哪里出生、成长过程、爱好是什么、做什么工作、和怎样的家人共同生活等等。工作尤其问得详细。
所以在采访对象的个人背景上如此花时间和占如此大的比重,是因为想让“受害者”每个人长相的细部更真切地浮现出来,而不想让其中活生生的人变成“面目模糊的众多受害者的一个(one of them)。身为职业作家这点或许是一个原因,而另一方面,我对“综合性概念性”信息这种东西提不起多大兴致,只对每一个人具体的——不能(难以)交换的——存在状态怀有兴趣。因此,面对采访对象,我在有限的两个小时内尽可能竭尽全力去深入具体理解“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并力图以其本来面目写成文章传达给读者。尽管由于采访对象的情由有很多情况写不进去。
所以用这样的姿态采访,是因为相对于“施害者=奥姆相关者”每一个人的情况通过媒体采访而被细致入微地呈现出来,作为一种富有蛊惑性的信息物语在世间广为传播,而作为另一方的“受害者=普通市民”的情况则完全显得支离破碎。那里存在的几乎全是仅仅被赋予的角色(行人A),极少提供能让人侧耳倾听那样的物语。而且,即使那种少量物语也清一色是以模式化的文脉讲述的。
想必是因为普通媒体是想将受害者以“被伤害的无辜的一般市民”这一印象固定下来的缘故。进一步说来,受害者没有活生生的面孔更能使文脉顺利展开。并且,“(没有面孔的)健全的市民”对“有面孔的坏蛋”这一古典对比能使得绘画变得容易操作。
如果可能,我想把这种固定模式消除掉。这是因为,那天早上地铁上的每一位乘客都是好端端有鼻有眼、有生活、有人生、有家人、有欢乐、有纠葛、有戏剧、有矛盾和烦恼——有将这些综合起来的物语的。不可能没有。那是你,也是我。
所以,我首先要了解他/她的为人,无论其结果能否具体写成文章。
听完这些个人信息之后,转入事件发生当天的情况。无须说,这是正题。我倾听每个人的叙说并且发问。
“对于您那是怎样的一天呢?”
“您在那里看见了什么、体验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呢?”
(某种情况下)“您因那起事件遭受了怎样的(肉体上、精神上)痛苦呢?”
“那种痛苦后来也持续吗?”
事件造成的受害程度,委实千差万别。既有微乎其微的,又有不幸去世的,还有至今仍在康复治疗过程中的重患者。也有当时没什么大事而后来受困于(持续性受困于)PTSD
 症状的。从一般性报道角度来说,重点罗列重症患者的情况或许更有社会价值。
症状的。从一般性报道角度来说,重点罗列重症患者的情况或许更有社会价值。
但我这本书不是这样。只要不巧身在现场多少遭受沙林伤害,无论症状轻重我都主动采访,并在取得对方同意后将采访对象的话完完整整收进书中。诚然,轻度受害者重返正常生活的速度快,影响也小。但他们自有他们的感受、恐惧和教训。读一读就会得知,那也并非可以等闲视之的症状。三月二十日这一天对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份量不同的特殊的一天。
此外我还有这样一种预感:不分症状轻重地将多数受害者的情况完整地收在这里,可以使得事件的整个过程重新以另一种形式显现出来。这点一读之下即可了然。
接受采访的几个人此前接受过媒体采访,都抱怨说“自己真正想说的最后却被删掉,被弄得缺头少尾”。也就是说,“媒体只适当地选用了容易报道的部分”。
因为人们的不满情绪很大,所以我们这次采访为取得其理解——理解我们的目的和方法截然不同——有时候花了相当长时间。遗憾的是,有的直到最后也未能取得理解。
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想把这次采访中听得的情况尽可能多地作为信息收录进来,但由于篇幅限制和阅读量的限制,只能分别适当划一条线,平均份量在400字稿纸写20—30页左右。个别长的达50页。
虽说不分症状轻重,但症状严重的无论如何原稿页数都要多些。因为讲述的内容多,如住院经过、康复过程,或感触之深、创伤之大等等。
下面就请听一听他们的讲述吧。
不,听之前请先想像一下。
时间是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一。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晴朗的初春早晨。昨天是星期日,明天春分休息,即连休的“山谷”。也许你心想今天也休息多好。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缘由你无法请假休息。
这样,你在平日那个时刻睁开眼睛,洗脸,吃早餐,穿上西服走去车站,像往常那样钻进拥挤的地铁上班。平平常常的一如平日的清晨,人生中无从区别的普普通通的一天。
在五个化装男子将用研磨机磨尖的伞杆尖头捅进装有奇妙液体的塑料袋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