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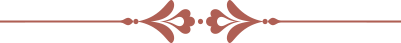
卡拉瓦乔在西西里待了一年左右。马里奥·米尼蒂是昔日在罗马的旧相识,曾为他的画作“水果”和“鲁特琴”担任模特,如今已经是西西里的希拉库塞城的大画家了。米尼蒂或许在工作和食宿方面为卡拉瓦乔提供了帮助,但是无法给他最需要的东西:宁静、赦免和恢复名誉。如果说卡拉瓦乔的天才画家之名在逃亡期间一直跟随着他,并为他带来了工作,那么他的罪行也一样如影随形,且从未放过他。他的变动不居也体现在西西里的大型祭坛画中,他在流亡到希拉库塞和迈锡纳的时候创作了这些作品。近来某些意在修正的艺术史家过于渴望修改一切浪漫主义的传奇,千方百计地想要说明,卡拉瓦乔的西西里时期的作品,无论是与他在马耳他所作、启示深远的鼎盛作品《斩首》相比,还是与他昔日在罗马的荣耀年代的作品相比,并非彼此一致,而是非常不同:更加黑暗,更加静寂——即使多了一些朴素的、扣动人心的东西。这个过分的修正观点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1608年的《圣露西入殓》( The Burial of St Lucy )、1608年至1609年的《牧羊人的仰望》( The Adoration of the Shepherds )以及1609年的《拉撒路的复活》( The Raising of Lazarus )这些作品中,仍然具有某些深切的动人之处,有心怀忏悔的质朴。不过,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卡拉瓦乔在此选用这种更加粗略也更毛糙的技巧表明了一种精心设计的质朴画风,但是这个判断也可以被看成浪漫主义计划的一个结果。而且,这些看起来较为粗糙的画作也可能只是尚未完成。卡拉瓦乔可能非常匆忙地完成了这些作品,由于心中的绝望日益加深,他也需要这样做。除了接近苍白的单一色调之外,这些画作几乎都具有同一个特点,由于画面都十分巨大,因此它们都令人感到行动被重新禁锢在画框之内:静谧,难以触及,它们被封存于画面之后,远离了画前的信众。对于卡拉瓦乔来说,这的确是一种新的绘画方式。但它并不是更好的方式。
事实上,他在西西里期间总是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当然这也是有理由的。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向他寻仇。不管他在马耳他做了什么,也不管他曾经得罪了谁(如果不是整个骑士团的话),总之,他这次是招惹了极为可怕的仇家。唯一可能的获救机会就是回到罗马并取得宽恕。那才是他渴望生活的地方,他的画作也将在那里展出。而且他不知从哪儿听说,由于深信他能创造奇迹,有很多身份显赫的人正在努力帮他争取赦免。这些人包括弗朗切斯科·贡察伽主教(Cardinal Francesco Gonzaga),以及更有分量的西庇奥涅·博尔盖塞主教(Cardinal Scipione Borghese),他是教皇保禄五世的侄子,对艺术极为热爱。
于是,1609年10月,卡拉瓦乔再次乘船去北方寻找被赦免的希望。为了慎重起见,他先回到了西班牙治下的那不勒斯。而他旧日的保护人、科隆纳的卡拉瓦乔侯爵夫人(是她最早介绍卡拉瓦乔来到罗马这个艺术之都的)当时也在那不勒斯,就在她位于契埃亚的别墅里。这不可能只是巧合。侯爵夫人是通往罗马的纽带,或许也是通向赦免的桥梁。卡拉瓦乔渴望赦免。而他最早的保护人可能也是他最后的,甚至是仅有的机会了,因为他的职业生涯已经从当时辉煌灿烂的拱顶一路跌落至眼前这湾闪亮的浅滩。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使他在10月24日离开切利戈里奥客栈时放松了警惕。就在那时,他突然被不知名的刺客袭击,毁了容,挨了一顿痛打,最后被扔在那里等死。消息传到他的朋友和保护人耳中,大家都感到震惊,但是并不意外。是啊,谁想要卡拉瓦乔的命呢?说得更准确点儿,谁会不想要卡拉瓦乔的命呢?首先就是罗马的那些艺术家,他们都受过他的言辞侮辱和拳打脚踢。其次就是马里亚诺·帕斯夸洛内,他在纳沃那广场竭尽全力想要杀死的公证人。还有权势显赫、人脉深广的托马索尼家族,他们的儿子/兄弟丧命于卡拉瓦乔的剑下。最近的还有那些在打架闹事中受伤的马耳他人,由于我们的画家跑了,他们的索赔和审判请求都遭到驳回……这些人里,谁不想要他死呢?
不过还是有些人希望卡拉瓦乔活着,为了教廷也为了他们自己而作画。所以,当卡拉瓦乔在契埃亚别墅的茉莉花丛与柠檬树下疗伤(不过这次的袭击是如此凶狠,以至于他的脸和身体再也无法彻底康复了)的时候,他所画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了自我辩护,以此来证明:尽管差点丢了性命,但他还是以前那个不可思议的卡拉瓦乔。西西里的祭坛画中那种充满毛糙感的温柔质地再次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旧日作品中那种最锐利,也最富戏剧性的方式,不过这一次,连一丝闪光的暗示也没有了。这些新画作里,有几幅是要献给可能替他求得赦免的人(尤其是西庇奥涅·博尔盖塞),画中代表救赎的形象又一次遭受了斩首的酷刑,就好像他无法摆脱对自己被砍头、被处以极刑的想象。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圣安德鲁惨烈的受难,看到他痛苦扭曲的面孔,可以看到又一个施洗约翰的头颅。这一次是盛在浅盘里,托着它的莎乐美显然不开心,她看起来忧心忡忡,而非欣喜若狂,似乎对自己手中这暧昧的战利品半信半疑。卡拉瓦乔似乎成心要让那些胜利者犹疑不定。因为在《大卫手提歌利亚的头》( David with the Head of Goliath ,1605—1606)这幅画中,这位牧羊的少年英雄也是一脸忧色,这是一切雕塑与绘画作品中曾经出现过的、最富张力的大卫形象。
这种表达有违常规。然而卡拉瓦乔的整个艺术生涯,甚至他的全部生命都与常规格格不入。他一度是头野兽,这野兽却能表现最虔敬的庄严。他的手上染过他人的血,这最坏的行径践踏了信仰。而他在画布上所做的最好的事也正是苦心传布信仰。因此,现在,就在他即将如自己所盼望的那样,从切利戈里奥客栈那场血腥与混乱之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卡拉瓦乔却再次颠倒了一切。而这次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寻求红衣主教与教皇的宽容,同时也是为了寻求我们的,甚至他自己的理解。
在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中(也包括另一位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大卫的形象都被表现为神圣美德与英雄力量的结合。当佛罗伦萨人从西涅奥拉广场上那些伟大的雕塑身边经过时,他们想象着能够从自己身上、从自己的城市中看到的,正是这两种美好的特质。在基督教传统中,大卫是鼻祖般的人物,因此,对他的描绘总是联系着善对恶的胜利,总是涉及成功地将神恩从恶魔的罪孽中拯救出来。当我们注视这纯洁、充满英雄气概又神圣的大卫,也就看到了基督教艺术的宗旨:美是一种拯救的力量。因此,即使米开朗基罗没有将自己的形象刻入他的雕塑作品,但是他所具备的、有关这份职业的一切,他那份神授的天赋,都被投入到这完美形式的塑造中。其他的画家则更忠于这一宗旨。在一幅未能存世的画作中,乔奇奥尼据说把自己画成了大卫:大乔治,那个击败异教罪孽的征服者。
现在看看卡拉瓦乔的作品,这简直难以置信,不是吗?其实这幅角色颠倒的作品比初看上去要复杂得多。《大卫手提歌利亚的头》是否真如人们曾论证的那样,实际上是一幅双重意义上的自画像?大卫那年轻身体的上半部沐浴着光芒,他就是那个曾经蒙受神恩的卡拉瓦乔,那个开端便令人惊叹的卡拉瓦乔,那个“基督教的美”的创作者(大卫用作武器的弹弓与上衣一起,松散地系在腰间,这块白色的织物具有一切画家所能表现的最为精致的触感)。然而,当同样的光芒向下流泻、笼罩上那张怪物的面孔,这就是现在的卡拉瓦乔:是双性的山羊、杀人犯,是一切罪恶的集大成者。

《大卫手提歌利亚的头》
1605—1606
布面油画
博尔盖塞美术馆,罗马
卡拉瓦乔最早的传记作家之一曾经写道:“大卫”的模特实际上就是画家心中的“卡拉瓦乔”——那个“与他同在的小卡拉瓦乔”。表面看来或许确实如此,但是当然,这无法排除一种更深层的可能性:这就是画家想要成为的“另一个自我”。美与兽性,那束倾斜的光线将这二者紧紧结合在一起,就好像大卫紧紧抓住了歌利亚的头颅。它们似乎不是在呈现那种英雄胜利而邪恶落败的对立内涵,而是通过某种悲剧性的自我认识结合在一起。事实上,在一幅触及几乎所有最重大主题(性、死亡与救赎)的画作里,美德与邪恶各自的比重竟是出乎意料地持平。几乎每一位评论者都已经注意到大卫的剑指向(实际上已经触到)自己的胯间(卡拉瓦乔正是给了拉努奇奥·托马索尼那里以致命的一击),上衣从他的腰间垂下直到画幅底部,形状则隐约可见阴茎的长度。年轻的大卫已然成为神圣勇气的化身,而年老的大卫王却成了一个荒淫之徒,一个已经被宣判的杀人犯;他垂涎拔士巴的美色,与她欢好之后又想方设法除掉她那碍事的丈夫。
一切事情都并非看起来那样简单。这世间没有纯粹的英雄,也没有不可救药的恶棍。尽管歌利亚的头颅淌着令人作呕的涎水、外露的牙齿、灰黄的皮肤以及低垂的眼睑,但是卡拉瓦乔的自画像中最令人震撼的一点(并非他本人被画成“被斩首的美杜莎”那样),则是画家在镜中的最后所见:不是怪物,而是一个人。尽管这个人能做出可怕的行径,但他终究是一个人。即使歌利亚那致命的创伤被奇怪地凝缩为一双深蹙的眉头(卡拉瓦乔或许想要把这创伤表现得更血腥一点,可以肯定他会这么想),那是一个人在行将死去的一瞬依然挣扎着想要理解一些重要事情时所流露的表情。卡拉瓦乔的美杜莎曾经见证了映像艺术的致命力量,但是女怪的脸上写满了拒绝的恐怖。歌利亚的形象似乎也是在即将死灭的一刹那被映像捕捉,然而对自我的认识通过某种方式,在杀戮之后依然存在,因为大卫手中的那颗头颅仍是鲜活到令人不安,嘴唇依旧张开,似乎仍在发出最后的嘶吼。
正如美杜莎的头颅喷溅的鲜血,以及毡布上面约翰汩汩流出的污血一样,歌利亚的断颈之下不断喷涌的鲜血再一次使邪恶到救赎的转变成为有形。不可饶恕的罪孽如今得到了宽恕,好似经过洗礼通向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