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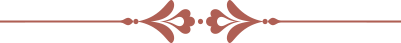
这是卡拉瓦乔的时代,也是罗马的时代,二者极为契合。1600年很快就要到了,这也正是克莱门特八世教皇(Pope ClementⅧ)的大赦年。这是热诚、朝圣和恩典的一年,通常情况下无法得到救赎的罪人们(比如卡拉瓦乔)都将在这一年获得赦免。不过,圣城自身也需要时间来修整平复。卡拉瓦乔寄宿在宫中,但是每一天,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清楚,另一个罗马(那个有十万极为穷困的人生活于其间的城市)遭受过瘟疫的打击,负担着沉重的赋税以供应教皇那些不起眼的小战争。人们食不果腹,密切关注着庄稼的产量并祈祷能有一个好收成,这样才能买得起面包和意大利面。1598年,台伯河水患严重,冲垮了圣母大桥(该桥后来得一别名“断桥”),看起来,罗马城也需要奇迹。

《亚历山德里亚的凯瑟琳》
1598
布面油画
提森——博内米萨博物馆,马德里
奇迹很快就会降临。委托卡拉瓦乔创作壁画的礼拜堂,正好位于圣路易济这座法国教堂之内。这次要描绘的历史题材是圣马太,因为一位名叫马修·康特莱尔(Mathieu Cointrel)的法国主教为了使与他同名的圣人受到后人崇奉而留下了一笔遗产,同时也对如何表现相关场景(殉难以及税吏受到耶稣召唤)提出了非常详细的要求,例如画中要出现多少人物,如何设置背景环境,等等。礼拜堂的穹顶画已经由裘里奥·切萨里(现在他已经是鼎鼎大名的德·阿尔皮诺骑士了)在1593年完成,年轻的卡拉瓦乔当时很可能是他的助手。但是作为罗马最受欢迎的历史画家,因接受的委托一直源源不断,德·阿尔皮诺最终未能完成礼拜堂其他部分的绘画。圣彼得大教堂的建造总管接手了礼拜堂的修竣任务,他将这项任务交给德·蒙蒂,后者则指派了卡拉瓦乔。
这个机会既令人兴奋也令人畏惧。无论是作品尺寸还是公共影响,这几幅圣马太画作都是卡拉瓦乔迄今为止画过的最大规模的作品。在此之前,他笔下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内,即使像《美杜莎》这样特殊定制的作品也是如此。以前那些作品都是架上绘画,在他工作室明亮的灯光下直接画成,他自己决定画中人物的数量及其在画面空间内的位置。但是现在,他必须遵照康特莱尔的详细说明,甚至可能还要与德·阿皮尔诺此前在穹顶上绘制的作品相一致——人物群像,神圣的光辉,宏伟的结构以及深邃的空间。卡拉瓦乔也清楚,以前他或许可以描绘那些类型化的场景和静物画,可以用妓女作为模特来描绘尽善尽美的圣人,但是这一次,这份工作可能是他的机会,也可能是场噩梦。
卡拉瓦乔于是着手创作《圣马太受难》( The Martyrdom of St Matthew ,1599—1600),圣马太在自己主持的祭坛旁,被埃塞俄比亚国王派来的人杀死。卡拉瓦乔试图满足教堂纵深的建筑空间要求,让圣马太的受难在这个空间里重新上演,设置众多的配角,将受难转化为临死的那一瞬间——然后,或许也是有生以来头一次,他卡壳了。法国主教的要求简直就像束缚人的锁链。于是,卡拉瓦乔放弃了纵深空间,当然也没去刻画众多人物。他的戏剧化的全部力量都在于切近,而非远距,在于凝缩,而非宏大的全景。这力量的核心在于个人化的直接认同。而一个人又怎么可能与一群人认同?
他越是努力,那些限制性的说明就将他缚得越牢,使他行动不得。于是,卡拉瓦乔暂时放弃了创作受难题材,转向左手那面墙,在那里他拥有更多观念上的自由来创作《圣马太蒙召》( The Calling of St Matthew ,1598—1601)。这不仅是因为《福音书》对这个命运转折点描述得极为简略:“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男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里表达的观点对卡拉瓦乔来说很重要,出于自己的理由,他专门研究了最没希望、最冷酷麻木的罪人获得救赎的可能。他曾经没用多久就认识到“受难”的思路一时难以成形,同样,“蒙召”的灵感也来得很快,而且很轻松。在这儿,他可以画他最清楚的事,可以写实,可以画罗马真实生活中的某个场景——这就是他的生活,而那些看到这幅画的人立刻就能认出来,这也是他们的生活。
卡拉瓦乔又使用了《作弊者》中的那张牌桌和其中一个男孩儿,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天花板很高的下等小酒馆里,脏乎乎的墙面,一扇油纸糊的窗,其中一个窗格还破了——画家当然精心描绘了这些破损。每一个走进这间礼拜堂的人,立刻就会发觉这个场景十分熟悉:浮华的衣着、牌桌、数硬币发出的“叮当”声、正在核对的收据,还有在场那些粗鲁的男人和天真的小男孩儿。人们熟悉这些底层场所。卡拉瓦乔身上具有的反直观的天赋在此展露无遗。接下来,既然已经打破了一个规则(即画中故事发生在高雅的环境里),那么何不索性打破最大的规则呢?卡拉瓦乔的构图没有将焦点引向基督和税吏之间那场转变命运的相遇,而是让这个场景乍看起来完全是个偶然。画面中没有被这个重大时刻惊呆的人群,事实上,某些人物甚至都没有看见耶稣和圣彼得走进门口。一个人伏在牌桌和钱币上,紧挨着他的那位长者(他的眼镜既表明了他的近视也象征着他的道德)根本懒得抬眼看。有两个蓄着胡子的客人走进来了,他们似乎想要点点什么,于是有人前去“接待”了——也就是告诉他们“谢谢惠顾,不过我们没空儿接待二位”。
卡拉瓦乔接着将这种戏谑推向极致。他没有把基督放在画面的中心,反而使其模糊不清;观看者最好是自己把基督找出来。在神学意义上,这一着儿堪称完美(对于罗马大赦年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就像圣彼得从制度上确立了教皇的地位一样,在这幅画里,他在视觉上也处于我们和基督之间。不仅如此,这个表达在心理层面也同样成功,由于人们无法完整地看到基督的身体,这就使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基督伸出的右臂,以及指向某处的手指。这是神圣与世俗的完美结合——毕竟这正是这个故事的核心要义。他的姿势借自罗马最著名的一个绘画细节,也就是那个神圣的开端:米开朗基罗所作的西斯廷穹顶画中,天父与亚当的指尖相触。从基督指向某处的手——而不是从那扇肮脏的窗户——发出一道光芒,这就是福音之光,它完全笼罩了那位天真的小听差的脸庞,他原本不应该跑到这个地方来与这些卑污的人们混在一起的。而这个男孩儿看起来甚至有些轻慢地躲开了那道光芒,他把胳膊搭在圣马太的肩上,这是一种本能的、毫无遮掩的自我保护。这束光线继续照向那个不知所措的人物,也就是圣马太本人,他因为自己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之下而突然脸红起来,并以一个动作来回答这神圣的召唤,所有的罗马人、每一个朝圣者都能理解这个回答:“你说谁?我?”当然,就像有些学者已经论证过的,这个姿势的方向也可以被理解为“你不是在说他吧?”,同时手指向下指着他右边的那个人。不过,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正是这个留着胡子的男人才是将要成为使徒马太的那个人。因为他的穿着华贵,是卡拉瓦乔自己喜爱的黑色天鹅绒衣料,这为他向着谦卑的皈依赋予了更多含义。

《圣马太受难》
1599—1600
布面油画
康塔莱里礼拜堂,弗兰切西的圣路易济教堂,罗马

细部
卡拉瓦乔本人

《圣马太蒙召》
1598—1601
布面油画
康塔莱里礼拜堂,弗兰切西的圣路易济教堂,罗马
另外还有一些变化。卡拉瓦乔一度对画中人和我们这些观看者之间直接的目光接触毫无兴趣,这种讨好姿态也确实是太低贱。我们只是作为隐蔽的目击者,偶然遇见了正在发生的一幕,躲在礼拜堂的黑暗之处秘密倾听。而画中人都似真人大小,这个事实制造出了一种幻觉,让人以为这一幕此刻正在真实上演,从而更加兴奋紧张。
卡拉瓦乔知道《蒙召》已经实现了预想的效果,凭着这股自信,他又回来创作《受难》,而这次,他不再为康特莱尔的烦琐要求所困。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忽略这些要求。按照他的以往的标准,画布已经很拥挤了,但是他没有用深凹而宏大的建筑空间来使人物缩小,反而是用一种近得令人透不过气的距离,让人物在我们的眼前行动。没有巍峨高耸的教堂,画作仅以寥寥数级石阶暗示了祭坛的存在,旁边还有一个正要逃跑的唱诗班男孩。这两幅巨大的画作位于相对的两面墙上,卡拉瓦乔冥思苦想,要找出某种方式令它们在情感上相互呼应。惊人的缄默和静止覆上《蒙召》,在那之后的《受难》却呈现出一个混乱的旋涡,人物四散逃开,中间却定定地站着那位裸身的刺客。这是卡拉瓦乔的典型手法:创造唯一的静止不动的形象,强健有力的裸体正处在整个动作的支点位置,它就是邪恶的化身。他伸出的手臂紧紧攥住圣马太的手腕以便再次攻击(汩汩而出的鲜血——这一次描绘得十分逼真——已经溅满了殉道者身上的白色长袍),这与对面墙上耶稣伸出的手臂恰恰形成相反的、邪恶的呼应。另一个戏剧性的天才之举则令一场道德角力得以上演。圣马太将要死去的身体正在落向看起来像是洗礼池的深黑处,他的左臂和左手按照透视的比例缩短了,看起来仿佛在向我们寻求帮助。但是一位天使降临到他的上方,手中拿着象征殉道者的棕榈枝,它也会引圣马太获得天国的奖赏。
这幅画则将我们这些凡人留在某个中间位置,惊恐、尖叫(如果说《蒙召》是沉默的,那么这幅画则是嘈杂的),光线仿佛镁光灯不停闪烁,从一具身体到另一具身体,从这张面孔到那张面孔,恐慌的氛围由此被推向极致。但是,在人群后面(在这场戏剧的远处,与身处事件前方的我们在想象中处于同等的距离),一个人暂时停下了逃跑的脚步。他汗涔涔的,蓬头垢面,头发打着结,眉头紧皱:卡拉瓦乔把自己画成了一个懦弱的罪人,明知应该(为了自己逃命而)远离罪行的现场,而且越快越好——但是同时他又不能不去观看。他所保留的唯一悲悯就是手中提着一盏灯。毕竟他是带来光的人,尽管这与他的天性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