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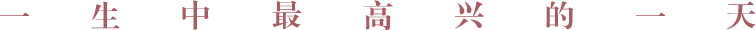

赵大娘站在垃畔上,两只手捏弄着围裙,眼盯着对面山上那条小路,咀里叱叨着:“什么时候了,人家早拾掇了碗筷睡了觉,还不见那死鬼的影子……”
太阳,在头顶喷射着强烈的火焰。黄土高原这个小小的山村,宁静得无一点声响。
六月啊!这是一个多么关键的季候:麦子等着抢收,秋苗盼着喂水,人们每天都是起鸡叫睡半夜地在地里泡着,操劳着,疲乏到了极点。午饭后这一阵香甜的小憩,谁连个梦都不做。
窑檐影子已经变成了窄条条,小路上还是什么也没有。赵大娘轻轻地叹了口气,转回到自己窑里去了。
南山上,一个光着上身,赤着脚片子的老头,背着一捆苜蓿蹒跚着下来了。他,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微微眯瞌着,以防额上的汗水浸入。在那一脸松针胡子上,黑黧黧的胸脯上,弯曲的胳膊肘上到处都挂着汗珠,窜着汗流,浑身上下冒着热腾腾的气。
这人就是赵大娘的老伴、赵湾生产队的贫农社员——不,代理队长——赵万山。
这赵万山说话少,管事多,在这一带是出了名的。不过他只管外,不管里。生产队场边抛撒几颗粮食,他都能发现,一粒一粒捡起来,放在手心里吹掉土。装在集体的口袋里。如果谁家的猪跑到生产队的庄稼地里,他手里捏几块土疙瘩,连追带打。把人家的猪追回圈,拉上门,还要把主人叫出来,喘着粗气说:“再要叫猪跑到地里,我非把猪腿打折不行!”至于自己家里鸡下了多少蛋,猪掉膘了没有,这些“内政事务”,他很少查问,为这些,能干的赵大娘对他有意见得太大哩!有意见你有意见,赵万山还是那样:说话少,管事多;只管外,不管里。
今天一大早,生产队长贺虎去公社开会,临走时对大家说:“我明天才能回来,这几天活路正紧张,看谁把队长代理一天?”大伙七嘴八舌地说:“就让赵万山代上!”
赵万山一句话没说,操起榆木棍,敲响了上工钟。接着,他把全队人马安排成三路:一路锄草,一路放水浇地,他自己带着一路去割麦。
赵万山把苜蓿放在饲养室门前,用毛巾擦了擦身上的汗水,这才不紧不慢地向自己家里走去。
一进门,赵大娘瞅了他一眼,说:“还晓得回来哩?!你人挣气,肚子可不给你挣气!”她见赵万山不说话,就一边给他倒丝豆汤,一边继续说:“你一不当官,二没补贴,常出那些外余力顶什么!你看看这顿饭吃到什么时候啦?”
赵万山正要擦火柴抽烟。听老婆数说他,便把烟锅从嘴里拔出来,瞪着眼睛说:“看你说些什么话!给社里多做一点活儿,是为了当官挣补贴?!死脑筋!”他点着烟吧嗒了两口,不在意地说:“贺虎开会去了。我今儿给他代理当队长。”
“代理,代理,代理一天队长还耍你那二百五!亮红晌午,你不给那牲口砍苜蓿不行?人家常是后晌派一个人去砍,你收了工不回来吃饭……”
“你瞎唠叨啥?活计这么紧,能节省一个人力就节省一个!等连阴雨把麦子沤在地里,你这死脑筋就高兴了?!”
赵大娘“扑哧”一笑:“好,好!就数你能!你那外余力出得有理,快吃饭吧!”说着,把筷子往他跟前“啪”的一放。
赵万山磕了烟灰,随即端起了一碗红豆角角菜,用筷子扎了一个白面馍,正准备下口。突然,他透过窗上的玻璃,瞥见他的堂兄赵有贵扛了一捆干酸枣刺晃了过去。他不禁一愣,心想:赵有贵不是中午照水坝吗?这会儿不在,那水漫过坝堰咋办?再说,他那捆干酸枣刺是哪里来的?……坏了,准是后渠羊圈门上的!赵万山放下碗筷,三脚两步冲出了门坎。
“死人!你又到哪里去?!”赵大娘困惑不解地在窑里喊着。
“寻赵有贵去!”老汉在院外回答。
赵大娘无可奈何地把饭收拾到锅里,坐在小板凳上,轻轻地叹了口气。
赵有贵是个一辈子没成家的单身汉,旧社会给国民党当了几年兵,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恶习,并且手脚也不太干净。平时,别说是给队里好好做活,就是个人的自留地,也常是草长得比庄稼高。赵万山常指教他这个同族,但赵有贵总是今天宣布洗手不干,明天又旧病重犯。
今天,赵万山分配他去后沟的自流水坝放水。本来这是个轻便营生:放水时,拔开水眼,顺便在渠上跑一跑,看有没有漏洞;中午不放水了,就在水坝上照看着。防止坝里水过堰,后晌上工时来一个人再顶他去吃饭。可赵有贵乘中午人睡定了,却悄悄离开水坝,把压在羊圈门上防备狼的那捆干酸枣刺扛回家。
“好我的万山兄弟哩!当时就烧不开了,贺虎不在家,你就饶了这一回,本家本姓的……”赵有贵的音调。
“滚远!你不会上山自己砍一点柴?不要磨牙了,送回去!水过了坝堰有你好看的哩!”赵万山斥责的声音。
赵大娘从小板凳上站起来,手里不断地捏弄着围裙。这时,她透过窗子上的玻璃,看见赵万山扛着那捆干酸枣刺走在前面,赵有贵耷拉着脑袋跟在后面,朝后沟走去。
赵大娘长长地叹了口气,转过身往灶里投了一把碎柴,晃悠悠地拉起了风箱……
赵万山还没踏进门槛,赵大娘便嚷开了:“算了吃这顿饭啦!”嘴里嚷着,手里却揭开锅盖麻利地往盘子里拾馍馍。她一边拾,一边继续嚷着:“代理人家当一天队长,不知你管些什么!代理,代理,把劳动生产代理一下就对啦,惹那些人干什么!”
赵万山气头来了:“代理队长就什么也要管!代理要管,不代理也要管!不光要管赵有贵,还要管你!”
“我情愿你咋样管理!赵有贵那号人你管他做什么?那是个死黑皮,小心往后咬你一口!”赵大娘一边端饭一边说着。
“咱不歪门邪道,怕他什么?!”赵万山端起饭碗出了门,向院外那棵槐荫走去。
他刚蹲下咬了一口馍馍,突然像被蜂蜇了一下,“腾”地跳起来:一渠水满满地淌了出来!糟糕,一定是水口脱了!他把菜碗往地上一撂,把咬了一口的馍馍往怀里一揣,跑进窑里拉了把铁铣,风一样窜出了门。
“又咋啦?”赵大娘手忙脚乱地追了出来。
“水口脱了!”赵万山边跑边说。
“把其他人叫醒去堵吧,死人,你还没吃饭哩!”赵大娘慌乱地捏弄着围裙。
“不要叫!众人都熬得要命,让他们多睡会儿!”赵万山头也不回地跑了。
赵大娘叹着气转回到屋里,对着炕上的一盘子饭菜发愣。
赵万山气喘吁吁地跑着。他终究老了,加上又累又饿,等到了水坝,几乎昏晕了过去。
水坝上,不见赵有贵的人影子,只见水口子的泥块全都豁了,碗口粗的一股水直往外窜。
赵万山一下扑在水口子旁边,甩过铁铣,双膝跪在烂泥里,用手捧起一把把泥浆,使劲地堵住了水口子。
随后,他抓起铁锨又反转身直奔村前的玉米地。他知道这股水到了地里,会把那些血汗筑起来的畦园地冲得七缺八豁。本来,把水渠中间的闸门拉开,让水流到沟里就没事了,但六月里的水啊,滴滴都宝贵!谁忍心浪费?
赵万山胸口像塞了一块火炭,两条腿已经疲乏得难以起动,全身又洗了一次“汗澡”,但他还是跑着,与奔流的渠水争时间。
他正跑得起劲,忽然,发现路下边的一棵柳树下睡着一个人——啊,是赵有贵!
他从路上跌撞着跑到柳树底下,朝赵有贵的屁股就是一脚:“你死下啦!”
赵有贵神经质地一蹦起来,瞪大了迷糊着的眼睛。
“水快跑光了!你这个二流子!”赵万山狠狠瞪了他一眼,车转身子就跑了。
赵有贵还没完全清醒过来,糊里糊涂地向水坝跑去。
等赵万山急忙赶来时,水头已经越过了上午浇过的畦园,向四面漫溢着。他一纵身就从路上跳到玉米地里,不料,那个咬了一口的馍馍也同时跟着从怀里跳了出来,滚落在地上!他赶忙弯腰捡起来,使劲地吹着上面的土,哪能吹掉呀!本来就热腾腾的馍馍,又被汗水浸得湿渍渍的,上面粘上的土变成了一层泥巴。
“咳!”赵万山丧气地摇了摇头,把这个粘满泥巴的馍馍,随手放在了玉米地一棵小枣树的权上,提着铁铣又往流水泛滥的畦园奔去。
到了跟前,他顾不得喘口气,马上把水头拨进没浇过的一畦,又东一铣,西一铣地铲来土,加高那积水过剩的畦园。
干完这些后,赵万山浑身瘫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把水拨进了另一畦,便双手拄着铁铣把,靠在田埂上。火辣辣的太阳烤得老汉头昏眼花,早已饥饿了的肚子,这会儿“咕咕”地叫得更欢了!
这时,小路上走来了赵大娘。看那份神态,准是要大喊大叫的。
她走到赵万山跳下去的那个地方,正要扯开嗓门,突然,小枣树杈上那个粘满泥巴的馍馍撞进了她的眼帘。啊,一股热辣辣的激流涌上了她的心!两行泪水在那张皱纹脸上不断线地淌……她猛然觉得,阳光下,她那光着脊背的丈夫,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先进啊!
赵大娘用围裙揩去脸上的泪痕,溜下土塄子,急匆匆地向赵万山走去。
她到了他的身边,用亲昵的声调说:“代理队长,你这营生叫我代理上,你回去吃饭吧,菜和馍馍都在锅里热着哩!”
赵万山把铁铣交给他的老伴,用手搭个凉棚,抬头望着太阳,说:“已经过晌午了,这工作你可以代理上。我得和大伙一块儿上工了。”
他走过去在小枣树权上取下那个吃了一口的馍馍,用布衫襟子揩掉泥巴,走一步,咬一口,向村前老柳树上那口古铜大钟走去……
(原载《山花》1973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