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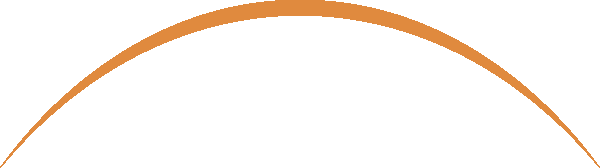

|
亡命鸳鸯 |

|
叶葆恒从医院回来,心中最沉重的一块大石被移走了,步履也轻快起来,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顾忌了,可以协助大哥放手一搏了——他相信,兄长有获胜的把握,因为手里掌握着“关系到整个战争的全局的秘密”,而且还掌握着戴笠放纵手下走私的确凿证据。
叶葆恒在洗脸刮胡子时不禁哼起了小曲。
陆婉宜见叶葆恒容光焕发,问:“怎么今天心情这么好?”
叶葆恒笑着说:“医生检查过了,我没什么毛病。”
陆婉宜也笑着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希特勒完蛋了,纳粹完蛋了!”这天,她从电台广播里听到了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身亡的消息。
叶葆恒一听,抱起陆婉宜原地转了几个圈子:“太好了,我们也快胜利啦,霍去病可以成家啦!”
陆婉宜用粉拳捶他的胸膛:“想得美,鬼子还占着我们半壁河山呐。”
东方的战争并没有结束的迹象,日本仍在负隅顽抗。日本政府在广播里发表声明称:“日本为求自存自卫与东亚解放而作战之决心,丝毫未感动摇。德国之降服,不能令日本之作战目标有丝毫之变更。” 汪伪的《民国日报》转发日本同盟通讯社的社论“为政者要想人民之所想”,大意是:德国人民是想打的,但德国政府屈服了,日本人民“一亿一心”誓死抵抗到底,日本政府将顺应民意,还说,“中华民国”作为日本的盟邦,将“一心一德”协力维护“大东亚共荣圈”。
“无耻!”叶葆恒愤怒地把报纸拍到桌案上。他所居住的四马路的路口原本有一座普希金铜像,但现在被拆走了,沿路的铁栅栏、铁门把手也都被统统拆掉——日本人正到处搜罗废铜烂铁送兵工厂制造枪炮子弹。路边的墙上贴着“打倒鬼畜米英”等字样的反美英标语,窗户玻璃上贴着“米”字形防震胶布。为了巩固上海防御迎击有可能到来的美军登陆,驻上海的日本第十三军“登部队”补充了许多原关东军部队,这些头戴狗皮帽子的日军一到上海便四处抢占民宅作为营房仓库。陆婉宜说,对面的大厦就新进驻了一支日军通信部队,在屋顶架设了大功率电台,她在收发无线电报时,常常受到干扰和吸引,生怕被发觉。
叶葆恒一想到未来这座大都市将在战火中化为废墟、无数市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景象,就不寒而栗,怎样才能尽快结束战争呢?但这显然是个人能力办不到的。
傍晚,到了和兄长一起出逃的时候了。叶葆恒平静地与陆婉宜吃晚饭,连饭量也和平常一样,吃过饭,他说要将借来的《春明外史》还给书店,悠哉悠哉出了家门,往四马路而去。他出门时除了那本小说,什么也没有带,家中的东西也都原样不动,看上去的确就是饭后在家附近溜达溜达。
叶葆恒在书店看了一会儿书,看了看表,时间差不多了,周围没发现有人盯梢,他从书店后门出去。那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秀珠正等候他,一把挽住他:“亲爱的,怎么现在才到,叫人家好等。”叶葆恒被一阵甜腻的香气包绕,脸上不禁一红,想挣脱。秀珠低声说:“你要装像一点儿,来,把手搭到我的腰上。”叶葆恒轻轻把手伸过去,因为有些紧张搁在了她圆润丰满的臀部,又闹了个大红脸。秀珠“格格”一笑,把他的手拉上一些,依偎着走向暗处。
两人穿过几条狭窄的小巷,来到一家土耳其烤肉店,旁边停着一辆别克轿车,车牌号末尾的数字是“15”。秀珠说:“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叶葆恒忙不迭松了手,说了声“谢谢”,俯身敲了敲车窗。司机探头问:“先生有事吗?”叶葆恒说:“请送我去孟先生的表哥家。”司机点了点头,打开车门,叶葆恒上了车,汽车迅速驶离。秀珠站在原地看了看,确定没有跟踪这才转身返回。
汽车开到新闸路的“欧斯克”咖啡馆门口停下,司机带着叶葆恒下车,用钥匙开了门,登上旋转的楼梯,来到二楼。屋子里没有人,窗户全部遮上厚厚的窗帘,外面的光线一丝也透不进来,一片漆黑。司机打开手电筒,叶葆恒跟着走进去。
司机说:“你就在这儿等吧,你哥哥马上就到。”见叶葆恒有些疑虑,解释说,“咖啡馆早就停业了,这里很安全,你先休息一下,半夜时,我们会送你俩上船。”
叶葆恒说:“好。”
司机说:“你们的行李、身份证和船票都在汽车里,我先下去,你呆在这,哪儿也别去。记住,不要打开窗帘!这屋子很长时间没人来了,巡警如果看到这么晚还有人,没准会上来查问。”
司机下楼了,叶葆恒打开电灯,随手在身边的卡座上一摸,上面是薄薄的一层灰,屋子里都是霉味,看来确实停业很久了。他随意挑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无聊地张望,忽然发现这个座位上没有灰尘,心中一动,又查看了一下,发现靠窗口的几个座位都是如此,显然有人刚坐过。这些天来叶葆恒迭经风波,心思慎密了许多,他仔细巡视了一遍房间,在角落里找到几个烟蒂头,从剥开的烟丝看,应该是新近丢下的。
叶葆恒心跳加速:“这司机说屋子里很长时间没人来,但明明刚刚进过人,而且有好几个人。”
他挑开窗帘一道缝朝下看,昏暗的路灯下,马路两边是整齐的梧桐树,树根部分涂上去的白石灰粉已有些脱落,枝头上宽大的叶子迎风“沙沙”地摆动着,那辆别克轿车还是停在原地。
周围很安静,叶葆恒却感到一股莫名的惧意。他想了想,走下了旋梯,来到门口。司机从车里出来,对他说:“你怎么下来了?快回去。”
叶葆恒说:“上面太气闷,我和你一起在下面等。”
司机说:“叶先生,这里是什么地方?我劝你还是听话,不然闹出动静就不好办了。”
叶葆恒说:“我就呆一会。”
“不行!”司机右手插在外衣口袋里,眼露凶光。
叶葆恒见状,更是明白了几分,说:“好,我回去。”慢慢倒退。
司机这才从口袋里抽出右手,转身走到车旁。
这时,远处亮起了车灯,一辆轿车驶近,停在马路对面,下来一人,看身形正是叶葆杰。
叶葆恒猛然返身,一把抱住司机,放声大喊:“大哥,快跑!”
远处的叶葆杰一愣,叶葆恒已经和司机扭打在一起。
这时,送叶葆杰的那辆车里的司机拎着手枪钻了出来,叶葆杰已有防备,迅速返身猛力一关车门,那司机惨叫一声,胳膊被夹伤,手枪掉在地上。叶葆杰捡起手枪,奔来相救弟弟。叶葆恒大叫:“别管我,你快走!”
“砰”一声尖利的枪声划破夜空,枪声接二连三响起,咖啡馆旁边紧闭的店面里窜出几条黑影,向叶葆杰包抄过去。
叶葆恒的心一揪:“果然有埋伏。”
叶葆杰见机极快,迅速后撤,一边还击,一边利用车辆和树木做掩护,一个黑影追得太急,被一枪撂倒在马路上,其余几个便不敢太逼近。这时警笛响起,眼看着叶葆杰越跑越远,最后消失在街头,带头的那人骂了一句脏话,说:“带上那小子,还有受伤的兄弟,撤!”
两个持枪的人跑到叶葆恒身前,把他和司机分开,用绳子捆了个结实,嘴里堵上破布,塞进汽车。叶葆恒拼命挣扎,吃了好几记拳脚,一个人倒转枪柄狠狠砸他后脑勺。叶葆恒眼前金光乱冒,昏厥过去。其余几个人架着受伤的同伙上了另一辆汽车,汽车一溜烟开走,街道又恢复了平静。
不知过了多久,叶葆恒渐渐苏醒过来,试着动了动,发现动不了,他睁开眼,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头和脸刚被浇过冷水,身上湿漉漉的,借着微弱灯光打量四周,只见这是一个散发着潮气的狭小地下室,面前摆着一张小桌子,旁边站着一个壮汉,手里端着剩下半盆水的脸盆,桌后站着两个人,一个是胡培义,不过这时穿了便装,一个是张觐光,都是军统的人。叶葆恒的后脑还在隐隐作痛,回想起来,明白是孟兴麟背信弃义,向军统告密,军统暗中布下罗网逮捕叶葆杰,只是不知现在兄长是否安全逃脱?
胡培义首先开了腔:“葆恒,我们又见面了。”
叶葆恒一见此人,就想起他诓自己打“毒针”之事,“哼”了一声,没有搭理。
胡培义说:“想必有些事你已经知道,但我还是要奉劝你几句:你哥哥叶葆杰背叛国家和领袖,勾结日伪,出卖同志,罪该万死!你要想活命,趁早和他划清界限,老老实实坦白你们联络的方式,帮助我们找到他,如果拒绝合作,则等同叛逆!你也是在罗家湾十九号呆过的,叛徒是什么下场,就不用我废话了。”
叶葆恒听了,心中反而一宽,这说明兄长没有落入军统之手,说:“你的话我不太明白,我哥是我哥,我是我,我可没有做对不起国家和领袖的事,你们这样对我,算什么道理?”
胡培义说:“戴老板给你的重要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你整天吃喝玩乐,说你畏缩渎职那都是轻的,你投靠伪政府的参赞武官公署,光这一条,就可以定你的汉奸罪。”
叶葆恒猜测“渔夫”这样的机密胡培义等人不一定知道内情,说:“戴局长交待的任务我尽力了,我去参赞武官公署也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至于我哥哥,你也知道,他是老军统,藏身之处多得是,逃走后我也不知他去了哪里。”
“葆恒,你是一个大好青年,可不要自毁前程。我再问一句:你真的不知道他的下落?”
“不知道!”叶葆恒断然回答。
胡培义冷笑:“我苦口婆心劝你,是不忍你同流合污,你可不要以为我们没办法让你老实交代。”朝一旁的张觐光一努嘴。
张觐光转身出去,过了一会儿,带来一个同样被绑得严严实实的人,那是秀珠。叶葆恒心中一凉。胡培义说:“这个女人是你哥哥的姘头,你不肯说,我们就先问问她。等问过她之后,我看你嘴还硬不硬?”伸手扯出秀珠嘴里的布团,“秀珠姑娘,如果不想吃苦头,就好好跟我们合作,我们问一句,你答一句,明白吗?”
秀珠大口大口喘气,没有理他。
胡培义指着叶葆恒问:“这个人你认识吧?你跟他哥哥这么久,他哥哥在上海有什么藏身之所?怎么联系?你要是说出来,这个就是你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金戒子,在她面前晃了晃。
秀珠狠狠“呸”了一声,把脸别过去。
胡培义摸着她的下巴,轻佻地说:“听说你的艺名叫‘花蘑菇’?果然是个亭亭丽人,不过,越漂亮的蘑菇毒性越大。你要是这么不识时务,就别怪我们以毒攻毒了!”对那个壮汉吆喝一声,“蛤蟆!”
那个壮汉长着一双宽大的嘴巴,两眼凸出,确实有些像蛤蟆,胡培义说完,他便开始往桌子上摆放一些奇怪的东西,酒精灯、竹扦、火柴……
张觐光狞笑着划根火柴点着了酒精灯,把竹扦的尖端放在灯火上慢慢地烤着,很快,竹扦的表面烤出了一层油,他凶狠的脸上也涔出了汗珠。
秀珠突然战栗起来,她明白他们要干什么——向指甲里钉竹扦,再用火烤!
叶葆恒大叫:“你们不要胡来!折磨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他知道,指尖是人体中最敏感的神经集中的地方,如果被拷问者不开口,竹扦就要一个接一个个钉进去。
张觐光捡起一团破布塞进叶葆恒嘴里,秀珠大喊:“救命啊!”叫声在狭小的地下室回荡,非常刺耳。张觐光又拿了一块破毛巾去堵秀珠的嘴,秀珠死死闭上,张觐光捏住她鼻孔,她憋不过,张开了嘴巴,张觐光顺势就将毛巾塞进嘴里,还拿木棍将毛巾往她嘴里面捅,大半条毛巾都被强行塞进嘴里,秀珠发不出一点声音,脸憋得通红。
胡培义看到叶葆恒和秀珠惊恐的表情,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对这种残酷的刑讯如醉如痴,搬了张凳子坐下,翘起二郎腿:“现在招还来得及,只要你们点点头。”
竹扦已经烤得火热了,秀珠还是摇头,胡培义向张觐光打了个响指。
张觐光和“蛤蟆”一下子抓住了秀珠的右手手腕。秀珠就像被套上了两个铁箍,右手一时血脉不通。张觐光不急不慢地把竹扦平翻过来又烤上了,然后端详了一下拿着的竹扦,把它举到秀珠的右手食指跟前。
秀珠用尽全身气力往回拽她的右手,但纹丝不动,她只得闭上眼睛,咬紧牙关。
猛然,竹扦如同一把尖刀似的,一下子就扎进秀珠的指甲里。秀珠尽管嘴巴被死死堵住,仍发出了一声含糊不清的呜咽,她虽知逃脱不掉,但仍不死心,拚命挣扎折腾。
叶葆恒看得睚眦欲裂,但嘴巴被堵住,只发出“呜呜”的声响。
张觐光把酒精灯挪到竹扦下面,竹扦又烤得吱吱响。
竹扦烤后,秀珠疼得越发厉害,全身都疼出了汗,接着,中指又被钉进了第二根竹扦。
胡培义慢悠悠地说:“喂,说吧,老实交代,不然你的右手就废了。”
秀珠的忍耐已经快到了极限。她漂浮在一个黑洞洞的世界里,恶鬼从四面八方向她追来,右边的鬼龇着牙想咬断她的喉管,左边的鬼伸出利爪来抓她的衣襟,她左闪右躲,拚命地逃,但到处是张开血盆大口狞笑的魔鬼,像刀子一样的利爪撕破了她的脖子,挖出了她的心……
秀珠昏死过去,两眼翻白。
张觐光费了好大劲才从秀珠嘴里拔出毛巾,毛巾上都是血,还有两颗牙齿,试了试她的鼻息,向胡培义低声耳语:“再钉下去,这臭婊子可能缓不过来了。”
胡培义站了起来,拔下叶葆恒嘴里的布团:“现在轮到你了!招不招?只要你招供,就可以将功抵过,既往不咎,这个女人我也可以放掉,这一点,我以人格担保!”
叶葆恒破口大骂:“你们这帮丧尽天良的禽兽,有人格吗?”
胡培义不怒反笑:“骂得好!”重新坐下,又是一个响指。
张觐光和“蛤蟆”抓住叶葆恒的右臂。叶葆恒兀自大骂不止,又是紧张又是恐惧,不知即将面临的怎样的痛楚,只有靠骂声壮胆。
这时,门口传来了话音:“住手!”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了进来,叶葆恒不禁叫了起来:“老牛,老石!”
胡培义见牛世杰和石武进来了,站了起来:“两位特派员要亲审?”
牛世杰看了一眼地上的秀珠,皱眉说:“外面老远就听见鬼哭狼嚎的,闹出这么大动静,唱大戏吗?”
胡培义悻悻地说:“这小子倔得很,不给点颜色,他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叶葆恒叫道:“老牛,我冤枉啊,我没有背叛国家和领袖……老石,在宪兵队监狱里,我们一起受过刑,你是知道的……”
石武点了点头,说:“葆恒的为人,我是清楚的,这其中可能有些误会。”
“误会?”胡培义冷笑一声,“你把戴老板的手令当儿戏吗?就在几个钟头前,他和叶葆杰当街拒捕,还开枪打伤了我们一个弟兄,如果不是心藏鬼胎,怎么会狗急跳墙?”
叶葆恒大声说:“不,我哥哥绝不是汉奸!他如果是汉奸,还用得着偷偷摸摸找孟兴麟,请他送我们去重庆?你们要是不信,只管去找这个姓孟过来和我对质!”
牛世杰“嗯”了一声:“你哥哥想去重庆?那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叶葆恒心想:“事已至此,我索性当着他们的面说个明白!”他说:“我哥哥之所以敢去重庆,就是因为他忠贞不二,问心无愧!他潜伏敌后多年,手里掌握着一个关系到整个战争全局的大秘密,他要带去重庆表示自己的忠诚!”
牛世杰说:“既然如此,你哥哥何必兜圈子跑到重庆去?在这里就可以坦白嘛。”望了一眼石武,“我和老石都是重庆派来的,可以给你们做主。”
石武点了点头:“你还是配合我们找到你哥哥,我们和他都是有交情的,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一切不都清楚了嘛。”
叶葆恒脖子一梗:“他信不过戴局长!”
牛世杰问:“你哥哥是戴老板一手栽培出来的,为什么信不过他?戴老板德高望尊,军统上上下下对他都是敬仰有加。”
叶葆恒说:“戴笠因为一点个人恩怨便诬我哥哥投敌,这样陷害忠良,怎能服众?”
胡培义骂道:“死到临头,还嘴硬!”挥起手臂就要打他。
石武伸手制止,问:“你哥哥说的那个大秘密到底是什么?”
叶葆恒摇头:“我不知道,他要到了重庆才会说出来……”
胡培义把布团重新塞到叶葆恒嘴里,说:“不必理会这小子的胡说八道。”和牛世杰、石武一起出门,原来这里是“张记”猪肉铺的地窖,三人拾级而上,来到厨房间,因为长期不开火,厨房灶台冷冷清清,地面堆满了煤球。
胡培义关紧门,说:“我记得上峰没给二位安排审理叶葆恒的任务啊。”
牛世杰说:“叶葆杰叛变一案,其中不明不白的地方很多,我们想搞搞清楚,回到重庆也好复命。”
胡培义说:“不要有这种想法,这个案子上峰早已裁定,我们只管拿人。叶葆恒的那些话,听了未必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好处,我奉劝二位不要自找麻烦。”
论职衔和资历,胡培义要低于牛、石二人,但语气咄咄逼人,显然是有恃无恐,牛世杰和石武当然心知肚明。牛世杰说:“如果我们不来,你是要对叶葆恒动刑了?”
胡培义说:“软的不吃,只有来硬的。”
牛世杰问:“如果他还是不招呢?你打算怎么收场?”
“再换几个花样,他总有撑不住的时候。”胡培义有些底气不足。
石武说:“叶葆恒受过日本人的酷刑,别看他像个白面书生,骨头还是很硬的,只怕闹到后来你收不了场。别忘了这是在沦陷区,折腾久了,就怕有变。”
胡培义讥嘲地说:“这么说,石特派员是特地帮小弟来收场的?”
石武不以为忤,平静地说:“不错。”
胡培义说:“哦,还请指教。”
石武说:“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叶葆杰。我这个计策,说出来并不新鲜,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如果二位觉得可行,即刻电告重庆请示批准。”当下将自己的计策说了。
胡培义犹豫不决。
石武说:“我只是提个建议,组织实施都以你为主,如果行动成功,功劳簿上自然以你居首。”
牛世杰说:“如果胡老弟另有高招,不妨也说出来,大家一起合计合计。”
胡培义左思右想,说:“那就按石特派员说的办,我先去请示。”
他转身回到地下室,把张觐光和“蛤蟆”叫出来,和他们耳语了一番。
张觐光望了望地下室,低声问:“那婊子怎么处理?”
胡培义眼露凶光:“她已经没用了,留着是个祸害,赶快处理掉!”
张觐光点了点头。
胡培义叮嘱:“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干湿活,手脚给我放干净点。”
地下室,叶葆恒见那些人都出去了,挣扎着爬到秀珠身边,侧耳倾听,见她还有呼吸,稍觉宽心,他双手被绑住,见留在地上的那只脸盆还有半盆冷水,便用嘴叼起盆将水泼洒到秀珠脸上。
秀珠“嘤”了一声,叶葆恒努力伸出手指去掐她人中,秀珠渐渐醒转过来,两眼空洞洞地望着他。
叶葆恒含泪说:“秀珠,你为什么要这样?”这个他原先看不起的舞女,此时却令他肃然起敬,他不知道,是什么让秀珠能顶住如此的折磨?
秀珠虚弱地说:“因为你们是好人,他们是坏人。”
叶葆恒苦笑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好人?”
秀珠眼睛里有了一点光彩:“别瞒我了,你哥不是做烟土生意的,你们是抗日的,是做大事的。”
叶葆恒一怔:“我哥跟你说过了?”
秀珠摇了摇头:“我猜到了。”她喘了几口气,“我比你们更恨日本人!不是这帮畜生,我们全家就不会死得只剩我一个,我也不会堕落成千人骑万人骂的婊子,连带祖宗八辈都跟着丢脸……我只恨自己没本事,杀不了日本人……这帮人逼问你哥哥的下落,不是汉奸是什么……”
说到这里,她上气不接下气。
看着秀珠皮开肉绽的手指和地上带血的竹扦,叶葆恒真是百感交集,不禁流下来泪,想起兄长说过的话,说秀珠并不可靠,只是他早先发展的一个落脚点,碰到日伪宪警搜查时就在她那儿躲一躲,她是做皮肉生意的,给钱就能留宿……没想到,这个身份低贱的女子却做出了令男子汉汗颜的壮举。
这时,胡培义带着张觐光回到了地下室,不由分说,将秀珠拖走。
叶葆恒叫道:“你们想干什么?放过她,她什么也不知道。”胡培义一脚重重踢到他脸上。叶葆恒眼冒金星,鼻子一阵酸痛,嘴巴一股咸味,吐出了一口鲜血。
胡培义冷冷地说:“你就呆在这里发霉吧!”转身出去,锁上了门。
冰冷潮湿的地下室,只剩下叶葆恒一人,他惴惴不安,不知等待秀珠和自己的命运是什么,由于体力不支,恍惚之中昏睡过去,但难耐的饥渴又让他醒转过来,只得趴在地上,试着舔洒落在地上的积水,嘴巴里有了一丝凉意,但嗓子眼仍在冒火。
又不知过了多久,地下室厚厚的石门再次打开,走进两人,前面一人是张觐光,后面一人居然是陆婉宜!叶葆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使劲咬了一口下唇,这才相信不是做梦,他惊喜之下,正想开口相问,只见陆婉宜向他眨了眨眼,目光中大有深意,他顿时住口,静观其变。
张觐光说:“姓叶的,胡长官念你原来也是革命同志,也要求过进步,因此,我们还要做最后的挽救,这次把婉宜同志请过来相劝,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忠诚还是背叛,就在你一念之间,好自为之吧。”
陆婉宜脸如寒霜,走近几步,将手里拎着的饭盒和水壶放到叶葆恒面前,一言不发地退后。
张觐光说:“你们先聊,我在门口守着。”就要出去。
陆婉宜双手抱胸,冷冷地说:“老张,你急什么,先给他松绑,不然怎么吃?”
张觐光说:“松绑?我怕他跑了。还是你喂他吧,以前又不是没喂过。”说到这里嘴角露出一丝淫笑。
陆婉宜秀眉微蹙:“我可没这份闲心。”一撩衣角,露出腰间的左轮手枪,“有这个,还怕他这半死不活的人跑了?”
张觐光说:“那倒也是。”俯下身去给叶葆恒松绑,陆婉宜忽然抄起墙角的木棒狠狠砸到他的后脑勺上。张觐光冷不防她会来这一手,哼也没哼便像一袋面粉一样重重摔落到地上,一动不动。
叶葆恒大喜过望,叫道:“婉宜!”
陆婉宜解开叶葆恒身上的绳索,问:“能走吗?”
叶葆恒紧紧抱住爱人,泪水直流,站起身来,试着走了几步,便歪倒在地,他实在太虚弱了,全身像散了架。
陆婉宜扶起他,将水和饭送到他嘴边:“快吃点,补充一下体力。”
叶葆恒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含含糊糊地问:“婉宜,你为什么要冒这个险?你这样会被军统视为叛徒的?”
陆婉宜说:“为什么?为了你。”
叶葆恒心情激动,差点咽住:“你……你不怕他们……不怕戴笠?”
陆婉宜扶着他的手慢慢喂水,说:“你怕不怕?你不怕,我也不怕!他们说你们兄弟俩是叛徒汉奸,我压根儿就不信,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常言道得好,除死无大事,别忘了,这个世上还有天理,我就不信他们能一手遮天,总能找到说理的地方。再说,他们也知道,我和你早就是一体的了,你犯了事,我也不能置身事外。”说到这里,脸上微现红晕。
叶葆恒说:“跟着我亡命天涯,随时会有危险,你不后悔?”
陆婉宜说:“就是天涯海角、刀山火海,我也跟你走!一起活,一起死!”这话说得十分坚决。
叶葆恒心中大是欣慰:“都说患难见真情,一点儿也不错。婉宜为了我,做出了多大牺牲!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回锅肉,香菇鸡丁,这些饭菜都是他平时爱吃的,是陆婉宜精心烹饪的,他吃了全身暖流涌动,精神大振,似乎元气一下子就恢复,“忽”地站了起来:“走,我们一起走!”
陆婉宜一手持枪,一手扶着叶葆恒出了“张记”肉铺。叶葆恒见外面一片漆黑,原来在里面已经呆了一天一夜,想找秀珠,但房子里里外外一个人影都没有。陆婉宜说:“这里不能久留,胡培义他们很快就会回来。”两人拦了一辆黄包车离开了此地。
去哪里?叶葆恒和陆婉宜商量了半天,原先在四马路望平街的住所肯定不能去了,孟兴麟知道的沪西大旅社也不能去。叶葆恒想去找舅舅麦砚田,在麦家暂时避难,料军统也不敢杀上门来。这看似是一个安全的方案,但陆婉宜却反对,说:“麦砚田近来起劲地巴结军统,因为你是军统的人,才救你出狱,现在军统正追杀我们,他会为了帮我们去得罪戴笠吗?肯定会向军统报信的。”叶葆恒说:“他是我舅舅,总会顾念骨肉之情的。”陆婉宜说:“唉,你太天真了,现在这世道,至亲好友都不能轻信。你忘了你哥哥的教训了吗?那姓孟的和你哥哥称兄道弟,一转身就出卖了你们。而且,你舅舅是明摆着的汉奸,你找他庇护,不正给军统以口实吗?”叶葆恒抓耳挠腮:“那你说该怎么办?”陆婉宜说:“你我都是初到上海,人地两疏,两眼一抹黑,能有什么好去处?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闯,不是被日伪抓住,就是被军统抓住。为今之计,只有尽快找到你哥哥,他长期在上海活动,黑白两道都有关系,找到他,我们就有了主心骨,他会想办法带我们一起摆脱困境。”叶葆恒想起兄长曾说过,以后有事要联系他,可以找范勉初。叶葆恒此前去过几次圣慈医院,担心军统会盯上这个医院,但陆婉宜说军统并没有察觉其中的异常,于是,叶葆恒装成病人,裹上毛毯,由装成家属的陆婉宜陪同,前往圣慈医院。
路上换了好几辆黄包车,确认后面没有跟踪,七拐八拐终于到了医院,这天晚上范勉初并没有值班。叶葆恒的后脑勺挨了一枪柄,现在还有一个大血包,便说是被掉下的砖头砸的,说了一堆头疼头晕的症状,值班医生给他做了检查,包扎了伤口,让他去了急诊室挂盐水。圣慈医院并不大,外面下着雨,又是深夜,急诊室里没有几个人。叶葆恒和陆婉宜依偎在角落的长椅上,不时往门口张望,生怕军统的人会突然冲进来,不过急诊室一直静悄悄的。
挨到后半夜,陆婉宜有些撑不住,打起了盹。叶葆恒望着那张精致的鹅蛋脸,不知道是因为恐惧还是寒冷,长长的睫毛正微微颤抖,他爱怜无比,轻轻吻了她。陆婉宜惊醒了,伸手就去抓衣袋里的手枪,睁开眼来,见是叶葆恒,这才舒了一口气。
叶葆恒轻声问:“刚才做噩梦了?”
陆婉宜叹了口气:“今后不知要什么时候才能睡个安生觉。”
叶葆恒搂紧她:“你跟了我受委屈了。今生如不能让你过上安稳日子,我真是枉自为人。”
陆婉宜苦涩地说:“别这么说,不是你的错,也许命中注定,我们就是一对亡命鸳鸯。”
叶葆恒说:“天下之大,总会有我们两个人的容身之地。”
“你别安慰我了。”陆婉宜幽幽地说,“上海是日伪的地盘,军统的势力也很大,要在他们的夹缝里找出一条生路,难得很。”
叶葆恒说:“天下又不是只有日本人和国民党。”
陆婉宜转过头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哥哥另外还有路子,是不是?”
叶葆恒“嗯”了一声:“你接触过共产党吗?”
陆婉宜惊讶地问:“你哥哥想投共?”
叶葆恒说:“还没到那一步,不过,我大哥确实有这个念头,倒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他手里掌握的秘密实在关系重大,如果重庆这边不能容他,也不能让这个秘密就此堙没,必须交到真正抗日的组织手里,那就只有去找共产党。”
陆婉宜连连摇头:“我哪敢接触共产党?民国二十九年的军统电台共谍案抓了多少人?那些人现在狱中生不如死……”言下还有余悸,不愿再说此事,又问,“你哥哥掌握着什么大机密,说得这么玄乎?”
叶葆恒说:“我真不知道那是什么机密,。”
陆婉宜说:“在重庆好歹还有卖《新华日报》,还有个公开挂牌的曾家岩五十号,要想在上海找共产党谈何容易?”
叶葆恒说:“我大哥认识一个叫罗朝立的商人,闸北有一家‘锦丰’绸缎庄,就是他开的。这个罗朝立以前在新四军教导总队当过政治指导员,皖南事变时被俘,关在上饶集中营,后来参加赤石暴动逃了出来,回到浙江杭县老家,在沪杭一带做丝绸生意。几个月前,罗朝立生意场上得罪的一个小人,跑到江浙皖赣机动卫戍司令部稽查科去举报说他当过共产党。我大哥正好担任稽查科顾问,见这个小人只是妄自猜测,意图陷害,并没有掌握真实凭据,便连吓带骗打发了此人,压下了这个案子,救了罗朝立,从此成了朋友。”
“这个人以前是共产党,现在还是吗?”
“我大哥估计,这个人其实还在为共产党干活儿。”
“你大哥当初救他,说不定就存了投共的心思,否则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救他?”
“从事情报工作自然要交游广阔,这样才能耳听八方。”叶葆恒嘴上这么说,内心却觉得陆婉宜的猜测有道理。叶葆杰“假投降”出任伪江浙皖赣机动卫戍司令部稽查科顾问期间,和戴笠矛盾激化,必然做了多手准备——大哥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陆婉宜轻轻地说:“你把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告诉我,不怕我泄密吗?”
叶葆恒搂紧她:“对你我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假如以后我们走散了,或者我不在了……”
陆婉宜掩住他的嘴:“不许胡说。”
叶葆恒说:“我说的是‘假如’,现在形势太凶险,得以防万一。假如只剩你一个人,你就去‘锦丰’绸缎庄找罗老板,报出我大哥的名字,他或许会帮你。”
“这可得有把握才行,不然的话,我的命就送他手里了。”
“像我们现在这种处境,不冒险不行,哪能坐等百分之百的好事,只要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就可以去试一试。”
陆婉宜“嗯”了一声:“你还觉得谁是共产党?”
叶葆恒说:“你瞧那个石武,像不像共产党?”
“他?”陆婉宜歪头想了一下,“我和他是初识,如果连我都看出他是共产党,那他还怎么在军统里混下去?”
叶葆恒一想也是,又想起一事,说:“没想到你平时娇滴滴的,却这么利落就把姓张的干翻了,一招制敌,真想不到。”
陆婉宜淡淡一笑:“你几次到圣慈医院和你哥哥见面,我也一直蒙在鼓里。”
叶葆恒笑着说:“你这么厉害,我以后要怕你了。”
陆婉宜作势一抡粉拳:“看你以后还敢不听我的话。”
叶葆恒低声叫:“饶命。”
两人相视而笑,紧张的心情得到少许放松。
天亮了,医院里面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叶葆恒挂了范勉初的号,和陆婉宜一起早早等候在诊室门口。这时,一个护士走来,见到叶葆恒“咦”了一声:“怎么又是你?病还没好吗?”叶葆恒认得这个护士,当初来找范勉初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就是她,说:“是啊,最近身体一直不好,越来越虚弱,来找范医生看看。”这本来是他的敷衍之词,但那护士却很关心,仔细打量一下:“嗯,你的脸色是不太好。”叶葆恒苦笑了一下,心想:“这段时间折腾得死去活来,脸色能好吗?”随口说:“也不知范医生能不能看好。”想起自身的前途,脸上更有郁郁之色。那护士安慰说:“你别担心,范医生的水平那是没得说,治过很多别人治疗不的疑难重症。”范勉初还没有到,叶葆恒便搭讪了几句:“噢,上次听范医生说起过,有个犹太人得了一种怪病,身体越来越虚弱,无药可救,到后来,全身衰竭而死……”那护士脸露恐怖神色:“那个病人是个例外。”这倒勾起了叶葆恒的好奇心:“怎么个例外?”
那护士说:“那还是去年的事,但我一直忘不了那可怕的一幕。那个病人进了房间,仍戴着一副宽大的墨镜,当我摘下墨镜时,他发出了一阵瘆人的尖叫,叫声中充满了痛楚,仿佛明亮的光线是割肉的尖刀……后来这个病人不停地吐血,吐出来的都是腐烂的内脏渣子……”说到这里声音都颤抖起来,连连摆手,“不说了,你别多想啊,范医生不是说了嘛,你跟他得的不是一种病。”
说了一阵子闲话,上班时间到了,范勉初来了,看到叶葆恒,迅速把他拉进诊室,关上门,低声问:“你怎么来了?”叶葆恒说:“我想找我哥,你知道他的落脚点吗?”范勉初说:“你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他一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叶葆恒坚持:“不,你一定知道!我哥让我紧急时来找你!”范勉初沉吟了一下,说:“我只知道一个地点。”叶葆恒忙问:“哪儿?”“黄浦江边的一个废旧仓库。”“黄浦江这么长,仓库多如牛毛,究竟是哪个仓库?”范勉初挑开窗帘瞄了一眼,外面等候的病人排起了长队,说:“白天去不方便,这样吧,下午五点,你来医院门口等我,我叫车送你们去。”
圣慈医院就在静安寺路上,从静安寺路由西往东,一直走到山西路口的中国国货公司,马路对面就是大江南饭店。陆婉宜挽着叶葆恒快步赶到大江南饭店,上了电梯到四楼,开了个大套房,说:“赶快洗洗吧,一身臭烘烘的,不然晚上别碰我。”笑靥如花,媚眼如丝,叶葆恒一阵意乱神迷,陆婉宜笑着推他进了淋浴间。
叶葆恒洗漱完毕,出了来一看,陆婉宜已不知去向,他吃了一惊,再看门锁完好,刚才也没有听到什么异动,估计是她出去买东西了。果然,过了一会儿,陆婉宜带着一个大包回来了。叶葆恒责怪她不该单独出去,这样会有危险。陆婉宜说:“这里是闹市,坏人要下手,总是挑僻静的地方,而且我注意了,后面没有盯梢。”叶葆恒还想再说,陆婉宜说:“好了,好了。”吻了他一下,“亲爱的,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打开包袱,里面都是新买的衣裤,“你身上那些脏兮兮的衣服还能穿么?别人一看就是从哪儿逃出来的。”叶葆恒换了衣裤,全身上下焕然一新,陆婉宜又说:“附近爱多亚路有家卡萨诺瓦餐厅,听说西餐很好吃。”叶葆恒说:“恐怕不安全。”陆婉宜说:“你不要担心,我打电话订餐。”
中午时分,有人敲门,叶葆恒从锁眼望去,见是送餐的侍者,便开了门。送来的午餐很丰盛,有煎牛扒、吐司卷、布丁、果蔬色拉、鸡尾酒等。叶葆恒自幼家贫,出身军旅,很久没有吃过这样的美味,险些连舌头都咽下去了。陆婉宜喝了酒后双颊红晕,更增艳色。叶葆恒望着爱人娇美的脸蛋痴痴地说:“真想天天都是这样的好日子。”陆婉宜抿嘴一笑:“走得匆忙,没带什么钱,好日子可长久不了。”
叶葆恒听到“好日子可长久不了”,心一沉,一种似曾相识的不祥之感又弥漫开来,香甜可口的饭食似乎变了味——从他接受那个可恶而又莫名其妙的“渔夫”计划开始,就一直被噩运笼罩,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
下午五点,范勉初准时在医院门口与叶陆二人碰面,他已经预订了“祥生”汽车行的一辆出租车,车子就停在医院旁边一条小巷子。三人上了车之后,范勉初只是告诉出租车司机往哪个方向走,没有告诉他具体去哪儿。范勉初悄悄向叶葆恒解释,这样可以避免有人知道他们的最终下落,现在的上海,所有出租汽车和黄包车的车行都由日本人监管,发放的每一张牌照都登记在册,如果发生什么意外,需要协查,日本人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手上掌握的车行渠道,顺藤摸瓜找到可疑分子的去向,这是需要防备的。叶葆恒深以为然,兄长曾认为秀珠和范勉初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不能派上大用,但他们在关键时候的表现却令人刮目相看。
汽车一路前行,从租界的精华部分逐渐转移到了下只角地区,两旁的房屋越来越低矮破旧,不久,周围就只剩下东倒西歪的破屋子和肮脏不堪的街道了。
到了沿黄浦江的仓储区,此时夜幕落下,周围没什么人。范勉初带着两人下了车,这一带原来有很多座仓库,主要用来储存棉纱和粮食,门口马路修得很宽,不过很多仓库早已在战火中破坏,显得千疮百孔,被卡车碾压而成的路面长满了荒草,最近的生意之惨淡可想而知。路灯稀稀拉拉,只有少数几盏还在发光,远处是大片的菜地,景色荒芜。范勉初没有停步,带着他们继续往前走,七转八绕,经过几座破墙头,遥指一座废旧仓库,说:“到了。”
这几天一直下着雨,这段几百米的泥土道路显得格外湿滑,范勉初打着手电筒走在前面,叶葆恒扶着陆婉宜,一脚深一脚浅跟着走。路面上没有新鲜车辙,说明最近这里没有车辆经过。仓库周围是破烂不堪的红砖围墙,门口的网状铁栅栏满是黄锈,虚掩着,“亨通”货栈的牌子歪斜下来,一半掉进了黄浦江里。仓库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可见昔日还是很繁忙的,但现在长满了齐膝高的茂盛蒿草,其间散落着几个破烂不堪的箱子。
范勉初来到仓库大门前,用钥匙打开门,叶葆恒见大门虽然生锈,但打开很顺畅,再看锁口磨得很新,显然这里正住着人,问:“我大哥住在这儿?”范勉初点了点头:“风头紧的时候,他会来这里避一避,这里很隐蔽,一般人不敢进来。”叶葆恒问:“不敢?”范勉初“嗯”了一声,不再说什么,进了门,叶葆恒和陆婉宜跟着进去。仓库里黑漆漆一片,范勉初熟门熟路地取下门后挂着的煤油灯,点亮了,说:“这里早就断电了,晚上就靠这个。”叶葆恒听不到其他人的声音,问:“我大哥不在?”范勉初带他上了一个小阁楼,里面隔开了三个小单间,有两个单间里放着床,显然这里住着两个人,阁楼一角有一个满身油污的小气炉,支架上搁着一把烧开水的洋铁壶,旁边堆着肮脏的锅盆碗筷,墙上挂着熏鱼干、腊肉和菜梗,算是个简陋的厨房。这个阁楼估计是过去看守仓库的人居住的。整个阁楼里弥漫着霉味和一股说不出的怪味,陆婉宜不禁掩住了口鼻,想打开窗户,却推不动,原来窗户已被木板条钉死,根本不透风。
范勉初说:“你大哥出去了,你们就在这儿等他吧。”
叶葆恒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范勉初说:“这个说不准,也许今晚,也许要几天。你们安心等他好了,这里虽然条件差了点儿,但大上海就数这个屋子最安全了。”说着把仓库大门钥匙给了叶葆恒,“出门往北三里地有个码头集市,真要缺什么就去买,不过不要在外面久呆,这个地方很乱,鱼龙混杂。”
陆婉宜忍不住问:“你说这里很乱,怎么又说这屋子很安全?”
范勉初似乎急于离开,没有回答,只是说:“两位多保重吧。”
叶葆恒拉住范勉初:“我看这里有两个人住,不止我大哥一人,怎么回事?”
范勉初说:“噢,是的,还有一个人,是你大哥的一个好朋友。对了,这是我住所的电话,如果我不在医院,可以打这个电话找我。”塞给叶葆恒一个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匆匆离去。
叶葆恒举着煤油灯巡视了一下这个仓库,仓库很大,占地两亩多,墙壁布满大大小小的裂缝,红棕色的水渍像吊死鬼的舌头似的从缝隙里延伸下来,有的墙缝里长出七扭八歪的藤蔓植物。仓库里是成堆的大铁桶,粗略一数有七八百个。由于年久失修,仓库的天棚露出几个大口子,日晒雨淋,铁桶都已锈迹斑斑,有些铁桶则被撬开砸烂,里面装的矿石四处散落,显然有贼光顾过这里,但见都是些石头便未加理会。铁桶上用白漆写着的外国文字依稀可辨,叶葆恒认识一些英文和德文,但这些文字像是法文,估计是公司名称以及货名货号之类的内容,也不在意。
这时,在楼上收拾东西打地铺的陆婉宜叫道:“葆恒,你来看。”
叶葆恒转身上楼,陆婉宜站在一个小单间门口,手里拿着一支烟枪。叶葆恒见里面只放一张床就已经满当当的,地下满是烟蒂纸片火柴梗,床的一头架高,床上有一个座垫和一个大枕头,床头边的小桌子上放着一截蜡烛、一个搪瓷盆,盆上放着一盏装香油的玻璃烟灯。陆婉宜举起那支烟枪:“你大哥吸大烟吗?”
叶葆恒说:“不会,他虽然掩护身份是烟商,但他要执行任务,绝不会吸大烟。”
陆婉宜把烟枪扔到床上:“看来,你大哥这个朋友是个瘾君子噢,怪不得这里有一股怪味……不过,穿的衣服料子还可以呢……”
叶葆恒见墙上挂着一件法兰绒西装,一顶巴拿马金丝草帽,品质上乘,只是积满了灰尘,心想:“女孩子就关注这些东西。”一低头,发现床下有什么东西亮晶晶的,仔细一看,是个金属的注射针头,一时也没有在意。
陆婉宜问:“那……他们去哪儿了?”
叶葆恒笑着说:“你问我,我问谁去?”
当下,两人就挤在临时打的地铺上囫囵睡了一宿,叶葆恒不时醒来,生怕有人会闯进来,好在一晚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