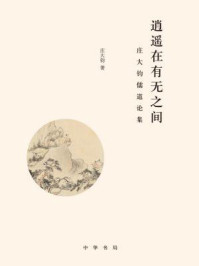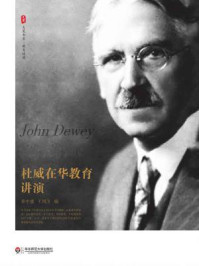1941年秋,我和一位同时考取西南联大经济系的中学同学共坐一辆“黄鱼车”(抗战时期往来于缅甸和昆明、重庆之间,载运战时物资的封闭型大卡车,司机私自拉乘客从中赚钱,把乘客“闷”在车厢里,人称“闷黄鱼”),途经贵阳,走了七天七夜,才到昆明。山路崎岖艰险,虽非蜀道,却比蜀道更“难于上青天”。我们两个人一路上尽发感慨:“大学之道难,难于上青天!”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西南联大的校址位于昆明城西边缘,校园前门一块大横匾上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几个大字,赫然而立,令我俩肃然起敬。我俩笑着说:“总算经过大学之道,走进了大学之门!”
西南联大校舍本部是一排排的人字形茅草房,办公处、教室和老生宿舍都在本部,唯独一年级新生宿舍是附近昆华中学的校舍,两层楼洋房,居住条件比老生好得多,我们对联大的第一感觉是“不欺生”。
从中学到大学,就像乡下人进城,刘姥姥进大观园,觉得花样多,什么都新鲜都神秘。这系、那系,这样的课程、那样的课程且不说,新生谈论最多的是:昨天见到大名鼎鼎的冯友兰,满脸大胡子;今天见到数学天才华罗庚,一跛一瘸;忽而看见一位长袍马褂模样的教授,就猜想可能是北大的;忽而又见到一位西装革履模样的教授,就猜想可能是清华的。总之,眼花缭乱,充满了敬仰之情,以考入这样的大学而自豪。
西南联大的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一样浓重。进校不太久,就碰上由联大学生带头的倒孔运动。据说身为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从香港带洋狗乘飞机到重庆,国难期间,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自然引起学生的愤怒。可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白天游行示威,晚上却照样自学到深夜;白天在大街上高喊“打倒孔祥熙”、“要民主”,晚上在宿舍里交谈数学方程式和“边际效用”(从经济学著名教授陈岱孙讲授的“经济学概论”课程上刚刚学到的名词),还学着陈先生的腔调,故意拖长了声音:“Marginal utility”。在西南联大,“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两位北大旧交,似乎友情依旧,往往携手同行。还记得有一次(时间已经记不清),孔祥熙到昆明,据说原想到西南联大作一次讲演,但又不敢,改到云南大学,云大与联大只一道破土墙之隔,西南联大的同学闻讯后,成群结队,蜂拥而至,先占领了云南大学大讲堂最前面的地盘,大讲堂没有座位,学生们都是站立着的。孔祥熙尚未露面,一片怒吼声已经震撼了全场,他的侍从黄仁霖把手指插在口内,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想借以压场,同学们更加愤怒,高喊“流氓!”“流氓!”孔祥熙出场了,一站到台中间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姓孔,孔子的后人呀!我也是个教师,当过小学教员,还兼校工,摇过铃,让学生上课……”显然是想用这些话来打动我们,引他为同类,以博得同情。同学们看他这气短的模样,总算放过了他。这一幕惊心动魄而又带有喜剧性的场面,令我终生难忘。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这样的场面恐怕也只有在西南联大才能见到。与此相对照,另一番同样轰动了几乎全校师生的学术场面,也是西南联大的标志。联大校门前的一侧,是校本部的内墙,也是同学们最爱聚集的热闹区,各式各样的海报和小广告都贴在这里,联大的几次民主运动也都从这里发端,颇有点像后来北京大学的“三角地”。有一天,我从这里路过,见同学们三三两两在一起谈说着,一打听,原来是刘文典当晚在昆北食堂讲《红楼梦》;找海报,真有其事,也不过是两三尺见方的一张破红纸。海报不起眼,却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关注。离讲座还有半个多小时,昆北食堂挤满了听众,时间越来越近,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只好换地方,连换两次,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露天大院,安顿了下来。听众焦急地也静静地等待刘先生出场。一等再等,还不见刘先生的身影。有人说:刘文典可能抽大烟还没有下床。有人问:刘文典是不是被蒋介石传召去了?(当时,西南联大很多人都知道刘文典抽大烟和任安徽大学校长期间敢于顶撞蒋介石的逸事。)超过预定开讲时间半个多小时,刘文典总算姗姗而来,嘴里叼着一支纸烟,吞云吐雾,好一会儿一言不发。大家席地而坐,鸦雀无声,静候刘先生开口。我的化学老师、著名教授严先生就坐在我身旁,我小声问他:“严先生,您怎么也来听《红楼梦》呀?”答曰:“我学化学的,怎么就不能来听点《红楼梦》呀?”问得我哑口无言,又觉得他的话很值得玩味。好不容易,刘文典开了口,第一句话:“啊啊啊!你们各位都是林黛玉、贾宝玉呀?”全场哈哈大笑。严先生早已等得不耐烦,便应声回答说:“什么贾宝玉、林黛玉的,都是大混蛋、小混蛋!”其实,他是为了泄愤,骂刘文典的,他的声音很小,估计没有什么人听见。刘文典不紧不慢地讲了很长时间,却没有一个人退场。讲完已经夜深,还有人不断向他提问,探讨一些文学甚至佛学的问题。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所春风化雨、弦诵不绝的学术殿堂。我在西南联大,感受最深的也正是它的学术层面。至于它的政治氛围,至少我在联大前期生活中,仍然对之感到淡漠。
联大规定,“大一国文”、“大一英文”是全校的必修课,“逻辑”、“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是文科生必修课。文科学生还必修一门理科的课程,我选修的是化学,但我对化学最无兴趣,尤其是其中的实验部分,我经常旷课,考试得零分,以致整个化学成绩不及格,一直到四年级时选修微积分,才算满足了学校规定的要求。
历史课就像化学课一样引不起我的兴趣,这一方面是因为我记忆力一向不好,而历史和化学都要靠记忆(我喜欢谈理,我对理科的兴趣也主要在数学和物理,对文科的兴趣则主要在写说理文,而不在背历史),一方面也是因为教我中国通史的老师吴先生讲课语言干瘪,一上讲台就拿起讲稿遮住自己的脸,一直照念到下课,下课铃声一响,他卷起讲稿就走。他念的内容又尽是些官制史之类的东西,一点故事情节也没有,把一个本应生动活泼、发人深省的课程讲得枯燥无味,令人生畏。吴先生在上面扯起嗓门念,我们在下面急急忙忙记,考试前总算有个死记硬背的依据。我的历史课考试成绩平平。好在联大往往是几个教授开设同一门课。和吴先生通史课同学期开设的,是雷海宗教授的“中国通史”。他的课堂上总是门里窗外都挤满了听众,原来是旁听的人太多。我们同年级的同学,谁选吴先生的,谁选雷先生的,不知为什么不是按联大的惯例由我们自愿,而是由主管部门分派下来的。我被分到吴先生名下,只好经常去做雷先生的旁听生。雷先生学识渊博,语言生动,讲课完全脱离讲稿,年代与历史事迹记得烂熟,还贯穿着一些深刻的思想,令人回味。我的许多历史知识是从雷先生那里旁听得来的,至今不忘。雷先生是史学界一代宗师,终生没有像吴先生那样为官。据说,雷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曾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学者的命运,往往不是与他的学问大小相对应的。
至于经济系的本专业课程,只有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讲授的“经济学概论”——他讲得特别清楚、简洁——对我确有吸引力,其余的什么“会计学”、“簿记”、“统计学”,我都感到索然无味。我原以为经济学讲的是济世救民之道,不料尽是些“生意经”。在经济系念完一个学期之后,我就萌生了转系的念头。但经济系的陈岱孙先生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不但讲课好,而且衣冠楚楚,谈吐简洁,办事认真、严谨,特别守时。昆明市每到正午12点鸣炮报时,陈先生的课正好是12点下课。陈先生一听到炮声,便伸左手看表,说一声“下课”,正好他的讲课内容也告结束,不留尾巴。他的系主任办公时间是早八点到八点半,我们同学找他签字,早去一分钟,他的办公室门紧闭,一到八点整,他从门侧走出来开锁,办公用品都是前天晚上准备好了的,办起事来极快。过了八点半,如果想请他签字,他便用大拇指指向背后,眼看手表,不言不语,意思是要我们看他背后的钟,办公时间已过。他的手表和背后的时钟似乎也是经他校准过的。陈先生的风格与我们只讲“差不多”的民族传统形成了鲜明对照,也是一位良师。我们经济系的同学都很敬重陈先生,大家谈论到他刚20岁出头就拿了美国的博士学位,得过Golden Key(联大学生平日交谈中往往爱带一句半句英文),不胜敬羡之情。
我念一年级时最感兴趣的是“大一国文”。“大一国文”共分26个班,接英文字母排列顺序,我那个班的老师是文学家李广田先生。李先生后来当过清华大学副校长、云南大学校长,在给我们讲“大一国文”时就有些名声。他讲课语言生动,爱与同学交谈。“大一国文”的课本中选有王国维《人间词话》,三种境界说给我印象极深:“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李先生讲完三种境界的内涵之后,留下作业,要我们思考自己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境界,并写篇短文交给他评阅。李先生在看了全班作业之后,似乎在班上边笑边介绍,说了这样几句:大部分同学都主要谈“第二境”的经历,或因恋爱而“为伊消得人憔悴”,或因考大学开夜车而“衣带渐宽终不悔”,大多没有谈“第一境”和“第三境”的经历。李先生特意表扬了我,说我谈的“第三境”还“有点意思”,那是在解决了一道几何难题之后所得到的快乐,就好比“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很高兴李先生给了我表扬,但现在想来,只有“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才有“第三境”,我何人也?哪来此境?至于“第一境”,李先生在总评时似乎没有对同学们的作业做什么介绍,我对此亦无印象。依照我现在的回顾,对于一个刚从穷山沟里走出来的中学生来说,大学特别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我面前所展现的丰富多彩、无限广阔的前景,实在令我迷惘,也令我向往,我尽情地观望,无穷地选择,我在初进西南联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才真是处在一个“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第一境”里。
在联大的“大一国文”课堂上,我第一次用白话文写文章,这是西南联大的特殊规定,我不习惯,问李先生是否可以写文言文,李先生说:“应该改一改了。”没有多作解释。我写了一篇题为《人与枯骨的对话》的短文,内容主要是寄托自己的大同理想。李先生在文末批写了一句评语——“有妙想自有妙文”,给了我92分。我有点得意,后来投稿到昆明一家报纸《扫荡报》的文艺副刊上,很快就发表了。
1942年秋到1943年夏,我休学一年,到昆明附近的县城中学教书,贴补一点生活费用。当时联大学生大多来自沦陷区,经济来源断绝,靠政府以“贷金”名义(实际上从无偿还一说。我从1938年武汉沦陷后去后方继续念高中,直到1946年大学毕业,食宿全靠国民党政府以“贷金”名义供给,“贷金”这一措施挽救了一代青年,应该向它致谢!)维持最低生活,所以很多同学都在外面“兼差”:有的当家庭教师,叫作“教家馆”;有的当中小学教员;听说还有一种“差事”,即每到中午12点就去市中心的近日楼上敲钟,向全市报时。“兼差”只能利用课余时间,很多同学在外面“兼差”到深夜,归来后还伴着一盏油灯,复习功课或读些课外读物,第二天清晨,照样“闻鸡起舞”,吃点稀饭加咸菜,便夹着书去图书馆。我在休学期间,着重学英语,想提高英语水平,我那时很想效法联大许多知名教授,将来出国留学,回国当教授。由于教中学赚了一点钱,便约了经济系一位原中学老同学陈才昌,请英语系的老师王佐良先生为我俩补习英语,每月给王先生一点报酬。王先生是教我“大一英文”课的老师,英语水平很好(后来也是著名文学家),他似乎对报酬之低毫不在意,逐字逐句地、耐心地给我们讲解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英文原文,还要求我们背诵其中一些段落。我从《哈姆雷特》中学习到的,不仅是语言,更多的是其中的人生哲理。我特别爱背诵其中的一句名言:“To be or not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我很服膺这句话,哲学最终其实就是讲一个“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我在《北京大学教授推荐:我最喜爱的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中,列了我最喜爱的十本书,其中就有《哈姆雷特》。
1943年秋,我因不满经济系一些课程中的“生意经”而转入社会系。念社会系的一年中,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英语的学习上。“大二英文”课的老师是李斌宁先生,他当时是讲师,后来也是著名文学家。李先生英语水平高,对我们要求严,批改作业也很认真,对提高我的英语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还自学阅读了易卜生的好几种英文版剧本。为了学口语,我和另一位同学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附近的一个小教堂——文林堂去“做礼拜”,从牧师那里学口语。我的那位同学也有志学西学,两人一致认为,不学好英语,很难学好西学。社会系的“人口调查”之类的课程,特别其中一门课是老师带领我们去妓院搞调查,令我厌烦。正好这一年选修了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这是一个转机,我在“望尽天涯路”的迷惘中,终于追寻到了一条终生以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