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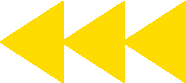
哲学是人类全部意识形式中最具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式。它的这种特性,往往容易使人以为哲学家可以撇开世界,只是咀嚼自我,单纯以自我为对象,因而哲学只不过是哲学家的自我意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全部哲学就只有一个字——人,全部哲学史和哲学体系的变化也都将成为自我意识的更替。在纯哲学思维范围内思考哲学,是很难弄清哲学的本质的。
人所研究的世界是人所面对的世界,是有人的世界,是不能离开人的世界。这当然对。正如我们说,凡认识的对象都处在人的认识范围之内,人不可能在认识之外去认识对象一样,认识之外的认识对象是逻辑矛盾。可我们绝不能说,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是人与世界的唯一的、绝对的、永恒的关系,承认人的认识范围之外的世界就是形而上学,就是拜物教。世界是全体,世界在实践过程中进入人的实践和认识范围内的是极其有限的一部分,世界永远留下一个无穷的世界等待人们去实践去认识。因此,承认自在世界的客观性和不可穷尽性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前提。如果我们的哲学只在已知世界里打圈圈,把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作为人与世界的唯一关系,就从根本上抽去了辩证唯物主义借以立足的基础,截断了人的实践和认识的来路与进路,人也就被困死在认识与被认识关系的范围内。
而且就人与世界的认识与被认识关系来说,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不能违背的。不错,人是按照人的方式去认识世界的。人的实践活动、人的感性和理性、人感知对象和在理性中把握对象的方式都具有人的特点。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人在对象中看到的只是人自身,或者说人通过世界认识的只是人类自己,因而哲学的本质就是人对自己的认识。这个结论无论对科学、对常识、对人的实践活动都是不利的。
人把自身的特点反射到自然界,在人类的幼年时期是有的,如人从万物有灵论中看到是人从自己推论到万物,或从上帝的万能和智慧的本性中看到是人把自己的本性化为上帝。而且在一定范围内,人通过自己对象性的存在物来直观自身是可以的。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在艺术创作中,人通过自己的活动结果返观人类自身,可以看到人的创造能力、特定时期的生产水平和审美意境。但不能把这种特定状况概括为普遍的哲学命题,即人对对象世界的认识就是人对人自身的认识,人通过对象不是发现对象自身的规律而是发现人自身。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是对象世界本身的对象,正如世界的辩证运动是对象自身的辩证运动一样。任何称得上是具有客观内容的哲学认识都是对对象世界(当然也包括对人自身的认识,当人被当成认识对象时,对研究者来说同样具有客观实在性)的认识。
哲学命题是具有普遍性的命题。如果哲学家从世界中看到的是人自身,世界只是人认识自己的中介物,是一面认识自我的镜子,那么为什么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的研究不是对自我的研究呢?人为自然立法的观点过去有过现在仍然有,全部自然科学证明自然规律是世界本身的规律,自然科学家是发现自然规律而不是为自然立法。同样,人在实践和日常生活中,人要达到预期成果而不被人认为是患有妄想妄听症,就一定要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直接接触的对象看成是对对象的认识,而不是看成我对自我的认识。对象世界作为认识自我的中介,只有在由实践对象化的存在中才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即使在这个范围内,人之所以能从对象化的世界中看到自身,也并不是因为对象世界是人的镜子而是因为人通过实践把自己的目的和意愿体现在自己的创造物上,即给自然界打上人类的烙印。人正是从自己打上的烙印中看到人自身的创造力的。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离开人在自然的附加物或创造物,人就不能从世界中认识人类自身。在当代,我们要正确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看到天人合一中某些合理的东西,但不能重复其中的唯心主义的和迷信的东西。当然,我的这种主张可以被看成是很肤浅的,没有哲学味道。不过全部科学、全部人的实践、全部人类的日常生活以及全部哲学史都无法接受人对世界的认识就是对自我的认识这种过于深奥的理论。我以为任何具有真理性的哲学都不应该与人的常识、与人的全部实践活动相违背。
不能认为哲学对世界的认识就只是对自我的认识,哲学不能说只是自我意识。当然,哲学家是用头脑思维的,因此任何哲学体系都必然表现为哲学家的一种哲学意识,问题是这种哲学意识是从哪里来的?是仅仅源自哲学对自我的意识、对人的意识,还是在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对世界的一种哲学的把握。马克思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上对这个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承认,哲学首先是通过人脑与世界相联系的,没有人和人的思维就没有哲学。可是,哲学不能归结为人的能思维着的头脑即哲学家的自我意识,“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
 。所以马克思的著名的众所周知的结论是“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所以马克思的著名的众所周知的结论是“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这并不是马克思一个人的意见,恩格斯也是这样认为的,他曾说过任何哲学都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看,就连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也是这样说的,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把哲学说成是被握在哲学思维中的时代。对哲学工作者来说,这似乎已经是了无新意,但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并不是马克思一个人的意见,恩格斯也是这样认为的,他曾说过任何哲学都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看,就连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也是这样说的,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把哲学说成是被握在哲学思维中的时代。对哲学工作者来说,这似乎已经是了无新意,但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哲学绝不能仅仅是哲学家的自我意识。黑格尔都不敢这样说,而是说是绝对观念的自我认识,因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囊括一切,把整个世界及其发展都包括在内。可青年黑格尔派片面强调自我意识,就显得单薄和力不胜任,把如此丰富的世界和多种多样的哲学思维都塞进人的自我意识就等于把人变为了上帝。无怪乎自我意识的理论曾经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猛烈抨击。
哲学史当然是哲学发展的历史,是哲学家的思想发展史。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看,那我们只是说了一个表面的现象,说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哲学有自己的历史,但这种历史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不是思想的自我运动,而是社会历史的作用。如果哲学就是哲学家的自我意识,哲学史是自我意识的历史,那么除了能满足思辨的欲望外,对哲学和哲学史的理解必将陷入误区。哲学不能归结为人对自身的认识,哲学史也不能归结为自我意识的历史。哲学史当然是哲学发展的历史,但又不能仅限于哲学自身。应该说哲学史中的“史”字,包括从社会历史运动角度来看哲学发展的意思。当年罗素写的著名的《西方哲学史》全名就是《西方哲学史及其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这个书名本身就表明了这种联系。所以哲学史不仅是哲学的历史,而且是当作历史运动的一个侧面的哲学。不从历史的现实内容角度来看待哲学,把哲学说成是哲学家的自我意识,哲学家就变为不可理解的怪物,哲学史也变为毫无原由的自我意识更替的历史,哲学的内容及其变迁都将重新陷入不可理解之中。其实,从历史角度来看哲学就容易理解多了。懂得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就容易理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理解18、19世纪的德国,就容易理解康德、谢林、黑格尔。哲学的差别,内在地隐含着时代的差别,可这种时代的差别一旦化为哲学的差别,就肯定具有哲学的特点,即真正的哲学是以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面目出现的,它把一个时代所达到的科学和实践的智慧凝结其中。一部中国哲学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历史,一部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和政治史。西方哲学史同样如此。放开眼界,从整个历史过程来考察哲学家及其思想,探求何以如此的原因和根据,我们就可以看到,哲学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哲学家们从一个侧面对世界(或者是自然或者是社会或者是人自身)的把握。哲学认识只要它仍然是认识,它就是对对象的认识。这种对象可以包括自我但绝不能归结为自我。自我连同它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方式都是被制约的。人是在一定条件下认识的,条件达到什么水平认识就达到什么水平。这对科学认识是真理,对于哲学认识也是真理,只是这种被制约的范围、程度、形式各有特点而已。绝不能认为实证科学是对世界的认识而哲学只是一种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