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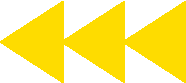
第二国际的一些非常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功绩赫赫,在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表现非凡,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方面却每每存在不足,或者说,哲学问题成为他们的较薄弱的方面。如果从主观方面寻找原因,那就是“第二国际几乎所有的理论家和领导人的哲学水平,对哲学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认识水平,都是非常之低”
 。考茨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考茨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考茨基在背叛马克思主义以前,曾写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著作,其中有《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解说》(1892年)、《土地革命》(1899年),列宁认为这些著作“将永远是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但考茨基的深刻见解主要是在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至于在哲学领域,却显露出与他的才华不相称的肤浅来。他在1901年致普列汉诺夫的信中作了坦率的表白:“哲学从来不是我的专长。”
。但考茨基的深刻见解主要是在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至于在哲学领域,却显露出与他的才华不相称的肤浅来。他在1901年致普列汉诺夫的信中作了坦率的表白:“哲学从来不是我的专长。”

1909年,《斗争杂志》登载了考茨基两年前给一个俄国工人的回信。信中说:“您问道:马赫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要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怎样理解。我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验科学,即一种特殊的社会观。……马克思没有宣布
任何哲学
,而是宣布了所有哲学的终结。”
 在1901年致普列汉诺夫的信中他也说过:“我想即使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新康德主义者,他也可以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和经济学说。”
在1901年致普列汉诺夫的信中他也说过:“我想即使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新康德主义者,他也可以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和经济学说。”
 这无异于在说,马克思没有自己的哲学,马克思只是一个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而不是哲学家!这种近乎荒唐的判断不能被简单地归咎为出于对马克思学说的无知。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木箱,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
这无异于在说,马克思没有自己的哲学,马克思只是一个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而不是哲学家!这种近乎荒唐的判断不能被简单地归咎为出于对马克思学说的无知。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木箱,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
 。事实上,考茨基曾在许多著作中都肯定和阐释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但他并不把它们理解成一种哲学。他把唯物史观仅仅理解成一种社会学,把辩证法仅仅理解成一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不依赖某种哲学,“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与一种唯物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的。它可以与任何一种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的世界观合得拢,或者至少与它不发生合不拢的矛盾。不管这种历史观把自己称为唯物主义的,或是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宁愿采用实在论或一元论、实证主义或感觉主义、经验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等名称的,都没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考茨基曾在许多著作中都肯定和阐释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但他并不把它们理解成一种哲学。他把唯物史观仅仅理解成一种社会学,把辩证法仅仅理解成一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不依赖某种哲学,“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与一种唯物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的。它可以与任何一种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的世界观合得拢,或者至少与它不发生合不拢的矛盾。不管这种历史观把自己称为唯物主义的,或是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宁愿采用实在论或一元论、实证主义或感觉主义、经验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等名称的,都没有什么关系”
 ,“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可以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合得拢,而且可以与许多别的哲学合得拢”
,“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可以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合得拢,而且可以与许多别的哲学合得拢”
 。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受到了两方面的曲解。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而遭到否定。唯物史观被当作一种实证科学——社会学。这种把唯物史观实证化的倾向在第二国际时期较为普遍。另一方面是否定了马克思历史观的哲学唯物主义基础。既然随便什么哲学世界观都能同马克思的历史观“合得拢”,那么自然就可以用种种哲学来解释马克思学说的基础,或“补充”马克思的历史观。这样一种逻辑不仅表现在考茨基的身上,而且表现在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上。
。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受到了两方面的曲解。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而遭到否定。唯物史观被当作一种实证科学——社会学。这种把唯物史观实证化的倾向在第二国际时期较为普遍。另一方面是否定了马克思历史观的哲学唯物主义基础。既然随便什么哲学世界观都能同马克思的历史观“合得拢”,那么自然就可以用种种哲学来解释马克思学说的基础,或“补充”马克思的历史观。这样一种逻辑不仅表现在考茨基的身上,而且表现在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上。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上,被普列汉诺夫称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几乎是唯一的)懂哲学的一个”的梅林也存在着肤浅和片面的倾向。他没有摆脱当时在第二国际流行的一种观点:把哲学仅仅看作一种意识形态。不过他没有像考茨基那样简单地认为马克思宣布终结了一切哲学,而是认为,哲学仅仅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思想形式,随着阶级斗争的消灭,哲学也将消失。梅林在把唯物史观理解成一种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刻板的公式,并运用它来分析历史方面,曾受到过恩格斯的高度赞扬,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认识,特别是对唯物史观的哲学性质的认识却存在模糊乃至错误之处。他在《康德、狄慈根、马赫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任何哲学割断了联系,但是却把哲学的历史成果(历史发展思想)带进了唯物主义,即把这一思想首先带进历史领域,而不是自然领域,其主观原因在于他们俩都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历史学家。这种观点把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变革仅仅局限于哲学历史观,而把哲学自然观排除在外。换言之,梅林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观上仍旧同旧唯物主义保持同一水平。因而他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只不过把唯物主义运用到历史领域从而扩大和加深了这一观点;简单明了地说,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是机械唯物主义者,就像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一样。”
 在辩证法问题上,考茨基和梅林都把辩证法当作一种考察社会历史的方法,或“历史的辩证法”。这里所说的历史,显然是不包括自然界在内的。
在辩证法问题上,考茨基和梅林都把辩证法当作一种考察社会历史的方法,或“历史的辩证法”。这里所说的历史,显然是不包括自然界在内的。
无论是考茨基还是梅林的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第二国际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普遍倾向,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或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而哲学则无足轻重。这就涉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体系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诚然,撇开术语上的混乱和误解,可以说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一般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甚至作了较好的发挥。但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缺乏全面理解,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的认识也颇为混乱,这就难免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的内在联系缺乏完整的认识。当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盛行一时,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便被这种时髦所打动,并以此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可以相容的,这就不足为怪了。当然,即使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完整的认识,但只要能真正领会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那么对新康德主义的错误也会察觉的。例如梅林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就明确地批判过新康德主义,尽管这种批判的哲学高度不够。
包括考茨基、梅林在内的第二国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否认唯物史观有一个一般的哲学前提,或一般的唯物主义前提。从第二国际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引起了较多的争议。马克思一生致力于社会历史领域问题的研究,因而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体系阐述得较多,但这并未影响他对关于包括自然和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的一般唯物主义见解作了全面的表述。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它是对社会历史一般规律的哲学把握。而这种哲学把握的基础是以实践观点为核心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无论是马克思的自然观还是历史观,都贯穿了承认自然存在的先在性和包括社会存在在内的物质存在的客观实在性及发展的辩证性,同时也贯穿了以实践活动为媒介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观点。正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然观和历史观上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变革的意义所在。如果丢掉唯物主义这一哲学前提,或者把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简单等同于旧唯物主义,那么就既难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为何冠之以“唯物主义”,也难以理解唯物史观在解决自然与社会统一问题上的科学性。
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能够比较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是普列汉诺夫。当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特别是在俄国泛滥之时,“他是当时唯一能够和那些主要是新康德主义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在专门的哲学方面(不单纯在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方面)进行论战的理论家”
 。这是由于他超越了一般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狭隘理解。他不仅一般地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的历史观,而且关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说明。考茨基、梅林等主要是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哲学的区别,而普列汉诺夫则强调了一般的唯物主义哲学。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是人类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是最伟大的革命。”
。这是由于他超越了一般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狭隘理解。他不仅一般地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的历史观,而且关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说明。考茨基、梅林等主要是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哲学的区别,而普列汉诺夫则强调了一般的唯物主义哲学。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是人类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是最伟大的革命。”
 普列汉诺夫对一般唯物主义哲学的说明集中表现在他的物质定义上:“我们所说的物质的对象(物体),就是那些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对象,这些对象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唤起我们一定的
感觉
,而这些感觉反过来又成为我们关于外部世界,即关于这些物质对象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观念的基础。”
普列汉诺夫对一般唯物主义哲学的说明集中表现在他的物质定义上:“我们所说的物质的对象(物体),就是那些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对象,这些对象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唤起我们一定的
感觉
,而这些感觉反过来又成为我们关于外部世界,即关于这些物质对象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观念的基础。”
 当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普列汉诺夫的这一定义并非十全十美,而且没有贯穿实践的观点。但在普列汉诺夫的整个哲学思想中,仍然是领会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例如他明确说:“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
当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普列汉诺夫的这一定义并非十全十美,而且没有贯穿实践的观点。但在普列汉诺夫的整个哲学思想中,仍然是领会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例如他明确说:“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普列汉诺夫首次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并认为用“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
 。值得注意的是,普列汉诺夫所使用的这一术语同后来人们一般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如目前流行的教科书把它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起来使用)的内涵不同。他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不是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使用的,而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历史。无论是在自然界或在历史方面,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辩证的’。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历史,所以恩格斯有时将它叫做历史的。”
。值得注意的是,普列汉诺夫所使用的这一术语同后来人们一般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如目前流行的教科书把它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起来使用)的内涵不同。他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不是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使用的,而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历史。无论是在自然界或在历史方面,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辩证的’。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历史,所以恩格斯有时将它叫做历史的。”
 这清楚地表明,普列汉诺夫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方面。他明确表示了对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看法的否定态度。“难道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整个世界观吗?当然不是!它只是世界观的一部分。”
这清楚地表明,普列汉诺夫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方面。他明确表示了对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看法的否定态度。“难道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整个世界观吗?当然不是!它只是世界观的一部分。”

普列汉诺夫的上述见解比起考茨基、梅林等人来,无疑要全面和深刻得多。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但是它在反对用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