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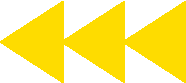
在第二国际时期,最富有戏剧性色彩的人物莫过于伯恩施坦。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在第二国际前期,曾是名噪一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并担任过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当他于1896—1898年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后,顿时在第二国际内部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他将自己关于对马克思主义“修正”的观点系统整理成书,于1899年2月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列宁将此书斥之为“马克思主义内部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的宣言”
 ,并认为在这本书中,“曾经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
,并认为在这本书中,“曾经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
 。
。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理论上的折射。这种“修正”,既非像有的人简单指责的那样是“精神错乱”的结果,也不尽是纯粹在书斋里杜撰出来的东西。当资本主义的命运和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策略等问题在新形势下更尖锐地提出来的时候,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对此作出回答。伯恩施坦的观点最具有欺骗性的是他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帜。在他看来,新时代已来临,必须审视社会民主党用来迎接这个时代的“精神武器”。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的首要任务就是克服空想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前提——教条主义。在他看来,那种曾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过的自命为“替未来的餐馆开的菜单”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对未来社会组织作详细描绘、设计的空想社会主义已经绝迹,但另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却还存在。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假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飞跃”。伯恩施坦说:“他们画了一条界线:这边是资本主义社会,那边是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有系统的工作。”
 这些空想社会主义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口号来“装饰”。“即使是最科学的理论,如果对它的结论作出教条主义的解释,也会引导到空想主义。”
这些空想社会主义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口号来“装饰”。“即使是最科学的理论,如果对它的结论作出教条主义的解释,也会引导到空想主义。”
 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下,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理论作出了“新”的解释,并以此来论证他关于反对“崩溃论”和“暴力论”的观点。
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下,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理论作出了“新”的解释,并以此来论证他关于反对“崩溃论”和“暴力论”的观点。
伯恩施坦不仅同第二国际的“正统派”展开论战,而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批评,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据以建立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他们的历史观,而他们的历史观的核心是只强调历史的必然性,把历史的一切过程、因素归结为机械的物质运动的必然性。伯恩施坦专门分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认为它存在着严重的机械论倾向。“‘意识’和‘存在’被如此截然地对立起来,以致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整个说来,人的意识和意愿表现为非常从属于物质运动的因素。”
 他还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同样有“带有宿命论音调的句子”。据此,伯恩施坦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进行“修正”,即主张不应局限于马克思关于历史观的论述,而应充分考虑到当代社会中个人和整个民族使自己生活的愈来愈大的部分摆脱了无须他们的意志或者违反他们的意志实现的必然性的影响,并用这种观点来“扩充”唯物史观,而这种经过“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不认为各民族生活的经济基础对各民族生活的形态具有无条件的决定性影响。
他还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同样有“带有宿命论音调的句子”。据此,伯恩施坦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进行“修正”,即主张不应局限于马克思关于历史观的论述,而应充分考虑到当代社会中个人和整个民族使自己生活的愈来愈大的部分摆脱了无须他们的意志或者违反他们的意志实现的必然性的影响,并用这种观点来“扩充”唯物史观,而这种经过“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不认为各民族生活的经济基础对各民族生活的形态具有无条件的决定性影响。
伯恩施坦所关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辩证法问题。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最致命之点”
 。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时,受到了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残余的“蒙骗”。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一生都没有彻底摆脱这一残余。黑格尔的矛盾逻辑会使人们不知不觉地进入“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一旦根据这些原理来演绎地预测发展,那末任意构想的危险也就已经开始出现。其发展被论及的事物愈复杂,这种危险就愈大。”
。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时,受到了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残余的“蒙骗”。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一生都没有彻底摆脱这一残余。黑格尔的矛盾逻辑会使人们不知不觉地进入“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一旦根据这些原理来演绎地预测发展,那末任意构想的危险也就已经开始出现。其发展被论及的事物愈复杂,这种危险就愈大。”
 由此推论,“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
由此推论,“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
 。因而可以得出结论,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辩证法来考察政治斗争的专著,以及他们关于以经验对于暴力的决定性影响为出发点的理论,都应从与他们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考察。
。因而可以得出结论,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辩证法来考察政治斗争的专著,以及他们关于以经验对于暴力的决定性影响为出发点的理论,都应从与他们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考察。
伯恩施坦的上述观点,表明了他在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根据的理解方面,试图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历史必然性,特别是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性的观点,而突出历史过程中的主观因素。伯恩施坦附和了“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因为这一口号从认识论的角度“直接启发”了他。在他看来,康德尽管是先验的唯心主义者,但事实上却是比许多唯物主义者还要严格得多的实在论者。康德不奢求经验世界以外的东西。而在经验世界里,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关注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就是利益、认识和道德意识这三种观念力量。在这三种“观念力量”中,要特别注意道德意识。正义等道德力量是一个能起创造作用的力量,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是极强大的动力。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解释,旨在反对把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建立在社会经济运动的必然性基础之上,而主张以伦理要求或伦理冲动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源。这显然同马克思主义的本意相去甚远。
伯恩施坦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颇多微词,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科学性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而“剩余价值”也不过是“单纯的公式”,是“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这种价值学说“与哥森—杰冯斯—柏姆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并无不同。两者都以现实的关系为基础,但是两者都建筑在抽象上面”
 。“劳动价值绝对不过是一把钥匙……但是从某一点开始这一钥匙就失灵了,因此成了对于马克思的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致命的东西。”因而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是“不能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论证的”
。“劳动价值绝对不过是一把钥匙……但是从某一点开始这一钥匙就失灵了,因此成了对于马克思的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致命的东西。”因而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是“不能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论证的”
 。
。
对于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的序言中所作的马克思是根据日益实现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来论证他的共产主义要求的这一论断,伯恩施坦也持反对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理论不符合现实。他说:“如果社会是按照社会主义学说迄今所设想的那样构成或者发展下来的,那末经济崩溃当然只能是一个很短时期内就要发生的问题了。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情况恰好不是这样。社会结构同从前比起来远没有简单化,不如说它无论就收入水平还是就职业活动来说,都高度地分极和分化了。”
 他从两方面说明社会各阶级的收入状况不会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一方面,工人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的绝大多数并不为资产阶级所占有,纵使资本家比工人的肚子还要大十倍,有着多于实际所有的十倍的仆人,但他们的消费所用只不过是剩余产品这一“天平上的一根羽毛”而已。那些剩余产品如不是以种种方式流入无产阶级手中,那么它们一定正好是被其他阶级拿去了。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的分散导致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的出现,导致了有产者的人数绝对地而且相对地增加了。概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在逐渐消失。
他从两方面说明社会各阶级的收入状况不会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一方面,工人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的绝大多数并不为资产阶级所占有,纵使资本家比工人的肚子还要大十倍,有着多于实际所有的十倍的仆人,但他们的消费所用只不过是剩余产品这一“天平上的一根羽毛”而已。那些剩余产品如不是以种种方式流入无产阶级手中,那么它们一定正好是被其他阶级拿去了。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的分散导致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的出现,导致了有产者的人数绝对地而且相对地增加了。概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在逐渐消失。
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消除了它的尖锐对立。“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所以必须抛弃一切把它当成巨大社会变革的前导的那种冥想。”
 资本垄断的出现使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消除了竞争。世界市场的扩大,通讯和交通运输的改进,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和卡特尔的兴起,以至于至少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像以前类型的经济危机。伯恩施坦断言,如果认为普遍危机应当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那么它必须在现在或者在最近的将来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否则它的不可避免性的证据就浮在抽象思辨的空中了。
资本垄断的出现使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消除了竞争。世界市场的扩大,通讯和交通运输的改进,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和卡特尔的兴起,以至于至少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像以前类型的经济危机。伯恩施坦断言,如果认为普遍危机应当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那么它必须在现在或者在最近的将来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否则它的不可避免性的证据就浮在抽象思辨的空中了。
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修正”之后,伯恩施坦又进一步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即科学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激进的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达到了同布朗基主义十分相似的学说。”
 “《共产党宣言》的革命的行动纲领是彻头彻尾布朗基主义的。”
“《共产党宣言》的革命的行动纲领是彻头彻尾布朗基主义的。”
 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学说,不过是崇尚暴力斗争的布朗基主义的翻版,因为它过高估计了革命暴力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力。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经济为出发点而把暴力崇拜发挥到顶点的理论。对布朗基主义的批判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其中首先是它的辩证法的自我批判。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句今天已经完全过时,以致只有把它的实际意义去掉并且赋予它随便什么削弱了的意义,才能使它和现实相一致。阶级专政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一种政治上的返祖现象。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应热衷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而应关注普选权等这样的民主权利。
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学说,不过是崇尚暴力斗争的布朗基主义的翻版,因为它过高估计了革命暴力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力。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经济为出发点而把暴力崇拜发挥到顶点的理论。对布朗基主义的批判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其中首先是它的辩证法的自我批判。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句今天已经完全过时,以致只有把它的实际意义去掉并且赋予它随便什么削弱了的意义,才能使它和现实相一致。阶级专政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一种政治上的返祖现象。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应热衷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而应关注普选权等这样的民主权利。
伯恩施坦把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建构比作“在一个现成的脚手架的框框里建造一座巨大的建筑物”
 。当辩证法这个脚手架限制了建筑物,从而使建筑物不能自由发展时,马克思不去拆毁脚手架,却不惜牺牲比例而在建筑物上作了改变,从而使建筑物更加从属于脚手架。这就表明马克思这位“伟大的科学天才原来到底是一种教义的俘虏”
。当辩证法这个脚手架限制了建筑物,从而使建筑物不能自由发展时,马克思不去拆毁脚手架,却不惜牺牲比例而在建筑物上作了改变,从而使建筑物更加从属于脚手架。这就表明马克思这位“伟大的科学天才原来到底是一种教义的俘虏”
 。于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伯恩施坦眼里就成了一种削足适履的产物。那么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理论应该是怎样的呢?他说:“我实际上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要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不如说我认为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于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伯恩施坦眼里就成了一种削足适履的产物。那么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理论应该是怎样的呢?他说:“我实际上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要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不如说我认为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他还认为,社会主义者所应关心的不是比较遥远的将来,而是现在和最近的将来要做些什么。争取民主和造成政治的和经济的民主机关,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自由制度同以往的各种封建主义制度不同,具有伸缩性,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为此需要组织和积极的行动,而不需要革命的专政。消费合作社是一种有生命力的社会机体,是克服剥削的一种手段,工人阶级依靠它就能夺取社会财富的很大一部分,不必诉诸暴力。正是基于这些论点,伯恩施坦提出了他的最著名的公式:“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所谓运动,我所指的既是社会的总运动,即社会进步,也是为促成这一进步而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他还认为,社会主义者所应关心的不是比较遥远的将来,而是现在和最近的将来要做些什么。争取民主和造成政治的和经济的民主机关,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自由制度同以往的各种封建主义制度不同,具有伸缩性,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为此需要组织和积极的行动,而不需要革命的专政。消费合作社是一种有生命力的社会机体,是克服剥削的一种手段,工人阶级依靠它就能夺取社会财富的很大一部分,不必诉诸暴力。正是基于这些论点,伯恩施坦提出了他的最著名的公式:“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所谓运动,我所指的既是社会的总运动,即社会进步,也是为促成这一进步而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这的确是“坦白”。“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比千言万语更能表达伯恩施坦背叛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从伯恩施坦的论述中不难看到,他劝告人们不要期待也不必期待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即刻崩溃;无产阶级政党目前和今后长时期应当做的工作,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和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按民主的精神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人们不必为最终目的而奋斗,社会愈富足,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愈容易而且愈有把握。总而言之,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完全可能和平进入社会主义。
这的确是“坦白”。“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比千言万语更能表达伯恩施坦背叛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从伯恩施坦的论述中不难看到,他劝告人们不要期待也不必期待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即刻崩溃;无产阶级政党目前和今后长时期应当做的工作,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和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按民主的精神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人们不必为最终目的而奋斗,社会愈富足,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愈容易而且愈有把握。总而言之,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完全可能和平进入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从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修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如果承认他的“修正”是正确的,那么无疑是宣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陷入全面的危机;如果简单地宣布他是在发一通“热昏的胡话”,那么无疑又是在回避问题,无助于人们认真解决现实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有必要结合第二国际内部的正统派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来进一步分析伯恩施坦等人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