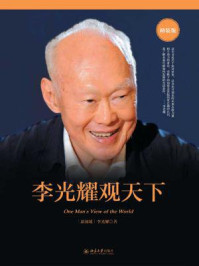1946年5月~1948年11月在东京举行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积累了大量的日本侵略战争暴行资料,特别是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和战争暴行资料,值得好好发掘利用。
东京审判的史料内容非常丰富,具有重要价值。东京审判的史料大都是控辩方精心搜集、整理的证据资料,而这些资料大都是经过了法庭严格审查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的重要性和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东京审判研究本身不可或缺的,而且可以广泛应用到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史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对日本战争暴行的揭露上。在这方面,中国学界将其用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就很成功。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的审理资料,成为认定日本大屠杀罪行的核心证据和依据,对中国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争得国际话语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南京大屠杀研究积极使用东京审判的史料仅仅是一个事例,在日本战争暴行整体研究上,对东京审判资料的使用还远远不够,还有大量可利用的空间。希望国内外研究者下大力气,进一步挖掘、利用东京审判的系列史料,推进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研究。
1946年5月3日,反法西斯盟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判东条英机等所有被告有罪并分别被判处绞刑或徒刑,这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这场历时两年多的国际大审判不仅是对被起诉战犯的审判,也是对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政策和罪行的总清算。
东京审判不仅惩罚了日本主要战争罪犯,而且为日本近代历史研究特别是对外侵略战争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宝贵资料。为参加东京审判,检察方和被告及辩护方都准备了大量的资料。记录法庭审理全过程的英文庭审记录达48412页,洋洋千万字。2013年,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影印出版了这部庭审记录,长达80卷。审判期间,控辩双方共提供书面证据4336件,仅法庭受理的证据资料经中国整理出版的就达50卷,约3万页。法庭判决书长达1213页,光宣读就整整用去了一周时间。而出庭作证的证人也达到12个国家的419人,均创世界审判史之最。上述各类审判资料基本概括了日本自1920年代末到1945年战败投降的历史,特别是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揭露了日本竭力隐瞒的一系列战争暴行,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历史资料库。
由于战乱和政治因素影响,中国几乎没有保存东京审判的资料,公开出版的仅有一部删节版的法庭判决书。直到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历史实事求是路线的确立,中国对东京审判的研究才正式开始。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国家对东京审判研究的重视,大批海外的东京审判资料开始被引入并出版发行,已经形成规模庞大的东京审判系列资料,为东京审判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这些资料主要有:
(1)《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8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2)《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5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3)《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7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4)《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报刊资料选编》(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5)《东京审判历史图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6)《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英文版)》(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7)《横滨审判文献汇编》(10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8)《马尼拉审判文献汇编》(5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其中,(1)~(6)为甲级战犯资料,(7)~(8)是乙级战犯资料,史料价值都很大。
侵华战争是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主要部分,在14年战争期间,大半个中国领土被侵占,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遭受日军屠杀,财产损失无数。因此,日本侵华战争在东京审判中分量最重,是东京审判的主要审理对象。东京审判追究了日军犯下的几起重大的屠杀罪行,其中最大的一起就是发生在1937年底的南京大屠杀。国际检察局在中国方面的支持帮助下,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组织了有力的证人和证据材料,促使法庭最终严惩了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以及相关责任人广田弘毅等罪犯。
在东京审判的准备阶段,负责起诉的国际检察局除已掌握的战时资料、证据外,还派人来华,实地进行深入的调查取证。1946年3~4月,美国检察官萨顿、莫罗和数名美国检察人员以及首席检察官基南分批赴华,对日本的侵华罪行进行实地调查取证。来华时,他们给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罪证纲要》,还提出了67项具体的调查项目,南京大屠杀是其调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他们在中国政府有关人员的陪同下,走访了上海、北京、重庆、南京,获得了重要的第一手日军暴行资料。毫无疑问,中方在提供人证、资料、协助调查方面,对检察方起诉南京大屠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中国政府有关人员的陪同下,走访了上海、北京、重庆、南京,获得了重要的第一手日军暴行资料。毫无疑问,中方在提供人证、资料、协助调查方面,对检察方起诉南京大屠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中国方面外,实际上,由于南京大屠杀战时就在美国广为人知,又有数名美国人目睹了大屠杀的惨状,美方已掌握相当可靠的证据,南京大屠杀的首要责任者松井石根早就进入了美国的甲级战犯嫌疑人名单。1945年11月19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GHQ)下令逮捕甲级战争嫌疑人松井石根,并将其关押在巢鸭监狱。
在赴中国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国际检察局还对东京在押的日本战犯嫌疑人进行了讯问调查,获取了有价值的证据。检察人员先后对南京大屠杀的首要责任人松井石根、武藤章以及当事人外交官福田笃泰、福井淳以及知情人前陆军省军务局长田中隆吉(中将)进行了讯问,获得了具有重要价值的证据资料。尽管松井石根企图否认或蒙混过关,但其都无法否认暴行的存在。而田中隆吉的交代,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和松井石根的责任。我们可以看一段其中的讯问记录:
(检察人员)问:将军,关于南京事件,请告诉我们你知道些什么或听说过什么,松井大将作为司令官与此有些怎样的关系?
(田中)答:在从上海到南京进行的交战中,特别是在被征服后的南京,尽管没有松井大将的命令,但他的部下犯下了在我看来是世界史上最残酷的暴行。
问:你认为,松井大将即使没有下命令或指示,也知道出现了怎样的事态。
答:他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肯定完全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曾经对我讲过“为了制止该事态,该做的我都做了。但仅我的力量于事无补。为此,我必须承担这一责任”。
问:你知道松井大将是否处罚过一些责任者。
答:他处罚过几个有关人。但根据我的判断,这些处罚是轻微的。“已经处罚过了”——具有敷衍搪塞的性质。
问:陆军对南京的残暴行为进行过调查吗?
答:是的。调查是由宪兵队进行的,我收到过他们提供的报告书。
问:将军,根据调查的结果,是否召开了军法会议,或者进行了其他的处罚。
答:我们是想把他们付诸军法会议的,但因反对的势力很强,最后此事不了了之。后来第十六师团长被罢免。

毫无疑问,田中的讯问证词为检察方追究松井石根的责任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东京审判开始后,检察方动用大量的证人、证据,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日军犯下屠杀、强奸、抢劫、放火等惨绝人寰的罪行,令世界震惊,也令日本人民瞠目。就连坐在被告席上的战犯重光葵,目睹了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审理,也在其日记中写道:日军的“丑态令人掩耳,日本魂腐烂了吗?”证人证明日军暴行“残酷之极”,“令吾人掩面,作为日本人真应愧死”,“呜呼圣战”。

在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审理中,面对检方的指控,南京大屠杀的首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其辩护人为了逃避责任和减轻处罚,采取了“两个辩解战略”。第一是主动出击,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如大屠杀本身都不存在,也就不应负大屠杀的责任。第二是屠杀也许存在,我不知道或听说过一点儿,但没有权限和机会介入,所以也不应由我负责。
 尽管以松井石根为首的责任人百般抵赖,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证据确凿,无法否认。
尽管以松井石根为首的责任人百般抵赖,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证据确凿,无法否认。
在经过了法庭马拉松式的审理之后,1948年2月10日开始,以首席检察官基南为首,检察方在法庭上做总结陈述。2月18~19日,检察官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总结陈述,提出了《1937~1945年期间日本人在中国所犯残暴行为证据概述》文件。该文件对法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审理进行了梳理,对检察方的起诉内容和证据进行了概括总结。检察方的这一总结陈述及提出的文件,对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定性和判决具有重要意义。11月4日,法庭开始宣判。鉴于南京大屠杀事实确凿,罪恶巨大,法庭判决书在第八章“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中专门设节对南京大屠杀做出判决,比较详细地指出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屠杀、掠夺、强奸等骇人听闻的暴行和屠杀20万人以上平民和俘虏的事实。
对于被告松井石根,法庭最终认定其作为进攻和驻扎南京的日军最高负责人,对南京大屠杀知情却不认真予以制止,是一种渎职犯罪行为。判决书指出:“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制他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怠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法庭最后判处松井石根绞刑。另一名对南京大屠杀犯有不作为罪行的被告广田弘毅(时任外务大臣)数罪并罚,也被判处绞刑。这是人类正义得到伸张的体现,也是对南京大屠杀中惨遭杀害的无数亡灵的祭奠。
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的审理和判决,把日军在华所犯罪行公之于天下,揭露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罪恶行径,惩罚了犯罪,教育了人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东京审判所涉及的日本战争暴行的资料非常多,除侵略、大屠杀外,对日本在战争期间在华制毒贩毒的罪行也进行了揭露。
对于日本在中国建立制毒贩毒体系,进行大规模的对华毒化战争,东京审判的资料也多有揭露,如起诉书、庭审记录和检方所提证据以及战犯的讯问记录等。在起诉书中,检方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起诉日本政府和军方有组织地利用鸦片“削弱人民的抗战意志”,其收入成为“准备及进行侵略战争的财源,有的用于日本政府在占领区扶植的诸多傀儡政权”的罪行。

5月3日法庭开庭后,基南检察长即在“开场陈述”中提到日本使用鸦片用于战争的罪行。在其后的检方提证阶段,检方提供了大量的日本在中国利用鸦片等毒品毒害中国人民的证据。如8月15日检方在提证陈述中指出:“作为他们征服中国计划的一部分,日本领导者把鸦片和其他麻醉品作为准备和扩大侵略中国的武器。”“随着日本武力侵略的扩大,不仅在日租界,而且在中国所有地区,日本的军方和各种民间机构,都大肆进行鸦片等毒品交易。”陈述指出,证据显示,从伪满洲国建立开始,到日本侵略深入华北、华中、华南后,日本操纵的各地傀儡政权废除了中国的禁毒法令,建立鸦片专卖垄断。鸦片专卖表面上是控制鸦片泛滥,实际上是借专卖制度垄断鸦片和其他麻醉品交易。日本这样做的目的有二:“(1)削弱中国民众的体力,以此削弱他们的抗战意志力。(2)为日本军事和经济侵略提供巨大的资金来源。”
 也就是说,这是一项“以毒养战”的肮脏国策。
也就是说,这是一项“以毒养战”的肮脏国策。
制毒贩毒是违反国际法和人道的无耻的行为。所以,日本政府和军方都竭力掩盖,尤其是在战败投降的时候,将相关的政策文件都竭力销毁,不留痕迹。由此,参与这些活动的人证和证言就显得非常重要。作为参与日本贩卖鸦片活动的重要人物、上海特务机构“里见机关”的头目里见甫,他的口供书以及在法庭上的证言,对揭露日本政府和军部操纵、参与贩毒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证据。里见在口供书中承认,自己奉日本中国派遣军特务部和日本政府“兴亚院”之命,组织“宏济善堂”,专门从事贩卖、销售鸦片的活动。
1937年9月或10月,我作为新闻记者到了上海,在这之前我在天津。1938年1月或2月,楠本实隆中佐问我能不能为特务部大批贩卖鸦片,他说这些鸦片正在从波斯运来的途中。
特务部是中国日军派遣军参谋部的一个部,其职责是处理日军占领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诸问题。
这一大批鸦片1938年春运抵上海,存放在军用码头的一个仓库里,码头和仓库都派有卫兵。波斯鸦片放在160英镑的箱子也就是1920两(原文如此)的箱子内。
波斯来的鸦片抵达后,我开始少量地向中国商人出售。当我从中国商人那里接到订货后,就派部下去特务部。特务部就命令仓库向我的部下发放多少量的鸦片。从仓库取出后,转交给那些商人。
时间和地点都是预先商定的,商人在交货时付款。我把贩卖鸦片得来的钱以我的名义存入台湾银行,一个月向楠本中佐报告一两次。
我贩卖鸦片的价格,由特务部的军官和我协商决定。我告诉他们当时的市价,他们就我的贩卖价格发出指示。这个程序得到了特务部承认。
根据特务部的指令,我从以我的名义储存的款中向三井物产会社支付原价,再扣除我自身的各种费用,余款交付特务部。
从波斯来的鸦片到货起,到1939年3月维新政府成立,我把鸦片卖给中国商人,按上述方法支付款项。
维新政府设立的同时,上海的特务部解散了。但又设立了兴亚院的支部……楠本中佐担任兴亚院上海支部的副支部长。兴亚院经济部负责鸦片和麻醉品。兴亚院决定把办理鸦片转交给维新政府,维新政府在内政部下设立了戒烟总局。
为了分配鸦片,组织了宏济善堂。它是一个商业会社,其股东是8个大鸦片商。我受戒烟总局局长朱曜之托,坐上了宏济善堂副董事长(副理事长)的交椅,宏济善堂没有董事长。宏济善堂的契约及诸规定都是在与维新政府协商之后,由兴亚院起草的。经兴亚院承认,我接受并在副董事长的交椅上就座。

法庭审理过程中,检方证人奎尔在法庭作证时也证明日本军政勾结,在中国占领区贩毒的罪行。
萨顿检察官:日军占领前,在上海地区,公然买卖鸦片的情况,有还是没有?
奎尔证人:根本没有。因为……在严厉的法律下,上海的人们不愿冒着被处以非常严厉刑罚的危险……如果做这种买卖的话,有的会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
萨顿:日军占领以后,有关鸦片的状况,在上海地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奎尔:状况恶化了……1938年10月前后,日本官宪及傀儡政权的官吏之间,就有关设置鸦片局或转卖机关的问题,进行了交涉……交涉的事项之一,就是上海西部,设置两处鸦片吸食所……条件之一是这些鸦片吸食所每家应有20名鸦片贩卖者……1939年前后,在公共租界外,向人民贩卖鸦片的贩卖所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
萨顿:你知道宏济善堂吗?
奎尔:宏济善堂是1939年5月建立的组织,是为分配上海地区的鸦片而设立的组织。
萨顿:他们是怎样活动的?请简单介绍一下。
奎尔:就我职务上所知,在上海,鸦片几乎肯定是由日本的船输送来的。这些船到了上海,就在日本方面的码头上卸货……鸦片就是从这些码头上运到仓库的。然后,是从那里弄到鸦片贩卖所去的。
萨顿:日本占领以前,上海地区麻醉品……的贩卖情况如何?
奎尔:1938年以前,在上海没有看到过大量的麻醉品。关于麻醉品,中国人有个习惯,就是吸食过红色块状的鸦片。它是由鸦片的渣滓、海洛因、糖精以及染色的药做成的。但是,这种习惯被逐渐清除,到1938、1939年前后,已经很难看到。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进行鸦片战的罪行,经过东京审判被揭露出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法庭在判决时,对日本的这一罪行进行了一定的追究,指出“日本签署并批准了禁烟公约,有不得从事麻醉品交易的义务”。但是,日本“为了筹措经费,和为了削弱中国的抵抗力,认可并扩大了鸦片及麻醉品的交易”。
 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一直进行鸦片等麻醉品的交易,而且,日本军方、政府都参与其中,形成了丑恶的“以毒养战”的战略。东京审判虽然揭露了日本的这一罪行,但没有进行深究,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一直进行鸦片等麻醉品的交易,而且,日本军方、政府都参与其中,形成了丑恶的“以毒养战”的战略。东京审判虽然揭露了日本的这一罪行,但没有进行深究,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东京审判的资料库中,日本对中国及亚洲的侵略的资料极为丰富。无论是政策的策划、决定过程,还是侵略行动的具体实施,都有有力的证据材料。例如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检方都展示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了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战争暴行。
而关于日本对亚洲人的暴行资料,在东京审判及相关的BC级战犯审判中,也都有丰富的收藏,特别是在检方资料中。但除了众所周知的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等个别大规模暴行外,其他日军大屠杀、残酷虐待战俘及平民、扶植伪政权、经济掠夺、制毒贩毒等暴行资料,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和利用。例如法庭判决书中提到的日军在东南亚下述地区犯下了战争暴行:
马来亚的怡保(lpoh)(1941年12月);
马来亚的巴利特苏龙(Parlt Sulong)和奠尔(Maur)之间(1942年1月);
马来亚的巴利特苏龙(1942年1月);
马来亚的卡冬加(Katonga)(1942年1月);
马来亚的亚历山大医院(1942年1月);
马来亚的新加坡(1942年1~3月);
马来亚的班江(Panjang)(1942年2月);
马来亚的莫尔(1942年2月);
泰国的琼蓬角(Jampong Jod)(1941年12月);
婆罗洲的朗那瓦(Longna'wa)(1942年8月);
婆罗洲的达拉甘(Tarakan)(1942年1月);
荷属东印度的望涯群岛(Banka lsland)(1942年2月);
苏门答腊的库达拉查(Kota Radja)(1942年3月);
爪哇的南望(Lembang)(1942年3月);
爪哇的苏班(Soebang)(1942年3月);
爪哇的加达尔·巴士(Tjlatar pass)(1942年3月);
爪哇的万隆(Bandoeng)(1942年3月);
摩鹿加群岛的安蓬岛(Ambong Island)的拉哈( Laha)(1942年2月);
荷属帝汶岛(Timor)的奥卡贝其(Okabeti)(1942年2月);
荷属帝汶岛的奥帕·贝萨尔(Oesapa Besar)(1942年4月);
葡属帝汶岛的述子·梅达(Tatu Meta)(1942年2月);
英属新几内亚的米尔纳湾(Mllne Bay)(1942年8月);
英属新几内亚的布纳(Buna Bay)(1942年8月);
新不列颠的多尔(Tol)(1942年2月);
达拉瓦岛(Tarawa)(1942年10月);
菲律宾的奥多尼尔俘虏营(Camp O'Donnell)(1942年4月);
菲律宾的马尼拉的圣达·克鲁斯(Santa Cruz)(1942年4月)。

在法属印度支那,日军对于自由法国各种组织成员进行了围剿屠杀。此外,还在以下各地对俘虏及被拘禁的平民进行了屠杀:
郎孙(Langson)(1945年3月);
丁·拉普(Din.h Lap)(1945年3月);
塔奎克(Thakhek)(1945年3月);
东(Tong)(1945年3月);
坦·奎(Tan Qui)(1945年3月);
劳斯(Loas)(1945年3月);
董·丹(Dong Dang)(1945年3月);
哈京(Hagiang)(1945年3月)等。

这些大量的屠杀事件的罪证在东京审判检方的资料中都有收藏。
再如日军违反国际法,虐待甚至处死俘虏等事件,除在中国大量发生外,还在亚洲其他国家如下地方的俘虏营中大量发生:
马来亚新加坡(1942年3月);
缅甸墨吉(Merg-Lii)(1942年);
婆罗洲达拉甘(1942年及1945年);
婆罗洲坤旬(1942年6月);
婆罗洲邦加马辛(Bandiermasin)(1942年7月);
婆罗洲三马林达(1945年1月);
苏门答腊巨港(1942年3月);
爪哇巴达维亚(1942年4月);
爪哇左卡波米(Soekaboemi)(1942年5月);
爪哇佐加卡达(Jogjakarta)(1942年5月);
爪哇贾第南戈尔(Djati Nanggor)(1942年3月);
爪哇的万隆(1942年4月);
爪哇贾玛希(Tjlmahi)(1942年5月);
西里伯斯马加撒(1942年9月);
摩鹿加群岛安披那(1942年11月);
荷属帝汶奥萨帕、贝萨尔(1942年2月);
菲律宾卡巴纳坦(Ca-banatuan)(1942年6月);
日本本山(1942年11月);
日本福冈(1944年5月);
威克岛(1943年10月);
婆罗洲拉鲁(1945年8月)等。

东京审判资料中包含大量的日军虐待和屠杀俘虏的资料。其中虐待和屠杀中国战俘的情况国内已有不少的介绍,但对日军虐待欧美战俘的情况的介绍还不太多。下面介绍几例日军在中国上海和沈阳的英美战俘营中,虐待英美战俘和被关押的英美平民的暴行。
美军海军陆战队一等兵在欧内斯特·P.希格斯(Ernest Philip Higgs)宣誓供述书(法庭证据1889号)中揭露了1943年8月日本宪兵在上海杀害普通拘留者的事件。
被拘留的威廉姆斯·哈顿(William Hutton)从海防路集中营(Haiphong Road Camp)被带到日本宪兵司令部接受讯问,后被送回集中营时已神志不清。他身上无数的划伤显示,其曾遭受用剃刀片切割的拷问。他在几天后死去。欧内斯特·所罗门(Ernest Solomon)的宣誓供述书(法庭证据1889号)则进一步确认了威廉姆斯·哈顿被杀害的事实。
詹姆斯·H.科尔(James Hector Cole,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的供述书(法庭证据1890号)中提到,1943年3月,日本看守在上海战俘营射杀了一名美国人。该美国人正站在离战俘营围栏不远处,看守无缘无故地向他开了枪。
此外,詹姆斯·S.布朗宁(James Scott Browning,美军海军陆战队一等兵)宣誓供述书(法庭证据1895号)和罗伯特·迈克劳·布莱文(Robert McCulloch Brown,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士)的宣誓供述书(法庭证据1896号)都表明,1944年2月,上海战俘营约50名美军战俘因与中国人买卖私人物品而遭到惩罚。他们被赤身赶到雪中,遭到胃里被大量灌水的“水刑”,之后日本人还跳到他们身上。如果战俘失去意识,则把战俘绑在雪地的柱子上,然后浇冰水使其苏醒。他们还被用带铅锤的短马鞭殴打。
爱德华·E.威廉森上尉(Edward E.Williamson,上海某警区总督察)宣誓供述书(法庭证据1893号)与威廉·S.邦杰(William Slade Bungey,颐中[Yee Tsoong]烟草分销有限公司理事)的宣誓供述书(法庭证据1893号)都揭露,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后逮捕了公司总裁或机构负责人中的盟国有名人士,并将其带到日本宪兵队总部所在地——大桥集中营(Bridge House)。这些人无论男女都被关在一个虱蚤肆虐的房间,在房间的角落放有一个桶,作为共用的厕所。提供的食物只有少量的粥和淡茶,还不时遭受“水刑”“电刑”“毒打”等各同形式的酷刑。
约翰·R.德拉勒(John Robert De Lara,美国外国保险协会经理助理)的证言(法庭证据1904号)提到,1944年、1945年冬天,浦东集中营的气温降到华氏20度(零下6.67摄氏度)。日本看守虽有取暖设备但丝毫不用于集中营,被拘者从未得到衣物。食物配给逐步减少,到后期肉类供应只有起初的1/4。被拘留者暴露在空袭的危险之下,并且直到二战结束一周后还不许在建筑上贴集中营的标志。
温菲尔德·S.坎宁安上校(Winfield Scott Cunningham,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的证言(法庭证据1900号)指出,1942年3月他从吴淞盟军战俘营逃跑后再次被捕,之后作为日本陆军的逃犯被交付日军军法会议接受审判。依据国际法,对逃兵最重的刑罚是30天单独监禁,但日军军法会议号称不受日内瓦条约约束,判了他10年监禁。他于1944年10月从华德路(提篮桥)监狱(Ward Road Jail)战俘营逃跑,之后再被捕时则被判终身监禁。
C.D.史密斯海军中校(C.D.Smith,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宣誓供述书(法庭证据1901号)提到,他从吴淞盟军战俘营逃跑后被捕,在大桥集中营(Bridge House)待了30天,后又被带到江湾盟军战俘营,被单独监禁53天。之后以“日本陆军的战争逃犯”罪名交付日军军法会议,被判服监10年并剥夺所有军人权利。
约翰·B.L.安德森(John B.L.Anderson,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宣誓供述书(法庭证据1907号)则提到,江湾盟军战俘营食物缺乏,劳动繁重。他在战俘营期间体重减少了40磅(约18公斤)。战俘被迫去建造日本军用步枪射击场,或擦炮弹,或维修坦克、卡车。
罗杰·D.班福德(Roger DickBamford,美国海军陆战队下士)宣誓供述书(法庭证据1909、1911号)也陈述了江湾与吴淞盟军战俘营的情况。在这两个战俘营,一天三次供应一小茶杯米饭,一天给两次很稀的汤。战俘们睡在地上,没有炉子或燃料。日本人完全不提供医疗支持,战俘唯一一次接受的医疗服务是来自俘虏中的一名军医。江湾盟军战俘营有四五名、吴淞盟军战俘营有三四十名战俘因营养不良、脚气病或痢疾而死亡。
莫里斯·利特曼(Morris Littman,美国陆军下士)宣誓供述书(法庭证据1899号)中作证说,1943年4月,奉天战俘营的三名美军战俘逃跑后再次被捕,先遭毒打后被斩首。
埃尔默·A.莫尔斯(Elmer A.Morse,美国陆军中士)证言记录(法庭证据1905号)和赫尔曼·F.法亚尔(Herman E.Fayal,美国陆军下士)宣誓供述书(法庭证据1906号)都提及,奉天战俘营的200多名战俘因营养不良、医药匮乏、燃料不足而死亡。虽有足够煤炭可以供应,但房屋供暖不足。起初一个半月,每天只给战俘玉米和白菜汤及两个酸面包。食物脏得无法下咽。增加食物、燃料或医疗支持的要求都被拒绝。
詹姆斯·A.吉尔伯特(James A.Gilbert,美国陆军一等兵)证言(法庭证据1912号)则证明,他在奉天战俘营的起初几个月,约有250名美军战俘因饥饿及痢疾死亡。无任何医疗支持。食物是玉米和大豆。战俘在附近工厂劳动,为日军制造钢盔、飞机部件、大口径炮弹装备等。他在铁厂一天工作16个小时。因繁重的劳动和饮食的匮乏,他在战俘营期间体重减少了60磅(约27公斤)。
赫尔曼·霍尔(Herman Hall,美国陆军下士)的证言记录(法庭证据1913号)证明,奉天战俘营离日本大型军工厂约600码(约540米),但在战俘营未张贴任何标志。当B-29轰炸机进行空袭时,19人被炸死,约30人受伤。

东京审判是国际社会对日本错误国策以及战争罪行的总清算。日本军国主义自1931年之后,先后发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并偷袭珍珠港,进攻东南亚和中国香港,进行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及“大东亚战争”,使被侵略国家和人民蒙受了巨大战争灾难和生命财产损失。在战争过程中,日本违反国际法,蔑视人类尊严,犯下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战争暴行,如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化学毒气战、活人身体实验等,累累罪行,罄竹难书。国际社会如果对这种反人类文明的罪行置之不理,国际公理将不复存在,国际秩序将失去人性,人类文明乃至生存都将受到危害。为挽救人类文明,捍卫世界和平,必须对日本的上述战争罪行进行彻底清算。东京审判正是通过揭露、批判日本错误的对外侵略国策,惩罚战争罪犯,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进行总清算,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把战争罪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东京审判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东京审判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东京审判向全世界表明,阴谋策划、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参与战争犯罪的个人,要对侵略战争负责。它昭示世界,谁胆敢策划、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不管地位多高,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由战胜国单独组成的,其合法性受到一些人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的质疑和攻击,认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片面审判”和“报复”。事实上,一方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然是由战胜国组成的,但并非“战胜者裁决战败者”,更不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法庭的设立以及对战争罪、反和平罪的控告也符合既有国际习惯法的法理依据。在审判过程中,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都严格遵循法理法律规定,控辩双方的权利尤其是被告方的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另一方面,法律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从国内法来说,法律体现的是统治者的政治要求。国际法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国际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要求法律与政治彻底割裂,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是相对独立于政治,不可能绝对独立于政治。这是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东京审判的最大政治前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盟国的胜利而结束,否则,就根本谈不上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法律制裁。总体来说,东京审判是比较公正的,体现了国际法的正义原则。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
东京审判揭露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罪行,为历史研究留下了宝贵史料。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其所到之处犯下了累累暴行,但由于战时实行新闻统制和封锁,这些让日本民族蒙羞的罪行都被掩盖起来了。而东京审判揭露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策划、实施侵略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犯下的大量罪行,如制造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残害俘虏等。日军犯下的这些骇人听闻的战争丑行被揭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极大地震撼了日本国民,让他们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本质。这对战后以来,日本反思侵略战争、拥护和平民主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