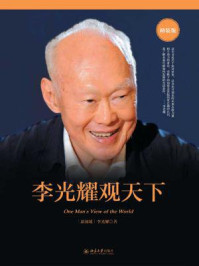今天,东亚是一个热点地区。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影响地区安全的传统因素未见消除,且在某些地区时有激化。美国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一直是这一地区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又搞起了“亚洲再平衡”战略。日本作为美国的东亚盟友到处挑起事端,积极追求其政治、军事大国梦想。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迅速和平崛起,一些国家在“中国威胁论”的蛊惑下,对中国产生了猜忌和担心。这些情况表明,中、美、日三国在和平发展为时代主流的当今世界如何处理好多边和双边关系,如何共同构建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关乎东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是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严峻的时代课题。回答并解决这一课题,并非一介学者力所能及,但由于自战前至战后中、美、日三国关系一直复杂多变,且是二战时期“大东亚共荣圈”的直接关系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在今天这种形势下,围绕二战时期日本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思考一些问题,对应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课题或许不无裨益。
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梦想从构想到实施是其从近世到近代扩张思想演变的结果。其思想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幕末、明治时期。从幕末时期的佐藤信渊到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再到明治时期的伊藤博文、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等,他们的扩张思想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他们既是日本民族觉醒的启蒙大师,同时也是日本走上对外扩张道路的奠基者和推动者。
幕末的佐藤信渊(1769~1850),倡导以“海外雄飞”论为核心的“征服支那”论,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的大陆扩张思想,可谓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理论的滥觞。他在1823年出版的《宇内混同秘策》中,宣称日本兼并亚洲各邻国是上天赋予的使命:“皇大御国(指日本)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悉课为其郡县,万国之君皆可为其臣仆。”“以此神州(日本)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他指出,征服中国应先攻略满洲。“满洲之地与我之山阴及北陆、奥羽、松前等隔海相对者凡八百余里”,“顺风举帆,一日夜即可到达彼之南岸”。如得满洲,则其全国之衰败必当从此始,“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他还具体拟定了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认为日本宜在衣食充裕的东京、关西、中州、筑紫、陆奥等八地域实行“富国强兵”,得雄兵20万人,然后由天皇渡海亲征,先锋直扑江南,取应天府,以南京为临时皇宫之所在,录用中国人中之人才,征服中国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
 佐藤信渊的扩张思想为日本近代扩张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本人后来也被日本的某些史家尊为“大东亚共荣圈之父”。
佐藤信渊的扩张思想为日本近代扩张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本人后来也被日本的某些史家尊为“大东亚共荣圈之父”。
倡导“和魂洋才”的佐久间象山(1811~1864)是佐藤信渊的得意门生。他对“内圣外王”的传统儒学进行了改造,提出“谁谓王者不尚力”的疑问,他认为实行“王道”也必须尽量扩充军事力量,国家的核心力量是强大的军事实力,以便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优势。佐久间象山观察19世纪中叶的国际形势,认为军事实力的强弱至关重要,在国家间的交往中实力就是一切,在他看来,“非但英国无道,西洋诸国,天地公共之道理均无可言”,而要想避免这种结果,唯有遵从丛林法则,建立本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世界一等强国。可见,佐久间象山的外交理念充满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佐久间象山曾于1839年开办私塾“象山书院”,吉田松阴成为入门弟子。
作为佐久间象山的私塾生,吉田松阴(1830~1859)继承了老师的衣钵,在对外方面继续鼓吹扩张,而且把老师的理想具体化。他为日本描绘了对外扩张的路线图,即“乘隙收满州而逼俄国,侵朝鲜而窥清国,取南州而袭印度”。
 另在1858年给友人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今日之计,当以谨守疆域,乘机垦拓虾夷,收取琉球,北取朝鲜,挫败满州,东压支那,南临印度,以此张进取之势,固退守之基,以遂神宫未遂之伟业,达丰国未成之大计。”
另在1858年给友人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今日之计,当以谨守疆域,乘机垦拓虾夷,收取琉球,北取朝鲜,挫败满州,东压支那,南临印度,以此张进取之势,固退守之基,以遂神宫未遂之伟业,达丰国未成之大计。”
 1859年,吉田松阴继承其叔父创办的“松下村塾”,继续传道授业,发展他的扩张思想,后来的维新名士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便出自其门下。
1859年,吉田松阴继承其叔父创办的“松下村塾”,继续传道授业,发展他的扩张思想,后来的维新名士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便出自其门下。
伊藤博文(1841~1909)是吉田松阴的高足,曾四度出任日本首相,也是日本明治时期从“内治优先”转向对外扩张的实力派推动者。他的一首汉诗也证明了他是日本幕末以来扩张思想的继承者:“道德文章叙彝伦,精忠大节感明神。如今庙廊栋梁器,多是松门受教人。”
 不仅如此,他还是幕末以来日本扩张思想的有效实践者,在他第二次组阁时(1892~1896),日本对中国的作战准备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只不过之前的第一次山县内阁和第一次松方内阁虽然都制定过以增加军备开支为主要内容的财政预算案,但都被议会否决了。而伊藤博文出任首相之后,没有采取解散议会或者贿赂议员的做法,而是游说天皇下发诏书,迫使议会遵从圣断做出让步,首开以天皇压制议会的先河。结果军备预算案得以通过,1894年7月,日本以朝鲜东学党起义为借口,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
不仅如此,他还是幕末以来日本扩张思想的有效实践者,在他第二次组阁时(1892~1896),日本对中国的作战准备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只不过之前的第一次山县内阁和第一次松方内阁虽然都制定过以增加军备开支为主要内容的财政预算案,但都被议会否决了。而伊藤博文出任首相之后,没有采取解散议会或者贿赂议员的做法,而是游说天皇下发诏书,迫使议会遵从圣断做出让步,首开以天皇压制议会的先河。结果军备预算案得以通过,1894年7月,日本以朝鲜东学党起义为借口,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
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日本的扩张理论也呈现了新的表现形态,即由此前的纸上谈兵演变为扩张理论与扩张实践的互动。福泽谕吉(1835~1901)就是明治之后第一位扩张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不遗余力地撰文鼓吹侵华,公开贩卖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上述的佐藤信渊、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人的侵华主张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言论,而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践。福泽谕吉则不同,他虽终身在野不仕,却通过开办学校、创办报刊和著书立说引导社会舆论,影响政府决策,为日本对外扩张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其在1882年3月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时政文章近千篇,对当时的国内外大事发表见解,对政府的内外施政建言献策。这些文章占福泽谕吉一生著述的一半以上,在岩波书店1961年版全16卷《福泽谕吉全集》中占了9卷,其中有大量涉及侵略中国的文章。
福泽谕吉在甲午战争中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最能表明他的扩张思想。他的核心理论包括崇尚武力和丛林法则,认为“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主张日本应该脱离亚洲,跻身欧洲列强文明国家。打着促进文明开化的旗号,以武力征服中国等亚洲国家。他在《眼中无清国》一文中宣称,割让台湾只是一个开头,分割中国四百余州是大势所趋,呼吁捐款支持战争,吁请天皇“御亲征”。其在《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一文中,对日军取得的胜利表示“欣喜若狂,可喜可贺”,翘首以盼日本的太阳旗尽早在北京城迎着晨风飘扬,四百余州的全图尽在“文明的阳光普照之下”。
 他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被其同辈和后辈付诸实践,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演变为美化战争的“大东亚共荣圈”。
他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被其同辈和后辈付诸实践,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演变为美化战争的“大东亚共荣圈”。
德富苏峰(1863~1957)本名德富猪一郎,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他继承福泽谕吉的衣钵,鼓吹极具侵略性的皇室中心主义。他出生于幕末,经历明治、大正、昭和,死于战后,活了94年。从1887年前后登上论坛至1957年病逝,70年笔耕不辍,且始终处于舆论的中心地位。其思想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对日本走上侵略扩张道路影响极大,20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泛滥的右翼思潮和政界的右翼思维与其思想一脉相承。
德富苏峰登上文坛之后非常狂妄,直言自己喜欢政治,要引导世间政治按着他的意愿运行。他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的1893年,发表了《大日本》一文,呼吁要寻找“扩张日本的途径”;在同年出版的《吉田松阴》一书中,把吉田松阴尊为“膨胀的帝国主义的先驱者”。1894年出版的《大日本膨胀论》是德富苏峰对外扩张及侵华理论的代表作。在该书中,德富苏峰系统地提出并论述了他的“大日本膨胀论”,
 认为日本前几百年是收缩的几百年,此后几百年将是膨胀的几百年。甲午战争胜利之后,他和福泽谕吉一样欣喜若狂。“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他又愤怒沮丧,用手帕包上旅顺口的沙土以示纪念,颇有回国卧薪尝胆之意味。
认为日本前几百年是收缩的几百年,此后几百年将是膨胀的几百年。甲午战争胜利之后,他和福泽谕吉一样欣喜若狂。“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他又愤怒沮丧,用手帕包上旅顺口的沙土以示纪念,颇有回国卧薪尝胆之意味。
果然在回国之后,德富苏峰积极鼓动日本政府扩军备战,撰文鼓噪“十年磨一剑”,必报“还辽之仇”的军国主义舆论。
九一八事变后,年届七旬的德富苏峰声称这一事件是实现他的主张的最好机会,是日俄战争之后最愉快的时刻。他不遗余力地与军部势力勾结,鼓动各界知识分子为侵略战争效力,倡议“文学报国”“言论报国”,撰文为日本侵略升级辩护,鼓吹超国家主义,并于1942年12月出任日本新闻界“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1943年,德富苏峰因宣传皇室中心主义和法西斯思想有功被授予文化勋章。战后他虽被列为“A级战犯”,但1947年后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变化,德富苏峰被解除拘禁,后又被解除“公职追放”令。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德富苏峰的写作依然充满着不甘失败的复仇情绪。他在1957年去世时,曾高呼“再等500年”。可见,他是一位死心塌地、死不悔改的侵略扩张主义思想家。
从幕末到二战,日本扩张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至二战时期“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这种一脉相承的扩张思想的泛滥又不是孤立的,它和明治以后日本近代化进程及其伴随出现的实力增长互激互动,两者形成一个正相关关系。从日本近代化发展和实力增长的历程看,“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形成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推行殖产兴业政策,自上而下地推动近代化运动,把国内经济发展当作“燃眉之急”。经过20年的经济发展,日本实现了早期的工业化。财大气粗之后,其战略重点由“内治优先”转变为对外扩张,其对外战略也由“条约改正”转向实质的武力扩张。“脱亚入欧”不仅表现在文化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军事强大之后跻身欧洲列强,搭上殖民争霸的末班车,且大有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之势。1874年侵略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1894~1895年甲午一役打败清政府,打破了清政府的朝贡体系,改变了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日本利用相当于当时年财政收入4倍多的战争赔款,大办工厂企业,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并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化。1904年,更加膨胀的日本发动了旨在侵占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1905年迫使俄国求和签约。这次战争胜利令日本人得意忘形,自认为黑头发第一次打败了黄头发,由此奠定了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霸权地位。实际上,这时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已经萌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日本为缓解内外交困的局面,企图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独占中国和夺取德国在南洋群岛的殖民地。实践也证明,日本抓住了这个“大正新时代的天赐良机”。
 1914年10月,日本占领了胶济铁路沿线和青岛,不久又占领了德领南洋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并取得了“委任统治权”。
1914年10月,日本占领了胶济铁路沿线和青岛,不久又占领了德领南洋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并取得了“委任统治权”。
其实,随着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不断扩张,“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轮廓逐渐浮现出来。曾任满铁总裁的后藤新平在1916年向当时的寺内正毅内阁建言,日本必须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的姿态,建立与欧美诸同盟相抗衡的“东亚经济同盟”。
 1917年,西原龟三又提出建立“东洋自给圈”,以“日华经济区”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置于日本统治之下,其统治方法就是“王道亲善”。
1917年,西原龟三又提出建立“东洋自给圈”,以“日华经济区”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置于日本统治之下,其统治方法就是“王道亲善”。
 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雏形阶段,其“王道亲善”的实质已经暴露出来了,那就是打着王道的旗号干霸道的勾当。
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雏形阶段,其“王道亲善”的实质已经暴露出来了,那就是打着王道的旗号干霸道的勾当。
日本通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摆脱了国内危机,而且大发战争之财,之后虽出现过短暂的经济不景气,但总体看经济实力仍处于上升阶段。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逐步占领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随着侵占领土的不断扩大,其野心也越来越膨胀。特别是欧战爆发之后,荷、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或降或败,无暇东顾;又由于美日大部分的战略物资来自东南亚,因此东南亚成为美日的必争之地。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并尽快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就成为日本的紧迫任务。1940年7月19日的荻洼会议决定了“南进”方针,9月6日,划定了“大东亚共荣圈”范围,即“以日、满、支为骨干,包括原德属诸岛、法属印度支那及附属诸岛、泰国、英属马来、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为避免过分刺激美欧,日本对外宣称的目标限定在缅甸以东、新几内亚以北,而把澳、新、印三国作为第二步目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同时进攻中国香港、马来亚、菲律宾,不到半年时间,加上原来已占领的朝鲜、中国沦陷区和印度支那,日本统治了大约5亿人口和7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大东亚共荣圈”似具雏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同时进攻中国香港、马来亚、菲律宾,不到半年时间,加上原来已占领的朝鲜、中国沦陷区和印度支那,日本统治了大约5亿人口和7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大东亚共荣圈”似具雏形。
日本把依靠武力扩张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行为美化为实现“共存共荣”的“解放战争”,然而,不管日本侵略者怎样美化“大东亚共荣圈”,在其推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两个问题是无法否认的,这两个问题决定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性质和命运。一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推行表现为以武力掠夺他国资源,侵占他国领土;二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推行威胁甚至直接挤压了老牌殖民者的既得利益。前者决定了“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本质,即非正义性;后者决定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过度膨胀破坏了“利益均沾”原则。由于非正义性,它必然受到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奋起抵抗,直至把侵略者驱逐出去;由于它破坏了“利益均沾”原则,老牌殖民者必然会与被侵略国家的抵抗力量形成合力。因此,“大东亚共荣圈”最后走向破灭也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发展也证明,日本的扩张理论和侵略行为互激互动所形成的正相关关系,不可能像德富苏峰所预测的那样永远良性膨胀下去,到一定阶段必然破裂。
对于日本不断膨胀的侵略野心,西方新老殖民主义者一开始都采取了绥靖主义政策。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宣称日本及其他各国“有在华北驻扎军队的权利”,等于公开承认日本侵华合法;首相张伯伦认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和动用武力是错误的,要为“与日本绥靖”而努力。欧洲老牌殖民者的绥靖主义行为,无疑为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提供了便利条件。
美国这个后来居上的新殖民者,早在20世纪初就与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开始了争霸行动。由于在二战中西方老牌殖民者无暇东顾,东南亚地区又是美日战略资源的重要供给地,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梦想自然与美国的西太平洋战略发生了冲突。因此,这里主要从美日在西太平洋地区争霸的历史,略谈一下美国在“大东亚共荣圈”形成和破灭过程中的作用。
美日争夺西太平洋的霸权由来已久。19世纪中叶之后,西方列强开始觊觎广袤富饶而又孱弱多病的中国,从琉球到菲律宾这一岛链自然成为其窥视并进而侵蚀中国大陆的战略要地。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菲律宾。当时,俄亥俄州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在审议美西和约时说:“在未来岁月里,太平洋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地区,谁控制太平洋,谁就能控制世界。” [1]
美国欲把太平洋变为其内湖的战略野心,受到了日本这个后起之秀的挑战。日本经甲午一役打败清朝,后又经日俄战争击败俄国,控制了朝鲜、中国的辽东半岛和南库页群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又利用西方列强忙于欧战之机,抢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同时把马里亚纳、马绍尔和加罗林群岛收入囊中。这几处位于太平洋中部的群岛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日本把美国从夏威夷向西连接西太平洋的岛链梦想拦腰斩断,由此对美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构成了直接挑战。
对于日本这个“暴发户”的挑战,美国当然不会坐视。1919年,美国建立了太平洋舰队。1922年,美国联合英法等欧洲盟国召开华盛顿会议,以法律条约的形式迫使日本放弃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武力攫取的殖民利益,同时确立了美国对日本的海军优势;而日本也取得了美国不继续在太平洋中部岛屿设防并建造海空军基地的许诺,两者取得了暂时的战略平衡。然而,这种暂时的战略平衡无法解决美日在西太平洋地区互不容染指这一根本矛盾。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很快就修改了它的国防方针,将美国列为第一假想敌,制定了针对美国的作战计划。
从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到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美国的态度是复杂的。由于它在西太平洋地区有利益诉求,所以既不愿意看到日本独吞中国,也不愿意看到日本挥师南下东南亚。又由于它存在孤立主义传统,就决定了它会在不触动其根本利益的情况下袖手旁观,坐收渔利。纵观美国在二战期间的表现,便可明白这一点。如果说中国坚持持久战是基于当时国力的无奈选择,那么,把日本拖入持久战则是美国基于其西太平洋战略利益的一种主动选择。
卢沟桥事变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张伯伦遥相呼应,于1937年10月5日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
 其实质就是联合国际社会把日本的侵略战火“隔离”在中国境内,使日本陷入持久战,这样,日本便不能迅速抽身向东南亚扩张。当然,美国政府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也为了防止中国国民政府倒向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还是顶着孤立主义思潮的压力,对日本实施了部分禁运,同时也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了一些财政和军事援助。可见,这时美国的基本策略还是“大西洋第一,太平洋第二”,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和冲突。这也是日本侵略野心一再膨胀、“大东亚共荣圈”迅速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质就是联合国际社会把日本的侵略战火“隔离”在中国境内,使日本陷入持久战,这样,日本便不能迅速抽身向东南亚扩张。当然,美国政府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也为了防止中国国民政府倒向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还是顶着孤立主义思潮的压力,对日本实施了部分禁运,同时也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了一些财政和军事援助。可见,这时美国的基本策略还是“大西洋第一,太平洋第二”,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和冲突。这也是日本侵略野心一再膨胀、“大东亚共荣圈”迅速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0年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8月,日军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北部;9月27日,德、意、日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其中第三条警告美国不得干预欧洲和亚洲的战争。面对这一严峻形势,美国确定对日政策四原则:第一,避免在太平洋与日本发生公开冲突;第二,继续对日施加经济压力,援助中国,但以不刺激日本军方开战为限度;第三,让日本知道美国在太平洋的力量是强大的;第四,克制争吵,不关闭沟通渠道,让日本知道必要时美国不会坐视。 [2] 至此,美国依然在旁观避战。1941年7月23日,日军进入印度支那南部。7月2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对日实行全面禁运,并冻结日本在美一切资产。11月25日,日本的联合舰队秘密驶离千岛群岛奔向夏威夷。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日本驻美大使递交了《美日协定基本纲要草案》(“赫尔备忘录”),该草案要求日本无条件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放弃日本在华各种权益,不承认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等。这对于日本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日本在东亚数十年的经营将化为乌有,难怪日本人视赫尔备忘录为美国的“最后通牒”。至此,“大东亚共荣圈”的过度膨胀已经直接挤压了美国的利益空间,也就是说日本失控的战车已经触碰到了美国的底线。因此,美国彻底放弃袖手旁观、坐收渔利的孤立主义传统,与中国的抗战力量形成合力便在情理之中,也正因此,“大东亚共荣圈”梦想提前破灭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如何认识和评估中国抗战对打破“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贡献,是二战史、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并且涉及“战争记忆”、历史认识和当代东亚国际关系等重要现实问题。
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出于纠正战时日本舆论宣传的目的,于1945年12月8~17日指使《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读卖报知》连载其授意编写的《太平洋战争史——从九一八事变到无条件投降》,连载内容随后由高山书院出版单行本《太平洋战争史》。连载揭露了日军的残暴,让日本国民了解了许多之前不知道的真相,有拨乱反正之意义。但从书名到内容,也不难看出美国占领当局认识上的偏差,以及可能对之后日本建立正确的战争认识的不良影响。早在战时的1941年12月12日,日本内阁就做出决议,要求对其发动的战争统一使用“大东亚战争”的称谓。美国占领当局认为这种称谓有美化战争之嫌,遂强迫连载文章使用“太平洋战争”这一称谓,显然这一称谓突出了美国在东方战场的作用。从单行本内容看也是这样,对中国战场的叙述内容不到全书的1/7,且在三报连载时被大量删减。
 《太平洋战争史》的内容架构对战后日本人战争记忆的影响是深远的。右翼分子抨击《太平洋战争史》贯穿着“自虐史观”,依然把大东亚战争粉饰为“民族解放战争”;另一方面,由于涉及中国战场的内容被简化,普通国民难以形成集体的加害意识,而只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受害意识,这是中日之间在历史认识、战争记忆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的重要原因之一。
《太平洋战争史》的内容架构对战后日本人战争记忆的影响是深远的。右翼分子抨击《太平洋战争史》贯穿着“自虐史观”,依然把大东亚战争粉饰为“民族解放战争”;另一方面,由于涉及中国战场的内容被简化,普通国民难以形成集体的加害意识,而只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受害意识,这是中日之间在历史认识、战争记忆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抗战为打破“大东亚共荣圈”做出了主要贡献,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首先,中国的抗战时间最长,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大东亚共荣圈”的最早受害者和反抗者。“大东亚共荣圈”由思想到设想再到实施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中国的反抗早在其萌芽阶段就开始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法西斯开启了对亚洲侵略的战端。虽然九一八事变不像后来德国入侵波兰那样立即引起其他国家对法西斯势力的直接对抗,却成为世界局势演变的节点,即法西斯侵略开始对人类和平产生巨大威胁。也正因为如此,战后苏联检察官克伦斯基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才说:“如果我们可以指出一定的日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段血腥时期的开端的话,1931年9月18日恐怕是最有根据的。”

九一八事变后,在英美等国尚对法西斯国家采取绥靖政策的情况下,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等,率先举起了反法西斯侵略的旗帜,开展了保卫中华民族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各种武装力量为抗日救国而奋斗。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国形成了全民族一致对外的局面。事态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人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中国很快就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
中国很快就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
其次,中国抗战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破灭创造了条件。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由局部抗战走向全面抗战,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据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所资料载,投入侵华战争的日本陆军兵力,1937年占总兵力的88%;1938年占94%;1939年占83%;1940年占78%。中国的长期英勇抗战牵制了日本侵略军的主力,为提前打破日本的“共荣圈”迷梦奠定了基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中国的抗战阻止了日本的“北进”战略计划。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的用兵纲领就曾有“北进”方案,这对苏联的远东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面临着德、日法西斯东西夹击的极大困境。当时,华北地区的抗日战争虽然越来越艰难,但国共两党的武装力量仍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日本侵略军为全面占领中国和东亚首先要建立一个巩固的华北基地,因此不得不向华北派遣更多的部队推行“肃正扫荡”。由此可以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对牵制日军,对迫使日军放弃“北进”方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故此,当德国入侵苏联要求日本配合的时候,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表示:“日本现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很大,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日本最终放弃“北进”:“帝国政府将继续努力解决中国事变……暂不介入德苏战争。”没有了东线威胁,苏联才敢把远东地区的大量兵力调往西线。苏联元帅崔可夫也承认: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第三,中国的抗战延缓了日本的“南进”战略计划。“南进”是日本对外扩张的另一个方案,而且在日本决策者中主张“南进”的比主张“北进”的更占优势,原因就是要与欧美国家争夺资源丰厚的东南亚地区。欧战爆发后,法、荷很快投降,英、美等国无暇东顾,于是日本认为南洋几成“真空地带”,这正是完成“南进”的天赐良机。但是,由于中国军民顽强抗日的牵制作用,美英又刻意推行“隔离政策”,日本没敢贸然“南进”,直到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时,日本仍然表现出了对“南进”的犹豫。中国战场对于日军的战略牵制作用,任何尊重历史的人都应予以肯定。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就曾说:“中国一崩溃,至少可以使日本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攻印度,就确实可能了。”
 而事实是,中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崩溃”,仍然以顽强不屈的精神陷日本侵略者于泥沼之中。
而事实是,中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崩溃”,仍然以顽强不屈的精神陷日本侵略者于泥沼之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继续牵制着日本陆军主要兵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用于东南亚战场的陆军兵力只有10个师团,不及侵华兵力的20%;战争结束时日军向中国战区投降的兵力达128万余人,这个数目超过了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各岛的日军兵力总和,约占日军投降兵力总数的50%。中国抗战为打破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梦想、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的上述贡献,是以中华民族的重大牺牲为代价的。在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伤亡和损失超过了任何一个参战的国家。
第四,中国的抗战为东南亚各国树立了民族解放的榜样,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为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了榜样。长期的抗日战争不仅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而且使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成为泡影。中国对人类正义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43年,西方国家不得不宣布废除历史上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重新与中国签订新条约,这在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上都是一件大事。中华民族为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其他弱小国家和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榜样。
[1] 转引自F.R.Dulles, China and Americ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6),p.99.
[2] 转引自Hull.Cordell, The Memories of Cordell Hul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8),pp.99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