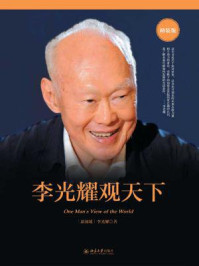韩国和中国自古以来一直保持着良好友善的邻邦关系,这种关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甲午战争给韩中两国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特别是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更巩固了其在东亚的霸主地位。1905年的韩日《乙巳条约》实际上使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韩国领导阶层为了避免韩国的殖民地命运,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挽回国家主权的运动。但韩国最终还是于1910年8月被日本强行吞并。
韩国民族主义反日团体“新民会”为了克服这一危机,着手在国外建立独立运动根据地。他们的活动地点主要包括与韩国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和苏联沿海州地区,这些地方都是韩人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开辟出来的新的活动区域。这些先觉者则将这些地区视为未来抗日武装斗争的根据地。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韩国国内,韩国国内反日独立运动家纷纷流亡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区。这些韩国流亡者在中国共和革命成功中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和鼓舞,
 进而开始了促成韩中联合的努力,其代表人物是申圭植和他的侄子申衡浩及柳东说等人。
[1]
从此,开始有韩人以留学或者生活为目的而迁入中国关内地区。这些人组织起了抗日斗争的中心团体,并不断顺应时局而有所变化。
进而开始了促成韩中联合的努力,其代表人物是申圭植和他的侄子申衡浩及柳东说等人。
[1]
从此,开始有韩人以留学或者生活为目的而迁入中国关内地区。这些人组织起了抗日斗争的中心团体,并不断顺应时局而有所变化。
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的爆发,使国内外独立运动家受到极大的鼓舞,其结果是在中国上海建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临时政府)。这给韩中联合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国革命力量清醒意识到唇亡齿寒,毫不吝惜对韩国的扶持和支援。1932年,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的义举深深感动了中国人。在中国的全面支持下,临时政府为了培养反日独立军指挥员,将学员委托给中国军官学校进行训练。在中国的有力支持下,临时政府最终于1940年9月在重庆组建了韩国光复军。
与此同时,活跃在中国各地的独立运动家接受了各种社会思想,依靠韩中联合开展了抗日斗争。以国际主义者自居的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同中国的革命者,还同东亚其他国家的革命者一起建立了共同战线,其中东方无政府主义联盟是具有代表性的团体之一。自1931年日帝开始大陆侵略战争以来,韩人武装力量与吉林自卫军联合作战,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 [2] 毋庸置疑,韩中联合的共同抗日斗争是迫使日本帝国主义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重新探讨韩中联合抗日的意义。韩国革命者参与和支持了中国辛亥革命,这是他们拓宽眼界的决定性契机。之后的临时政府,在此基础之上发展成为抗日斗争的核心组织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在探索韩中两国的未来指向性关系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就是韩中联合的结果之一。
1905年11月韩日《乙巳条约》的签订,使韩国面临着生存危机。韩人的危机意识日益强烈,各种各样的抵抗运动揭竿而起。新闻人张志渊在《皇城堡新闻》上发表了题为《是日也放声大哭》的文章,反映出了当时韩国人的愤怒。一些卸任和在职的官僚以及在野的进步人士以自决或殉国的方式表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殖民统治以及通过武力疯狂镇压抵抗运动,在韩国全境造成了恐怖氛围。日本的血腥镇压和严密管制进一步加重了韩国社会的不安。
此时,值得关注的中国人是潘宗礼。在日本留学结束归国途中,他访问了京城(首尔)并目睹了日本人虐待韩国人的状况,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感到极为愤怒。他在船上碰巧从一位商人那里看到一份闵泳焕的遗书, [3] 然后说道:“忠臣之死还是晚了一步,就算想要捐躯救国也应该在死之前找到救国的方法。现在大势已去,流血又有什么用。中韩两国处于唇亡齿寒之紧密关系,韩国已经亡国了,中国也已经危在旦夕。但国民还没有这样的觉悟,我们不得不用鲜血去警醒他们。”潘宗礼写了多达14个条目的时局文章,拜托友人一定要转交给中国政府,之后纵身跳入大海壮烈殉国。对此,韩国人罗炳奎在1906年6月10日《大韩每日申报》上发表吊唁文章,标题为《吊清国义士潘公宗礼》,悼念潘宗礼的悲壮之死。 [4] 清朝大臣袁世凯在告知朝廷的同时,亲笔写下悲壮的悼词,以慰潘宗礼英魂。这一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对韩国的感情。
在此种危机意识之下,韩国启蒙论者和反日武装力量都在努力探索恢复国权的新方法。这是1907年大韩帝国时期最大的秘密团体新民会组织诞生的时代背景。当最主要的国家力量——军队被日本解散之后,新民会会员在倾力为守护国权而秘密地开展活动的同时,开始努力建立国外的抗日运动据点。他们直接到中国东北地区考察,选定了几个抗日根据地。为了培养反日独立军,他们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新兴武官学校。毕业于这一武官学校的军官在青山里战斗中发挥了中坚作用并取得了胜利, [5] 此次战斗在韩国反日独立战争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当韩民族正处在千钧一发之时,在中国,以建立共和制为目标的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金奎兴(别名金福)协助革命派势力并直接参加了辛亥革命。 [6] 申圭植是听到武昌起义消息之后下决心流亡中国的。他于1911年12月前后途经沈阳到达北京。当时住在北京的曹成焕给身居美国的安昌浩写信说:“申圭植等几个人听到这次中国事变的消息之后,已经从内地(即韩国——引者)来到了中国。” [7]
郑元泽也于1912年流亡到中国东北地区,他听到 “以孙文和黄兴为中心的革命运动已经在中国展开”的消息之后便来到南京留学。
 此外,李泰俊、金奎植等人也在获悉辛亥革命的消息后,下决心流亡到中国。曹成焕将“中国政变”的消息详细地报告给了安昌浩,也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时局的强烈关注。说当时韩国社会活动家或反日运动领导人等流亡中国是“时代的趋势”并不为过。
[8]
此外,李泰俊、金奎植等人也在获悉辛亥革命的消息后,下决心流亡到中国。曹成焕将“中国政变”的消息详细地报告给了安昌浩,也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时局的强烈关注。说当时韩国社会活动家或反日运动领导人等流亡中国是“时代的趋势”并不为过。
[8]
这些人中,金奎兴是从1908年开始接触中国革命派领导人并直接参与其革命活动的,主要任务是传达和保管宣传革命的传单或秘密文件。因为工作成绩被认可,后被任命为“广东护军使顾问”。
[9]
申衡浩在上海自愿加入中华学生军团后,做了一个月左右的事务工作。申圭植和曹成焕与黄兴见面时,表明了韩国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态度,并拿出自己的部分旅费赠给黄兴作军费。
 当时的韩中联合关系,可从申圭植所留下的五篇汉诗中得以一瞥。
当时的韩中联合关系,可从申圭植所留下的五篇汉诗中得以一瞥。
特别是申圭植与孙文的面谈内容,既表明了韩国人对辛亥革命的深切期待,也成为日后韩国人正式同中国人交往的基础。“听到孙文先生回到了上海并又要前往广东的消息,我非常渴望能见上一面。昨日晚上去了汇中旅馆,在胡汉民的介绍下见到了先生。在胡汉民恳切的邀请下一同乘坐电梯来到了先生的房间。先生让我坐下,但我还是站着先喊出了‘中华民国万岁,亚洲的第一位总统万岁’的口号。先生在百忙当中也对我亲切谈话,这是我无上的荣幸……孙先生表现出了对同胞无限的博爱以及对邻邦亡国的悲痛。我赞颂先生救世救民的伟大事业。”

与孙文会面以后,申圭植与中方关系变得更密切了。1912年8月初,发生了北京警察厅逮捕八名韩国人并移交给驻天津日本领事馆的事件。申圭植四处奔波,成功使这八名韩国人获释。
 申圭植与中国舆论界的关系也在摸索中前进。申圭植就任民权报社的经理后,报社就成为上海韩人留学生的联络处。这两件事并非毫无关系,它表明申圭植拟通过舆论界来为韩国独立运动寻求支持的意图。他与革命派的陈其美和宋教仁的接触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申圭植与中国舆论界的关系也在摸索中前进。申圭植就任民权报社的经理后,报社就成为上海韩人留学生的联络处。这两件事并非毫无关系,它表明申圭植拟通过舆论界来为韩国独立运动寻求支持的意图。他与革命派的陈其美和宋教仁的接触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与此同时,申圭植组建了由300余韩人组成的同济社,其主要人物为朴殷植、金奎植、申采浩、文一平、朴赞翊、申健植等。为了增进同中国革命志士的友谊,他们还成立了新亚同济社,中国方面的主要人物有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邹鲁、徐谦等。同济社和新亚同济社都是韩国独立运动的中心团体,也为新韩青年团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新亚同济社作为韩中联合的“出发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新亚同济社作为韩中联合的“出发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一运动以后建立的临时政府非常重视外交活动,在巴黎和会上采取怎样的因应战略成为首要的问题。以同济社为基础建立的新韩青年团推定金奎植为代表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他是临时政府建立后的首任外务总长兼巴黎委员部代表。他向大会提出《独立巩固书》之后,请各国代表将韩国问题提到会议议程。尽管在日本顽强的阻挠下最终失败,但这一努力并非毫无意义。
1920年7月,万国社会党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巴黎委员部副院长李灌镕和赵素昂作为代表参加会议,并设法让承认韩国独立的决议案在会议上获得通过。李灌镕作为代理委员长,散发英文版和法文版的《自由韩国》等杂志,并在欧美181家报刊上登载有关韩国的消息,展开宣传活动。在他们的努力下,最终在英国成立了大英帝国韩国亲友会。
 他们在伦敦和巴黎的外交活动,对韩国争取外交地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他们在伦敦和巴黎的外交活动,对韩国争取外交地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临时政府欧美委员部负责在美国的外交活动。李承晚在华盛顿开设了临时大总统公馆和欧美委员部事务所,在北美和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等地也都建立了地方委员会。徐载弼负责的位于费城的韩国通信部和金奎植曾经工作过的巴黎韩国代表部都隶属欧美委员部。1919年6月,李承晚以总统的名义向与大韩帝国缔结过条约的各国发出通告:业已建立了共和政府的新韩国诞生了。在美国也成立了支持韩国人独立运动的团体。这些团体成为韩国在北美地区开展反日独立运动的骨干力量。
从1920年开始苏俄也成为韩国主要的外交对象国家。时任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李东辉主要负责此事。1月22日,临时政府国务会议上选定韩亨权、吕运亨、安恭根三人为派驻苏俄的外交官。但李东辉私下里只委派了韩亨权一个人,引起了争议。与列宁的会面等,成了临时政府同苏俄正式交往的第一次活动。
 1921年5月,申圭植以国务总理的名义派遣安恭根为新任代表,并一直努力维持同苏俄的关系。
1921年5月,申圭植以国务总理的名义派遣安恭根为新任代表,并一直努力维持同苏俄的关系。
对中国的外交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中国是韩人开展反日独立运动的现场。但同中国的外交,因为受到中国政局不稳的影响时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北京和广东势力的分裂局面给临时政府造成了混乱,临时政府将视线瞄向了广东。与那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中国人的交往,对临时政府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特别是政治理念的相似,提供了很好的氛围。临时政府成立后,同中国的交涉或交流合作就成为重要的政策,受到了重视。具体的外交方案都由“对中国外交团”制定,写入“同各国的外交事务”当中。 [10] 同中国的正式外交关系一直持续到1948年。这是韩中友好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
对中国外交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申圭植访问广东护法政府。护法政府在孙文的领导下于1921年5月成立。当时正是李承晚居住上海6个月之后即将返回美国的时期,“根据阁下(指李承晚——引者注)前往美国之前业已内部下达的命令事项,9月22日国务会议决定任命本职为特使派遣至广东。”

9月末,临时政府代国务总理兼外务总长申圭植在广东会见孙文,提出了“互惠条约五款”,其主要内容如下:
(1)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护法政府是中国的正统政府,同时尊重其元首和国权;
(2)请中华民国护法政府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3)请中华民国军官学校招收韩国学生;
(4)请求借款500万元;
(5)请求允许租借场地并帮助培养韩国独立军。

(1)和(2)是要求双方政府相互承认,(3)是请求中国帮助培养独立军干部,(4)和(5)是经济支持和提供根据地。孙文说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予以答复。当时孙文领导的护法政府只掌控广东一省,处于不被其他国家承认的状态,在活动地区和财政方面都有很大局限性。虽然形式上双方没有相互承认,但实际上可以认为是相互之间已经承认的状态。首先,孙文在广东国会上制定并通过了“韩国独立承认案”。其次,申圭植正式会见孙文象征着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式确立。最后,1922年2月,临时政府任命外事局局长朴赞翊为驻广东代表,掌管其外交事务。 [11]
临时政府的外交活动,在韩国近代外交史当中被评价为是非常重要的外交活动。自己国家丧失后,在其他国家建立的临时政府进行外交活动,这在世界史上也是绝无先例的。其外交活动并不排除军事活动,也不是排他性地进行的,而是支援独立战争或与独立战争并行的重要战略行动。临时政府认识到外交战略是军事战略的基础,他们认为,为了最终完成独立,要通过国际外交活动争取援助,培养军事力量是更为明智的方针策略。

真正的韩中联合是在1932年4月尹奉吉上海虹口公园义举之后。外交斗争策略和反日战争准备策略确定之后,“义烈斗争方略”又作为一个重要的形式,使停滞不前的韩国独立运动再一次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尹奉吉义举之后,临时政府从中国各界收到了多达3万美金的支援款。
 中国的支援并不限于资金,以国民党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为主,陈立夫、贡沛诚等共同负责组织调配中国政府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援。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在同蒋介石会面时,请求帮助培养反日独立军士官。国民党政府在军官学校开设了韩人特别班,以此积极支援以临时政府为首的韩国独立运动团体。韩人特别班的正式名称为“中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第二总队第四大队陆军军官训练班第十七队”,其设置的目的在于帮助韩人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建设完全独立的国家,培养可以指挥工人和农民的独立运动的干部。课程教育则根据学员的中文会话能力编为两个班。
中国的支援并不限于资金,以国民党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为主,陈立夫、贡沛诚等共同负责组织调配中国政府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援。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在同蒋介石会面时,请求帮助培养反日独立军士官。国民党政府在军官学校开设了韩人特别班,以此积极支援以临时政府为首的韩国独立运动团体。韩人特别班的正式名称为“中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第二总队第四大队陆军军官训练班第十七队”,其设置的目的在于帮助韩人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建设完全独立的国家,培养可以指挥工人和农民的独立运动的干部。课程教育则根据学员的中文会话能力编为两个班。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活跃在中国军队,金弘壹、安昌南、权基玉、李相定等是这些人中的代表。中国政府将韩国毕业生编成教导队,将其划归到别动队中。他们的任务是“编入中国军队中参加反满抗日活动;派遣到满洲地区,联系反满抗日团体侦察日、‘满’军的军事设施和侵略机关,并且为军官学校招募生源”。
[12]
在此基础上,金九将韩人爱国团、韩国特务队独立军和学生训练所进行整合,编为特务组织。韩国特务队独立军是支持金九的最实质性的中心机构。

1935年日本成立兴中公司,其目的是强化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让日本民营企业进入华北地区,并掌握其资源和市场,妄图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将华北地区变为日本的原料供给地。 [13]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东、武汉之后,由进攻转入相持状态。《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后,苏联增强了对中国的武器援助。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进入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势力相争的阶段。日本的侵略政策将“点与线”视为根本,即将主要城市视为据点,而在连接各大城市的主要铁道上配置日军兵力。
同时,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的韩国独立军由于日伪军队的攻势以及韩人社会团体的瓦解等,开始向关内地区转移。日帝对韩人社会的严厉管制,使韩人的活动空间变得更加狭小。“满洲就像蜕皮后的蚕壳,只剩下了空壳一般无力的表象。”“各地朝鲜人社会中,人们身在险恶的政治形势下左顾右盼,不能鲜明地表达态度。从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中脱离或隐藏起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道路上出现了巨大的障碍。”
 这些叙述都反证了当时的情况。1932年夏天,韩人开始讨论向关内地区派遣特使的问题,目的是争取中国政府和抗日势力的支援,同时与关内地区韩人势力实现联合。在此情况下,金九的“移动提案”和财政支援是适合时宜和鼓舞人心的。
这些叙述都反证了当时的情况。1932年夏天,韩人开始讨论向关内地区派遣特使的问题,目的是争取中国政府和抗日势力的支援,同时与关内地区韩人势力实现联合。在此情况下,金九的“移动提案”和财政支援是适合时宜和鼓舞人心的。
尹奉吉的虹口公园事件以后,临时政府在日本军警的疯狂追捕下,不得不在中国各地频繁转移,过着极不稳定、极不安全的生活。“1938年12月27日上午11点左右警报声响起来了。为了躲避敌机,我们跑向了唯一一处避难处。这地方虽然是平地,但有一块公墓,还有茂盛的竹林。据说,曾躲在树下面的人群遭受了敌机的扫射,我们就紧躺在坟墓的两侧。像我们这样躺在坟墓旁边、躲在草丛中的避难者,在田野中到处躲藏,卧倒在地。这是最令人窒息的瞬间。我们都不知道谁将是下一枚炸弹的牺牲品。我们抬着头望着天空,看着炸弹黑压压地落下来。” [14]
临时政府在1937年8月20日以“临时政府国务院”的名义发布公告说:“我们不论从人类道德上,还是从历史的亲姻关系上都应该用尽所有力量援助中国。不仅如此,为了报复对倭敌二千余年来积攒的仇恨,我们期待倭敌的灭亡,并且为消灭倭敌而努力……就算在倭敌极端的压迫和统治之下,人的意志也会像钢铁一样坚定;已经参加运动团体的要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团体当中,没有参加团体的可以直接来政府献力。” [15]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韩中联合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迁至重庆的临时政府着手建立韩国光复军。临时政府提出,光复军的建立将有利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以此说服中国政府。创设委员长金九说:“光复军将与中华民国国民合作,为恢复两国的独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共同的敌人。为此我们将作为联合军的一员继续抗战到底。”1940年9月17日,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的光复军成立典礼上,吴铁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国各方面的代表人士出席,仪式显得格外隆盛。美洲的韩人也予以积极的支持,临时政府的军备资金也随之大幅增加。
光复军指挥官是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军官学校、东北新兴武官学校等军校出身者担任的。中国不仅支援光复军的军需物资,还积极予以经济上的援助。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和朝鲜义勇队被编入光复军,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完成的。战地工作队原是无政府主义团体,是由在西安活动的100余韩人组成的。被日军强征的韩人士兵也都纷纷逃离侵略军,加入光复军。至1945年8月,光复军总人数达到了700余名,已经发展成为拥有3个支队的军事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军队。
 为了祖国光复而组建的国内挺进队,完全是在中国的支援下建立的。
为了祖国光复而组建的国内挺进队,完全是在中国的支援下建立的。
为了促进韩中联合的发展而成立的“中韩文化协会”,在促进韩中人士交往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42年10月,韩国的金九、赵素昂、金元凤、池青天等和中国方面的冯玉祥、白崇禧等400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是民间层面的友好团体,理事长是孙文之子孙科,副理事长是赵素昂、金奎植等。成立大会的主题是团结,中共代表周恩来谈到他在军校时与韩国同志一起学习、工作的事情。他说朝鲜志士们的热血洒到了中国的大地上,所有人的目标都是恢复国权与独立,如果说有差异,那也只是方法上的不同而已。

中韩文化协会经常举办演讲会等,一般是在三一运动纪念日、临时政府成立纪念日或国耻纪念日等进行,讨论韩中合作、临时政府承认问题以及韩国独立问题等。冯玉祥在强调中韩合作时说,中韩两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的胜利和同盟国的胜利就是韩国的胜利。中韩要相互帮助,相互关心,要对胜利充满信心。国民参政会也在1944年9月提案要求国民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中韩文化协会在重庆还创办了机关杂志《中韩文化》和《中韩会讯》。
中韩文化协会不仅在韩国独立运动史上,而且在韩中关系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它将韩国的地位设定在与中国对等的高度上,这是提高临时政府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中韩文化协会带头组织演讲会、座谈会等各种活动,为进一步促成韩中合作以及临时政府的国际承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光复以后,在华韩人归国的时候,中韩文化协会又起到了窗口的作用。
光复以后,在华韩人归国的时候,中韩文化协会又起到了窗口的作用。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韩中联合为黑暗的韩人社会点亮了一盏明灯。
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使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针对大陆的侵略。继台湾之后,日本加快了对大韩帝国的殖民进程。1905年的《乙巳条约》剥夺了大韩帝国的外交权,使其在实质上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韩国的先驱们一方面谋求恢复国权,另一方面开始在国外建立反日独立运动的基地。大韩帝国末期最大的秘密反日团体新民会是主导这一伟业的核心团体,业已形成韩人移民社会的中国东北和苏联沿海州地区成为他们的目标。东北新兴的武官学校培养出的独立军骨干在韩国反日独立战争史上留下了辉煌的战果。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唤起了韩国人对独立运动的关注。1908年流亡到中国广东地区的金奎兴直接参与了中国革命运动,负责传达和保管秘密文件,并且全身投入在宣传工作上。申圭植、朴赞翊、郑元泽等也同中国革命派人士接触并且无私地援助了中国革命。新亚同济社作为韩中联合的起点,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1919年4月在上海建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点开展了外交活动。金圭植作为临时政府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将韩国成立独立的临时政府的消息向国际社会广泛宣传。在欧美组织韩国亲友会也是这一时期外交上的一大成果。李承晚以美国为中心开展外交活动。当然最主要的是对中国的外交活动。金圭植代表临时政府与广东护法政府结成了友好关系,使临时政府在外交实务上迈出了第一步。
临时政府以尹奉吉义举事件为契机,从中国方面得到了大量支援。为了培养独立军干部,金九在同蒋介石会面时要求予以协助,并得到了蒋的同意。在中国军官学校内设置韩人特别班,毫无疑问,这彰显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1940年迁往重庆的临时政府为建立韩国光复军奔走努力,国民党政府提供了武器和军费作为支援,使韩国独立军士气振奋。在民间层面上则建立了中韩文化协会,这是专门促进两国交流的中心团体。日本战败后,直到1948年,中韩文化协会一直在两国间发挥纽带作用。韩中两国间强有力的联合关系是日帝殖民统治时期韩国独立运动发展的源泉,韩中联合如此受到重视也源于此。
(孙泓 译)
[1]
姜英心,「申圭植
 生涯与独立运动」,『韩国独立运动史硏究』1,1989,41页。
生涯与独立运动」,『韩国独立运动史硏究』1,1989,41页。
[2]
『中外日报』1929
 2
2
 16
16
 「东邦无政聨盟
「东邦无政聨盟
 李丁奎公判」;韩国独立运动史硏究所,『韩国独立运动
李丁奎公判」;韩国独立运动史硏究所,『韩国独立运动
 大甸子岭战鬪』,2013。
大甸子岭战鬪』,2013。
[3]
金炯睦,「义烈·殉国

 乙巳勒约
乙巳勒约
 不法性
不法性


 民草等
民草等
 外国人」,『官报』6月号,独立纪念馆,1911。
外国人」,『官报』6月号,独立纪念馆,1911。
[4]
『大韩每日申报』1906
 6
6
 2、3、8、10、126
2、3、8、10、126
 杂报「吊淸国义士潘公宗礼文」。
杂报「吊淸国义士潘公宗礼文」。
[5]
愼镛厦,「独立军
 靑山里战鬪」,『军史』8,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1984;朴桓,「满洲地域
靑山里战鬪」,『军史』8,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1984;朴桓,「满洲地域
 新兴武官学校」,『史学研究』40,1989;徐仲锡,「靑山里战争独立军
新兴武官学校」,『史学研究』40,1989;徐仲锡,「靑山里战争独立军
 背景」,『韩国史研究』 111,2000。
背景」,『韩国史研究』 111,2000。
[6]
裴京汉,「韩国独立运动
 辛亥革命」,『韩国近现代史硏究』75,2015,79页。
辛亥革命」,『韩国近现代史硏究』75,2015,79页。
[7]
「曺成焕
 安昌浩
安昌浩



 便纸(1911年12月 11日)」,國會圖書館收書整理局編,『島山安昌浩資料集』2,國會圖書館,1998。
便纸(1911年12月 11日)」,國會圖書館收書整理局編,『島山安昌浩資料集』2,國會圖書館,1998。
[8]
裴京汉,「韩国独立运动
 辛亥革命」『韩国近现代史研究』75、82页。
辛亥革命」『韩国近现代史研究』75、82页。
[9]
《护军使署职员表》,《广东公报》1913
 1
1
 18
18
 。
。
[10]
裵京汉,『孙文
 韩国』,
韩国』,
 ,2007,76页。
,2007,76页。
[11]
金俊燁,「韩国独立运动
 协助
协助
 中国人士」,『石麟閔弼鎬傳』,146页。
中国人士」,『石麟閔弼鎬傳』,146页。
[12]
金弘壹,『大陆
 愤怒:老兵
愤怒:老兵
 回想记』,文潮社,1972,297页。
回想记』,文潮社,1972,297页。
[13]
『每日申报』 1937
 10
10
 20
20
 「北支开发着手兴中公司
「北支开发着手兴中公司
 旣定计」;「興中公司の足跡(一) 占據地の建設工作擔當/努力!今や完全に結實」『满洲日日新闻』1940年12月4日。
旣定计」;「興中公司の足跡(一) 占據地の建設工作擔當/努力!今や完全に結實」『满洲日日新闻』1940年12月4日。
[14]
楊宇朝、崔善嬅,『


 日記』,
日記』,



 (金枝)出版社,1999,55~56页。
(金枝)出版社,1999,55~56页。
[15]
『新韩民报』1937
 10
10
 7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