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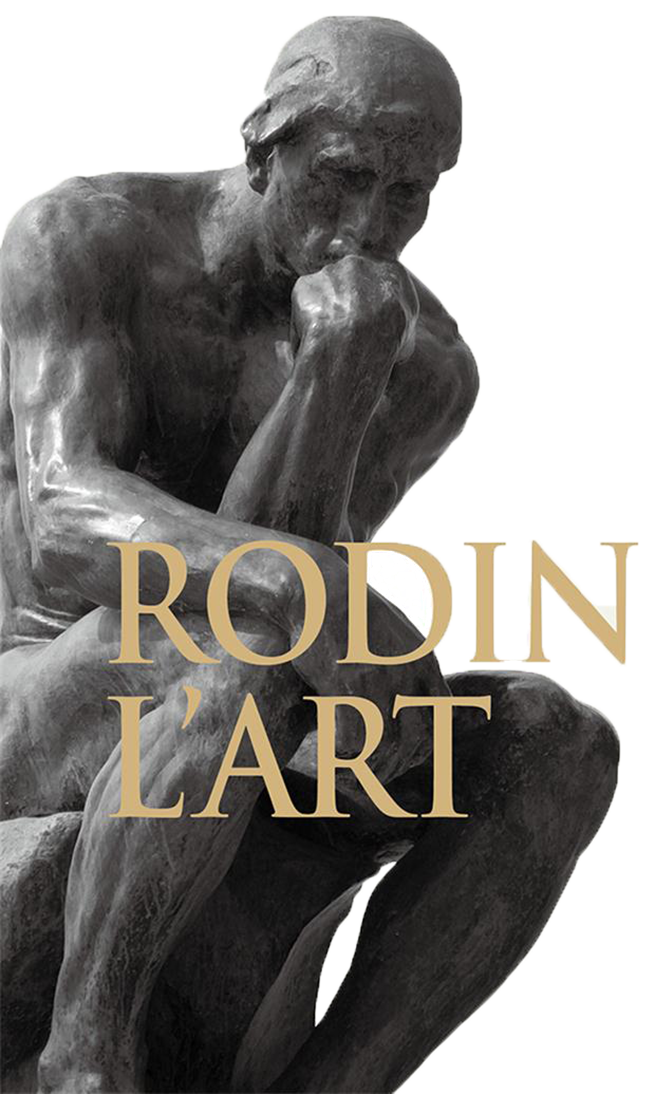
一个傍晚,我到罗丹的工作室中去访他,天色很快地黑暗下来,我们尽自在谈话。
忽然,主人问道:
“你有没有在灯光下看过古代雕像?”
“没有。”我错愕地回答。
“你觉得奇怪罢,且你将以为不在白日下去赏鉴雕像的念头有些异想天开吧?
“固然,在自然的光亮之下,我们是能鉴赏一件艺术品的全部……但是,且慢,我要使你多一些经验,广广你的眼界。”
一面说,一面就点起灯来。
他拿了灯,领我走向放在工作室一隅的一座雕像面前去。
这是《梅迭西斯的维纳斯》(Venus de Medicis)的小小的临本,罗丹把他放在这里,以备在工作时,可以激动灵感。
“走近来!”他和我说。
他把灯从侧面最逼近的地方照着雕像的腹部。
“你注意到什么东西?”他问我。
一眼望去,我就被吸引住了。在这样安置的光线之下,使我看到在白石的面上,有无数的细微的凹凸,为我从来没有梦想到的。
我把这发现告诉了罗丹。
“对呵!”他首肯着回答。
接着,又说:
“看仔细!”
同时,他把承托维纳斯的座子缓缓地转动。在这当儿,我继续留意到在全个腹部的形体上,有着不知多少为感觉捉摸不到的凹凸。最初看来似乎是简单的东西,实际上是复杂无比。我又把这观察告诉了这位大师。
他微笑颔首:
“不是神奇吗?”他重复着说,“你当初一定想不到会发现这些隐秘吧?照!……照这些从腹部到大腿间的无穷的波纹,与臀部的富有肉感的曲折。还有,那边,腰部的可爱的小窝。”
他讲话的声音很低,充满着虔敬之情。他俯身在白石上,如偎依着他的爱人一般。
“这是真正的肉呢!”他说,“几可说是受尽了亲吻与爱抚。”
他又突然把手掌平放在像的臀部:
“在抚摩这半身像
 时,竟觉得它的温暖。”
时,竟觉得它的温暖。”
一会儿之后:
“那么,你现在觉得一般人对于希腊艺术的见解和批判是如何?
“他们——尤其是学院派专在鼓吹,古人在注重理想的探求中,蔑视肉体,以其为粗鄙的、卑下的,故他们不准把现实的各种精微之处尽情表现。
“他们以用简洁的形式,创造抽象的美为口实,而改变自然。这抽象的美只与精神相通而与感官则绝不激动。
“唱这种调子的人,自以为在古艺术中就有他们的根据,于是改变自然,剪削自然,把他归纳于枯索的轮廓之中,冰冷的,单调的,与‘真实’毫无关系的形式。
“你刚才目击的情形,就足以证明他们是如何谬误了。
“无疑的,具有特别的论理的头脑的希腊人,本能地就把主要特点标明出来,他们把统辖人体的主要线条勾画了,但同时,他们也从不省略生动的局部,他们要把局部融冶于全体中,因为他们爱好沉静的节奏,故他们不知不觉地把次要的起伏凹凸删减了,惟恐这些次要的部分破坏整个动作的平和清明的调子,然而他们并不完全抹煞局部。
“他们从没有把欺诈的手段当作一种方法。
“充满着对于自然的钟爱和尊敬,他们只表现他们所见到的自然。到处他们表示着对于肉体的崇拜。说他们轻蔑肉体,岂非笑话。任何民族,都没有对于肉体的美引起同样温柔的感觉。他们的作品,即是浮沉在这种肉的沉醉之中。
“希腊艺术之别于矫伪的学院派者即在此。
“古艺中之线条的概括是一种归纳,是无数局部的综合。至于学院派之所谓简洁,却是贫乏、空疏与松懈。
“生命之血在希腊雕像的筋肉中横流奔腾;学院派的作品只是冰冷的木偶,它是死。”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我告诉你一桩秘密罢。
“刚才你在维纳斯面前所感到的生命活跃的印象,你道是怎样来的?
“是靠了模塑的方法得来的。
“这句话你初听也许觉得平凡,觉得是老生常谈,但你得知道它的重要。
“模塑的学问,是一个叫作公斯当的教我的,他当时和我在一个工作室里正开始学雕塑。
“一天,他看我做一个饰有树叶的帽子的泥塑:
“‘罗丹,’他和我说,‘你做坏了。你的树叶都是平扁的,故看来就觉得是假的。把它们塑得使尖瓣正向着你,要令人看了有深厚的感觉。’”
“我依了他的劝告做,我对着这工作的结果,不胜惊喜。
“‘牢记我的话罢,’公斯当接着说,‘你以后雕塑的时候,切不要从广处着眼,而要从深处着眼……要永远把一个平面当作是一个体积的边线看,当作向着你的一个尖端看。这样你便可悟得模塑的学问了。’”
“这个教训使我得到丰富的收获。
“我把这方法应用于人体,我的观察人体各部,并不把它看成一片或低陷或平坦的面,而专心去表现它的体积的凹凸,在臀部或四肢的饱满处,我务使它有筋肉在皮下潜伏伸张的感觉。
“于是我的人体不但是表面的真实,而是由内而外的真实,有如我们的生命一般……
“而我发现古艺人正是用的同样的模塑法。他们作品之有力而又柔和,即得力于此。”
罗丹重新观察着他的希腊的维纳斯,突然说:
“葛赛尔,你以为色彩是画家的技巧呢,还是雕刻家也有的?”
“自然是画家的啰。”
“那么请观察这座像。”
他说完便高举着灯,使光从上面下射到雕像上。
“你瞧这胸部的强烈的光,皮肤褶叠处的深暗的影,还有那褐色,那布满于这神圣的躯体上的颤动着的半明的雾雰,这是沐浴于空气中而像要溶解一般的部分。你怎么说?这里,岂不是一阕奇妙的黑与白的交响乐么?”
我只有表示同意。
“说来似乎有些大胆,然而大雕刻家确和大画家大镂刻师
 一样富有色感。
一样富有色感。
“他们深悟一切色阶之旋律,他们把强烈的光明与微弱的阴影配置得如是奇妙,以至他们的雕像可与最动人的镂版有同样深厚的韵味。
“可是色彩——我特别要提出这一点——有如美的模塑之花。模塑与色彩两者是不可分离的。而一切雕塑的杰作,其动人的肉感,也即是由这两个条件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