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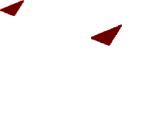 前言
前言
《童年》《少年》《青年》这三个中篇小说是托尔斯泰的成名作。《童年》最早发表于一八五二年,托尔斯泰那时只有二十四岁;两年后《少年》发表,一八五七年《青年》发表。评论界把这三部作品习惯合称“自传体三部曲”。自传体文学固然有回忆录的形式,并且具有对当时生活记录的真实性,但其主要功能并不在于回顾作者的既往生活,所以不能把它当作“自传”来看,托尔斯泰在晚年谈到这部作品的时候也说,他写的并不仅仅是自己的经历,而是他所熟悉的人们的经历和他自己的童年体验的“混合”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些不同人的经历混合到一个或几个人物身上来表现呢?这就涉及自传体文学的功能,就是有选择地表现人生历程,从而反省人的生活之路到底如何走,借助于对主人公生活的描写来表达作家本人对这个世界、对人自身的存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价值立场。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些不同人的经历混合到一个或几个人物身上来表现呢?这就涉及自传体文学的功能,就是有选择地表现人生历程,从而反省人的生活之路到底如何走,借助于对主人公生活的描写来表达作家本人对这个世界、对人自身的存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价值立场。
因此,我们通过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既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一个俄罗斯贵族家庭的真实生活,更主要的是发现作家本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对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理念。这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托尔斯泰诞辰一百九十周年出版这个自传体三部曲的一个重要原因。
托尔斯泰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尽管他在幼年的时候父母就相继去世,是被姑姑带养成人,但这并不妨碍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生活在富裕,甚至是奢华的环境之中。也就是说,他一直是作为俄罗斯极少数拥有巨大财富的统治阶级的一员而存在,而这个时候的俄国还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在赤贫状态。这种社会状况在俄国持续了几个世纪后,到了十九世纪,俄国的贵族知识阶层首先觉醒,意识到俄国如果想要进入现代文明国家行列,必须要解决野蛮的农奴制问题。农奴制是俄国特有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大量农奴的存在意味着俄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在十九世纪中叶前高达30%—46%
 )在从事最原始的经济活动,这阻碍了俄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西欧国家即将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其次是专制压迫的问题,农奴不仅失去了经济自主权,也被剥夺了思想的自由。因此,从一八一二年反法战争胜利之后,俄国社会中废除农奴制的呼声便越来越高,直到一八六一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解放农奴宣言。这就是托尔斯泰前半生所面对的俄国的现实。
)在从事最原始的经济活动,这阻碍了俄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西欧国家即将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其次是专制压迫的问题,农奴不仅失去了经济自主权,也被剥夺了思想的自由。因此,从一八一二年反法战争胜利之后,俄国社会中废除农奴制的呼声便越来越高,直到一八六一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解放农奴宣言。这就是托尔斯泰前半生所面对的俄国的现实。
当时的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主要考虑制度变革的方法,而托尔斯泰的解决方案与当时俄国的主流观念相对立。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制度是原始的农耕社会、宗法制社会,既不是当时的帝国专制,也不是西欧的代议制。在他看来,人类生存状况的恶化就在于国家制度破坏了人类原初的和谐状态,而更重要的是导致人类心灵的恶化。所以,托尔斯泰提出:俄国社会亟须变革,但不能仅靠国家制度的变革,更不能通过暴力革命,因为暴力即使能够暂时带来转机,却会埋下更多暴力的种子。这就是托尔斯泰主义的首要原则。
我们以往对托尔斯泰主义的理解更多地夸大了这一原则,却忽略了这只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个前提,而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命题是:通过人的心灵改造来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主要是说在他身上反映了俄国社会的深刻矛盾。基于列宁的评价,此后的许多评论都过分强调了托尔斯泰主义中的批判性和妥协性的部分,却遮蔽了这其中在今天看来十分重要的东西——作为统治阶层的贵族的心灵忏悔、道德完善的内容。而这一点恰恰是俄罗斯文化精神中最具合理性的特点。当托尔斯泰在宣扬他的道德主义的时候,绝不是什么“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而是一个伟大的人类精神的维护者。在他看来,任何社会制度的设计者如果没有人的道德支撑,这个制度都将成为当代的奴隶制。因此,就俄国而言,贵族作为这个社会的主导阶级,首先要从他们的灵魂开始更新,从而引导整个社会走向真正的和谐。
高尔基说,托尔斯泰的创作实践“就是企图把良善的俄罗斯贵族安插在俄罗斯生活里面”,而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
 高尔基所说的这件艰巨的工作,就是从自传体三部曲开始的。这是年轻的托尔斯泰最初的文学活动,他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加以描写,但无形中开创了他一生文学创作的重大使命——从一个贵族的成长来思考人的存在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托尔斯泰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个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
高尔基所说的这件艰巨的工作,就是从自传体三部曲开始的。这是年轻的托尔斯泰最初的文学活动,他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加以描写,但无形中开创了他一生文学创作的重大使命——从一个贵族的成长来思考人的存在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托尔斯泰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个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在自传体三部曲中看到的主人公,贵族少年尼古连卡,就是高尔基所说的“宛若太阳反映在一滴水点上”的那个“水点”。可以说,整个三部曲就是尼古连卡心灵成长的历史,这个自幼缺少爱的孩子,最大的特点不是对这个世界发出抱怨,而是不断的自我反省。在他身上,无疑会有在那个特定环境中养成的等级观念,但每当这种念头产生的时候,他的心中就会有另一个声音发出自我谴责。“爱和羞愧”,这就是托尔斯泰对人与上帝关系的基本理解。
在托尔斯泰看来,越是那些生活在底层、没有受过所谓当代教育的人,心灵离上帝越近。所以,在小说中,托尔斯泰把这种爱的品格更多地赋予了那些侍仆。
比如,在托尔斯泰心目中,娜塔利娅就是上帝仆人的典范。娜塔利娅生命中唯一的精神寄托便是上帝,正因为如此,她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人。有评论认为这个形象反映了托尔斯泰本人固有的贵族立场,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个形象反映了托尔斯泰对他所身处的贵族阶级的反叛。在他的笔下,作为贵族的父亲、外祖母以及大量身份显赫的人物,从来没有想到过上帝,而作为下人的娜塔利娅,直到临死的时候还 “呼唤上帝”——祈祷,是东正教文化的一个特色。《童年》中描写了一个圣愚苦行者格里沙,他的神圣性就体现在他的祈祷上。格里沙白天行事乖张,夜晚却久久地向上帝祷告、忏悔、哭泣。这个情节本是托尔斯泰童年的亲身经历。托尔斯泰把人在内心与上帝进行交流视为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虽然他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东正教徒。可以这样理解,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带有明确的世俗生活目的,在内心深处与上帝同在的现实意义就是时刻在心中呼唤良知。
总之,人面对上帝的问题也就是人面对他人的问题,两者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面对上帝——忏悔;二是面对他人——爱。也就是小说中说的“爱和羞愧”。
小说围绕着主人公尼古连卡主要写了他的三种人际关系:“我”与贵族圈中的人(包括家中的长辈),与侍仆,与朋友(包括兄弟姐妹和恋人)。
非常明显,作者对贵族圈中的人普遍持否定态度,因为在作者看来,这些人就是亟须灵魂改造的人,他们掌握着大量奴仆的命运,甚至掌握着整个俄国的命运,但俄国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些人缺少对自己灵魂之恶的反省。
在尼古连卡与侍仆的关系上,小说不吝笔墨,把人与人之间美好的爱寄寓其中。这首先体现在自幼看着他长大的娜塔利娅·萨维什娜身上。尼古连卡与她的关系,与其说是主仆的关系,不如说她既是他的知心朋友,也是他成长的一个“镜像”。这个知心朋友给了他从父母和兄弟姐妹那里无法获得的真正的理解和抚慰,他从这个镜像中学到了爱,学到了自我反省。
小说还对家庭教师卡尔·伊万内奇这个人物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小尼古连卡在悲伤的时候常常想,他自己的命运甚至与卡尔是一样的,都是被命运所抛弃的人。
尼古连卡与同龄人的关系才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他从来都是怀着强烈的渴望融入对方的心灵世界,然而不幸的是,他遭遇得更多的是拒绝和隔膜。他渴望与所有人相爱,他天真地以为所有人都爱他,理解他,但其实这往往成为他自己的“一厢情愿”。作为一个童真未泯、良知清醒的贵族少年,尼古连卡就这样被他自己的阶级拒绝,成为一个孤独的觉醒者。在尼古连卡的同龄人中,有一个人物甚至对于整个托尔斯泰的创作来说都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就是德米特里·涅赫柳多夫。
《复活》中的涅赫柳多夫是最后一次出场,而他的第一次出场就是在自传体三部曲中。如果说尼古连卡这个形象的原型更多的是托尔斯泰本人,那么涅赫柳多夫则完全是作家按照他的理念设计出来的人物,或者说是托尔斯泰理想中的自我。高尔基甚至认为,涅赫柳多夫形象就是俄罗斯生活的象征:“六十年来,涅赫柳多夫公爵驰骋于俄罗斯……六十年来,他的严厉而正直的呼声在呐喊,在揭发一切;他告诉我们俄罗斯生活,几不下于全部俄国文学。”

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具有明显的特色,是对其生命理念的极为出色的表达形式。
一般评论都把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看作“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但这类小说的一个特点是主人公的“成长”,即巴赫金所说的“人在历史中成长”,因为历史发生了变化,人不能不随之而变化。
 但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不是典型的此类成长小说,因为其中既没有写出历史的变化,也没有写出人物的成长。托尔斯泰的基本立场是描写人的心灵变化,无论历史如何变动,人的心灵的“历史”是同一性的,如果说它有一个变化或成长过程,那么这也是一个永恒的模式:纯真——罪孽——复活。而实质上,这三个生命阶段往往是在同一个时间中存在的,这也源于托尔斯泰对于生命的理解。每个人同时既受到原初的纯净的灵魂的支配,同时也受到世俗之恶的诱惑,而这两种力量的博弈就是人的复活的表征。托尔斯泰对孩子有着特殊的喜爱,原因就是他在孩子身上看到了人的美好品格,一方面他说:“孩子也并非无罪。在他们身上比成年人较少罪孽而已,但他们已有肉体罪孽。……没有罪孽,就没有生活。”一方面他又说:“孩子比成年人更睿智。小孩不会分辨人们的称谓,而是用全副的灵魂去感受人人身上存在的、对他和所有人来说都是同一的东西。” “不要相信无法做到人人平等、或者它只能在遥远的将来才可能实现的说法。要向孩子学习。”
但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不是典型的此类成长小说,因为其中既没有写出历史的变化,也没有写出人物的成长。托尔斯泰的基本立场是描写人的心灵变化,无论历史如何变动,人的心灵的“历史”是同一性的,如果说它有一个变化或成长过程,那么这也是一个永恒的模式:纯真——罪孽——复活。而实质上,这三个生命阶段往往是在同一个时间中存在的,这也源于托尔斯泰对于生命的理解。每个人同时既受到原初的纯净的灵魂的支配,同时也受到世俗之恶的诱惑,而这两种力量的博弈就是人的复活的表征。托尔斯泰对孩子有着特殊的喜爱,原因就是他在孩子身上看到了人的美好品格,一方面他说:“孩子也并非无罪。在他们身上比成年人较少罪孽而已,但他们已有肉体罪孽。……没有罪孽,就没有生活。”一方面他又说:“孩子比成年人更睿智。小孩不会分辨人们的称谓,而是用全副的灵魂去感受人人身上存在的、对他和所有人来说都是同一的东西。” “不要相信无法做到人人平等、或者它只能在遥远的将来才可能实现的说法。要向孩子学习。”
 这就是托尔斯泰的成长观:人在童年时代一方面是纯真的,一方面靠着某些本能生活,所以,他需要把这些生物性本能清除掉,才能真正成为只靠灵魂生活的人;然而,成长的过程同时也是被世界污染的过程,所以,人在步入成年后应该努力回归童真。
这就是托尔斯泰的成长观:人在童年时代一方面是纯真的,一方面靠着某些本能生活,所以,他需要把这些生物性本能清除掉,才能真正成为只靠灵魂生活的人;然而,成长的过程同时也是被世界污染的过程,所以,人在步入成年后应该努力回归童真。
高尔基曾说:“托尔斯泰的创作之历史意义,今日已被评为整个十九世纪俄国社会一切经验之总结,他的作品将永世留存,俨若天才的顽强劳动的纪念碑,他的作品乃是说明一个顽强个性在十九世纪为了替自己在俄国历史上寻求地位和事业这目的而做的一切探索的文献。”
 而我要说,托尔斯泰的意义远不只对十九世纪的总结,更重要的是对人类未来的精神发展的永恒预言。
而我要说,托尔斯泰的意义远不只对十九世纪的总结,更重要的是对人类未来的精神发展的永恒预言。
王志耕
二一八年九月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