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red Diamond
贾雷德·戴蒙德
美国进化生物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地理学家
著有《枪炮、病菌与钢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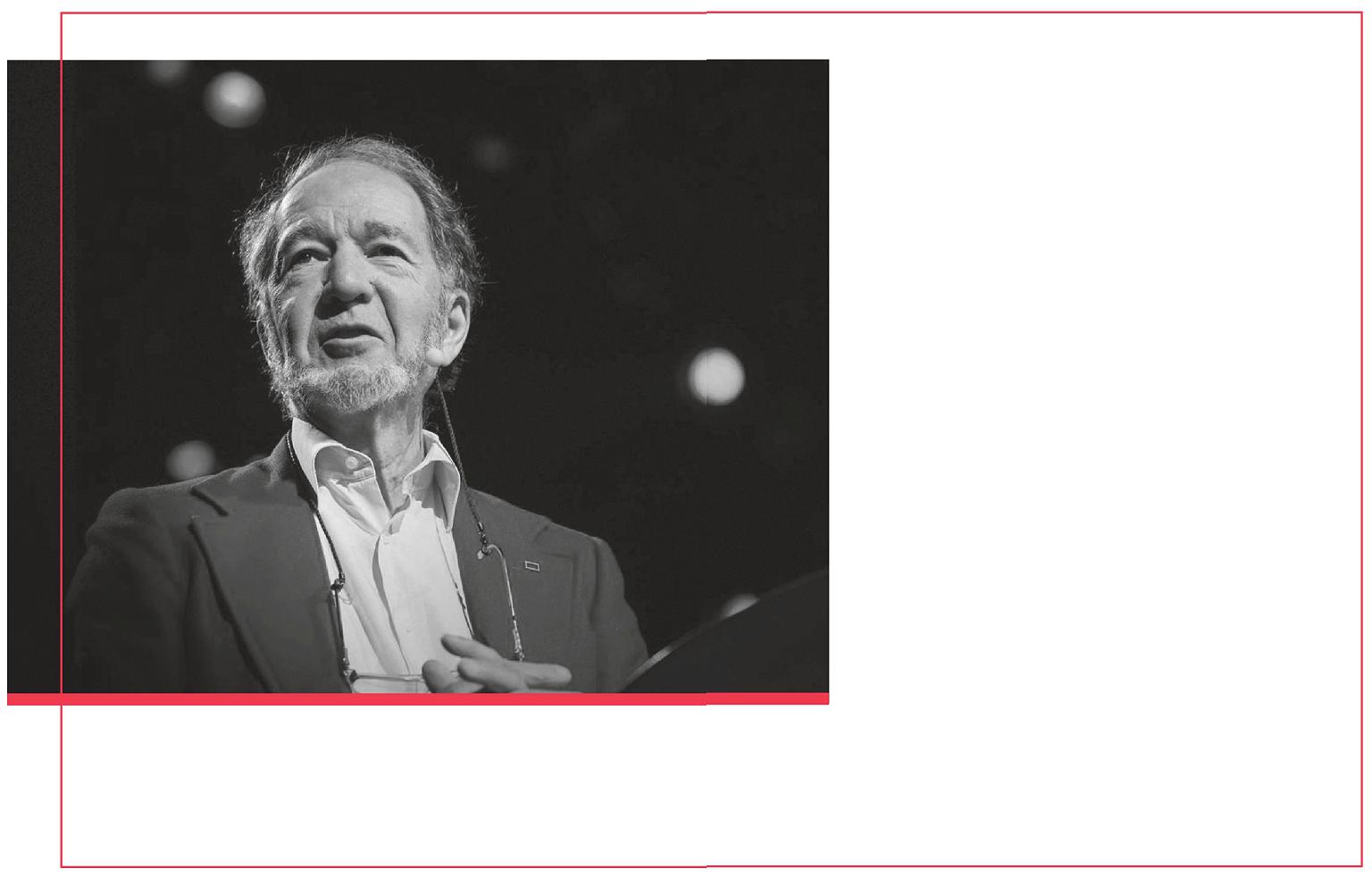
I HOPE THAT, BY RECOGNIZING THE SIGN POSTS OF FAILED DECISION MAKING, WE MAY BECOME MORE CONSCIOUSLY AWARE OF HOW OTHERS HAVE FAILED, AND OF WHAT WE NEED TO DO IN ORDER TO GET IT RIGHT.
我希望大家通过认识前人在决策失误时犯下的错误,更加清楚地明白他们是如何失败的,从而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
——《为什么一些社会做出了灾难性的决策?》
教育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但是,每个教师都知道,如果你有一群优秀的学生,那么,教育其实也是学生向教师传授知识,并对教师的假设提出挑战。这正是我在过去几个月中的经历。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第一次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本科生开了一门课,课程的主题是社会的崩溃。为什么有些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土崩瓦解,而有些社会却能一直维持到现在?
课上,我和学生一起探讨一些著名文明的衰落,比如美国西南部的阿纳萨齐印第安人、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古玛雅文明、复活节岛上的社群、东南亚的吴哥窟、非洲的大津巴布韦遗址、两河流域新月沃地上的部族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等。从最近20年的考古发现来看,由于过度开采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这些文明将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破坏殆尽,并最终将自己毁灭得支离破碎。
比如,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他们生存的岛屿原本植被繁茂,甚至拥有世界上最高大的棕榈树。渐渐地,岛民们开始砍伐森林,用木材制造独木舟、生火、运送雕塑、抬雕塑、做木雕等。终于有一天,他们伐倒了所有的森林,岛上所有的树木都灭绝了,他们再也没有木材用来制作独木舟、竖立雕塑了,也没有树木来保持水土、防止侵蚀了。他们的社会最终崩溃于一场由于食人引发的瘟疫,造成90%的岛民死亡。
最让我的学生费解的一个问题,我以前却从未想过:一个社会究竟是怎么做出这样一个灾难性的决策的,竟然将自己赖以生存的树木全部砍倒了?我的学生想知道,当复活节岛上的岛民砍倒最后一棵棕榈树时,他们说了什么。他们是在说“我们可是伐木工人,别管那些树”,还是在说“这是我的树,我有权这么干,请尊重我的私有产权”?当然,所有这些岛民一定早已意识到将森林砍尽会给自己造成怎样的后果。要知道,把树砍光可不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还有学生想知道,如果100年后人类还存在的话,那时的人们会不会像现在我们惊讶于这些岛民的愚昧无知一样,也震惊于我们的愚昧无知呢?
为什么一些社会做出了灾难性的决策?这个问题不仅让我的学生感到震惊,同样也困扰着研究社会崩溃的专业历史学家。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泰恩特(Joseph Tainter)的《复杂社会的崩溃》( 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 )是这个领域被引用最多的一本书。泰恩特在讨论古老社会的崩溃时,否定了文明崩溃是由于环境管理不善的可能性,他觉得这种假设看起来很不可靠。他在书中写道:
他们有完善的管理结构,再加上分配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能力,应对不良的环境条件可能是复杂社会体系最擅长的事情之一了。在面对那些他们完全有条件规避的环境条件时,社会却崩溃了,这真是令人费解……
随着资源储备日渐枯竭的问题在复杂社会的成员或管理者间越来越明显,最合情理的假设似乎是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找出解决方案。
泰恩特得出结论,所有这些古老社会的崩溃不可能是由于对环境管理不善,因为他们永远不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但是,现在事实很明显,这些社会确实犯了这些糟糕的错误。
我的学生,还有泰恩特,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令人费解的问题:群体决策的失败。这个群体可以是整个社会,或是政府、小团体、公司、大学学术机构等。群体决策失败的问题与个人决策失败的问题其实是相似的。个人会做出错误的决策,比如不幸的婚姻、亏本的投资、失败的生意。但是,比起个体决策,群体决策失败还有一些额外的因素,尤其是群体成员间的利益冲突,个体决策时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这显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也不会有大家一致同意的答案。
接下来,我想提出一幅解决群体决策失败问题的路线图。我将把答案按照顺序模糊地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群体可能在问题实际发生之前没能预见问题的存在;第二,当问题发生时,群体可能没有察觉到问题的发生;第三,在发现问题后,群体可能没有试着去解决问题;第四,群体可能试着去解决问题,但经过多次尝试却没能成功。虽然一直讨论的关于社会决策失误与社会崩溃的问题可能显得有些悲观,但问题的另一面却是乐观的,也就是成功的决策。或许,如果我们理解了群体决策失误的原因,就可以用这些知识做一个备忘录,从而帮助群体做出正确的决策。
在这张解决问题的路线图上,群体可能会做出灾难性决策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在问题发生之前,他们并没有预见到问题的存在。未能预见到问题的存在,可能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人们可能没有类似问题的前车之鉴,因此并未察觉到问题发生的可能性。以美国西部的森林大火为例。我和我的妻子、孩子,每年夏天会去蒙大拿州生活一段时间。每年当我们乘飞机去蒙大拿州的时候,我都会向窗外眺望,去数一数这一天发生了多少起森林大火。森林大火并不只是蒙大拿州的主要问题,而是美国西部山区的普遍问题。规模如此之大的森林大火,在美国东部和欧洲鲜有人知。当美国东部或欧洲的居民搬到蒙大拿州定居时,遇上森林起火,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应该赶紧扑灭。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林业局的工作目标一直是自接到报案起,到第二天上午10点之前,一定要将大火扑灭。
来自美国东部和欧洲的居民,之所以对西部的森林大火有这样的态度,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在这样干燥的环境中处理森林大火的经验。在美国西部的森林里,倒在森林底层的树木,并不能像倒在湿润的欧洲或美国东部的树木一样腐烂,它们会作为燃料,在干燥的环境中囤积起来。事实证明,频繁的小规模燃烧,可以将这些燃料烧尽。如果这些小规模的森林火灾被迅速扑灭,那么最后,一旦燃起大火,火势会蔓延发展到远超人们可以控制的程度,造成灾难性的大火。但是,美国东部和欧洲的居民,对于这样的森林火灾,并没有经验。任由大火燃烧,破坏宝贵的森林,这样的想法如此违背直觉,以至于美国林业局花了100年才搞清楚这个问题,改变了救火策略,任由大火燃烧。这个例子恰恰说明,一个对于问题没有经验的社会,可能根本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就像美国东部或是欧洲的居民不会意识到,在干燥的森林中倒下的树木,会累积成为大型火灾的燃料。
然而,对于一个社会为什么不能在问题发生之前预见到问题的存在,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人们虽然对问题有经验,但这种经验已经被遗忘。一个没有读写传承的社会,可能无法保存口述历史,而这些口口相传的记忆,可能记载的是很久之前发生的事情。据说,古玛雅文明最终毁灭于大约发生在公元800年的一场大旱灾。在玛雅王朝的历史上发生过大旱灾,但玛雅人未能从之前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玛雅人虽然有一些文字记录,但他们的文字记录主要记载了国王的征战和功绩,而没有与旱灾相关的文字记录。玛雅的旱灾以208年为间隔复发,所以,当公元800年的旱灾来袭的时候,他们没有也无法记起发生在公元592年的事情。
在现代文明社会,虽有文字记录,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可以从前车之鉴中吸取经验,我们总是倾向遗忘,比如,现在美国人的所作所为,就好像他们已经忘记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在石油危机发生后的一两年内,美国人极力避免使用高油耗的汽车,但很快他们就忘记了这一点。无独有偶,20世纪60年代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经历了严重的旱灾,灾情过后,市民发誓要比从前更为妥善地管理他们的水资源。但是还不到一二十年,市民就重新开始用过去那种非常耗水的方式来灌溉高尔夫球场和自家的花园。因此,对于一个社会为什么无法在灾难发生之前预见到它的存在,有许多原因。
为什么在事态扩大之前一个社会可能无法预见到问题的存在,还有第三个原因:错误的类比。当我们处于一个不熟悉的情景中时,我们会回忆自己熟悉的情景,然后进行类比。如果旧的情景和新的情景真的具有可比性,那么这就是一种可以助你继续向前的好方法。但如果旧的情景和新的情景只是表面上相似,那么,类比也可以很危险。
挪威的维京人自公元871年开始向冰岛移民。在他们熟悉的家乡挪威,土地是由冰川运动形成的厚重的黏土质土壤,这些土壤足够厚重,即使覆盖它们的植被被砍倒,土壤也不会被风吹走。但冰岛的土壤像滑石粉一样轻。它们并不是由冰川运动形成的,而是火山喷发时,被风吹来的轻质火山灰。为了能够给牲畜创造牧场,维京人砍伐了覆盖这些土壤的植被。非常不幸的是,这些轻到被风吹来的土壤,在覆盖它们的植被被砍伐以后,也轻得足以被风吹走。维京人来到冰岛后不过几代人,冰岛一半的表层土壤都被海水侵蚀。像这样由于错误类比而酿成大祸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问题发生时,社会可能根本没有察觉到问题已经发生,这是我的路线图上的第二站。无法察觉到问题已经发生,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一些问题的起源确实是无法感知的。对土壤肥沃程度起关键作用的营养成分,肉眼是无法察觉到的,直到现代,人们才可以通过化学分析的方法进行测量。在澳大利亚、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芒阿雷瓦群岛、美国西南部的一部分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土壤中大多数的营养成分,早已被雨水洗刷干净。人们到达这些地方并开始种植作物时,这些作物很快耗光了土壤中剩余的营养成分,因此农业很快就失败了。但是,这些营养贫瘠的土壤,往往覆盖着枝繁叶茂的植被。因为生态系统中大部分的营养成分,都蕴藏在了植被中,而非土壤中。因此,当人们砍伐植被时,营养成分也被带走了。澳大利亚和芒阿雷瓦群岛的第一批殖民者,不可能察觉到土壤营养成分枯竭的问题。
一个社会无法察觉到问题出现的第二个更为常见的原因是问题可能是以一种缓慢发展的形式存在的,而这个变化趋势掩藏在广泛的起伏波动中。在现代社会,能说明这一原因的最主要的案例,便是全球变暖。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大气变化,致使全球气温在最近的几十年中一直缓慢地上升。然而,实际情况并非那么简单,全球气温并不是每年比上一年无情地高上0.17℃。相反,我们都知道,气候每年都在起伏不定地波动着:这个夏天比上个夏天高3℃,下个夏天又要再高2℃,再下个夏天却突然低上4℃,然后,再低上1℃,然后又涨上5℃,等等。因为气候的波动幅度非常大,而且难以预测,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在这些嘈杂的信号中发现上升的趋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直到几年前,最后一位对全球气候变暖持怀疑态度的专业气候学家才被说服。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仍然不相信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他认为仍然需要更多的调查。中世纪格陵兰岛的居民,也面临着相似的困难,他们无法认识到气候正在逐渐地变冷。尤卡坦半岛的玛雅人也没有发现,气候正在逐渐变得干燥。
政客们用“逐渐变化的常态”(creeping normalcy)这个词,来形容这种隐藏于纷乱波动中的缓慢趋势。如果情况只是缓慢地恶化,人们很难认识到今年比去年差一点,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更差一点。因此,人们对于何为“常态”的基线标准也在几乎察觉不到的情况下逐渐改变。这种年复一年的微妙变化,人们可能要花上好几十年才会突然意识到,情况比几十年前变好了很多,或是人们所接受的常态变低了很多。
社会无法感知到问题已经发生的第三个常见的原因来自远程管理者。对于任何一个大型社会来说,这都是一个潜在的问题。比如,蒙大拿州最大的土地产权所有者和最大的木材公司总部并不在蒙大拿州,而是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由于不在现场,公司的管理者可能意识不到,他们所拥有的森林可能急需锄草。
逐渐发生而又不易察觉的问题、逐渐变化的常态、远程管理者,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即使身处其他社群,也可以想出几个类似的案例。
我在路线图的第三站提到的问题或许是导致决策失误最常见,也最让人震惊的问题:社会认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却没有试着去解决问题。
这样的失败之所以经常发生,用经济学家的话说,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的“理性行为”。一些人通过“正确推理”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可以通过损害别人利益的行为来提高自己的利益。经济学家称这种行为是“理性的”,尽管他们也承认,这种行为可能是不道德的。作恶者通常目标明确,而且能够在作恶之后逃之夭夭。因为,作为复杂现状中的胜利者,他们通常高度集中,人数很少,而且目的非常明确,因此能够立即得到大量确定的利益而动力十足。与之相比,失败者们是分散的,许许多多的个体分担了不良行为造成的损失。同时,失败者们还缺乏动力,因为,他们不去做“理性人”那种损人利己的勾当,这只能给他们带来少量而不确定的远期收益。
典型的不良理性行为便是“对我有益,对你和社会有害”,说白了就是自私。少数人可能会认识到,他们的一己私利与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相悖的。举个例子吧。在1971年之前,蒙大拿州的矿产公司将含铜和砷的有毒废弃物直接倾倒在河流和池塘里,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因为当时蒙大拿州的法律并没有要求矿产公司在废弃矿井后做好善后处理。1971年之后,蒙大拿州出台了相关的法律,但是矿产公司发现,他们可以在开采有价值的矿石之后直接宣布破产,以避免进行善后处理的花销。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数十亿美元的善后成本只能由美国政府和蒙大拿州的居民来承担了。矿产公司准确地找出了能够提高自身利益的方法,通过留下烂摊子给自己省了钱,但却把负担留给了社会。
这种利益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被称为“公地悲剧”,指的是这样一种情景:许多人从公有资源中有所收获,但没有有效的监管来控制每个人可以从中收获多少资源。比如,海洋里的鱼或是公共牧场上的草。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个消费者可以合理地推断“即使我不捕那条鱼,或是不让自己的牛马去吃那些草,别的渔民也会去捕那条鱼,别的牧民也会让他的牛马去吃那些草。那我为什么还要去操心过度捕鱼和过度放牧的事儿呢”!正确的“理性”行为告诉我们,哪怕最后资源枯竭甚至灭绝,面对利益,我们也要抢在别人前面。“理性行为”将因此危及整个社会。
当保护资源不能给消费者带来长期利益时,由利益冲突引起的“理性行为”也会出现,并造成不良的后果。比如,出于商业利益,国际伐木公司对热带雨林进行大量砍伐。他们在一个国家租借土地,砍伐那里所有的热带雨林,然后再转向下一个国家。国际伐木公司清楚地认识到,一旦交了租金,将租借到的土地上全部的树木砍得干干净净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正因为如此,伐木公司毁掉了马来半岛、加里曼丹岛、所罗门群岛、苏门答腊岛、菲律宾、新几内亚、亚马孙雨林和刚果盆地的大部分森林。长此以往,我们的下一代必食恶果,但下一代人却无法投票或者抱怨。
另一种涉及“理性行为”和利益冲突的情况,发生在制定决策的精英与社会的其他群体之间。如果精英们无须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负责,他们就特别倾向于做有对自己有利却危害他人的事情。这种冲突在当代美国越来越频繁,富人们住在装着门禁的封闭式社区里,喝着瓶装水。比如,安然公司的高管就准确地计算到,他们可以通过洗劫公司的金库和危害社会来赚取巨额的财富,豪赌之后,还可以安然无事地逃避惩罚。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精英决策层需要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负责,那么,由于精英与社会其他群体的利益冲突而导致问题未能解决的情况,就要少很多。比如,在当代荷兰,有相当多的公民参加了环境保护组织,公民参与的比例之高为全世界之最。我一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直到几年前拜访荷兰时,我才知道了问题的答案。当我和荷兰的同事们驱车穿过乡村时,我向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的荷兰朋友回答说:“看看四周你就知道原因了。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在海平面以下约6.7米。像荷兰的大部分地方一样,这儿曾经是一片浅湾,荷兰人将它用堤坝围起来,用水泵将水抽走,才创造出了现在这片低地,我们称其为圩田。为了保持适宜的环境,我们不断地用水泵将透过堤坝渗进来的海水抽出去。如果堤坝崩溃,住在圩田里的人们都会被淹死。这可不是说富人住在堤坝的高处就可以逃过一劫,穷人住在圩田低洼的地方就只能坐以待毙,而是堤坝一旦崩溃,所有的人,无论富有还是贫穷,都会被淹死。这一幕曾出现在1953年2月1日可怕的大洪水中,巨浪和风暴越过堤坝,将海水灌入荷兰泽兰省的圩田,有将近2 000名荷兰人淹没在了洪流之中。灾难之后,所有的荷兰人发誓‘永远不再这样’。于是,我们花了数十亿美元,建造了加固的堤坝来抵抗洪水。”在荷兰,决策的制定者们知道,一旦犯了错误,既难辞其咎,也躲不过危害,所以他们必须为尽可能多的人谋福祉。
以上这些例子说明,社会之所以没能解决已经发现的问题,是因为让问题悬而不决对某些人更有好处。还有另一类行为可以导致已经发现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济学家称这类行为为“非理性行为”。这类行为与所谓的“理性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不是损人利己,而是对所有人都有害无益。这类行为通常产生于人们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作祟,所以很容易让集体在一个糟糕的状况中停滞不前。
宗教价值观有时十分固执,因此也成为灾难性决策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比如,太平洋东部岛屿的毁林运动背后有一部分宗教动机。巨大的石质雕像是这些岛屿上宗教崇拜活动的基础,为了运输并将这些神像竖立起来,大量的森林被砍伐殆尽。现代社会,蒙大拿州的居民很不乐意去解决那些由于挖矿、伐木和放牧造成的日益明显的问题。原因之一在于这三个产业过去作为蒙大拿州经济的支柱产业,代表了蒙大拿州的先锋精神,已经与蒙大拿州居民的自我身份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解决已经发现的问题时,同一个体短期与长期目标的冲突也是频繁造成非理性失败的原因。在当代世界,数十亿人极度贫穷,他们能够奢望的不过是明天的食物。为了捕到栖息在珊瑚礁里的鱼类,热带海域的贫穷渔夫们不惜使用甘油炸药和氰化物。他们完全明白,这么做无异于毁掉自己未来的生计,但此时别无选择,他们近乎绝望地需要在今天得到食物来喂养他们的孩子。
同样,政府的运作也经常专注于短期的目标:迫在眉睫的灾难总是让政府不堪重负,政府的注意力也仅仅集中于千钧一发、临近爆发的问题,他们总觉得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来解决长期的麻烦。举个例子吧。我有一个与美国华盛顿特区现任联邦政府关系紧密的朋友。他告诉我,在2000年全国大选后,他第一次造访华盛顿。他发现那里的领导们有一个被他称为“90天焦点”的工作目标:领导们只谈论那些在未来90天可能会引起灾难的问题。经济学家们理性地认为政客们对于短期利益的非理性关注是合理的,因为未来的利益需要“折现”。他们争辩道,在今天就收获资源比把这些资源留在未来的某一天再收获要更好,因为今天收获的利润可以用来投资。与未来不变的收益相比,累积的投资收益让今天的收获比未来的收获更有价值。
为什么在发现问题后却未能试着解决?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想再提最后一个原因——心理否认。这是一个在个人心理学中被精确定义的专业术语,后来被引入了流行文化。如果你感知到某件事情让你产生了不可忍受的痛苦情绪,为了避免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你可能会下意识地忽略或否认这种感觉。即便忽略这种感觉可能在现实中造成极具灾难性的后果,你也在所不惜。引起心理否认最常见的情绪是恐惧、焦虑和悲伤。
举个典型的例子吧,比如你会拒绝假设你的丈夫、妻子、孩子或最好的朋友处于濒死状态,因为这个想法会让你感到悲痛欲绝。你会拒绝想象可怕的事情发生。比如,高耸的堤坝下是一道又深又窄的河谷,堤坝一旦崩塌,洪水会一泻千里淹到下游很远的地方。当民意调查员问下游的人们对于堤坝崩塌有多么担心时,离堤坝很远的居民最不害怕,随着离堤坝的距离越来越近,居民也越来越担心。出现这样的结果一点也不奇怪。而真正令人惊异的是,虽然离堤坝只有几公里的居民害怕堤坝崩塌的程度最高,但是,当距离堤坝更近时,居民担忧的程度却骤降为零。也就是说,紧挨堤坝居住的居民,也就是那些堤坝一旦崩塌一定会被淹死的人,反而声称自己一点也不担心。这正是由于心理否认:堤坝会崩塌的可能性一定存在,紧邻堤坝居住同时还想平静地生活,唯一的方法就是否认这种可能性了。
心理否认是一个在个体心理学领域相当成熟的概念。如今看来,这个现象似乎同样存在于群体心理。有很多证据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人们一直拒绝承认纳粹正在疯狂地屠杀自己的同胞。虽然不断有证据表明血腥的屠杀还在继续,但他们拒绝承认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因为这个想法实在是太恐怖了,所以他们不愿相信这个事实。某些引起社会崩溃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那些衰败的社会没能直面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心理否认或许可以解释。
最后,我想谈谈路线图上的最后一个原因:社会认识到了问题,也确实试着去解决了,但是没能成功。出现这样的结果,有很多可能的解释。首先可能是因为问题太复杂了,远超过了当时人们的能力。比如,蒙大拿州常年与斑点矢车菊、阔叶大戟等外来的杂草品种作斗争,但每年的损失都高达数亿美元。蒙大拿人不是没有察觉到这些杂草,也不是没有试着去锄掉它们,只是单纯因为用现在的技术很难清除掉这些杂草。阔叶大戟的根可以扎到地下约6.1米深的地方,徒手很难拔除,而若要使用特殊的除草剂,每3.8升就要花费800美元。
其次,未能解决问题常常还因为我们解决问题时不够尽力,或是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才亡羊补牢。比如,由于引进了欧洲的兔子和狐狸,澳大利亚本土的生态圈中又没有相应的生物及其天敌,澳大利亚每年都要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农业损失,同时澳大利亚本土的小型哺乳动物也面临着灭顶之灾。狐狸是捕食者,捕食羔羊和小鸡,同时还会杀死小型有袋类动物和啮齿类动物。一个多世纪以来,狐狸繁衍生息,已经遍布澳大利亚大陆。由于狐狸无法游过澳洲大陆和塔斯马尼亚岛之间又宽又险的海峡,所以直到最近,塔斯马尼亚岛上都未见狐狸的踪影。但几年前,几个人偷偷地在塔斯马尼亚岛上放生了32只狐狸,也不知他们是为了从狩猎狐狸中获得乐趣,还是单纯想要嘲弄环保主义者。这些狐狸对塔斯马尼亚岛上饲养羔羊和小鸡的居民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当然,还有塔斯马尼亚岛上的野生动物。2002年3月,岛上的环保主义者发现了狐狸的问题,他们向政府请愿,希望趁还来得及,尽快消灭岛上的狐狸。狐狸繁殖的季节一般是从7月开始。要是等到狐狸产了幼崽,从32只变成128只,幼崽成熟后再四散分布于全岛,想再消灭狐狸就要难得多了。不幸的是,塔斯马尼亚政府反复的讨论延误了时机,直到2002年6月才终于决定拨款100万美元用于消灭狐狸。可到了那个时候,危险已然升级,这笔钱太少也太晚了。塔斯马尼亚政府认识到,自己面临的问题已经变成一个既更加昂贵,又很难解决的问题了。到现在为止,都没听说灭狐行动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因此,人类社会或小型组织可能会因为一系列的原因做出灾难性的决策:未能预见到问题;问题发生后未能及时发现问题;未能尝试去解决问题;试着解决问题但是没能成功。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悲观,就好像人类的决策注定失败一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在自然界的竞技场中,还是在商业、学术界或是其他群体中,都不是这样。许多人类社会预见到了问题,发现了问题,尝试去解决问题,最后也成功地解决了问题。比如,古印加帝国、新几内亚高地人、18世纪的日本、19世纪的德国、南太平洋汤加群岛主岛上的居民,都意识到了砍伐森林的风险,并采取了成功的植树造林或是森林管理的政策。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在这儿讨论人类决策的失误并不是想要让你沮丧消沉,相反,我希望大家通过认识前人在决策失误时犯下的错误,更加清楚地明白他们是如何失败的,从而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