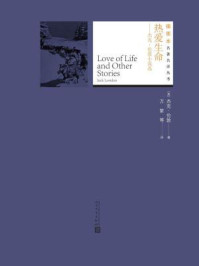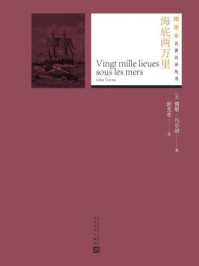添田害了病以后,穗积每天得把病状报告朝子。
最初添田并不那样消沉。在那阳光极好的,虽是冬天白天里却和和暖暖使人思睡的屋子正中,一层层地堆起那很温热的铺着很厚的棉花的奢侈的被褥,静静地仰卧着,但他还是很有元气的。
“终于我也睡倒了。偶然受点这样的罚也是没有法子的。”
“医生可怎么说的呢?”
“据说也是肾脏炎。”
“唔!说起来果然你的脸有一点浮肿起来了。”
穗积用和平常完全没有两样的冷静细细地打量着病人的样子。一切都照他所想的,毫无龌龊地进行着。他的计划着着地成熟。但不可思议地更加引动他那像科学家一样的冷酷和好奇心。
“所以我不是曾那样说过吗?我说那样的药是不能用的,一个不留心就要成肾脏炎的。”
“说是说过,但已经害上了这个病有什么办法呢。”
“若是病好了,以后可别用了。一定是分量错了。”
“不,病好了,也许还要用的。”
在那泡泡的已经带着水气的眼皮里的添田的眼睛,还顽强地笑着。
“并且还有哩。许是因为我平常绝少躺着的时候吧,害了病受着人家种种的看护倒很不坏。”
“那么干姑娘很尽心地看护你吗?”
“戏一完了她赶忙就回来,晚上和看护妇轮班几乎没有离过我,这在那家伙总算很尽心了。”
“怎么样呢?添田君,你太太也说要来看你一次。趁白天干姑娘不在的时候带她来好不好呢?”
“谢谢!够了,用不着了。”
“可是她很着急……因为你从不曾害过病,她说很想要晓得是怎么样的情形哩。”
“情形由你去告诉她不就得了吗?你告诉她说我虽然这样躺着,但还是好好的没有什么大病,叫她不用着急。”
“可是猜她本人的意思,至少想在你有病的时候在你旁边看护看护。啊,或是和干姑娘说明理由,得了她的谅解之后也可以……”
“我就是不要她来看病。让那家伙来了,看了我又呜呜地哭起来的时候,那我的病可更要加重了。”
忽然穗积想起多少年前的事了。距今六年前在长野作医生的时代,他曾替添田诊察过流行感冒,以此机缘两人才成了朋友的。添田在那时候对于病意外地神经过敏,因为曾对他说:“你心脏不好,得注意。”他甚至连最爱的酒都一时停止了。那样看起来,就是这次的病他口里虽然说着那样倔强的话,但肚子里一定多少有点担心吧。假使朝子来到这里在枕边抽抽噎噎地哭着,自己心里一软也许要哭起来,那在他不但是怪难看的而且好像是死的前兆,当然是很可怕的吧。
不日就要死的病人不知道“死”已经那样近了,到了这时候还依然拼命地说着平日的大话,摆着空架子,这在穗积是很便利的。甚至在他是快心的风景。他务想使这个人就那样恶魔的死去。“喂,添田君,任你口里怎样说,但你的气已经弱下来了。这虽是你快要死的预告,但是你还始终那样摆着架子。你到死还不能诚实,不矫正你那傲慢的脾气,这是充分给神舍弃了的证据啊。”熟视着病人眼睛的穗积的心里有时浮出这样坏心思的话。
渐渐如他所预期的,添田的病一天天沉重了。明朗高敞的屋子太阳和和暖暖地射进来,但到了这些日子已经没有那种愉快的感触了。屋子里面有许多白的东西,看护妇的制服,寝床的卧单,陶器的痰盂,洋瓷的面盆,这一些清清洁洁的东西,因着那药的臭味和由搁在火钵上的一个面盆里发出来的汤婆的水蒸气使人只觉得闷,只觉得头上像给什么东西压迫着似的沉郁。添田最初仰起睡着,脸朝着太阳射进来的纸槅子那方,但现在把右边在下心脏在上向阴暗的壁这边睡着。因为屋子里太暖了,病人屡次拜托看护妇给掀开被窝卷到腋下。许是因为动悸得太厉害吧,搁在心脏上边的冰囊,就像小动物的腹部似的细细的、有力的一下下弹着。进屋子来的人虽看不见望着壁那边的病人的脸,但他睡着一动也不动的日子,最多使人觉得他还活着的只是心脏,其余怕不都已经死了。伸在被窝上的左手,本来是又白又肥的,但因着水气肿得又粗,又黄,又腌脏,拇指之下的那浮肿的掌心对着光亮的这边,也不是握着,也不是开着,只是把指头半作圆形而已。仅得窥见的侧面之一部就在脸皮上也完全没有什么表情。
“怎么样了,添田君,很苦吗?”
在那枕边转了一圈走到病人的颜脸的正面坐下这样说着穗积问他时。
“唔,苦得很,小便一点也解不出来……”
虽然是字音很准的用朗朗的声音回答的,但他的眼睛决不看穗积,就像佛像的金面似的开着半眼,瞳仁藏在眼皮底下去了。并且脸上的任哪一个地方也没有表情。即算有也因整个脸儿都肿了看不出来,浮肿在眼皮上来得最厉害,就像给毒虫蛰了的一样,两个有圆的平滑的表面的桃子似的东西很阴郁地垂在两个眼睛上,这简直把添田的容貌变成了别人的一样,一见似乎很怕人,但在穗积反而觉得他因此换了一幅怪和善的好的相貌了。
“什么医生真是没有道理的,究竟那些药是吃了干吗的呢?”
病人渐渐话少了,没有事情的时候几个钟头也懒得开口。但有时发起脾气来突然说那样的话。
“现在得想种种法子出尿,只要尿出来浮肿一消,人就轻快了。”医生这样说着,每日午前午后来诊察两次,换了许多方子,但药石几乎是没有效果的。四五天中间只有一次尿而且又是极少量的,水气一天天显著,颜面皮肤渐肿得垂下来了。
“尿瓶,尿瓶……好像要小便了。”
病人一天多少次这样说着使看护妇惊喜,但放进便器把他抱起来时结果什么也没有。干子不知听得谁说朝鲜产的山牛蒡吃了是一定出尿的,这也讨来给他服用过了也还是没有效验。
医生虽然还不曾宣告什么,但最后的日子一天天逼紧了,在穗积已经是毫无疑义的。数年之间使他痛苦,虐待他的爱人的这可恨的仇敌,到了现在已经只有多则十天,少则一个礼拜的余命了。他早想到他有带着朝子到这里来送她丈夫的终的义务,那在穗积自然是最痛苦的场面,而且是得拼命地硬着心肠的时候。但好在那不幸的妻子,纵然号泣在临终的丈夫的枕边,而添田的精神多半已经衰微到没有改悔的力量,他的表情也变成无感觉的了。他因此想把他们夫妻见面的时机竭力使它短,竭力拖延到后面去。
“朝姑娘,这件事请你随我去办吧。”
他说。
“医生也不曾说没有救了,并且病也没有到那个程度。”
“可是等到医生说没有救了不是已经迟了吗?”
“迟了?病势还没有到那样沉重呢。尿毒病这东西即万一十分沉重了,也还不是几天就死得了的。现在一来有干子在那里不便;二来,你若是勉强去看他,使病人心里焦急起来反而不好。并且你若是见了他一定要哭的,这很刺激病人的神经。”
“不要紧,我不哭就是。”
“你瞧,你瞧,口里说不哭,不依然是哭起来了吗?”
“现在虽然哭了,到了那时候我就不哭了。”
“哈哈,谁晓得。”
“我一定,一定不哭的,你带我去吧。”
“到了那时候你就不说我也带你去的。哪里,人一有了要死的大病时自己也会晓得的。就是添田君假使到了那一天,一定说想要见见你和小孩的。”
“可是他要那样的心软起来我更加伤心了。”
“若是真有那样的事可了不得。别着急吧,这样那样地闹着的时候意外地好得很快也说不定。”
关于那件事,一辈子得瞒着自己的爱人的穗积,现在已经踏进了第一步了。他在恶魔的假面之下,瞧着那不顾自己和别人而为丈夫憔悴的她。那是恢复了圣母的容光的一个清纯,尊贵而崇高的女性。他的心虽然跪在那辉煌的圆光前面吻着那圣像的脚,但他那戴上了的恶魔的假面没有法子再取下来了。他是使他自己都惊讶的那样沉着而勇敢。越看着她的眼泪,他的复仇的念头反而越加坚决。
“干姑娘,我问你……”
在有一天晚上穗积要回去,干子把他送到大门口时他靠近她耳边这样说。
“医生今天不像是打了坎富尔针吗?”
“是啊,他说心脏很弱哩。”
因着看病连夜睡眠不足的关系吧,脸上看得出消瘦了许多,但干子的声音决不是感伤的,而是有气概的女人似的很干脆。
“他说这个病最不宜于心脏弱的人,他最担心的是这点。”
“是啊,添田君的心脏本来是不大强的啊。”
穗积不让她看见了脸色,坐在门口地板上扣着大衣的钮扣,向大门外暗处发出这言语来。
“那么,医生觉得有几分希望呢?”
“他说假使出尿就好了,不过照那样子很难,所以多半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医生这样说的吗?”
“是啊,今天才这样说的。又说不过还不至于那样快吧,以后渐渐陷入昏睡状态,一个礼拜总还不要紧。”
“那么这样好不好呢?你也大体算是尽了心了,这下马虎一点给把朝子叫来怎么样呢?病人不要告诉他也可以的,只要你谅解了就成了。”
“那好得很。我正那么想呢!假使就这样死了,我回头要给人怨恨一辈子的。”
她对于这个病人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吧,她一定想着早把他交给了朝子,自己也可以松肩了吧。穗积觉得大概看穿了干子的意思。
“你既是那样的明白人那就更好了。那一面每天都逼我带她来,我也弄得没有法子对付了。”
“你以为我是那样不明白的吗?”
“对不起得很,不过这一来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那么你也算对得起朝姑娘了,你得多少给我一点报酬才成。”
干子这样说着伸出手来,吃吃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