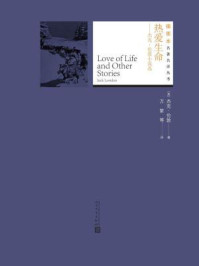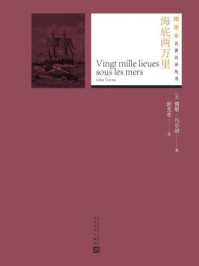添田躲的地方是离铁道省线的鹤见车站不远,靠近山窝里的Radium温泉的药草园,这是专供人们带女人来住的旅馆。朝子到公寓里来的第二天上戏院子后台找干子问好了地方的穗积立时就转身去找他。到了那里已经是太阳下山了,苍苍郁郁的宽广的亭园,这里那里有用树木围着的潇洒的厅室,倒是一个比预想的要好得多的地方。
“啊呀,你毕竟来了吗?”
添田一见了穗积的样子就好像早等着似的,这样说着哈哈地笑了。那房子是离本屋很远,新建筑在那白天里可以望海的空气新鲜的岗子上的一所别馆,席子和木料一切还带着它的本身的香气。燃着非常强烈的白光的电灯的屋子里散乱着各种色彩绚烂的女人的衣裳和饰物。添田也披着像什么时候干子缝过的条子缎的褞袍,在长火钵前面打着盘坐,用烟管吸着金丝烟,也许是正坐在电灯光下面的关系吧,比平常还要显得又白又胖,那种样子就像个“妖冶的情郎”。
“那么干子姑娘也住在这里了?”
“唔,那家伙也找到这里来了。怎么样,你看我们这新家庭的样子?”
添田志得意满地这样说了,把屋子的周围很会心地望了一转。
“这里真是一个很幽静的地方,我每天写一点点稿子,因为晚上干子是不在的。”
果然,里面那台子上,积下了二三十张正写着的原稿。照那样子添田似乎早就安居在这个地方,一面和干子夫妇一般的过着日子,一面从事创作,目前想他归家是没有望的。
“我今晚可不是因为上次那封信上的事情来的,反而好像是替朝姑娘来做使者的。”
穗积把昨天的事大体对他说着的时候,添田不过用鼻头“哼,哼!”地应着,忍俊不禁的听着。等他的话告了一段落,添田才敲着烟管说:
“那么大体都和我的想像差不多了。”
“你的想像是怎么样的?”
“我住的地方不晓得了,朝子心里很着急跑到你的公寓里去求你,那么一来你也不好不见朝子,结果只好受了她的拜托。然后你到干子的后台去要她告诉我的地方。我想反正总是这么一个顺序。前几天我就对干子说了,穗积快要上你的后台来哩。”
“那么,你难道是以这个为目的才离开家里的吗?”
“不是说目的如此,我是说我若把住的地方瞒住了,事情便会是那样发展的。”
“可是你看着我的信的时候不是听说你对朝姑娘这样说过吗?他虽说再也不见你了,我偏要叫他见你。”
“唔,是说过这样的话,并且事实上不已经是这样的吗?”
“因此我就是说这个啊。你瞒住你的地方自然目的也许仅仅在那一点吧。想要和干子姑娘一道住许是主要的动机吧。但至少你不会感觉得一种兴趣,以为这么着那两只家伙一定要会见的吗?”
“那是感觉,不是目的。不过那种兴趣是有的。但兴趣是自然涌出来的,对于那个我想我不应该负什么责任。”
“责任自然在我,即算你的目的是在那里。但凡我的意志坚固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总之,我不说过吗,我完全给你料定了,始终总陷入你的圈套,这使我不服气得很啊。”
“阿哈,哈,哈!那有什么值得那样不服气的呢?”
添田把两个手插在褞袍的怀里,用那手轻轻的拍着胸脯,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因为想表示那种绰有余裕的态度,他故意把脸向着旁边听着穗积的谈论。
“可真是不服气啊!因为好像不知道要怎样给你播弄才够。也许是我的瞎猜,就是你前些日子由箱根寄来的信不也是一样吗?那封信并没有特意寄给我的必要。单止要寄钱的话直接写给朝姑娘不就得了吗。”
“那么,照你的意思那封信该怎样解释呢?”
“你不说你不想让朝子知道你的地方所以拜托我吗?可是这不过是口实,我想你的真正的目的是让我和朝姑娘两人见面吧。因此看他们两人谈些什么话吧。说起来好像这么一种开玩笑似的意思。”
“哈,哈,哈!原来你是当作那种意思吗?”
“那么,你本不是那种意思吗?”
“那多少也许有那种意思。可是不管我的目的在哪里,反正你接了那封信的时候一定说‘这是好机会,此机不可失,趁她丈夫不在家去见见那个女人吧。’你没有这样想过吗?”
“那是想过的,老实说,和朝姑娘单独见面的机会我不知等了多少年。因此,接了你的信的时候虽然觉着眼见得堕入了你的术中,但我想人家既然要我中计我就将计就计吧。抓住这个不再来的机会吧。”
“那么说,不是半斤对八两吗?不,说起来你还得大大地感谢我哩。”
“是呀,我在某种意义很感谢你。整整五个年头第一次我才能够和她谈话,这确是亏着你的力。你给我的机会即算是出于恶意,在我也是可感谢的。因此,你的恶作剧若就是那样为止,那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有点不大懂得。”
“不,我这时候并不是来埋怨你的,你可别那么生气。我所说的也许在你觉得滑稽,不过请你虚心坦怀的听吧。”
穗积因为自己所说的渐渐激烈的、争辩的,带着刺入对方心坎的紧张味了,好像连他自己也觉得可怕起来,赶忙打着掩饰那种调子的怯懦的笑脸说。
“说‘等着机会’好像有点不稳当,反正就是说‘我想同她两个人谈谈话’。看着情形我想听到从前的回答,就是老早以前和我约过的那回答。本来到了现在就不问反正也晓得了。不过约束是约束,不由她本人口里清清楚楚地宣告出来我是不甘心的。就是,不管你怎样我的心事是没有了的。”
“哦,原来如此!”
添田依然装做不晓得似的用嘲弄的口吻说。
“那么朝子怎样的呢?你们谈得很亲热吗?”
“不,一点也不亲热。我想她怎样也应该对我讲几句亲切一点的话,也许我说话没有说得好吧,结果非常的不满意。”
“那么,‘从今以后再不见面’的话究竟是谁说起的呢。”
“是我说起的,可是朝姑娘那样执拗的态度,也逼起我要说出那样的话来,自然那就在我也早已想到这样的结果,但没有想到来得那样急促。分别就分别,不过总得稍为有点什么……供人回味的余情才好。”
“哈,哈,哈,哈!可是那可不能怪我啊。你是怎样想的?难道说我和朝子商量好了故意叫她那么执拗吗?”
“不,那错了。我所说的不是那个,不满意是不满意,但因此我也懂得朝姑娘的心了。假使就那样分别了反而可以断绝痴情。可是你的恶作剧并不停止,好好的分别了的你又使他们会面,这你也许说不是恶作剧,但怎奈这是很讨厌的。”
“讨厌的?为什么?”
“为什么呢?一句话就是我不高兴再做讨饭的叫花子了。”
“‘做讨饭的’是什么意思,再详细一点说吧。”
“可不是吗?从前的我为着要和朝姑娘见面不是老来求你的慈悲吗?我被你看清楚了心事,把我戏弄得一榻糊涂,但我不是一点事情也没有还得追随着你吗?”
“唔,那样说起来也许不错。不过可不是我要你做叫花子的吧。不是你自己高兴做叫花子吗?”
“那从前是这样的。一点也不是你的关系。说起来还算是我太没有志气了,所以增长了你的坏脾气。假使我不是这样卑屈的人,你一定也不会那样对你的太太不好,对于播弄人家也许没有那样高的兴趣。因为有我这个人,你也变坏了,朝姑娘也吃着苦头,连我自己也渐渐情性乖僻起来。因此像这样交际下去,在我们三人都不好。”
“可是我不觉得这样。”
添田给他说了这一句之后,变成了想掩饰也无法掩饰的怪真挚的表情。他那眸子里含着冰也似的冷酷。
“还是有了你在我们要好些,假使没有你我想我更得对朝子不好。”
“那为什么呢?”
“我的坏脾气是生来如此的,这东西恐怕一辈子也改不过来。从前有你这个人在中间,多少还可以缓和一点;假使没有你了那么就得朝子一个人受罪了。这种心理你恐怕不大晓得,但我很清楚。就是朝子我想也是一样。既然反正是没有好日子过的,有了你这个同情者时常帮忙,做做事情或是从旁边劝慰劝慰,不是还多少有些靠岸吗?并且任怎么说你是她从前的爱人啊……”
添田说到这里粲然含着可厌的笑。
“可是添田君,那朝姑娘本人已经说过用不着我了呢。”
“哈,哈,哈,哈!用不着那样悲观吧。前次是走到顺路上了,不能不那样,到了现在她也不见怎样讨厌你哩。你瞧后来她不是又到你的公寓里找你吗?”
“那么,你是叫我一辈子做朝姑娘的护兵吗?”
“你不满意吗,做护兵?你难道说任朝子将来怎样都不管了,你已经不祝她的幸福了吗?”
“没有的事,就是不见面了我也时常在暗中祝她的幸福的。我所谓绝交,是想把我脑子里关于朝姑娘的清纯的记忆珍藏起来不让它弄脏了。这在我恐怕是唯一的恋爱的纪念哩。”
“这是一种感伤主义,简直像一个中学生的……”
两个人是这样谈了好一些时候,一方而刚要短兵相接起来,一方面便马上把它当笑话说开。因此谈话始终不过是围着一个地方打圈子。穗积所想要晓得的是添田为什么缘故要那样胶执地恶作剧,那样使自己的老婆和朋友痛苦,究竟有什么乐趣呢?这单是坏脾气呢还是在坏脾气以外另有理由呢?对于添田的心理作用他更加不懂起来,因此他就从好奇心说也想要知道这心理的真相。但无论追寻到哪里去他还是“不晓得”。
“好哪,现在既是和好了,你依然去和她交际吧。又并非我们两人绝交你也用不着什么辩解了。”
“这真是没有法子,那么还是做定了她的护兵吗?”
说着话时他们两人中间不觉摆上了晚饭了,穗积又只好啰啰嗦嗦地红着脸,搔着头发做添田的酒伴。“我是来干什么的呢?对呀,对呀,朝子拜托我有要紧的事来的,关于那高利贷的问题。”在他想起了这件事时,添田自不用说,连他自己也觉得糊糊涂涂地喝醉了,正用很大的声音说着笑着。谈起高利贷的问题,结果徒然成了更加煽动添田的气焰的材料。“怕发封时还可以倒高利贷的债吗?值钱的东西都进了当店,就把家里东西拍卖了也不值几个钱。这情形高利贷那方面也晓得的。他不过说着吓唬人罢了。因此但凡丢着不去理它,他没有办法了,自然会怎样来妥协的。我时常用这个办法害得那般东西向我告饶哩。”他就像土匪头子似的姿势一只手端着酒杯,一口口地很痛快地喝着,一面夸他怎样欺负那些高利贷,穗积只好恭恭敬敬地听着。
“可是太不管的话,朝姑娘固然不好办,就是给街坊邻舍听了也不成话。”
“不要紧,不要紧,让他去吧。发封的事也干过两三次了,朝子大体也晓得是怎么回事了。那家伙不过故意拿那个做口实想逼出我住的地方哩。”
“可是总得有一个回信才好啊,要不然我也太不‘忠人之事’了。”
“不,不做一次弄清爽在你不反而要便当些吗?”
辛辣的嘲笑又开始了,但穗积已经没有把那嘲笑当嘲笑的气力了。他想既然这样也没有法子,率性什么也依着敌人所说的做吧。“世界上的事情都看各人心里怎样感觉。我这里说不愿再见情人的面了,对方却说偏要你见,那么不是用不着客气吗?干吗要捏出一些古板的道理来逃避这个呢?说做叫花子难为情吗?——哪里,没有的事。叫花子也好,卑怯也好,对方虽是坏心思来的,我却超越这个。超人?是啊,谁说我做不了超人。”
到十点半钟光景,从黑暗的院子里听见了一声“我回来了”,接着干子走进屋子来,这时穗积的眼色像从不曾见过这样东西的惊惶失措。那穿着舞台上的彩衣般的、极华丽的衣裳走上回廊进到厅子里来的她那浓艳的容光,婀娜的身段,不知如何在他的眼里感着一种荡人心魄的妖冶。于是重又喝起酒来,这下更使他酩酊大醉了。
“喂,穗积先生,请致意你的Sweet heart!”
他给干子拍着背直送到大门外边,是那晚将近十二点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