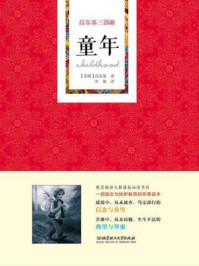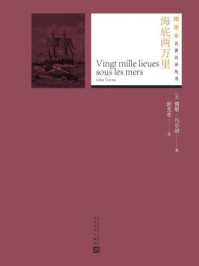添田君:
箱根那边怎么样好?想这时已经回来了吧。
你不在家的时候靠着你给我的机会我和你的太太谈过了,谈了一些什么这你大概已经由你太太那里听见过了吧。关于这个我想见你一次,这几天能到我这里来么?因为我这方面已经不想来奉访了。
穗积发出这样的信是第二天晚边,虽然现在就见了添田好像也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但一想起那太突兀的昨天早晨的事,觉得还想藉她丈夫再惜一次别。同时也含着想要看看在添田的面前很男子汉大丈夫地承认自己的失败,宣告绝交的时候添田会是怎样的颜色的好奇心。
“添田君”他想这样对他说。“长远搅扰了你了。你像在客人的脚边骗钱的、赶集的小贩似的把我愚弄得够了。我也为着想得到施与,甘心受你的侮辱,叫花子似的向你乞怜你固然不好,我也太卑鄙了。无论怎样我自己也对于自己实在太失望了。从今天起我想再也不学那种叫花子的行为,你应该也觉得清爽得多吧。”
假使这样一说添田不会感着寂寞吗?心思坏的人一旦失去了那发挥他的坏心的对手,一定要觉得寂寞的。穗积若从他离开,添田也没有像从来一样虐待朝子的争点,他会像剥夺了刑具的狱吏似的无聊吧。
但添田不知怎么,后来并不曾来过。这种在穗积是无聊的日子不觉过了一个礼拜。也许添田想就这样绝交吧,他是想既和朝子决别了用不着去再见穗积吗?既然不来供我愚弄就用不着那样的人,不如这方面反给他一个不理。为着使人痛苦,使人饮泣始终是执念很深务必做得很刻毒的添田就在这个时候也还要使他的拗性吗?
“你虽然说再不要学叫花子的举动了,可是不学了以后觉得怎样呢?不是虽然忍受些侮辱却还是时常能看看朝子的脸儿在你要幸福些吗?假使你后悔的话再做叫花子来我这儿吧,我随时都愚弄你的。”
在穗积的眼里映着敌人含着那种嘲笑等着他再去乞怜的样子。
可是这就是最后的,快到圆场的孤独吗?以后再不会有苦痛来了吗?所谓别后的寂寥就指这个境界吗?自己现在住着的地方是那样一个可怕的牢狱吗?这样反省时,穗积瞧了瞧自己的身边,到昨日为止要想看见时便可看见的人现在已经不能看见了,只要不老想着这一件事,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悲哀。辛酸苦痛从前已经尝过多少次了,给人家抛弃、欺负、羞辱也不在乎了,惯了。这完全痺麻了的他的心能够冷静地、平和地就像别人的事情一样凝视着这“最后的孤独”了。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就像无风状态一般的心绪同时也觉得莫非因为打击太大结果一时显不出来,要经过了一个月两个月才慢慢地会涌现吗?
有一天早上,是离分别之后约过了半月光景,刚洗过脸的穗积还穿着睡衣,凭着窗子一面喝茶一面展开报纸的时候。
“已经起来了吗?”
这样说着,一位女客从纸槅子外边走进来,那便是朝子。他虽然觉得有些意外,但一看见含着笑的她的眼色的那一瞬间,穗积也不觉轻轻地答道:
“啊呀,请进!”
她是那样平静地装着就像完全是当然的事似的进来的。
“怎么样了?又有了什么事吗?”
“是呀,添田到今天已经有十天没有回家了。我想问你或者晓得他的地方,所以来拜访你的。”
“我这里也没有一点消息,可是该已经不在箱根了吧?”
“那第二天就从箱根回来了,在家里住了两三天,就一直没有回来了。”
“那么,看见了我的信吗?”
“看见了啊,他还在我的面前读给我听了。”
“他说了些什么没有?”
“他说‘唔!暂且别管他怎样吧。虽然说不来了,回头看我叫他再来。’他做着怪样子笑了哩。”
“唔,这倒像添田君说的话。那么,因此在叫我到你那里去以前,倒先使你来我这里了吗?”
“可就是哩。虽然本想是不好意思来的。”
这样说着的时候,她的脸上才带着两点难为情的红晕。
“我想添田一定同那个女人一道住在东京的什么地方,是什么地方呢?你猜得出是什么地方吗?”
“猜不出,不过干子每晚要上戏馆唱戏的,问问干子不就晓得了吗?”
“可是我怎么好上干子姑娘那里去问她呢。”
“那么,你是说要我代你去问吗?”
“是啊,对不起。”
“我也想大半是这么回事。可怎么啦?那样嘴硬的。”
穗积用开玩笑的口调说,一面嬉嬉的笑着。
“不是说以后不拜托我做事了吗,现在那种威风呢?”
“还是除了拜托你没有别的法子想了,那么你是说不肯替我去问吗?”
“这可难说,高兴的时候也不妨替你去问问的,不过上趟的话可取消吗?”
“好啊,取消了吧。因此你千万替我帮帮忙啊!”
“若是问明白了地方,你去见他吗?”
“我去有点不好,你不能也替我去吗?”
“反正是你拜托我一遭,我不妨顺便去一去,不过我总不好用绳子把他拖回来呀。”
“那自然不必那样,他若是不回来就不回也不要紧,只请你传传话就得了。家里现在真没有办法,两三天以前执达吏来把什么都发封了,说这个月十号以前,若是不设法筹到钱就要把家里东西拍卖哩。”
“哦,那倒没有晓得。添田君怎么又借了那许多钱吗?”
“因为玩得太厉害了,单止透支稿费怎么样也不够用。他不管是印子钱也好,什么钱也好,一点也不思前虑后地胡乱借来用。”
“那么只要说家里因为这个缘故弄得没有办法,要他把高利贷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就够了。不回来也不要紧,是不是?”
“那他能够回来固然更好,但若是勉强催他,他反而要执拗起来的,所以我安排老老实实地等着他。我想他总不会一个月两个月不回的。”
“这很难说,假使隔一个月两个月也不回来可怎么办呢?”
“讨厌,别那样唬吓我了。”
“这有什么,你不是很安心地说‘不回来也不要紧’吗?”
“我哪里是安心哩,我是太受着他的欺负已经成了慢性了。假使真到了不回来的时候那我也会亲自跑起去,恃蛮也要把他拖回来的。”
“真的吗?丈夫是那样一种好东西吗?”
“不应该好吗?”
“不是不应该啊,我不过说添田君太幸福了啊。”
穗积这也原是当着笑话说的,但他的嘴唇上的微笑消失了,声音缠绵在喉嗓里却无法掩饰。朝子的表情也同时变了,她故意不回答男的叹伤,像畏惧他的视线似的低着眼睛默想了一回,便完全说着另一回事。
“可是我想今天也许不能见着你哩。我想你不会说‘不是约好不见了吗,来干吗呢?回去吧!’”
“因此你才不要人通报走进来的吗?”
“不是,我是请过他们通报的,娘姨说:‘在家,请上来吧。’就把我带进来了。”
“假使我说:‘你回去吧。’可怎么样哩?”
“那你可别想我随便就回去吧。像这样进了这屋子我想恃蛮也得拜托你的。”
“早晓得这样把你推出去,不许进门就好了,咳,可惜了。”
“哼,哼!”
朝子鼻子里笑了。
“那样的事我是惯了的,吓不倒我啊。”
穗积渐渐在谈话中间觉得自己的心里发生着一种说“憎恶”,许稍为弱一点,是一种对于这女人的淡淡的反感。平常一和她相对不管后来怎样总先觉得自己浴在一种甘美的情绪中间,但今天不知什么缘故和平常不同,他的心情怪尖锐的。那一来许是自己的心已经那样的粗犷了,但朝子今天早上确也变了。诀别的那天那样顽固,那样执拗的她怎么会这样宽心地跑来呢?从前她固然也有悠悠不迫的地方,但那种悠悠不迫之中从不曾失去她那特有的纯真。今天早晨的举动却有些地方甚至使人感觉得有些厚脸皮了。而最使穗积不愉快的是藏在那种厚脸皮里面的她那种“不自然的贞淑”。她不是以穗积为目的而是想念她丈夫到这里来的。仅仅为着想要知道她丈夫的地方不惜把她的性子和体面都不顾,蹂躏那个誓约跑到这儿来,若许他进一步猜想时她不是明明料得定懦弱的穗积没有拒绝她的勇气才来的吗?她不是那样打着无心的笑脸献着媚态来做她的辩解吗?这若是昔日的照千代决不是能弄这样的手段的女人。穗积所恋爱的朝子应该是使人想像为一切虚伪的东西,技巧的东西的完全相反的一个高贵的女性。
“她也许和我一样以那最后的一天为转换点没落起来了吧?”
他这样想着目不转睛地望着还含着笑的那哑谜似的女人的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