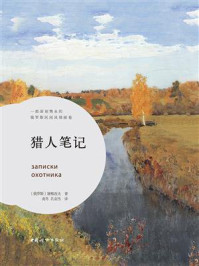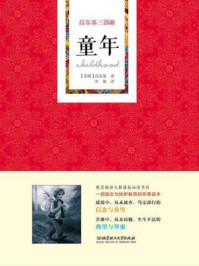从刚才起已经跳过多少次了,那一种是Waltz或是One Step这穗积一点也不懂得。只觉得那使人跃跃欲动的音乐的流波不断地在他的耳里震响着。他的前面还有一杯没有喝完的Cock tail,他一面慢慢的像舔着似的啜饮着那酒,随意听着音乐时,就好像大波小波以及种种东西不断地打他旁边通过似的。……喳,喳,喳地一面摇撼着满堂而涌起来得那强烈得音响,就像远远的退了潮以后忽然又听得微弱的波音,这波涛慢慢地加高。看着看着汪洋澎湃起来,穗积觉得连自己这凝然不动的身子都被这狂流卷起去了一样。“流吧,流吧,随便流到哪里去吧!”他有这样的感想。
眼前一切的东西,辉辉煌煌的无数的电灯,跳舞着的群集,高敞的屋顶,两层,三层,四层台阶上的人们……这些东西都给这洪水卷成一块儿流起去。这热闹的Dane Hall就像一艘巨大的船正在海洋上进行,我自己却成了那船上的乘客的一员,很渺小地伏在那甲板的一角。我也不知道这个船要开到哪里去,只好委之于自然的运命。谁也不来理我,他们的话是不懂什么意思的外国话,只晓得这同一条船上和我隔得很开地乘着添田和干子。”
这在穗积是不可思议的联想,使他想起五六年前为着收回爱人由长野到东京去的晚车里面那长得可怕的,无法排遣的旅行。“那时候我也是独自一个,可是那时我还有希望,有情热,有男儿的意气。但那一些东西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亏着谁把我弄到这样难堪的呢?这就是所谓惨败了。因此我才能这样喝着酒,也不觉得可悲,也不觉得可恨。这个状态便是供人践踏惯了的状态,不知不觉的使我堕落到这样了。现在想起来,那时是坐夜车去的。那是我对于恋爱的最后的努力,而且那便是绝顶了。以那为一个转换点我渐渐被坑陷在泥沼里了。”
照千代,Gretchen,被他们那样称呼的时候的她的影子,忽然呈现在穗积的眼底了。病着肺尖,提着药瓶每天到他的病室来的朝子。从那病院的诊察室,隔着玻璃窗,正当她坐在椅子上的头上的天空,可以看见冬天早上的信浓诸山带淡紫色地露着寒冷的肌肉。穗积在那屋子里拉着她的手,诊脉,轻轻地敲着她的胸脯,听她的内脏的声响。“我,这样的单弱真是能够活得长久吗?”蒲柳般的体质的她常是这样问他。好容易她开始自立起来是呀,那时候她才十六七岁吧!在某一个宴会的厅上舞着“京都的四季”做余兴的时候。她也曾有过在那种华灯影里舞扇轻翻的良宵啊。那时候对她寄着朦胧的爱慕的青年医学士便是他了。从那无可追还的遥远的过去岁月,直到今天之间的一切的情事,成为一个长的连锁无涯际地使人想起来。
“怎么样了,穗积先生,那杯酒还没有喝完吗?”
一面说着,回到桌上的是干子,那后面就像从者似的跟着添田,并且赶忙替她搬好椅子的位置,还替她披上大衣。
“啊,大衣请搁在那边。倒不如请你替我扇一扇呢。跳得太吃力了,出了一身冷汗。”
她从带子中间取出一把扇子,添田接着轻轻地替她扇起来。也是个额头很窄,圆圆的脸儿,眼睛很大,嘴唇很薄,低的狮子鼻的女人,和照千代的年轻的时候的容貌比起来虽然不成比较,但添田中意的恐怕是她的媚态和西洋人的表情吧。
穗积虽然对于这个女人从不曾感着什么兴味,但只记得她那非常柔软而肥白的手指头。看了那个他有点想起做小孩的时候喜欢的那面疙瘩,那些指头上时常灿烂着很怪异的指环都像添田买给她的。今晚她右手的无名指上又戴着新的宝石了,正中辉耀着玉虫色的巨大的眼珠,周围嵌想着金钢钻的细粒。
“那戒指很不坏,什么时候买的?”
穗积说。
“两三天以前才做好的。你看这个怎么样?”
干子正想从指头上取下来给他看,但她突然皱着眉头。
“啊呀,紧得很,真是紧得很!本来我的指头又粗又短,与其戴那种精致的还是这种粗大的东西合式得多。不过他说假使做得小一点紧紧地篏在肉上,指头要显得柔软些,所以特意要他做小一点。可是紧,紧的很,简直不容易取出来。”
“用不着勉强去取它,因为不是戒指好看,是戴着戒指那个手好看啦。”
“那么说,你就看看这个手吧。”
那粉嫩的,雪白的,像面疙瘩似的物质猛然搁在穗积的掌上。他觉得是一种湿润的含着毛毛汗的优婉的东西。
“怎么样?合式吗?”
“合式得很。确实这种魔性的图案同你的指头很调和。这样看去把女优的指头的特征完全显出来了。”
“什么缘故呢?”
“什么缘故可说不出来。”
穗积不知不觉地捻着她的指头弄着那宝石。
“那恐怕是这玉虫色的色调的关系吧。这到底是什么石头哩。随着光线的明暗,色彩的变化非常的好。看去很凄厉的有一种妖魔似的味儿。”
“那么,你说我是妖魔吗?”
“哈,哈,哈,哈!也不是那样的说法,不过……”
“女优大概都是妖魔啊。”
添田说着干了一杯whisky-Soda。
“那是叫Alexandlia的宝石,白天里看是紫色,到晚上变成红色。这是轻薄人的象征啊。”
“好吗,你那样说,今晚我不同你去了。”
“哦?那么难道你另外还有约吗?”
添田嬉嬉地笑着,斜眼瞪着那使性子的干子的脸。
“想要买的东西都要人家买了,当然用不着我这样的人了,是不是?”
“好吗,那么你这个捞什子戒指还给你吧。”
“得罪,得罪!刚才是说笑话的。第一你就想把它取出来也取不下,不好玩得很吗。”
“只要上点肥皂马上就取出来了。我一定还给你,请穗积先生做证人吧。”
他们两人这样的打情骂趣。穗积一时不能不静静地听着。照他们谈话的模样,添田要带她到箱根去。干子说是安排跳舞来的,所以故意穿得很少,到箱根去一定要着凉的,下一趟去吧。添田的脾气是一旦想做什么不管怎样都要做到的。他说再跳一次舞就坐汽车到东京驿赶十一点到国府津去的火车。
“好,就这样决定了。因为我今晚无论怎么样是不回家的。”
“唔,又来了,那么又和太太吵架了吗。”
“一点不错。这是穗积可以做证人的,对不对,穗积君?”
“哎呀,叫我来做证人可太不人情了。”
“真是哩,穗积先生才难为情哩。”
干子说。
“干吗老是那样在朋友面前给太太过不去呢?这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啊。”
“不是我对他骄傲,是他自己拼命要看我的老婆也没有法子。”
“哈,哈,哈,哈!这个酒席可吃不消。”
穗积说,可是在平常那样的卑屈的心理中有一种好像欢喜那种卑屈似的,给他们两人开玩笑反而愉快似的异样的高兴。“有点作怪我好像很醉了。”他一面这样想着,但他还是愉快。
“可是既然穗积先生那样爱上了她,把她收饰得好一点送给他不就得了吗。老是听得你说讨厌她,讨厌她,却又不能够离开她。看起来你还是没有志气呢!穗积先生,对不对?”
“哈,哈,哈,哈!”
穗积很掩饰的大声地笑了。在那一瞬间添田好像露出了一点不高兴的样子。
“在没有志气一点我没有攻击别人的资格,恐怕我是第一个弱者吧。”
“你自己标榜着自己是弱者还算老实的,像这个人的一样专是口里说得了不得。”干子回顾着添田说。
“你不是这样的吗?你说。”
“哼!”
“哼什么呀!不承认的话就把太太送给穗积先生看看。”
“可是不幸我的老婆又是没有我不能过日子的啊。”
“吹什么牛呀!”
“事实上是这样的又有什么办法呢?无论怎样打她,踢她,她总不肯离开我。”
“真的吗?穗积先生,真是这样的吗?”
“惭愧得很,好像真是那样的,这我倒可以作证。”
卑屈到了这个程度反而很有趣,在那里自有享乐的世界。“率性更卑屈一点竭力供他们开玩笑使他们欢喜吧!”忽然穗积浮上了某种滑稽的空想。“添田这东西虽然这样傲然地把我不看在眼下,可是假使我始终装作弱者暗暗地复仇,可怎么样呢?”想起来,那种方法也有的是。“比方说,用秘密的手段使干子生病。我现在虽是个穷文人,但从前也算是一位医学士,那样的事也没有什么难做。想法子使她害什么重的流行病,使她那肥嫩得像面疙瘩的纯白的指头黄瘦起来,指头上的戒指可以随便脱落。那么,添田一定很着急地守在她旁边看病,于是添田也传染了。假使没有传染也可以使他传染的,于是结果两个人都痛苦地死了。不,添田是很薄情的,假使干子害了可厌的病他也许到她的旁边来都不来的。可是那么着,朝子可幸福了。只要干子死了的话。不,这还是不成吧。抛弃了干子,添田一定会找第二第三的干子。一直不回到朝子那里来。比什么都好的办法,是使现在在这里,在我的眼前穿着晚礼服,拿着威士忌杯子露着恶魔一样的微笑的,肥胖的,凸肚子的添田这个人物一天忽然从地上消灭。那么着朝子不用说,就是我也多少可以幸福。只要我能极阴险地,谨慎地,用谁也不注意的方法,很巧妙地谋死添田的时候……是呀,那是非常容易的事,只要比现在再卑屈,再厚脸皮一点便毫不费力地可以做到。”
穗积又独自一个留在桌边了,因为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又起身跳舞去了。穗积的脑里好像想小说的情节似的长时间玩弄着那种空想。“本来我虽然是弱者,但弱者自弱,却有一种怪执拗的地方。强的人在某种机会可以忽然断折,可是我像蒟蒻似的黏巴巴的不容易断折。我这样的受着难堪的待遇却还是这样活着。照这样子就陷入再难堪的境地也许能意外地不觉得什么,像现在这样供敌人开玩笑和打定主意杀掉自己的敌人,在堕落的程度上可有多大的不同呢?除掉一个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事实以外,在我的心情上能起什么变化呢?侥幸社会上,特别是文坛上,一般的同情集注在我的身上。我已经被公认为老实的,循谨的好人。即算弄死了添田恐怕没有一个人会疑到我身上吧。就是朝子也一定连做梦都不会注意到那点。如是,我不难慰藉她,恢复她的爱,圆圆满满地结婚。社会上一定说是‘正义胜利,恶魔灭亡了’,大家都赏赞我说:‘难得你忍耐了这么长久的日子,支持这样长久的纯洁的恋爱。’我只要照样暧昧地卑屈地,嬉嬉地笑着就得了。对呀,把这个写作一篇小说不好吗?大家以为添田是恶魔,我是善人的时候,我反渐渐变成了真正的恶魔若是把这种心理的过程描写出来,的确有趣。”
一块儿坐汽车到东京驿把他们两人送上了到箱根去的车之后已经十一点半钟了。那时本还有电车,但酒还没有醒,因此穗积冒着寒风跄跄踉踉地走回龙冈町的公寓了。清朗的天空里高悬着寒月一轮,海上Building的建筑物像城郭似的朦朦胧胧地矗立着。“添田至少要到后天才得回来,现在去找一找朝子看吧。”这样想了一下他马上又像想了一件很蠢的事一样把它打消了。同时刚才的空想又在脑筋里反复了一遍,但把它写成小说的那一类的兴趣早一点没有了。现在的他既没有写成那样大作的手腕,也没有那样的精力。
他接到由箱根写来的一封信和环翠楼的画片是后来第三天晚上的事。画片上是和那女人一块写的,满列着开玩笑的话。“虽然冷但是好得很,红炉煮酒,至足乐也!”这样的句子的旁边添着干子的俏皮话:“穗积先生,别信他撒谎吧!他是不服输才那么写的。别说我,添田也着了凉,可不是活该吗?穿着晚礼服跑到箱根这样地方来。哈嚏,哈嚏!”但信是添田一人的手迹:
昨晚失礼得很,要是说‘再失礼一下’可对你不起,不过想拜托你做一点麻烦的事情,不是别的,你接了这封信的时候可否替我去吩咐朝子要她筹一百块钱来呢?请你对她说因为没有那笔钱我回不来,并且非赶快办不可。假使迟了,一百块还要不够。你取得了那笔钱便请你费心用电报汇来。这样的事本不必特别来麻烦你的,但实在因为我不想叫朝子知道我的地方。百来块钱大概是有办法的。不过我想与其我自己直接说,不如烦你代说反倒好些,一切都拜托你吧。因为好在在你这也不是十分不愿意演的脚色,哈,哈!
钱在后天正午以前一定要请汇来。
在这“好在在你这也不是十分不愿意演的脚色”,那一句的旁边加上了一些圈点。这自然是要紧的信,但穗积觉得那中间杂着嘲弄他的意思。因为添田没有不叫朝子知道他的地方的必要。两天三天不晓得丈夫到哪里去了的事在她是很平常的。有时就晓得了地方,朝子也并不想要怎么样,顶多不过是抽抽噎噎地躲在家里哭。那个样子解释虽然也许是穗积的偏见,但恐怕是添田以他那种奸猾的兴趣故意使穗积心里作难。他是想在自己不在家的时候,与这两个弱者以碰头的机会,看他们会谈些什么话。
“哼!他是作弄我的。好吧,既是这样我就给你作弄吧。”
即算现在就到她那里去也快十点钟了。像这样深夜和她两人对谈真是多少年来不曾有过的事啊?穗积觉得自己心里虽不能说是希望,可射进一缕微弱的光明了,他觉得大可以很顺从地感谢敌人所赐与的机会。凑巧故乡寄来的医院的租金还剩下了五十块没有用,他想着若是她不够的话也可以替她通融,并且暗暗的想像着那哭肿了眼睛的可怜的朝子,他便走回小石川那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