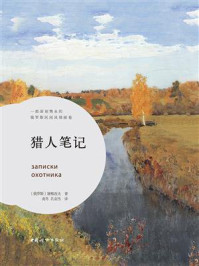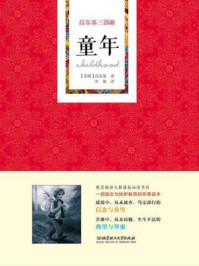那天晚上,他们俩用那种调子继续谈着,等到离开丰国馆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多钟了。
“那么,我在这里少陪了。”
添田走到电车路上时这样说着站住了。许是很醉了吧,呼吸也粗急得很。
“我看,我送你一程吧。”
“不,我这会儿还想到一个地方去。”
于是添田很威势地“喂!”的一声,唤那在街头等客的黄包车。
“唔,不错。反正今晚是不回去的了,后天总是在家的,你来吧,假使你那样想看见朝子的话。”
在车上让车夫用毛毯盖着膝头的时候,添田很高兴地豪快地笑了。
“只要你让我见她,我每天都来的。那么后天你一定在家了?”
“唔,总是在家的。要是来,晚边来吧。”
虽然是秋天,但已经是快到初冬的薄寒中人的晚上,所以添田紧披着上了獭皮领子的黑骆驼绒的大衣。本来他有一种夸豪奢的脾气,讲究穿那种很阔绰的衣服使人家当他是大少爷而不愿人家知道他是文士,同时,他那种肥满的体格也相当的使他和那衣裳相称。穗积悄然地站在街路上,充满着近于羡望的感情仰望着车子上那在黑夜里都显得白白胖胖的添田的脸儿里,在那很温暖的毛皮领子里面。这时“可恨的人”,“情敌”,这样的反感已经一点儿都没有了,只想着:“我也要像这个人一样厚着脸皮横行无忌,可多么好。”就像对于一个什么伟大人物一样的感想。
可是到了那“后天”的晚边,他像散步一样向小石川那方面走去的时候,忽然想道:“就是我自己的脸皮也不能算是不厚的了。”穗积独自一个人好笑了。“无论她丈夫怎样允许了,可是像我这样厚起脸皮去看那已经不见得怎样爱我的别人家的老婆的人,世界上怕没有几个。人家丈夫固然是那样的丈夫,我这情夫也就够混蛋了。可是我自己还要骗自己说是趁着散步顺便去走一走的,这真是更可笑了。”在一路上就像看见他自己的滑稽的样子映在镜子里似的,心里好笑得很。但他的脚步自然就转到他平常惯走的那条横街去了。
“哎呀,你来了吗?现在正演着一出全武行呢!”
应该是今天刚回来的,可又像安排到哪里去似的,穿着和早几天完全不同的漂亮的晚礼服的添田站在房子的正中这样说。不错,恐怕真吵过什么激烈的架吧,柜屉子哪,领子和衬衣哪,还有许多东西都撒了一满地,桌上的花瓶也打翻了,在这中间朝子背对着这边脸儿朝着厅子上,两个膝头靠着楣边的那么蹲着,蓬乱着松了把子的头发,悄悄的正用鼻纸揩着眼泪哩。
“这可不是添田知道我会来故意演这样的戏文给我看的吗?”首先使穗积感觉得的便是这种猜想。穗积知道自己做着添田鹅傀儡,单止那个还不要紧,但一想到那为着演给自己看,常常得做他所谓“全武行”的配角,在那残酷的鞭挞下面呻吟痛楚的亲爱的人的身上时,穗积首先不能不埋怨他自己。“只要我不到这儿来就得了。因为我在这儿,添田更增加他的恶魔的气焰,更加虐待朝子。这么说来,使她不幸的可不是我吗?添田也许为着打击我才那样打朝子的,可知道打朝子的不是添田而是我自己,就是我在这里使她痛苦呢!”
“添田君,要打朝姑娘时请打我吧。应该挨那鞭子的人在这儿哩。”
穗积的心里是这样的,他觉得就这样说着俯伏在添田的面前都可以。但是——
“讨厌,‘全武行’哪什么的,瞧你又说得那样了不得啦。没有什么,穂积先生。”
朝子红着两个眼圈儿含着嫣然的微笑这样说。她一面收着鼻涕,一面把抽屉依然插上柜子里,把花瓶摆好,用没有什么的表情把地下散乱的东西都收拾好。照她那态度推测起来,假使穗积说说愿意代她挨打,恐怕她一定要说“谢谢吧,用不着你费心”的吧。“夫妻俩的事情,夫妻俩了结,用不着别人来管。”她一定这样说吧。穗积好像觉得自己的眼前陡然间在暗暗地低低地沉下去似的。觉得这坐着各有各的心思的三个人的客堂里面,就像荒凉的沙漠一样,而且寂寥的并不止他自己一个人,添田和朝子也都被赶逐在这荒漠之中,一任风沙吹刮,雨雪侵凌,谁也没有人来救助,都渐渐这样地零落的死去。
“怎么样,我现在要上跳舞场去,你高兴同去玩玩吗?去见识见识一下也值得哩!”
添田一面把穿着折痕很整齐的裤子的两条腿伸出来躺着,从袋子里拿出表来用满不在乎的样子说。
“可是,你不是今天刚回来的吗?”
“唔,因此才演出刚才那样全武行了。不过那样的事已经过去了,无论怎么样现在是要出去的,你同我一道去怎么样呢?”
“去也可以,可是今晚你若不回来,我也要给人家埋怨的哩。”
这样说着的时候,朝子突然又背着穗积抽抽噎噎了一回,忽然又站起来跑到隔壁屋子里去了,一会儿只听得那里面有可爱的道子的娇啼声。那孩子刚才许躲在暗地里窥着她爹妈吵架的样子吧。很胆小似的紧抱着母亲的膝头,脸挨着脸从纸槅子缝里凝视着父亲这边的那小眼睛里,灿烂着一颗颗大的泪珠,平常是神经质的,虽然多病却很聪明的孩子,不大亲她的爸爸,而亲“穗积叔叔”的,但他觉得这孩子的眼睛美丽之中却很可怕。“给这孩子怨恨着的怕不止她的父亲吧?”他不能不这样想。
“你真是个‘超人’,不是连孩子也哭着吗?”
因着添田勉强催他“去去”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出来的穗积,一出大门便这样说。
“哪里,这是她惯玩的那一套。随便一件什么事情她就用孩子做枷来枷我。”添田耸着肩笑了。
今天吵架的起头是这样的。穗积因为是多回的事,那样的话已经不愿意听了,但据添田用凯旋将军似的口吻很得意地说明的话:因为正是月底了,预备了一百五十块钱任怎么样得开销账目的,添田却恃蛮地要拿去五十块,这样便开始争端了。“你虽把朝子恭维得像一个理想的会治家的老婆似的,其实她做起家庭的主妇来简直就没有运用经济的资格。幸亏我是个文士还不要紧,假使她做了商人的老婆可真吃不消了。”那么照添田的意见,反正诗人小说家的收入是不规则的,每月的开销没有法子按时候付清,而且照着他的意思巧妙地处理家务使做丈夫的不担心思,这应该是他们妻子的责任。可是朝子不但没有这个资格,更有使人不高兴的是她连这责任的自觉都没有。第一她就不会对付那些要账的,她以为三十号一来什么都得付清的。付自然也得付出一些,但家里总得剩下多少的余裕才成她却不顾前后,随着人家要多少给多少,因此存下的钱就这个手里进,那个手里出去了。
“因此她是个蠢东西。”
添田说。
“在这个地方已经住上五六年了,拉人家三两个月的账也不算什么。因为一来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急用,二来我自己随时也有零用钱不够的时候,多少必须要留下一点,她也不懂得。我问她一个月到底要用多少钱,要她记起账来,细细地査一查,这她也做不到。她的数理观念简直就等于零,这种没有教育的女人真没有法子。”
“不,这与其说是教育,恐怕还是性质的关系啊。比方你透支了稿费可以毫不在乎地不顾信用,那样的把戏我可就玩不了。善于对付要账的女人有时候固然也有很便利的地方但在我反而觉得有点可怕。那一种驯良的地方正是你太太的长处呢。”
“不过,你想连厨房里的账都管不了的那种女人还有什么可取呢?干吗娶这样的女人来做老婆呢?这样想起来更使人生气了。”
穗积不答他的话,却故意问他别的事情。
“那么,你总算把那五十块钱搜括来了哪?”
“我气极了拿了一百块钱来了。哪里!平常也不是这样的,因为昨晚和前晚都在外边过夜,刚回来马上又说要出去,她有点不高兴起来,硬不肯告诉我钱在哪里,我说‘你不拿出来,好!”我把柜子、箱子信手乱翻终于给我找出来了。这下她拼命来抢,任怎么样也不让我拿走啊。”
“哦,那么说抵抗得很厉害了,这因为是很紧要的钱吧。”
“她的意思与其说是不让我拿钱,不如说是不想让我走。我的脾气是吃不了那个的,气起来反而非走不可。可是她一辈子也不懂得丈夫的心理,真是个蠢东西。后来没有法子她只好说那么今天晚上请你一定要回来的呀。你想既是这样,干吗起初不那样说着好好的拿出来呢?现在无论有什么事今晚可是不回去的了。两晚三晚尽可能的不回家,尽所有的钱都给花掉吧。”
两个人这样谈着走向白山上那边去了。但那天的“全武行”许是特别的猛烈吧,添田用很兴奋的脸色。
“在这里喝一杯去吧。”
说着跑进一个咖啡店,站着喝了两三杯威士忌。
“到底我自己为着什么这样自在地跟着这个人去看跳舞呢?”穗积和添田并肩坐在向丸之内那方开去的汽车里独自这样想。“我至少今天的我一点也没有去窥探那种欢乐之乡的好奇心。我的心里只充满着刚才目击的情景,和由添田的话里所能想像的那可怜的她的姿态。可是我却又信人家的劝诱跟人家出来,和这残酷的丈夫一块儿去干那些逍遥自在的勾当,我该是怎样一种奇妙的人啊。”但这种心理他并非不能说明,到某一程度“这一来是因为我就想留在那里慰藉她和道子姑娘,但我已经没有那样的资格了。”
这种怪的僻见颇有作用。还有一种,自然也是由那种僻见产生的,就是“既承他特别相邀,若是不同他来,好像有点故意对他表示不必要的好意。”使人家觉得他全是以朝子为目的来交际的,对于添田没有什么感情。不,不是“觉得”而是事实上是这样,这是他自己和添田都公然承认的。不过这个时候他好像不愿意让朝子感觉得这样。
“那么为什不断绝对于朝子的念头呢?既然不能断绝为什么又不愿意她感觉得这样呢?为什么要这样啰啰嗦嗦地,哪一边都不是地,像钟摆似的活着呢?”这样想来想去,穗积自己对于自己也莫明其妙了,只起了一种自暴自弃的念头,好像说:“管他吧,反正我自己很忧郁,为着把这忧郁深刻化,管它跳舞场也好,什么也好,随便你把我带到那地方去能。尽管金鼓喧天的在我的眼前闹着跳着吧。瞧一瞧包围在那种热闹的狂乱的群集中间时这孤独的我究竟是怎样一种心理,这样试一遍也不坏吧。”
跳舞是在旅馆的Grill Room开始的。老实说,穗积既不明白Grill Room是什么意思,连到这个近来刚刚起成,以样式新奇著名于时的旅馆的内部来也都是第一次。刚进来那一瞬间,他的身子一轻像给人高高地提到了另一个世界似的,不如他所预期的那样郁闷。
屋子内部是个半圆形剧场的样子,中央很宽大,几乎直耸到那高的屋顶。周围就像一格格的摆东西的架子似的,有三层或是四层的台阶。并且很奢华地在四处的柱头和凸出的边上点着许多电球,那些电球的装置大体都是先反射在墙壁上然后间接地照明着场子里的穗积有了以多少的平静,甚至几分的空想与兴趣来观察这情境的余裕。那喧嚣的爵士乐队(Jazz Band)和华彩绚烂的舞客好像完全与自己无关的,就好像璀璨在远处的星光或是浪花似的,并不特别讨厌。
“你觉得怎么样,穗积先生,你的First Impression?”
干子已经在场子里一个屋角上占了一个台子,等着添田。
“不比想像的那样坏,陡然同到这样怪的地方来,这样看着,引起我种种的空想,倒也觉得很愉快。”
“那么,你学一学跳舞,怎么样?”
“跳舞吗?那可……”
穗积笑着,红着脸搔头发。
“那么,你喝喝酒好吧。单那样坐着看没有趣。”
“唔,喝一杯也可以。”
添田替他叫了一种Jim-cock tail便催着干子跳舞去了。
因为是很好喝的甜酒,不觉很大意地一点点喝下去了,穗积渐渐觉得身上火似的暖热起来,头上也有点感着发昏似的醉意。但很妙的是虽是这样却不像平常那样的难过。难过也是难过,但在那给人压着胸部似的呼息不匀的感觉中间,不知道怎么样却有一种荡气回肠的快美之感。他想“假使给朝子舍弃了走到外国去……是呀,假使去了我一定是这样的情味吧。可是这样又怕什么呢?就这样不也很好吗?这样不是也大可以生活吗?”
穗积听得那非常有的劲儿的,洋洋盈耳却又不大听得惯的曲调的巴利东的歌。乐队里有一个年轻的西洋人站起来,睥睨着广场的群众,做着各种奇妙的身段合着音乐像是正唱着一支很有趣的歌儿。他那面庞活像王尔德。许是光线的关系吧,他的眼睛就在西洋人里面也显得异样的蔚蓝,头发是红的。跳舞着的女人们虽然有一半是日本人,但谁都好像是和穗积没有关系的人种。从什么时候日本也产出了这样的女人了吗?头的梳法,眉毛的画法,以及种种地方都好像施着种种精细的技巧,她们的眼睛,鼻子也仿佛带着西洋人的味儿,都是那么老练得很的样子。拿起朝子那样的女性比起来,她们确是另一个人种。她们是住在和生长在信州山里的穗积和朝子完全不同的世界的人们。
“我和朝子假使生长在西洋可怎么样?假使我们俩是红颜的少男少女,现在要是能够像在那边跳着的那一对年轻的情侣似的携手跳舞的话,假使有那样的时代的话……”
穗积想着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