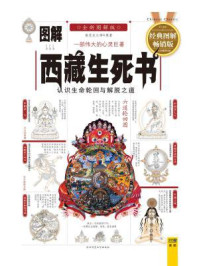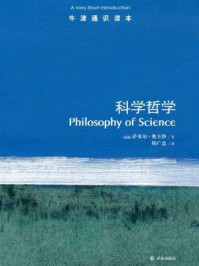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对国内汉语学界是相当陌生的一个名字,他只是偶尔在社会学概论或简介之类的教科书中卑微地占据一小节,或露一下名字而已。早早就盖在他身上的“新康德主义者”和“形式社会学家”的印记,更加模糊了西美尔独特的学术成就和富有生命力的多维文化思想。作为古典社会学思想家,他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成为与斯宾塞、孔德、马克思等人齐名的欧陆思想型学者。
[1]
在20世纪声名鹊起的卢卡奇(Georg Lukács)、布洛赫(Ernst Bloch)、舍勒(Max Scheler)、布伯(Martin Buber)等人都曾师承西美尔,却无人长久忠诚地继承他的思想遗产。在西美尔身后,将近有五十年的时间,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他和他的学术思想的存在。他的学说“飘到四方,消散于他人思想之中。”
 难道正如卢卡奇对其师的评价,西美尔从不是什么伟大的育人者,只是“整个现代哲学最重要、最有趣的过渡人物(bergangserscheinung)”,“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过渡哲学家(bergangsphilosoph)”?
[2]
或者西美尔追随尼采似真似假的说辞,以其过渡式的、毁灭性的存在方式昭示后人其悲观主义哲学思想?
难道正如卢卡奇对其师的评价,西美尔从不是什么伟大的育人者,只是“整个现代哲学最重要、最有趣的过渡人物(bergangserscheinung)”,“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过渡哲学家(bergangsphilosoph)”?
[2]
或者西美尔追随尼采似真似假的说辞,以其过渡式的、毁灭性的存在方式昭示后人其悲观主义哲学思想?

出版于1900年的大部头著作《货币哲学》(1907年增订版)是西美尔为数不多的大部头著作之一
 ,因他更以数量众多的学术小品文著称。这部几近600页、洋洋几十万言的作品,其中多数篇章也是由之前撰写的诸多小品文章敷衍扩展而成。西美尔在写作那些短文之时,已然在头脑中形成了一套有关金钱及其作用于社会和个体的哲学构想,因此这部书虽然论述面极广(纵向从古代社会推演至现代,横向则涉猎社会、经济、心理、宗教等层面),却并无支离破碎之感,堪称体大精深。全书分为“分析卷”和“综合卷”两大部分,按西美尔自己的说法,“第一部分将从那些承载货币之存在实质和意义的条件出发阐释货币,”第二部分则从货币对内在世界的影响的角度考察“货币的历史现象、货币的观念与结构”,即“对个体的生命情感、对个体命运的连结、对一般文化的影响。”顾名思义,“分析卷”从社会生活入手剖析货币的本质,剖析产生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所满足的需求,“综合卷”则反之,综合考察货币对整体的人类生活的影响,以此建立起西美尔式独特的世界图景(Weltbild)。据说,西美尔具有一种将分析与综合完美结合的天赋,是否这就是他如此安排该书的篇章布局的内在缘由呢?通常的研究者认为,“综合卷”更出色、更敏锐地体现了西美尔对金钱文化问题的真知灼见,西美尔本人更以“综合卷”最后一章“生活风格”为最,但也不乏侧重“分析卷”者(如Altmann,涂尔干),毕竟该部分所处理的乃是全书根基性的问题。
,因他更以数量众多的学术小品文著称。这部几近600页、洋洋几十万言的作品,其中多数篇章也是由之前撰写的诸多小品文章敷衍扩展而成。西美尔在写作那些短文之时,已然在头脑中形成了一套有关金钱及其作用于社会和个体的哲学构想,因此这部书虽然论述面极广(纵向从古代社会推演至现代,横向则涉猎社会、经济、心理、宗教等层面),却并无支离破碎之感,堪称体大精深。全书分为“分析卷”和“综合卷”两大部分,按西美尔自己的说法,“第一部分将从那些承载货币之存在实质和意义的条件出发阐释货币,”第二部分则从货币对内在世界的影响的角度考察“货币的历史现象、货币的观念与结构”,即“对个体的生命情感、对个体命运的连结、对一般文化的影响。”顾名思义,“分析卷”从社会生活入手剖析货币的本质,剖析产生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所满足的需求,“综合卷”则反之,综合考察货币对整体的人类生活的影响,以此建立起西美尔式独特的世界图景(Weltbild)。据说,西美尔具有一种将分析与综合完美结合的天赋,是否这就是他如此安排该书的篇章布局的内在缘由呢?通常的研究者认为,“综合卷”更出色、更敏锐地体现了西美尔对金钱文化问题的真知灼见,西美尔本人更以“综合卷”最后一章“生活风格”为最,但也不乏侧重“分析卷”者(如Altmann,涂尔干),毕竟该部分所处理的乃是全书根基性的问题。
《货币哲学》一书出现伊始就带给学术界很大的迷惑和震撼,迷惑是因为学界不清楚应该把它归为哲学类、社会学类、还是经济学类
[3]
,震撼是由于韦伯等名家对此书尤为重视,据说他在书中发现了一种精辟的货币-文化学说,在西美尔之前,尚未有人对货币这一经济-社会现象作如此透辟的文化现代性解说。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一样,《货币哲学》主要也阐释自近代以来的货币经济现象以及与它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不仅从社会学角度关注货币经济对社会及文化生活产生的作用,而且显示出建立一套文化哲学乃至生命形而上学的努力。《货币哲学》的立意并非那么单一,这也许是其同时代人难以全面理解这部书的原因。”
 《货币哲学》并非一部纯粹的经济学著作(西美尔言称“本书的这些考察没有一行字涉及经济学问题”),尽管它讨论了许多与金钱相关的经济现象。而且西美尔所倚重的独特阐释路向显然不同于韦伯对经济制度的分析,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批判,《货币哲学》是这位自称“哲学社会学家”以“哲学沉思精神”写就的(R.Goldscheid语),书中暗暗浮现着一种形而上的悲情。分析货币的社会经济机制不是西美尔货币理论的重点,货币及其制度化的现代发展对文化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的内在生活、精神品格的影响,才是西美尔货币文化-现代性理论的要旨所在。因此,弗里斯比(David Frisby)认为:“对西美尔而言,现代性以前的发展状况(prehistory)在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他认为后者,而非资本主义,对社会关系的转型和都市生活主要特征的根源负有责任……西美尔对成熟货币经济后果的反思代表了他的现代性分析的内核。”
[4]
西美尔认为货币制度是树根,而文化就是在树枝上开放的花朵。认识越接近树根,就越能揭示出货币制度与文化的内在关联。由此看来,西美尔主要是从货币经济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果,来探测这一对现代生活施以重大影响的经济事件。
《货币哲学》并非一部纯粹的经济学著作(西美尔言称“本书的这些考察没有一行字涉及经济学问题”),尽管它讨论了许多与金钱相关的经济现象。而且西美尔所倚重的独特阐释路向显然不同于韦伯对经济制度的分析,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批判,《货币哲学》是这位自称“哲学社会学家”以“哲学沉思精神”写就的(R.Goldscheid语),书中暗暗浮现着一种形而上的悲情。分析货币的社会经济机制不是西美尔货币理论的重点,货币及其制度化的现代发展对文化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的内在生活、精神品格的影响,才是西美尔货币文化-现代性理论的要旨所在。因此,弗里斯比(David Frisby)认为:“对西美尔而言,现代性以前的发展状况(prehistory)在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他认为后者,而非资本主义,对社会关系的转型和都市生活主要特征的根源负有责任……西美尔对成熟货币经济后果的反思代表了他的现代性分析的内核。”
[4]
西美尔认为货币制度是树根,而文化就是在树枝上开放的花朵。认识越接近树根,就越能揭示出货币制度与文化的内在关联。由此看来,西美尔主要是从货币经济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果,来探测这一对现代生活施以重大影响的经济事件。
货币和货币经济是经济现象,却又不只是经济现象,在西美尔看来,更是重要的文化事件。可以说《货币哲学》“处理了货币之前和之后的经济面;作者讨论的是金钱,但通过金钱,他让我们看到的是人和生活”。 [5] 西美尔认为,货币在社会经济事务中产生了宏观效应,但更重要的是,它所引发的社会文化主导精神观念的转变和对个体心理气质施加的影响。所以在《货币哲学》的“前言”中,西美尔声称其货币研究的方法论目标就是“为历史唯物主义建造底楼,从而,经济生活被纳入精神文化的原因的这种说法仍保证其阐释性价值,而与此同时,这些经济形式本身却被视为心理学的、甚至形而上学的前提的更深层的评价和潮流之结果”(《货币哲学》,页56。后文引用本书仅随文注英译本页码)。西美尔的货币学说并非要研究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货币经济学,他所谓的“货币哲学”,“货币心理学”是对货币在现代社会中引起的现代性现象作文化效应的分析,因而也是对货币的一种哲学式文化解说。特纳认为西美尔致力发展的是“货币作为人类社会现实中的经验之中介的现象学……《货币哲学》是对现代性和现代意识根源的经典研究”。 [6]
《货币哲学》所确立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当然不会令平庸的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满意,实际上也没有被涂尔干 [7] 、帕森斯(T.Parsons)等社会学家所接受。难道《货币哲学》(同其作者的命运一样)注定只是一个“过渡性作品”,一个“瞬间图景”?
最早从1889年撰述《货币心理学》一文开始,西美尔就开始着手检讨金钱所激发的形形色色的心理效应,尤其是金钱在现代产生的社会文化效果。在1896年撰写的《现代文化中的金钱》一文中,他论述了货币经济同时支撑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发展方向。
现代文化之流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奔涌:一方面,通过在同样条件将最遥不可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趋向于夷平、平均化,产生包容性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却趋向于强调最具个体性的东西,趋向于人的独立性和他们发展的自主性。货币经济同时支撑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一方面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程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金钱》,页6)
如果说前一种倾向是货币经济引发的社会文化的平均化、量化和客观化倾向,后一种倾向则同样是货币使之可能的现代社会保存个体自由和内心独立性的潮流。对于这两种势不两立的社会-文化倾向,货币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地予以支持。但货币是如何决定性地导致如此截然相反的社会品质产生,又如何不带偏见地游刃于两种发展方向之间,值得作一番深究。
货币的诞生可说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自此改变了人们对价值的看法。这与货币相伴相随的一个经济行为——交换相关联。现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内容的脱节,导致了货币功能的转化。
西美尔持一种主观的价值论,认为主体欲望的满足即可创造出价值,但他同时提出,通过经济活动主观价值得以客观化。在经济活动中,创造价值的——也就是满足千差万别的人的占有欲的——正是交换。“经济活动的明确特征……与其说是交换价值,毋宁说是交换价值。”
[8]
交换的意义在于使主体获得了各自所需的物品,满足了主观的需求,同时这种满足不只针对一个人,价值的主观性因此超越个体而客观化,“客观性=对主体的普遍有效性”(页81)。西美尔对交换的强调源于他的一个世界观原则——世界处于“基本互联性”之中。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同,西美尔认为商品的价值不可能产生于单独的因素,无论是劳动还是生产力,而是产生于相互的关系之中——此处即指交换。

传统社会的交换是人的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sociation)最纯粹、最原始的形式,“交换是创造了人与人之间内在联系的功能之一──社会,只不过替代了单纯的个体集合而已”(页175)。货币经济出现之前即已出现了自然经济中的物物交换行为,但由于物的价值依然固着于实物,并未导致人们价值观的转型。现代之前的货币交换由于经济活动的不发达(如雅典后期和罗马后期),还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货币经济和所谓的货币经济文化。现代的货币经济出现后,这一情形改观了。劳动分工的复杂化和社会关系互动的密集与扩大,是货币经济产生的前提,货币付酬方式也促进了劳动分工的发展。在货币经济的日渐发展中,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变得越来越纯粹,逐渐脱离了与其质料的关系。这就是在《货币哲学》第二章一开始,西美尔问的那个问题:“货币自身是否或应否成为某种价值?”或者:“货币可否仅仅是一种没有内在价值的符号或代用品呢?”
货币的双重本性──它是一种具体的、被衡量的物质实体,同时,它拥有自身的意义取决于把物质性彻底消解于运动和功能之中这一过程──源自这样一个事实: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reification),是一种纯粹功能的具体化。(页176)
货币兼具实物与功能的双重本性是一个历史的现象,货币的功能才是其本质特征:现代社会中的金钱早已没有什么实物的概念,而唯独是履行交换功能的载体,恰好印证了这一事实。所以,货币的双重本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分野越来越加大,货币的功能化倾向越来越显著。这对经济领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货币的经济价值不需假手物质实体(只需交换)便可获得。货币因其功能获得价值。这对文化领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货币成了价值的缔造者和符号表征。货币即价值,或可称为价值的流动(Mobilisierung)。
货币对文化过程的其他部分提供的所有隐含的意义都来自它的本质功能──为事物的经济价值提供最简明的可能表达形式和最凝缩的符号形式。对于价值的贮藏和转移功能,传统的看法是把它视为货币的主要功能,但这只是货币基本功能中较粗糙和第二位的表现。这种功能显然与货币的质料价值没有内在联系,但有一点也确实是通过这一功能而变得明显的,即:货币的本质所在正是结合于这种功能之中的那种远远超越了货币物质符号意义的观念。(页198) [9]
如果再联想到,如今的金融贸易直接通过银行转账完成,金钱只是数字,作为流通币的实在体消遁于无形——这一金融现象不正是把西美尔的“不管表征什么,货币都不是拥有功能,而是本身就是功能”(页169)的论断推向极端吗?质料性地使用货币是实物经济时期的事情,货币经济说到底就是要把货币货币性地使用。
西美尔观察到,现代货币经济的特点是货币交换在社会生活中的普泛和深入。随之,创造价值的货币作为衡量社会经济价值乃至个体价值的标准,以客观化、量化和平均化的导向渗透经济、文化和精神生活。货币如何实现它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统治呢?仍然是通过交换。在货币交换中,它把各种性质不同、形态迥异事物联系在一起,货币成了各种相互对立、距离遥远的社会分子的黏合剂;货币又像中央车站,所有事物都流经货币而互相关联,比重相等的万事万物都在滚滚流动的金钱浪潮中漂浮,由于漂浮在同一水平面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只有覆盖的尺寸大小的不同而已(页392)。“这一过程或许可以称作是货币日益增长的精神化过程(steigende Vergeistigung des Geldes),因为它是从多样性中实现统一的精神活动的本质。”(页198)
占据着社会-文化运作中心的货币经济重新组合了社会的各种质料,锻造出现代生活平均化、量化的价值取向。它赋予事物前所未有的客观性——一种无风格、无特点、无色彩的存在。
货币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区别。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严厉的调解者。货币挖空了事物的核心,挖空了事物的特性、特有的价值和特点,毫无挽回的余地。事物都以相同的比重在滚滚向前的货币洪流中漂流,全都处于同一个水平,仅仅是一个个的大小不同。

我并不想断言:我们的时代已经完全陷入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但是我们的时代正在接近这种状态,而与此相关的现象是: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纯粹计算多少的兴趣正在压倒品质的价值,尽管最终只有后者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金钱》,页8)
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公分母”,将所有不可计算的价值和特性化为可计算的量,它平均化了所有性质迥异的事物,质的差别不复存在。货币最直接也最有效地实现了社会价值平等的诉求。人的价值被物质化、客观化。更甚于,身处在这种完全以金钱价值为价值的文化中,人们已然忘却其他价值的存在。
[货币经济]最终让货币价值作为唯一有效的价值出现,人们越来越迅速地同事物中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对此的报应似乎就是产生了那些沉闷的、十分现代的感受:生活的核心和意义总是一再从我们手边滑落;我们越来越少获得确定无疑的满足,所有的操劳最终毫无价值可言。(《金钱》,页8)
现代文化价值的平等化、量化和客观化,造成的是终极追求和意义的失落。
货币经济也使人与人关系中的内在维度不再必需,人与人内在情感的维系被人与金钱物质的抽象的关系取代,人跟钱更亲近了,人跟人反倒疏远了。但令人悲伤的是,金钱对人跟它对其他所有东西一样,是完全中性的。
因此我们也抱怨货币经济:它以其核心价值充当一种完全百依百顺的工具为最卑鄙的阴谋诡计服务;尽管高尚的行动和卑鄙的行动得到的是同样的服务,这也于事无补。相反,这明显说明了一系列的金钱操作与我们的高级价值概念之间的关系纯属偶然,用这一个来衡量那一个毫无意义。(页432)
现代人对金钱或是拜神般地狂热,或是不屑一顾地清高,金钱根本无所谓。人的情感一旦寄托于这个无动于衷的中介物之上,生命感觉注定要随之萎缩。在西美尔看来,无论是聚敛钱财的吝啬还是挥霍无度的奢侈,无不折射出金钱文化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吞噬,只对金钱产生感觉以及对金钱的毫无感觉不过是生命感觉越来越枯萎,越来越无聊罢了。
货币对价值的僭越,在根本上表现为货币从方式上升为目的。价值与目的仅仅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一个物体的观念在它的理论感情意义上是价值,在实际意志意义中变成了目的。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分析了货币从手段成为价值或目的的内在原因,认为这是渐趋发达的现代文明的痼疾,与经济上的劳动分工不无干系。劳动分工使整一的劳动分裂为碎片,在此基础上,在越来越成熟的现代物质文明中,完成一个目标需要愈来愈复杂的手段。而对价值或目的最大的危险,就是人们过分专注于手段的应用,最后遗忘了要实现的目标。西美尔不无讽刺地写道:
现代,尤其看起来是在最近的阶段,浸透着焦虑、期望和没有消除的渴望的感觉,好像最重要的、终极性的事情要来了,那就是生活和事物的真正意义与中心点。这当然是手段剧增在感觉上带来的结果,我们复杂的生活技术迫使我们在手段之上建筑手段,直至手段应该服务的真正目标不断地退到意识的地平线上,并最终沉入地平线下。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金钱。(《金钱》,页11)
金钱不是一般的手段,而是纯粹的、绝对的手段,因为它完全由西美尔所谓的“目的序列”(Zweckreihen)决定,决不受其他序列的影响,而且,金钱从来没有自己的目的,从而可以作为目的序列里的中介一视同仁地发挥着功能(页211)。但是,金钱这个纯粹的手段过于完美,它似乎可以兑现成任意一种物质的价值,于是,产生的心理效果则是:金钱攀升至价值与目的的高度,从手段一跃而成为目的。
有这么一些东西,其自身价值完全来自其作为手段的特质、来自其能够转化为更具体价值的能力,但从来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能够像货币一样如此畅通无阻地、毫无保留地发展成为一种绝对的心理性价值,一种控制我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的……货币本质的内在两极性有两个原因:一,货币是一种绝对的手段;二,对大多数人来说,货币因此在心理上成为一种绝对目的。(页232)
货币从“绝对的手段”向“绝对目的”的转换是现代货币经济深度化的逻辑产物,西美尔认为,经济活动导致了人们心理认识和心理依附的重心偏移,货币替代其他的价值上升为生活追求的最终目标。货币僭越了终极目的,引起现代社会全面的方式与目的、技术与价值、物质与精神、外在与内在的倒置。不唯经济领域,美学和艺术中出现了装饰艺术、工业艺术,知识领域里盛行对方法和技术过程的青睐。这种生活的外在化“依靠的是物的完美,而不是人的完美”。
[10]
货币引发的手段与目的倒置的文化转型现象深入到现代人的精神领域。“方式凌驾于目的的过度增长,在外部生活凌驾于我们灵魂生命的力量中,找到了它的顶点。”
 最终,人的精神中最内在、最隐秘的领域也被货币这种“绝对目的”导致的物化和客观化占领了。
最终,人的精神中最内在、最隐秘的领域也被货币这种“绝对目的”导致的物化和客观化占领了。
这一切都加深了社会本已存在的世俗化倾向。现代精神中神性-形而上的品质消退,以货币为象征的工商主义精神取而代之,它的精神结构因子正是物化、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品性。从金钱的角度来看,世俗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含义就在于,金钱不仅成为物质-经济世界的流通物和统辖者,它还成为精神世界的流通物,占据了精神世界的地盘。这一过程加深了现代社会世俗化的精神景观。
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货币象征着目的论序列的终点,并提供给他们以各种兴趣统一联合的一个尺度、一种抽象的高度、对生活细节的统合,以至于它竟然减少了人们在宗教中寻找满足的需要。(页238)
人们经常抱怨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它成为一个中心,在这一中心处,彼此尖锐对立、遥远陌生的事物找到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并相互接触。所以,事实上也是货币导致了那种对具体事物的超越,使我们相信金钱的全能,就如同信赖一条最高原则的全能。(《金钱》,页12-13)
一言蔽之,货币成了现代社会的宗教。或者援引一位德国作家汉斯·萨克斯的说法,“金钱是世界的世俗之神”。但这个世俗之神本身并不据有价值,实际上也无法成为实质性目的,所以当金钱统辖精神世界后,凭借平均化的手段,将一切带有目的性的东西降格,损害了事物特有的价值。
货币到处都被视为目的,迫使众多真正目的性的事物降格为纯粹的手段。但,由于货币自身是无处不在的手段,存在的内容因而就放置于一种无所不包的目的论关系中,在这个关系中存在的要素既没有排第一名的也没有排最末一位的。(页431)
因此,货币在形式上——也只有在形式上——具有类似于上帝观念的客观性,它几近是现实的宗教,只不过是较低级的宗教。因为终究金钱只不过是手段,它是承载一切千差万别事物的等价物,而自身却空无一物。“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生命的情感若要寄托在这个空洞的世俗之神身上,最终的空虚就无从避免。“低俗”的金钱在现代社会无孔不入,注定使现代人的生命感觉枯萎凋零。所以现代人的拜金教缺乏对神性的宗教体验和虔诚的宗教感情。西美尔看到,由货币激发而壮大的现代精神力量只有一种——理智或理性。
理性本身只是精神手段。“尽管这种理智(Intellekt)自身包含着尽善尽美的手段,它却还不能把任何一个手段转变成现实,因为要使这些手段起作用,首先要确定一个目的;只有与这一目的相联系,这些现实的力量和关系才能成为手段,而目的本身唯有靠意志行为才能被创造出来。客观世界是没什么目的性的,除非有意志存在;理智世界亦然;理智仅仅是对世界内容或完美或不太完美的再现。”(页429)但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倾向却超越了手段和方式的设置,成为生活中“最富有价值的观念”——理性主义以及实证主义等价值观在现代社会生活(特别是大城市生活)中成为主导潮流。价值观一经转变,现代生活的意义话语随之改变,伴随着货币经济在文化生活中登场亮相。在讨论现代社会注重抽象符号表征所体现的理性主义倾向时,西美尔论述道:
当第二级符号在实际生活中日益替代了实体性的事物和价值的时候,指导我们生活的理智能力的重要性也就被提高了……这种生活形式不仅预示了精神过程的一种令人瞩目的扩张(例如,我们只要想一想用现金存储来代替钞票需要怎样一种复杂的心理先决条件),而且也预示了文化在朝向理智性(Intellektualität)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精神过程的强化和根本的方向重新调整。生活在本质上是建基于理智能力之上的,而理智能力在实际生活中是作为我们的精神力量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被接受下来的,这二者表现的观念与货币经济的增长是携手并行的……理智能力和抽象思维的发展刻画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在这个时代,货币就其内在价值而言越来越变成一种纯粹的符号、中立者。(页151-152)
货币带来的价值观的量化和物化已为生活的理性化基调作好了准备,因此,货币是现代社会理性化过程的基本条件。理性主义遂成为社会行为、经济行为和个体行为的行为准则,进一步加深了现代生活各方面的价值和结构的现代性转化。
夷平一切差异的金钱文化固然平庸至极,但西美尔以为,金钱也为人带来了另一个文化向度。在一开始我们就提到,货币支撑着文化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货币既承载和关联着千差万别的事物和社会阶层,使它们日趋平均化,从而导致社会文化价值的量化、世俗化和理性化;同时,货币又最大程度地保持和促进了个人自由和个体性的发展,经济-文化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几乎是与货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齐头并进的。作为中介,金钱表征的是彻头彻尾的客观性,所以,文化发展倾向中就必然有强调个性和自由之类的东西与之平行发展,否则人的内心生活就会失衡。西美尔不带任何道德批判,论述了货币如何“不偏不倚”(Indifferenz)地促进了这两种文化向度的形成。
人身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实现,历史地观之,是从封建社会的个人役务和财产占有方式的改变肇端的。在实物经济时代,役务者与主人、领臣与领主之间牢不可破的人身依附关系几乎没有给前者留下任何自由活动的空间。只有当货币租税决定性地取代了实物役务和租税时,义务关系才彻底去个人化(entpersonalisiert),承担役务的人才获得了人身自由。实物经济时代的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打上个人印记的、温情脉脉的关系,这种主观性的关系需要付出代价:过于紧密的关联束缚了人身的自由。以西美尔的话说,个体自由是“随着经济世界的客观化和去人格化而提高”(页303),即货币使人与人关系客观化,这正是保证个人自由的前提。
 同样地,货币转化了财产的性质和拥有方式,使个体从与有形实物的外在维系和外在局限中解放出来。西美尔认为,从人的存在(Sein)到财产拥有状态(Haben),再从财产拥有返回人的存在状态,这之间有一条链条,二者相互影响。人们越是根深蒂固地、强烈地把财产实际地据为己有,财产对主体的内外本质的影响就越清晰可见、越具有决定性,而由于对金钱的占有只是占有一种使用的可能性,所以“货币形式”的财产——钱财,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对人的存在的影响,赋予人最大程度的自由。故而,从传统的土地财产向金钱财产的转变绝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还导致了人的存在状态的改变——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的来临。
同样地,货币转化了财产的性质和拥有方式,使个体从与有形实物的外在维系和外在局限中解放出来。西美尔认为,从人的存在(Sein)到财产拥有状态(Haben),再从财产拥有返回人的存在状态,这之间有一条链条,二者相互影响。人们越是根深蒂固地、强烈地把财产实际地据为己有,财产对主体的内外本质的影响就越清晰可见、越具有决定性,而由于对金钱的占有只是占有一种使用的可能性,所以“货币形式”的财产——钱财,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对人的存在的影响,赋予人最大程度的自由。故而,从传统的土地财产向金钱财产的转变绝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还导致了人的存在状态的改变——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的来临。
除了财产方式的转变,从社会整体来看,西美尔认为,金钱也成为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润滑剂,为个体扩展交往和生存的空间创造了便利。货币经济领域的扩展可以说是跟个体生活空间的扩展同步进行的。现代人在社会中彼此依赖的方式前所未有:
虽然现代人比原始人——他们可以在非常狭小孤立的人群中过生活——更多地倚赖社会的整体,但我们却特别地不依靠社会的任何一个确定的成员,因为他对于我们的意义已经被转化成其劳动成就的单方面的客观性,这一成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由个性截然不同的其他任何一个人完成,我们与他们的联系不过就是完全以金钱表现的利益。(页298)
现代人特别少地依赖于任何一个单独的、确定的人,或者说在货币经济条件下,现代人无可比拟地只依赖于无名无姓的、数量众多的第三者,这就为个性和内心的独立感觉打开了一个特别大的活动空间,于是乎产生了强大的个人主义潮流。社会性意义上的自由,一如不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现代自由的发展意味着这种关系从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形式转变为不稳定的、人与人互换的形式。如果说自由就是不倚赖于他人的意志,那么首先它就是不倚赖于特定的个人意志。个人自由是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的自由,人与人交往的可能性越多,交往圈子越大,就越拥有自由。
如果说自由应该意味着个体性之发展,意味着确信以我们的自我之所有个别的意志和感情揭示出自我的内核,那么自由这一范畴包含的就不是纯粹的与他人脱离干系,而毋宁说是一种与他者完全确定的关系。这些他者必须在那儿存在,必须被感觉到在那儿存在,他们才能成为一种无关痛痒的存在。个体自由并非一个离群索居的主体纯粹内在的状态,而是一种互为关联的现象,没有对立面它亦丧失了意义。假设任何一种人际关系均由近的要素和远的要素组成,那么不依赖性指的是远的要素达到了最大值,但是相互接近的要素可能并未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如从左的概念才产生了右的概念。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为了促进不依赖性(作为客观事实以及主观意识)起见,什么是远近两边的要素最有利的具体状态。这样的状态似乎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存在,尽管跟他者之间还有大范围的关系交往,但一切真正是个人性质的因素都从关系中剔除出去了。(页298-299)
西美尔对自由的理解包含两层意思。首先,个体自由非关一人,而是与他人相关联,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二,所谓个体的自由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尽量地客观化,排除了主观的、人为的意志干预,或者说个体宁肯服从客观化的规则,也不臣服于他人的意志之下,这样他才感到是“自由”的。对于个体自由和客观性之间的关系,西美尔说得很清楚:“如果个性观念作为客观性观念的对立面和相关物必须与之同等幅度地发展,那么在这样的关联中显而易见的是,与一种更严格的客观性概念的形成携手并进的是一种更严格的个体自由概念的发展。”(页302)由于金钱是人与人的连结中不带任何感情的“客观”中介者,所以,金钱给现代人的个性和自由开辟了无限大的活动空间,现代人无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自由和个体化。利文(Donald Levine)甚至认为,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根据现代社会史无前例的个体化而“指示出一种人性的巨大提升”。 [11]
看来,金钱在封建义务、财产占有、社会关系中均扮演的是同一个角色——把个体从各种各样主观的、“确定”的关系中解脱出来,不管这种关系是跟主人、有形财产、社会成员的关系中的哪一种。但是,当这种主观“确定”的关系如人所愿地随着货币经济而去时,现代人的自由也出现了问题。在西美尔看来,金钱说到底只能给人一种负面的、消极的自由。自由并非只具有纯粹的负面性,并非只有相对于束缚,自由才有意义。按俗见,
自由一向是指不做某件事的自由(Freiheit von etwas),充盈着自由的是无所阻碍而表达出的概念。但自由的概念并不限于这层负面含义。假设摆脱责任的同时没有填补上获得财产或权力的话,自由就毫无意义、一钱不值:不做某事的自由同时蕴含的是做某件事的自由(Freiheit zu etwas)……但凡只有纯负面含义的自由在起作用,自由就被视为残缺不全、有辱人格……自由本身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这种形式只能在其他生活内容的发展中,以及凭借这种发展变得卓有成效、生机勃勃、富有价值。(页401-402)
金钱的确在、也只在纯粹消极的意义上,解决了人类实现自由的任务。但似乎只有自由主义——这种被西美尔称作“唯智论和金钱交易的历史代表”的观念——的自以为是,才把消极自由奉为圭臬。
 对交纳现金租税而获“解放”的农民而言,他们确实得到了自由,但只是不做什么事的自由,而非做什么事的自由。这种消极的自由使农民不知所措,因为它没有任何确定的内容。西美尔提醒我们,自由只是形式,需要以切实的内容填充。而金钱式的自由恰恰是充满种种可能性的、不系于任何实在之物的自由;它在解放我们的同时,只给了我们空虚的生命感觉。
对交纳现金租税而获“解放”的农民而言,他们确实得到了自由,但只是不做什么事的自由,而非做什么事的自由。这种消极的自由使农民不知所措,因为它没有任何确定的内容。西美尔提醒我们,自由只是形式,需要以切实的内容填充。而金钱式的自由恰恰是充满种种可能性的、不系于任何实在之物的自由;它在解放我们的同时,只给了我们空虚的生命感觉。
这种自由的状态是空虚、变化无常,使得人们毫无抵抗力地放纵在一时兴起的、诱人的冲动中。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自由与无安全感的人的命运作一比较,他弃绝了上帝后重新获得的“自由”只为他提供了从一切短暂易逝的价值中制造偶像崇拜物的机会。商人整天为生意忧心忡忡,迫切希望无论如何要把货物出手,他遭遇的是和弃绝上帝的人同样的命运。但,最后当钱到手商人真的“自由”了后,他却常常体会到食利者那种典型的厌倦无聊,生活毫无目的,内心烦躁不安,这种感受驱使商人以极端反常、自相矛盾的方式竭力使自己忙忙碌碌,目的是为“自由”填充一种实质性的内容……出钱获得解放的农民,变成赚钱机器的商人,领薪水的公务员,这些人似乎都把个体从种种限制——即与他们的财产或地位的具体状态紧密相关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但事实上,在这里所举到的这些人身上却发生了截然相反的情况。他们用钱交换了个体之自我中具有积极含义的内容,而钱却无法提供积极的内容。……因为货币所能提供的自由只是一种潜在的、形式化的、消极的自由,牺牲掉生活的积极内容来换钱暗示着出卖个人价值——除非其他价值立即填补上它们空缺后的位置。(页402-403)
本来,个体占有货币后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充满诱惑且含含糊糊地暗示了自我的扩展,但西美尔的锐利目光看到,其实金钱带来的是“自我的萎缩”,所以占有金钱所意味的自我扩展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彻底的,而另一方面又是最受局限的。在前现代,具体的租税或财产也许限制了个体,但它们的确定内容也支撑着个体。一旦人们摆脱了与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束缚后,也就绝不可能再发展内在于这些东西中的那种约束、融合、献身的质素了。
一如货币经济哺育出现代人对自由观念的诉求,金钱文化也支撑了现代社会构想中对平等观的追求。在消除差别、寻求平等这一向度之外,货币经济的确给现代文化带来了另一向度——诉诸自由,并且这一持续不断的自由解放过程在现代生活中占据了一个格外广阔的领域,不唯经济领域。在思想和精神品格上,西美尔明确地指出,货币经济确实和自由主义关联甚密,二者之间具有更为深刻的关联。但正由于金钱式的自由追求的是形式化的消极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自由产生了如此多的不稳定、秩序混乱、令人不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尽管从总体而言的确比过往任何年代都有更大的自由,我们却无法好好地享受自由”(页403)。在现代金钱文化不明就里、毫无定性的自由中,现代人品尝到十足的现代情绪的恶果:满心期望占有某件东西得到满足,一瞬间马上又有了超出这件东西的欲望,生命的内核与意义总是从人们手中滑落。现代人越是自由,对生命益发感到厌倦;越放纵个性,个人的价值何去何从益发没有着落。个人价值在金钱文化中已被连根拔起(Entwurzelung),所以“自由”的现代人现在带有几分疑惑、踌躇不决地要重新寻求物体自身当中那种力量、稳定性和内在的统一。他们慌不择路地要给予事物一种新的意义、一种更加深刻的意义、一种事物本身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活跃于现代艺术、宗教中的骚动,有这么多对新颖风格的探索,从象征主义一直到通神学、招魂术。这些蠢蠢不安的躁动均是渴望了解一种新的、更易察觉的事物意义的征兆——而不管是否每一件事物自身便拥有更具价值的,更精神性(seelenvollere)的着重点。
现代性条件下的个体自由和个性化,正如文化的夷平过程一样,在西美尔眼中亦是悲观的,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这依然是货币及货币经济予以现代生活的不那么负面的影响。在这位哲学家眼中,亘古至今(现代金钱文化时期也不例外),生活从来都是悲剧性的。
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无价值和令人失望的事(作为日常生活里单个的事件它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甚或那些具有幽默性的事件,都呈现出一种悲剧般的、深深令人不安的特性,这是当我们意识到它们惊人地四散弥漫、日复一日无从避免以及它们所影响的不是某一天而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的时候,才认识到的。(页264)
西美尔貌似客观冷静的现代文化描述,一向令文化批判者们或产生道德义愤,将其归咎为折衷的相对主义,或斥之为浅薄的印象主义和审美主义。西美尔对资质平庸的金钱文化的描述,虽然带有悲剧性的基调,却绝无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金钱社会”时的激愤。不去追究西美尔为什么不承纳马克思的批判立场,只贴上相对主义的标签,等于什么都没有说。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言明,每个时代都有与之相契合的理论世界观,恰如初期文化青睐绝对主义世界观,现代的相对论世界观则是由社会和主观生活的截然对峙决定的,金钱就是存在相对性之历史象征物。但西美尔决非历史阶段论的拥趸,在描述这种相对主义时,他流露出的是典型的(但非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心性——这从《货币哲学》结尾部分对“恒定”和“恒动”两种理解世界的范畴的论述可窥一斑。至于把西美尔的文化立场判定为审美主义,姑且不论其中的贬义色彩,如果说其意指西美尔超越历史主义的视野,倒还恰当。
西美尔其人其说,究竟该归于哪一类呢?
狄尔泰的弟子马克斯·弗里塞森-科勒(Max Frischeisen-Khler)曾在1919年西美尔辞世一周年时撰长文纪念,称西美尔这位“哲学小品文大师”(Meister des philosophischen Essai)从建构“货币哲学”起,就意图对迄今为止的社会-文化批判做“积极的补充”,《货币哲学》的问题意识一如松巴特和韦伯的国民经济研究、特洛尔奇的宗教研究,共同驳斥了历史唯物主义,以把握理解“资本主义精神”(Geistes des Kapitalismus)。
[12]
西美尔的思想立场不同于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是明摆着的——这种不同正如《货币哲学》和《资本论》的差异一样大,
 他是否因此就跻身于重塑“资本主义精神”的行列,倒值得一问。
他是否因此就跻身于重塑“资本主义精神”的行列,倒值得一问。
不错,《货币哲学》里描述的文化景观、分析的文化事件大多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但真正使西美尔忧虑的是更普遍意义上的文化问题,或人的在世问题。所谓“文化悲剧”是人的永恒命运——既非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罪恶使然,也非重塑某个历史阶段的文化精神所能够逃逸。毋宁说,西美尔所承纳的是超越左右两派的审美式悲观哲学立场,它实质上已在现代性文化景观中构成与文化保守主义(如丹尼尔·贝尔)和新老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如法兰克福派)的三足鼎立。这三者涉及的完全不是文化言说形式的差异,而是理论精神气质的迥异,涉及对待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三种态度。法兰克福派扮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抨击者的角色,贝尔则是文化监护人形象。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抨击者,法兰克福派的文化批判是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出发,从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理念、经济体制的批判转入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批判。它所秉承的道义价值立场是很明显的。以贝尔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
 反对批判理论的过激倾向和批判立场,偏向节制、实际的观点,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实质在于恢复资本主义社会道德与文化秩序,因此文化保守主义扮演的是社会文化理念监护人的形象,或可归于科勒所谓重塑“资本主义精神”之列,它对后工业社会中“现代主义”的文化时髦的批判,乃是出于文化监护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困境”、“文化危机”的疗救心态。
反对批判理论的过激倾向和批判立场,偏向节制、实际的观点,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实质在于恢复资本主义社会道德与文化秩序,因此文化保守主义扮演的是社会文化理念监护人的形象,或可归于科勒所谓重塑“资本主义精神”之列,它对后工业社会中“现代主义”的文化时髦的批判,乃是出于文化监护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困境”、“文化危机”的疗救心态。

关于西美尔的思想肖像,各种交相缠绕、砥砺交锋的说法颇多。即便在同时代人眼里,西美尔的形象也算不上清晰。他既是同仁认可的社会学和哲学思想的“启发者”(韦伯),又是“没有奠定社会学的牢固基础”的人(涂尔干);他既是学生眼里的“智者”(Arthur Salz),又是没有任何思想继承人的学院外的“局外人”(科瑟);他既是所属的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时代哲学家”(约尔),又似乎是迟早会被替代的“过渡哲学家”(卢卡奇)。及至现代,对西美尔的学术评价也是莫衷一是,弗里斯比称他为“游手好闲者”(flneur)
[13]
,严肃一点哈贝马斯说他是时代诊断者(Zeitdiagnostiker),
[14]
更有激进的左翼论者提出西美尔是“先锋派”、“毁灭性思想家”。
[15]
然而后现代主义者却抨击和扭转了左翼批评者的说法,他们借用列维-施特劳斯的提法,称西美尔是“利用现成工具干零碎杂活的人”(bricoleur),是“差异思想家”和零敲碎打补缀思想碎片的后现代主义者。
 左翼评价从传统到激进变化很大,
左翼评价从传统到激进变化很大,
 而且和后现代评论截然对峙,使得现代西美尔阐释的格局呈现出某种紧张的态势,但,二者都弄错了西美尔肖像的底色。
而且和后现代评论截然对峙,使得现代西美尔阐释的格局呈现出某种紧张的态势,但,二者都弄错了西美尔肖像的底色。
西美尔的思想形象虽然带有审美主义倾向,但决非事事无所住心的“游手好闲者”,他像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一样,从思考一开始就洞察到生命与形式的冲突无法通融,人的幸即不幸的悲剧性命运,以悲观-寂静主义(pessimistisch-quietistischen)化解于字里行间——对于思想得很彻底的西美尔,舍此别无他法,他只能带着形而上的悲情诠释对生命的自我理解。正是在此意义上,他是一位地道的悲剧性思想家。
西美尔谈到“冒险家”时曾说:
哲学家是精神上的冒险家,他毫无希望地但并非因此而毫无意义地企图把一种精神上的姿势,它对自身、世界、上帝的态度塑造成概念性固化成的知识。他处理这不可解决的问题就好像它是可以解决的。

这段话仿佛西美尔的精神自况。“冒险家”的说法别具深意,哲学家西美尔就是这样一个“精神上的冒险家”:他的思想探险“毫无希望”,因而是悲剧性的,但又并非“毫无意义”,故此会沉思到底。尽管是“悲剧性的思想家”,但西美尔的哲学-文化思想一直试图用一种精英主义的姿势、绝对主义的立场处理那些不可解决的精神问题。他的思想形象是一个寂寞而疏离的精英角色,一个要保护自己的精神个性的贵族主义哲学家——西美尔的古典主义和形而上气质正在于此。虽然被当作“时代哲学家”,虽然置身于现代喧闹的思想冲突中,他却超越了左翼和右翼的思想立场,保持着古典哲人的爱智传统。也许对他来说,做哲人,或做“精神冒险家”就意味着对任何一种现代的思想立场保持警醒和距离。哲学家作为“精神上的冒险家”,其思想气质在于孤绝、疏离、古典,因此西美尔的思想形象上承斯宾诺莎、叔本华、尼采,后启舍勒、马丁·布伯、海德格尔。
西美尔的文化哲学虽然在根本上是形而上的、哲学式的,但具体的文化分析使用的是景观角度,带有“碎片的”风格。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分析了很多琐细的、与货币这一纯粹的经济物相关联的社会精神-文化现象,诸如贪财吝啬、奢侈、禁欲式的贫困、血钱与罚金、买卖婚姻和嫁妆、卖淫,其中又有特别涉及现代生活的现象,如乐极生厌的腻烦、犬儒主义、算计特征、股票交易、信贷等不一而足。西美尔的形而上学思考一直盘旋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感性碎片之上,但他却“以沉思的姿态凝视这些流动的场景,把喧闹背后的寂静从容不迫地揭示出来。因而,他的生命感觉并非印象式的、散乱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哲学与历史底蕴”。

按主流社会学史家的眼光,西美尔忝列古典社会学的四大导师之末,不过排在他前面的三位,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历来被认为是“神圣三位一体”,西美尔充其量是最有实力的“替补”。
 所谓的历史叙述向来眼光近视得厉害。一个世纪过去了。西美尔到底是不是“过渡哲学家”,《货币哲学》到底是不是“过渡性作品”,看来不是由眼光近视的历史主义说了算的。西美尔思想的火花以其独特的熠熠之光启发了同时代和之后的社会文化人,虽然他自己在生前并未在当时的主流社会学中获得多大的理解。因此,恰切地重塑西美尔的思想肖像,对当今的西方和汉语学术界都不乏意义。
所谓的历史叙述向来眼光近视得厉害。一个世纪过去了。西美尔到底是不是“过渡哲学家”,《货币哲学》到底是不是“过渡性作品”,看来不是由眼光近视的历史主义说了算的。西美尔思想的火花以其独特的熠熠之光启发了同时代和之后的社会文化人,虽然他自己在生前并未在当时的主流社会学中获得多大的理解。因此,恰切地重塑西美尔的思想肖像,对当今的西方和汉语学术界都不乏意义。
本书汉译参考的翻译底本有:英译本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trans.by Tom Bottomore,David Frisb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8;德文本 Philosophie des Geldes ,Berlin:Duncker & Humblot Verlag,1900(1.Auflage)。
本书的翻译分工如下:前言、第一章,文聘元译;第二章、第三章,耿开君译;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陈戎女译;重要术语与人名对译表,陈戎女制作。正文所有注释均为各译者所注。
[1] Theodore Abel,“The Contribution of Georg Simmel”,in David Frisby(ed.), Georg Simmel :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III,London:Routledge,1994,pp.264-266。当时,帕累托、滕尼斯、韦伯乃至涂尔干的影响力均不及西美尔。
[2] Georg Lukács,“卢卡奇忆西美尔”,参Gassen,K./Michael Landmann(eds.), Buch des Dankes an Georg Simmel ,Berlin:Duncker & Humblot,1958,p.171,172。当然,卢卡奇这番话更多是想说明其师作为一位地道的“印象主义”哲学家的思维方式。这篇发表于1918年的文章对西美尔赞誉有加,但卢卡奇转向马克思主义后,于1955年发表的《理性的毁灭》则对其师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清点批判。见《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页389以下,对《货币哲学》的批判,399页以下。
[3] 含糊其辞的说法是,该书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内容是经济学的,论述人与人的关系的大框架是社会学的。B.H.Meyer,“Review of Philosophie des Geldes ”,参 Georg Simmel :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I,p.152。
[4] David Frisby, Fragments of Modernity : 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the Work of Simmel , Kracarer and Benjamin ,Cambridge:Polity Press,1985,p.87.
[5] S.P.Altmann,“Simmel's Philosophy of Money ”,参 Georg Simmel :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I,p.130.
[6] Bryan S.Turner,“Simmel,Rationalisation and the Sociology of Money”,in Georg Simmel :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II,p.288.
[7] 《货币哲学》甫现,涂尔干就在《社会学年鉴》(1900—1901)上撰文评论,语多否定,尤其是“综合卷”被斥之为毫无分析、全无逻辑,“能抽绎出最概括性的内容我们就相当满足了”,而西美尔的整体思维方法则被讥讽为混杂了像艺术中的主观性(但未企及艺术的鲜活生动性)和像科学中的抽象性(但缺乏科学的准确性)的不合逻辑的玄思。E.Durkheim,“Review of Georg Simmel's Philosophie des Geldes ”,trans.Peter Baehr,参 Georg Simmel :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I,pp.156-159。
[8] G.Simmel, The Conflict of Modern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K.Peter Etzkorn,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Columbia University,1968,p.48.
[9] 弗里斯比认为,西美尔对货币的象征意义的研究预示了后现代的消费理论:即我们消费的是商品的符号或象征,而不是它的具体实用性。参David Frisby, Simmel and Since ,London:Routledge,1992,p.171。
[10] Simmel,“Tendencies in German Life and Thought since 1870”,in D.Frisby(ed.), Georg Simmel :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I,pp.6-7.
[11] 利文挑战以往对西美尔的诸多定论,包括其思想倾向的冷淡主义(indifferentism)和悲观主义,力图建立起西美尔非常正面的、积极的教育家形象,但有矫枉过正之嫌。Donald Levine,“Simmel as Educator:On Individuality and Modern Culture”,参 Georg Simmel :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II,pp.352-354。
[12] Max Frischeisen-Khler,“Georg Simmel”,in Peter Ulrich Hein(ed.), Georg Simmel ,Frankfurt a.M.:Verlag Peter Lang,1990,p.38.
[13] 此乃弗里斯比借用本雅明评价波德莱尔的提法,参D.Frisby, Sociological Impressionism : A Reassessment of Georg Simmel ' s Social Theory ,London:Routledge,second edition,1992,pp.68-101。
[14] Jürgen Habermas,“Simmel als Zeitdiagnostiker”,G.Simmel, Philosophische Kultur ,Neuauflage,Berlin:Wagenbach,1983,pp.243-253.
[15] Ralph M.Leck, Georg Simmel and Avant - Garde Sociology : The Birth of Modernity ,1880-1920,New York:Humanity Books,2000,p.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