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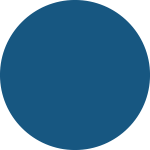
有些人在没有野生的东西的情况下也可以生活,而有些人就不行。这些随笔就是那些离不开野生的东西的人们之喜悦和身处两难的表达。
野生的东西在开始被摒弃之前,一直和风吹日落一样,被认为是极其平常而自然的。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一种平静的较高的“生活水准”,是否值得以牺牲自然的、野外的和无拘束的东西为代价。对我们这些少数人来说,能有机会看到大雁要比看电视更为重要,能有机会看到一朵白头翁花就如同言论自由一样,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些野外的东西,我承认,直到机械化为我们提供了美味的早餐,而科学又为我们揭示了它们的来源和如何生长的故事之前,是几乎没有什么关乎人类的价值的。全部矛盾由此而凝聚为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少数人看到了在进步中出现的报酬递减律,而我们的反对派们却并未看到。
* * *
人们必须设法回应他们所面临的现实。这些文章便是我的回应。它们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所描述的是我们一家人在周末时,在那远离过多的现代化的世外桃源——“木屋”中所看到和所做的事情。在这个先是被我们越来越傲慢和越来越完美的社会榨取殆尽,然后又被遗弃的威斯康星沙乡农场里,我们试图用铲子和斧子去重建我们在其他地方正在失去的那些东西。正是在这儿,我们探索着,而且发现了上帝赐予我们的本质。
这些“木屋”随笔按季节排列成《一个沙乡的年鉴》。
第二部分,《随笔——这儿和那儿》,则列举了我生活中给我以教导的那些插曲,即那些逐渐地,有时是很痛苦地与伙伴们分道扬镳的插曲。这些插曲遍布北美大陆,前后有四十年时间。它们为那些有着一个共同标签——资源保护主义的各种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板。
第三部分,《结论》,运用更加逻辑化的术语,提出了我们这些持不同意见者的某些观点,这些观点是对我们的看法的科学说明。只有那些具有同感的读者会希望去弄懂第三部分的这些理论问题。我想,也许可以认为,这些文章向同行们说明了怎样才能回过头来取得认识上的一致。
* * *
资源保护主义已逐渐沉寂了,因为它是与我们的亚伯拉罕式的土地观念所不相容的。我们蹂躏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属于我们的物品。当我们把土地看成是一个我们隶属于它的共同体时,我们可能就会带着热爱与尊敬来使用它。对土地来说,是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逃脱机械化的人类的影响的;对我们来说,也无其他方法从土地中得到它能够——在受制于科学的情况下——奉献给文化的美学收获。
土地是一个共同体的观念,是生态学的基本概念,但是,土地应该被热爱和被尊敬,却是一种伦理观念的延伸。土地产生了文化结果,这是长期以来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总是被人所忘却。
这些文章试图把这三种概念联结起来。
当然,这样一种关于土地和人的观点,是容易由于个人的经验和偏见而被混淆、歪曲的。然而,不论真理是否可能被误传,有一点却如水晶一般清晰:我们的自大和完美的社会,现在就像一个忧郁病患者,它是那样为其自身的经济健康而困扰着,结果反而失去了保持健康的能力。整个世界是那样贪婪地希望有更多的浴盆,以至失去了去建造这些浴盆,或者甚至是关掉水龙头所必需的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没有什么比从健康角度稍稍轻视一下过多的物质享受更有意义的了。
大概,通过重新评价非自然的、人工的,并且是以自然的、野生和自由的东西为条件而产生的东西,可以获得这样一种价值观上的转变。
奥尔多·利奥波德
一九四八年三月四日
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