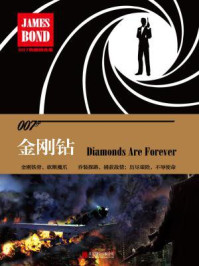一名护士正在处理内德·博蒙特的脸。
“我在哪儿?”他问。
“圣路克医院。”护士个子娇小,一双榛子色的眼睛大而明亮,嗓音如喘息般略带沙哑,身上带着含羞草的香味。
“今天星期几?”
“星期一。”
“哪年哪月?”他问。看到她冲着自己皱起眉头,于是说:“哦,算了,我在这里有多久了?”
“今天是第三天。”
“电话在哪儿?”他想坐起来。
“别动,”她说,“你不能打电话,而且绝对不能太激动。”
“那你帮我打。接哈特福六一六一,告诉马兹维先生我要马上见他。”
“马兹维先生每天下午都会来,”她说,“但我不认为泰特医生眼下会批准你跟任何人谈话。事实上,你现在就已经讲得太多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早上还是下午?”
“早上。”
“我等不了那么久,”他说,“你现在就打给他。”
“泰特医生稍后就会过来。”
“我才不需要什么泰特医生,”他急躁地说,“我要保罗·马兹维。”
“你得乖乖听话,”她回应道,“安静地躺在这儿,等泰特医生来。”
他恼怒地瞪着她。“你可真是个厉害的护士啊。没人告诉过你,和病人争论是不好的吗?”
她无视了他的问题。
他又说:“而且,你把我的下巴碰疼了。”
“如果你别动下巴,它就不会痛。”她说。
他安静了一会儿,然后问:“我怎么了?还是说你学艺不精,弄不明白啊?”
“大概是喝醉酒打架。”她告诉他,可是脸没朝着他的方向。她笑了笑,然后又开口,“不过说真的,你不该讲那么多话,而且除非医生答应,否则你不能见任何人。”
保罗·马兹维下午很早就到了。“老天,真高兴看到你又活过来了!”他说,双手抓着病人那只没缠绷带的左手。
内德·博蒙特说:“我没事。不过有件事我们必须得办:逮住沃尔特·伊万斯,带他去布瑞伍德指认那个卖枪的,他——”
“你全都告诉过我了,”马兹维说。“已经搞定了。”
内德·博蒙特皱起眉头。“我告诉过你?”
“当然——就在你被发现的那天早上。他们送你到急诊室,可是你在见到我之前都拒绝任何治疗。我一赶到,你就把伊万斯和布瑞伍德的事情告诉我,接着就晕过去了。”
“对我来讲那是一片空白。”内德·博蒙特说,“你逮到他们了吗?”
“我们逮到伊万斯了,没问题。沃尔特·伊万斯在布瑞伍德被指认后招了,大陪审团起诉了杰夫·加德纳和另外两个无名之辈,不过我们还没把沙德拉下水。加德纳是负责跟伊万斯接头的,大家知道他做什么都一定是沙德下的命令,所以……不过要证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杰夫就是那个长得像猴子的家伙,对吧?他被捕了吗?”
“没有。我猜你离开后,沙德就把他给藏了起来。他们捉住你了,对吧?”
“嗯,就在狗屋的楼上。我本来是打算去那儿给欧罗瑞设陷阱,结果反而中了他的圈套。”他皱起眉头,“我还记得是跟‘威士忌’·瓦索斯一起去的,然后被一只狗咬了,又被杰夫和一个金发小子揍了几顿。然后还有火灾什么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吧。谁发现我的?在哪儿?”
“有个警察清晨三点发现你手脚并用地在科曼街正中央爬,身后还拖着一条血迹。”
“我想干点儿有趣的事儿。”内德·博蒙特说。
那个大眼睛的小护士小心翼翼地打开门,探进头来。
内德·博蒙特用一种疲惫的声音朝她嚷着:“好吧——躲猫猫!不过你不觉得你玩这个有点儿太老了吗?”
护士把门又打开了一点儿,站在门框下,一手扶着门边。“难怪会有人揍你,”她说,“我想看看你醒了没,马兹维先生和——”她声音里面那种喘息般的成分更明显了,眼睛也更亮了,“一位小姐在这儿。”
内德·博蒙特好奇地看着她,有点嘲讽地问:“什么小姐?”
“珍妮特·亨利小姐,”她带着那种向人揭示意外惊喜般的语气回答。
内德·博蒙特转过身侧躺着,背对着那个护士。他闭上眼睛,嘴角扭曲了,但声音依旧不带任何感情:“告诉他们我还在睡。”
“你不能这样啊,”她说,“他们知道你没睡着——就算他们没听到你讲话——不然的话我早就离开了。”
他夸张地呻吟了一声,用胳膊肘撑起身子。“反正她没见到我,也还是会回来,”他发着牢骚,“到时候也得过这一关。”
那个护士轻蔑地看着他,挖苦道:“我们还得找警察来医院门口站岗,好把所有想见你的女人都挡在外面呢。”
“你当然说得轻松,”他说,“也许你对那些总是出现在报纸上的参议员女儿们印象不错,但你可没像我这样被追着不放。告诉你,她们把我搞惨了——她们,和印着她们的报纸版面。参议员的女儿……永远都是参议员的女儿,从来就不会是什么众议员的女儿、部长的女儿或者市议员的女儿,一点儿花样都没有,永远不会是其他的。难道你觉得参议员比别人会生孩子——”
“一点也不好笑,”护士说,“你继续这么自吹自擂吧。我去带他们进来。”她离开了病房。
内德·博蒙特深吸了一口气,眼神亮晶晶的。他舔湿嘴唇,然后把它们抿成一个隐秘的微笑。不过珍妮特·亨利进来时,他又换上了一副轻松有礼的面具。
她径直走到他床边后开口说道:“唔,博蒙特先生,听说你恢复得很好,我真高兴,非得来看看你不可。”她一只手放在他的手上,低头朝着他微笑。她的眼睛其实不是深棕色,但那头纯金的秀发衬得眸色格外深暗。“所以如果你不希望我来,可别责怪保罗。是我逼他带我来的。”
内德·博蒙特也回她一个笑容,然后说:“你能来我太高兴了,你真是非常好心。”
保罗·马兹维跟着珍妮特·亨利进了房间,走到了床的另一侧。他深挚地笑着,看看她又看看内德·博蒙特。“就知道你会高兴的,内德。我跟她说过了。今天怎么样啊?”
“老样子。拉几把椅子过来吧。”
“我们不能久留,”金发男人答道,“我得去格朗库尔跟麦拉弗林先生碰面。”
“可是我不用去,”珍妮特·亨利说。她又对着内德·博蒙特微笑起来。“也许我可以——多待一会儿?”
“荣幸之至。”内德·博蒙特对她说。同时马兹维绕过来,替她搬了把椅子,轮流给了两人一个欣喜的笑容,然后说:“很好。”等到这女子在床边坐下,黑大衣搭在椅背上,马兹维便看了看表,咕哝了一句:“我得走了。”他握了握内德·博蒙特的手,“需要我替你带什么吗?”
“不用。谢了,保罗。”
“好,那你好好休养。”金发男子转向珍妮特·亨利,停下来,又对内德·博蒙特说,“你觉得我跟麦拉弗林先生第一次见面时应该谈到什么地步?”
内德·博蒙特微微耸肩。“随你,只要别把话讲得太直白,那会吓着他的。不过你可以拐弯抹角地委托他杀人,比如说:‘假设有个叫史密斯的住在这么个地方,他得了病或者什么没法好转的玩意儿。然后有一次你刚好过来看我,恰巧有个信封寄过来,叫我转交给你。我怎会知道里面会有五百美元呢?’”
马兹维点点头。“我不想杀任何人,”他说,“不过我们的确需要铁路工人的票。”他皱皱眉,“我真希望你能好起来,内德。”
‘这一两天就差不多了。你早上看了《观察者》吗’?
“还没有。”
内德·博蒙特打量着房间四处。“有人把它给拿走了。那篇下流的社论就排在头版正中间的版面里。‘本市的警察打算怎么办?’一个列着六周以来犯罪事件的清单,表明近来犯罪突增,还有一个小得多的清单列出了伏法的犯人,显示出警方无能为力。而大部分的牢骚都是针对泰勒·亨利的谋杀案。”
听到弟弟的名字,珍妮特·亨利瑟缩了一下,嘴唇微张,无声地抽了一口气。马兹维看了她一眼,迅速转向内德·博蒙特,警告地摇了摇头。
内德·博蒙特无视自己的话对他人造成的影响,继续说下去:“他们真是无理取闹,指责警方整个星期都故意拖着不去办那桩谋杀案,好让高层政治圈的一个赌徒利用这个案子向另一个赌徒讨回一口气——就是指我追着德斯潘追讨赌债。真想知道亨利参议员对于他的新政治同盟利用他儿子的命案牟利这件事有何感想。”
马兹维涨红了脸,笨拙地摸着手表,匆忙地开口:“我会找一份来看,现在我得——”
“还有,”内德·博蒙特平静地继续,“他们还指责警方突然——在多年的保护之后——取缔了那些无意付出大笔政治献金的老板们经营的酒吧。这是把你和欧罗瑞的战争给挑明了。他们还说要登出一份仍在经营的酒吧名单,证明这些酒吧的主人是因为给了政治献金才不受影响的。”
“好啦,好啦,”马兹维不安地说,“再见,希望你们聊得愉快。”他对珍妮特·亨利这么说,又对内德·博蒙特说了句“回头见”,然后走了出去。
珍妮特·亨利坐在椅子里,身子前倾。“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她问内德·博蒙特。
“我想我说不定是喜欢你的。”他说。
她摇摇头。“你不喜欢我,我明白。”
“你受不了我的态度,”他说,“我态度一向很恶劣。”
“你不喜欢我,”她坚持这样说,没有回应他的微笑,“可是我希望你喜欢我。”
他谦恭了起来。“为什么?”
“因为你是保罗最要好的朋友。”她回答。
“保罗,”他斜眼看着她,“他朋友多得很。他是政客嘛。”
她不耐地摇摇头。“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她停下来,然后补上一句,“他是这么认为的。”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他半开玩笑地问道。
“我觉得没错,”她郑重地说,“否则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了。你不必为他吃这么多苦。”
他的唇角泛起一个淡漠的笑容,什么都没说。
明白他不再打算讲话之后,她诚挚地说:“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你会喜欢我。”
“说不定我喜欢你。”他又重复了一遍。
她摇头。“你才不喜欢我。”
他对她笑了,那微笑非常年轻而动人。他的眼神含蓄腼腆,声音里满是稚气的卑怯与信赖:“亨利小姐,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因为——你看,一年多以前,保罗可以说是把我从阴沟里捞了出来。所以跟你们这种属于社交圈和名人版的人相处时,我就尴尬又笨拙——但你误以为这种,呃,笨拙是仇恨与敌意,但其实完全不是。”
“你在奚落我。”她站了起来,语调中并无愤恨。
她离开之后,内德·博蒙特躺回枕头上,双眼发亮,瞪着天花板,直到护士进来。
护士一进来就问他:“你刚刚在搞什么啊?”
内德·博蒙特抬起头怏怏地看着她,一言不发。
那护士说话了:“她离开的时候忍着没哭,但也快了。”
内德·博蒙特又把头靠回枕头上。“我一定是没救了,”他说,“总是让参议员的女儿们流泪。”
一个男人走进来,中等身材、年轻利落、长着一张轮廓精致的深色脸孔,相貌相当漂亮。
内德·博蒙特在床上坐了起来。“哟,杰克。”
“你看起来没有我原先想的那么糟嘛。”杰克说着走到床边。
“还算是个完整的人吧。自己找把椅子。”
杰克坐了下来,掏出一包香烟。
内德·博蒙特说:“我又有个工作给你。”他把手探进枕头下,取出一个信封。
杰克点燃了香烟,然后从内德·博蒙特手中接过信封。那是个纯白的信封,上头写着“圣路克医院,内德·博蒙特收”,盖着当地邮戳,日期是两天之前。里头有一张打字的纸,杰克拿出来读了起来。
对于保罗·马兹维,你知道些什么?
有能让沙德·欧罗瑞求知若渴的事情吗?
那与泰勒·亨利的谋杀案有任何关联吗?
如果无关,那为什么你要费那么大工夫守住这个秘密?
杰克重新折好信纸,放回信封,然后抬起头来。“它说的是真的吗?”
“据我所知不是。我要你去查查是谁写的。”
杰克点头。“这信我留着?”
“好的。”
杰克把信封放进口袋。“想得到有谁可能干这事儿吗?”
“完全没头绪。”
杰克审视着点燃的香烟末端。“你知道,我是就事论事。”他很快地说。
“我明白,”内德·博蒙特表示同意,“我只能说,过去一个星期里,这种信来了一大堆——至少有好几封。这是我收到的第三封,我知道法尔至少收到一封,但我不知道还有谁也收到了。”
“我可以看看其他几封吗?”
内德·博蒙特说:“我只留着这一封。但它们都差不多——同样的纸张、同样都是打字,每封都是三个问题,谈的主题都一样。”
杰克探究似的注视着内德·博蒙特。“但问题却不尽相同?”他问。
“不完全一样,不过都谈到同一个重点。”
杰克抽着烟点点头。
内德·博蒙特说:“你得清楚,这事儿要极端保密。”
“当然了。”杰克把烟从嘴里拿出来。“你提到的‘同一个重点’就是马兹维和那桩谋杀案的关联吗?”
“对,”内德·博蒙特回答,两眼平视那黝黑又漂亮的年轻人,“而且事实上根本没有关联。”
杰克深色的面容难以揣测。“我看不出能有什么关联。”说着,他站了起来。
护士拿着一大篮子水果走了进来。“真棒啊,不是吗?”她放下水果。
内德·博蒙特谨慎地点了点头。
护士从篮子里拿出一个硬壳小信封。“我敢打赌这是她送的。”把信封递给内德·博蒙特时她这样说。
“赌什么?”
“你想赌什么都行。”
内德·博蒙特点着头,似乎确定了心里某种模糊的猜疑。“你看过了。”他说。
“为什么,你——”他一笑,她就停住了,可还是一脸的愤慨。
他从信封里抽出珍妮特·亨利的卡片。上头只有简单的一个词:“求你!”他对着那张卡片皱起眉头,“你赢了。”他对护士说,然后用大拇指的指甲弹了弹卡片,“那玩意归你了,多拿一些,免得看起来我一点都没吃。”
那个下午的晚些时候,他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亨利小姐:
您的慷慨令我万分感激——先是来看我,然后又送了水果。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但希望有朝一日我能更明白地表达谢意。
您诚挚的,
内德·博蒙特
写完以后,他看了一遍,撕掉,重新誊写在另一张信纸上。用的还是原来的字眼,只是重新排列了一下,把最后一句的结尾改成:“希望有朝一日能把我的谢意表达得更明白。”
这天早晨,奥珀尔·马兹维来访时,内德·博蒙特正穿着睡袍和拖鞋坐在病房窗边的早餐桌边,一边吃一边读着《观察者》。他折起报纸,正面朝下放在餐盘旁边的桌子上,然后站了起来。“哟,丫头。”他友善地开口,脸色很苍白。
“你从纽约回来后,为什么没打电话给我?”她一副责备的语气,脸色也是苍白的。这愈发凸显出她肌肤如孩子般细腻的质感,却让脸庞显得有些老气。她蓝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颜色因为激烈的情绪变深了,无法轻易从那里看穿她的思想。她僵硬地直立着,好像勉强维持着平衡,难以站稳,却无视了他从墙边挪过来的椅子。她只是重复着之前的逼问:“为什么?”
他对着她笑了,温柔而纵容。“我喜欢你穿这种棕色的衣服。”
“噢,内德,拜托——”
“这才像回事。”他说,“我本来要去你家的,可是——呃——我回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不在的时候也有一堆事情等着解决。等到我都搞定了,又碰到沙德·欧罗瑞,结果就被送到这儿来了。”他冲着病房一挥手。
他轻快的语调并未使她的严肃动摇。
“他们会吊死这个德斯潘吗?”她直截了当地问。
他又笑了,说:“这么谈下去的话,我们不会有太多进展的。”
她皱起眉,但还是说:“内德,他们会吗?”她略微放低了姿态。
“我想不会吧,”他微微摇了摇头,“因为他毕竟没杀泰勒嘛。”
她似乎并不感到意外。“你来找我,要我去……去帮你弄证据……或是……或是栽赃的时候,知道人不是他杀的吗?”
他露出一个责备的微笑。“丫头,当然不知道。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啊?”
“你根本就知道。”她的声音冰冷而轻蔑,就像她的蓝眼睛,“你只想讨回他欠你的钱,你还让我帮你利用泰勒命案来达成这个目的。”
“随你怎么想。”他漠不关心地回答。
她朝着他逼近一步。有那么一刹那,她的下巴微微一颤,然后坚定与无畏又重新浮现在那张年轻的脸上。“你知道谁杀了他吗?”她问道,探询地看着他的双眼。
他缓缓摇头。
“是爸爸吗?”
他眨眨眼。“你是说,保罗知道谁杀了他吗?”
她的脚一跺。“我是说,是爸爸杀了他吗?”她喊着。
他一手掩住她的嘴,眼睛扫向关着的门。“闭嘴。”他低声说。
她往后避开他的手,同时伸出一只手,把他的手推离自己的脸。“是他吗?”她不肯罢休。
他以一种低沉而愤怒的语调开口:“如果你非要做个白痴,至少别带着扩音器到处招摇。只要你不说出去,没有人在乎你脑袋里装了什么白痴念头,但是你不能说。”
她睁大了眼睛,然后眼神暗了下来。“那么他的确杀了他。”她的声音低微而呆板,但语气非常肯定。
他把脸凑到她面前。“不,亲爱的,”他用一种暴虐又甜蜜的声音说,“他没有杀他。”他的脸离她很近,一抹恶意的微笑扭曲了他的面容。
她没有后退,表情和声音依然坚定。“如果他没杀,那我就不明白了,我说些什么或说得多大声,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翘起一边嘴角,冷笑了一声。“你想不到自己有多少事情不明白呢。”他愤怒地说,“而要是你一直这个样子,就永远也不会懂。”他从她面前抽身,退了一大步,双手握拳揣进睡袍口袋。这会儿他两边嘴角都耷拉下来,前额现出沟纹。他眯起眼睛注视着她脚前的地板。“你这疯狂的念头是哪儿来的?”他低吼道。
“这念头不疯狂,你心里明白。”
他不耐地动了动肩膀,问道:“哪儿来的?”
她也动了动肩膀。“没有哪里来的。只是——只是突然想到的。”
“瞎扯!”他严厉地说,头仍然低着,抬起眼睛,“你今天早上看了《观察者》了吗?”他严酷多疑的双眼凝视着她。
她的脸上因为烦恼而泛起一丝血色。“我真没看过,”她说,“你为什么问这个?”
“没有吗?”他问话的语调显示出他不相信,眼里疑惑的闪光不见了,转为阴郁与深思,但忽然间又明亮了起来。他把右手从睡袍口袋里抽出来,伸向她,掌心朝上。“给我看看那封信。”他说。
“什么?”她双眼圆睁瞪着他。
“信,”他说,“打字机打出来的信——三句话,没签名。”
她垂下眼睛,避开他的目光,尴尬微微搅乱了她的表情。犹豫了一会儿,她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然后打开了她那只棕色手提袋。
“全城每个人都至少有一封,”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是你收到的第一封?”
“对。”她给了他一张揉皱的纸。
他把它展平,然后读了起来:
你真的笨到不明白你父亲杀了你的爱人吗?
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帮他和内德·博蒙特,企图把罪名加到一个无辜的人头上?
你知道因为帮助你父亲脱罪,你就成了他的帮凶吗?
内德·博蒙特点点头,微微一笑。“它们看起来都差不多。”他把信纸揉成一团,投进桌边的垃圾桶,“现在你已经在寄信名单里了,往后大概还会收到更多。”
奥珀尔·马兹维咬住下唇,蓝色的眼睛冷冷地闪烁着,打量着内德·博蒙特镇定的脸庞。
他说:“欧罗瑞正想从中挖出一些选举材料。你知道,我和他结怨是因为他以为我和你父亲翻脸了,就能收买我帮忙把谋杀案套在你父亲头上——至少足够让你父亲在民选中落败——但我不会这么做。”
她的眼神没变。“你跟爸爸为什么吵架?”她问。
“丫头,那是我们的事,跟旁人无关,”他和善地说,“如果我们真的吵过的话。”
“你们吵了,”她说,“在卡森酒馆。”她猛地咬紧牙关,大着胆子说,“你们吵架是在你发现他真的——真的杀了泰勒之后。”
他笑了起来,嘲讽地问:“怎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她的表情没被他的幽默打动。“你为什么问我看过《观察者》没有?”她问,“上头有什么?”
“更多同一类的瞎扯,”他心平气和地告诉她,“你想看的话,这里桌上就有。选举结束之前,还会有更多……都是这一套。你可以帮你父亲一个忙,如果——”他停了下来,不耐地做了个手势,因为她没在听。她已经走到桌边,拿起她来之前放在桌上的报纸。
他朝着她的背影笑得很愉快。“就在第一版,‘给市长的一封公开信’。”
她看着看着,开始发抖——膝盖、双手、嘴唇——抖得让内德·博蒙特焦虑地对着她皱起眉头。但当她读完了,把报纸放在桌上,转身正对着他的脸之后,她修长的身体与姣好的面容平静得如同雕像。她的双唇几乎没动,低声对他挤出一句:“如果那些不是真的,他们不敢这样写。”
“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会写些什么,”内德懒洋洋地说。他看上去似乎是被逗乐了,但眼底却闪烁着难抑的怒气。
她凝视他良久,然后什么也没说,转身走向房门。
“等一下。”他说。
她停住脚步,再次转向他。此刻他露出友善的笑容,带着讨好的意味。而她的脸如同光洁的雕像。
“丫头,政治是一场严苛的游戏,这次的玩法也一样。《观察者》站在阵营的另一边,他们不在乎什么样的事实可以伤害保罗,他们——”
“我不信,”她说,“我认识马修斯先生——他太太在学校里只比我高几届,我们以前是朋友——我不相信他会用这种话去讲爸爸,除非这是事实,或者他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这是事实。”
内德·博蒙特低声笑了。“你知道的倒挺多。马修斯都快被债务压死了;他的工厂和房子都已经抵押给了州中央信托公司;州中央公司是比尔·罗恩的;比尔·罗恩正在跟亨利打对台,竞选参议员。马修斯只是听命行事,人家叫他登什么他就登什么。”
奥珀尔·马兹维什么都没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被内德·博蒙特的观点说服。
他用一种亲热的劝诱口吻继续说下去:“这个——”他用手指弹了一下桌上的报纸,“比起往后会来的,实在算不上什么。他们还会继续啰唆泰勒·亨利的死,直到他们捏造出更坏的事情来。而在选举结束之前,我们会一再碰到这种事情。我们现在大概也都习惯了。而在所有人之中,你最不该让自己受到这种东西影响。保罗不是很在乎,他是个政客,而且——”
“他是凶手。”她的声音低而清晰。
“而他的女儿是个傻瓜!”他气冲冲地喊道,“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蠢?”
“我父亲是个杀人犯。”她说。
“你疯了。听我说,丫头,你父亲和泰勒的死绝对没有关系,他——”
“我不相信你,”她阴郁地说,“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他生气地瞪着她。
她转身走向门口。
“等一等,”他说,“让我——”
她走出去,在身后关了上门。
对着关上的门愤怒地扮了个鬼脸后,内德·博蒙特陷入深思。皱纹再度浮现在前额,他眯着深色眼睛,嘴唇在小胡子底下撅着。过了片刻,他把一根手指头伸到嘴边啃起了指甲。他的呼吸很规律,但比平常更深。
门外响起脚步声,他脸上思索的表情一扫而空,无所事事地走向窗边,一边哼着《迷失的小姐》。脚步声掠过他门外,他停止哼歌,弯腰拾起写着质问奥珀尔·马兹维那三个问题的信纸。他没把纸抚平,而是攥住它,将那团松散的纸球揣进浴袍的口袋里。
然后他找了根雪茄,点燃了咬在嘴里,站在桌边透过烟雾往下斜睨着桌上那份《观察者》。
给市长的一封公开信
市长先生:
《观察者》业已掌握了某些情报,相信对于厘清近日笼罩在泰勒·亨利谋杀案上的重重疑云至为重要。
这份资料包括数份证词,目前锁在《观察者》的保险箱里,其要点如下:
一、数月之前,保罗·马兹维曾因泰勒·亨利对其女的追求而与之争执,并禁止女儿与亨利再次相见。
二、虽然如此,保罗·马兹维之女依然与泰勒·亨利在他特地租下的一间套房中约会。
三、亨利遇害的当日下午,二人就在那个套房内相聚。
四、保罗·马兹维当晚到泰勒·亨利家,应当是为再度对泰勒或其父表示抗议。
五、泰勒·亨利遇害前数分钟,保罗·马兹维离开亨利家,看起来怒火中烧。
六、曾有人在陈尸地点不到一个街口处,见到保罗·马兹维和泰勒·亨利两人相距不过半个街区。而不到一刻钟后,泰勒·亨利的尸体被发现。
七、目前警方没有一名警探试图查出谋杀泰勒·亨利的凶手。
《观察者》坚信,您应该了解这些事情,选民和纳税人也同样如此。《观察者》别无所图,只渴求伸张正义。《观察者》乐于有机会把这些证词,以及掌握的所有其他资料提交给您,抑或任何有权的市辖或州辖法庭。此外,若能有助于执法,我们愿意停止公开这些证词中的任何细节。
但《观察者》不会容忍这些证词与资料被忽视。如果被选举出来,理当执行法律并管理市政府或州政府的官员,对此类重要证词竟不予采纳,《观察者》会将证词全文刊登,从而将此案诉诸更高层次的法庭——本市的全体公民。
发行人
H.K.马修斯
内德·博蒙特嘲弄地咕哝了一声,朝着这份宣告喷了口烟,但他的眼神依然深沉。
那天下午稍早,保罗·马兹维的母亲来探望内德·博蒙特。他双臂拥住她,亲吻她的双颊,直到她故作严厉地推开他。“给我停下,你比保罗以前那只艾尔谷小猎犬还讨厌。”
“我有点儿小猎犬的血统,”他说,“从我父亲那边传下来的。”然后他走到她身后,帮她脱下海豹皮大衣。
她整了整黑色的裙子,走到床边,坐在上头。
他替她把大衣挂上一把椅背,双脚分立,双手揣在浴袍口袋里,站在她面前。
她挑剔地打量他。“你看起来不太坏,”过了一会儿她说,“不过也不太好。感觉怎么样?”
“好得很。我是为了那些护士才继续待在这儿的。”
“那倒也不意外。”她告诉他,“不过别站在那儿,像只柴郡猫
 似的眯着眼睛看我,搞得我心神不宁的。坐吧。”她拍拍身旁的床。
似的眯着眼睛看我,搞得我心神不宁的。坐吧。”她拍拍身旁的床。
他在她身边坐下。
她说:“我不知道你干了些什么,保罗好像觉得你做的事很伟大也很高尚。但可别跟我说如果你行得端做得正,还能让人把你搞成这副德行。”
“噢,妈。”他开口。
她打断他,那双和她儿子一样灵动的蓝眸凝视着内德·博蒙特棕色的眼睛。“看着我,内德。保罗没杀那个毛头小伙子,对吧?”
内德·博蒙特惊讶得张口结舌。“他没有。”
“我想也是,”老太太说,“他一直是个好孩子,可是我也听到了一些难听的谣言。只有上帝才晓得政治是怎么回事,我是完全搞不懂。”
内德·博蒙特注视着她瘦削的脸庞,眼神里玩味与惊奇交织。
她说:“好,你就瞪我吧,可是我从来就没弄明白,也懒得去明白你们男人在想什么或不想什么。早在你们还没出娘胎之前,我就已经放弃了。”
他拍拍她的肩膀。“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妈。”他钦慕地说。
她抽离他的手,洞悉一切的严厉双眼再次瞪住他。“如果他杀了人,你会告诉我吗?”
他摇摇头表示否定。
“那我怎么知道他没干呢?”
他笑了起来。“因为,”他解释道,“即使是他杀的,我也会说‘不是’。但如果你问我要是他杀了人,我会不会说实话,我的回答是‘会’。”他眼神和声音里的欢欣消失了,“不是他杀的,妈。”他对着她微笑,只有嘴唇微微牵动,“如果全市除了我之外,还能有谁认为不是他杀的,那就太好了;而如果这个人是他的母亲,那就最好不过了。”
马兹维太太离开一小时后,内德·博蒙特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有四本书和一张珍妮特·亨利写的卡片。他正在写致谢的短笺时,杰克来了。
“我查到点儿东西了,不过你大概不会喜欢。”杰克抽着烟,吞云吐雾地说。
内德·博蒙特审视地看着那个漂亮的年轻人,用食指顺了顺左边的小胡子。“只要是我雇你去查的东西,我就会喜欢。”他跟杰克一样用就事论事的口气说道,“坐下来告诉我吧。”
杰克谨慎地坐下来,双腿交叠,帽子放在地板上,目光从他的香烟转到内德·博蒙特身上。他说:“那些信好像是马兹维的女儿写的。”
内德·博蒙特的眼睛稍稍睁大了片刻。他的脸略略失去血色,呼吸变得不规律起来,但他的声音没变。“有什么根据吗?”
杰克从内侧口袋掏出大小、质地与折叠方式都很相似的两张纸。递给了内德·博蒙特。他打开来,上头各有三个打字的问句,问题都是一样的。
“其中一张是你昨天给我的,”杰克说,“你认得出是哪张吗?”
内德·博蒙特缓缓摇头。
“没有差别,”杰克说,“另一张是我在查特街泰勒·亨利租的套房里打的,马兹维的女儿以前常去——用的是那里的科罗纳牌打字机和纸。目前查出来的是,那地方好像只有两把钥匙,他有一把,她有一把。他遇害之后,她至少回去过两次。”
内德·博蒙特对着手上的那两张纸蹙着眉,眼都不抬地点了点头。
杰克用正在抽着的那支香烟引着了一根新的,站起来走到桌边,把旧的那支捻熄在烟灰缸里,回到座位上。无论是从他脸上的表情还是态度,都看不出他对内德·博蒙特的反应有丝毫兴趣。
又沉默了片刻后,内德·博蒙特把头稍稍抬起来,问道:“你是怎么查到的?”
杰克嘴角的香烟随着他讲话而摇晃。“今天早上《观察者》的报道给了我提示。警方也因此去了那儿,而且他们比我先到。不过我逮到一个好机会:负责那里的警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叫弗莱德·赫利。给他十块钱,他就让我进去随便翻。”
内德·博蒙特弹着手上那两张纸。“警方知道吗?”
杰克耸耸肩。“我没告诉他们。我问了问赫利,可是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只是在那儿看着东西,直到警方决定要采取什么措施。也许他们知道,也许不。”他把烟灰抖到地板上,“我可以去查。”
“算了。你还查出些什么?”
“我只查这件事。”
内德·博蒙特迅速地瞥了一眼年轻人莫测高深的深色脸孔,又低下头看着那两张纸。“那地方什么样?”
“十三英尺宽,二十四英尺长,用法兰奇的名字租下来的,一室一卫。女管理员说,一直到今天警方去了,她才得知他们的真实身份。这也许是真的,因为那种地方通常不会过问太多。她说以前他们常去,大部分是在下午。而且据她所知,过去一星期左右,女的回去过几次。不过她也可以很轻易地偷偷进出,不被人看到。”
“确定是她吗?”
杰克举起一只手,比了个不置可否的手势。“根据描述是没错。”他停顿了一下,在喷出烟时漫不经心地补充,“他遇害之后,女管理员只见过她一个女人。”
内德·博蒙特再度抬起头,眼神冷酷。“泰勒还带着其他人去过?”他问。
杰克又比了个不明确的手势。“那女的没这么说。她说她不知道,不过从她讲话的态度看来,我敢打赌她准是在撒谎。”
“从那地方的东西看不出来吗?”
杰克摇摇头。“看不出来。里头女人的东西不多——只有一件和服式睡袍和盥洗用具、睡衣裤之类的。”
“他的东西多吗?”
“嗯,一套西装和一双鞋,还有些内衣、睡衣、袜子等等。”
“帽子呢?”
杰克笑了。“没有帽子。”他说。
内德·博蒙特站起来走到窗边。外头几乎全黑了,窗玻璃上沾了十来滴雨。内德·博蒙特站过去后,又有更多的雨点打了上去。他转身再次面对杰克。“多谢了,杰克,”他缓缓地说,心不在焉的双眼木然地看着杰克的脸,“我或许很快又会给你一份任务——搞不好就是今晚。我会给你电话。”
“好的。”杰克说着,然后起身出去。
内德·博蒙特走到衣柜前拿衣服,带进浴室里换上。他走出来时,病房里来了个护士,是个高大的女人,有着白皙而容光焕发的面孔。
“怎么了,穿得这么整齐!”她叫道。
“对,我得出门。”
她震惊的表情又掺进了警戒。“可是不行,博蒙特先生,”她抗议道,“现在这么晚,又开始下雨了,而且泰特医生会——”
“我知道,我知道。”他不耐烦地说,绕过她朝门口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