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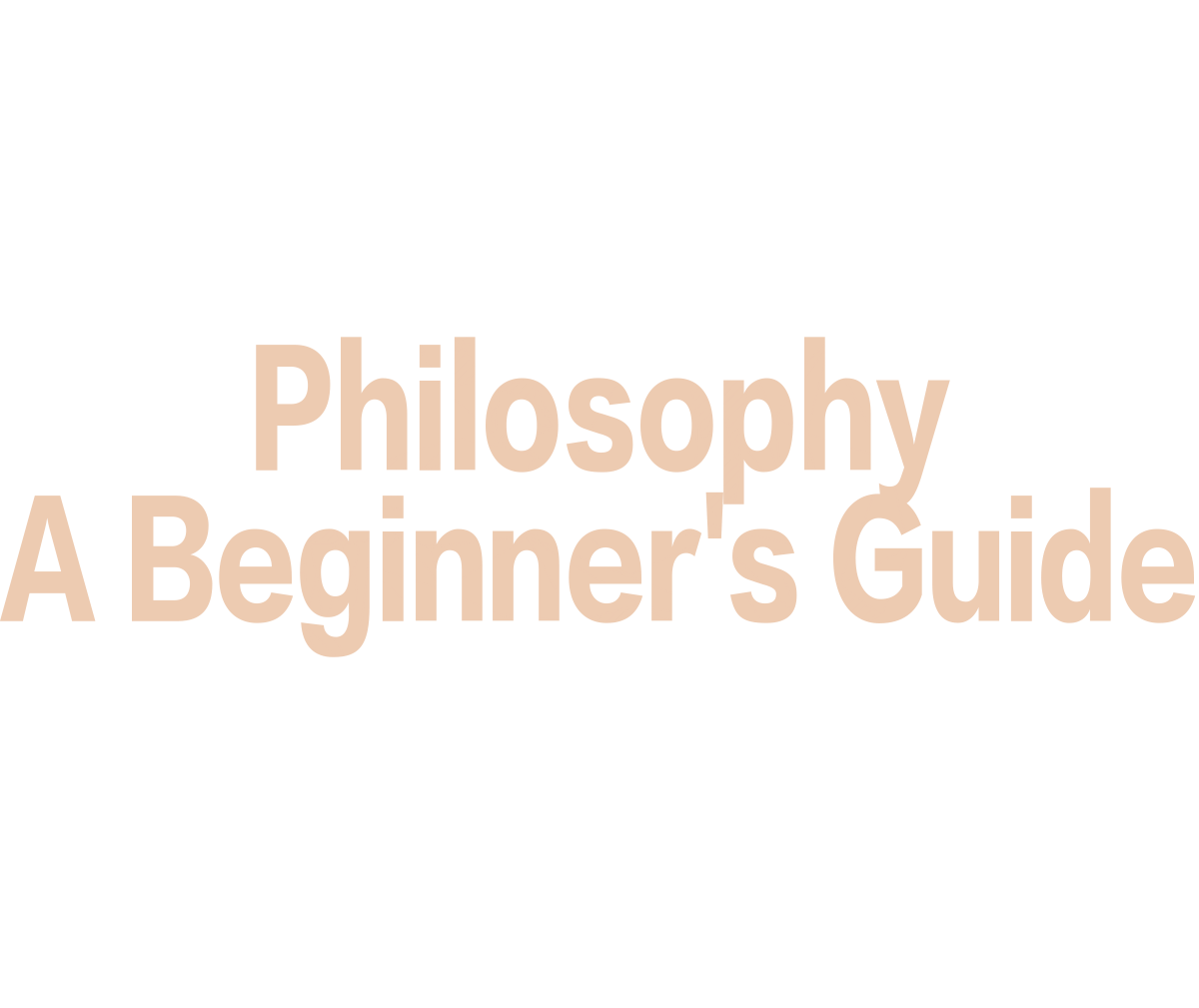
假设你在一台能模拟现实的机器的作用下获得了某些经验感受,你会认为这些经验是真实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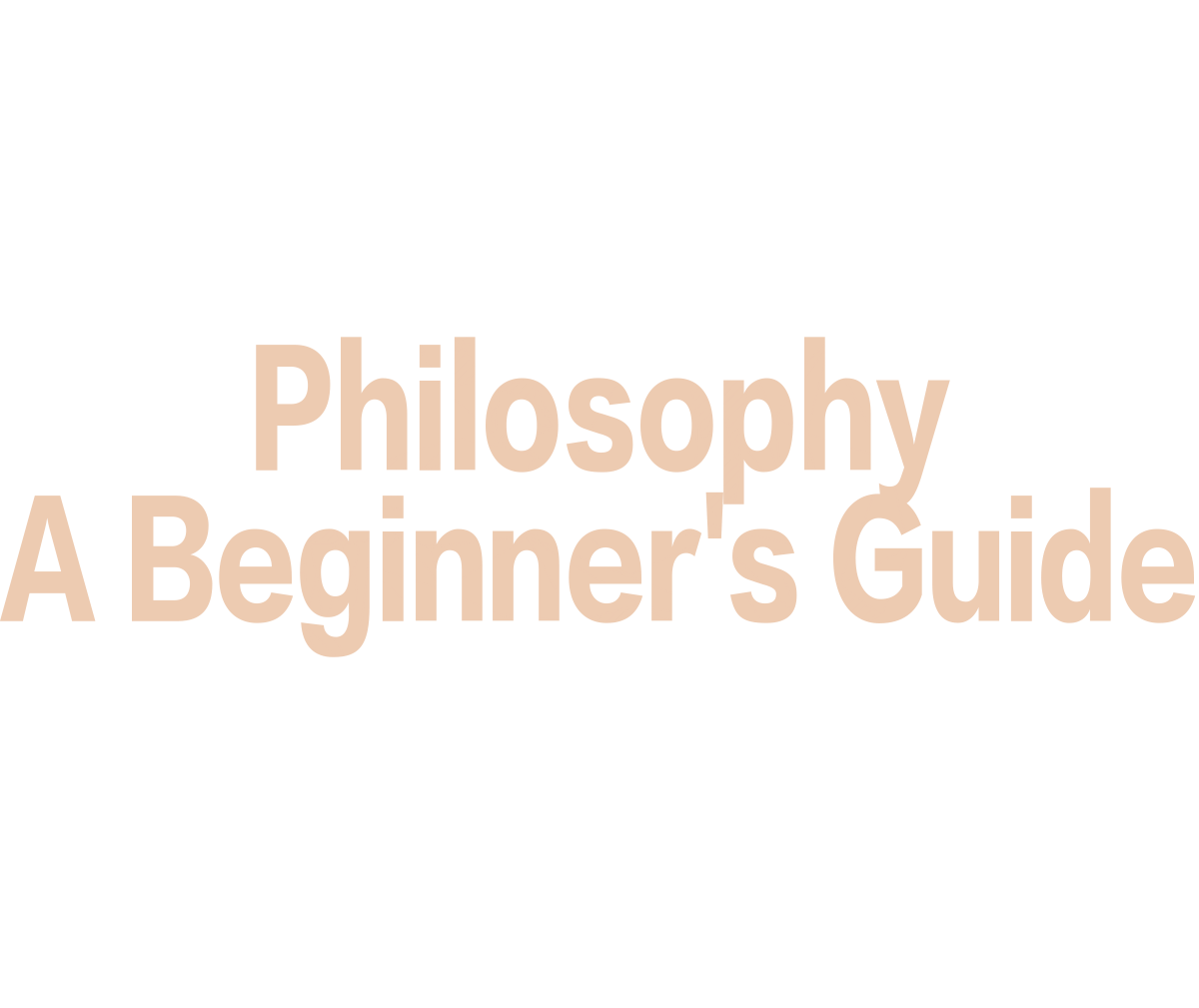
“人活着只需要在乎经验感受”,许多人都觉得这句话很肤浅,因为生命中有许多事都比经验感受重要。至少,我们还应该关注他人是否生活得好。然而,有人却回应道:“你说得没错,但他人生活得好,也不过说明他们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仍只是他们的经验感受而已。”
假设你所谓的朋友背叛了你,他在背后说你的坏话,或者合作伙伴欺骗了你;对此,你一无所知,并且一生都无法察觉。你的生活太平无事,甚至非常幸福。就此而言,你的经验感受毫无变化,如同从未被背叛过一样。然而,即便没有察觉,难道你的生活就真的可以被认为是幸福的吗?难道你不会更希望生活中没有人欺骗你吗?
此类问题可以引出令人困扰的、更深层的哲学思考。毫无疑问,假如没有经验感受,人类生活将会变得没有意义;但生活同样需要涵盖更多内容,作为人,我们无疑应该看得更深刻,拥有更高的价值理想。作为人,我们能看到表象与真实之间的差别,能看到事物呈现出的样子与事物真实的样子之间的差别,比如善意、笑脸、对爱与忠贞的誓言,和未被察觉的背叛之间的差别。
以上思索,可以把我们引入对人类本性及其价值,即人类“自我”的哲学讨论上来。后面,我们会讨论“经验机器”(experience machine),还会讨论名声显赫,或者可以说声名狼藉的笛卡尔先生,他可是所谓的“现代哲学之父”。这些讨论,将为后续的章节做好铺垫,而许多与之相关的问题也将在后续的章节中具体展开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哲学家而言,“现代”(modern)通常起始于17世纪初期。因为在这个阶段,至少从表面上看,笛卡尔开始凭借理性(reason)去理解这个世界,而不再依赖古典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或经院哲学的解释。不过,其实在笛卡尔之前,弗兰西斯·培根也开始鼓励以科学实验的方式去了解世界如何运行。
假设你热爱航海,想要独自环游世界,但是你却很懒、缺乏毅力,还特别容易晕船。再假设存在一台令人梦寐以求的机器——经验机器,它能够模拟现实,无论你想要什么经验感受,它都能提供给你。一旦接通电源,你将无法分辨真实与虚拟,并忘记你正在使用机器,而你所体验到的经验、感受、信念都与现实生活中的毫无差别。那么,这能说你实现了自己的追求吗?
古希腊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这是古希腊雅典的三位哲学巨头,他们对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以及被归为“自然哲学”时期的科学等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苏格拉底 (前469—前399):他是一个知识“牛虻”,刺痛了那些自以为懂得很多的、自满的富人和权贵。当时,雅典的人民认为他的思想会腐蚀年轻人,而且亵渎神明,于是判处他死刑。苏格拉底拒绝了学生们安排好的逃跑计划,毅然赴死。现在,我们对苏格拉底思想的了解大多来自其最伟大的学生柏拉图的著作。
柏拉图 (前429—前347):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柏拉图超越了这个不断变化的表象世界,进而去探索永恒不变的理念或概念。他提出了许多关于理想社会的观点,这些观点有些非常激进,例如认为男性与女性应该平起平坐等;此外,他还提出了很多关于爱、欲望和想法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 (前384—前322):他是柏拉图最伟大的学生,是第一个正式的逻辑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还曾经做过亚历山大的老师。没错,就是那个后来成为亚历山大大帝的亚历山大。在拉斐尔的画作《雅典学院》中,柏拉图手指向上方,而亚里士多德的手指向下方,这明显地表达了两人在思想上的分歧——柏拉图追求超越表象的理念,可以说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则更侧重于客观的存在。
前苏格拉底哲学: 指的是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流派。这一时期的哲学家的绝大多数作品都遗失了,没有保存下来,但其思想对此后的哲学仍然有重要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就是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 赫拉克利特 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哲学家,他提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流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针对这一观点,后来又有一位哲学家提出“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
巴门尼德 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一首名为《论自然》的诗中,而在这首诗《真理之路》的部分中,他认为唯一真实的存在就是“一”,而“一”是永恒不变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芝诺悖论(Zeno's paradox)的有力支持:你如何能到达那堵墙?首先,你需要到达路程的中点,然后再走到中点,然后再走到中点……如此循环往复,虽然每一半的距离都在缩短,但它却可以无穷无尽地分割下去,于是,你永远都到不了那堵墙。
古希腊其他哲学家
当我们把目光都集中在最伟大的哲学家身上时,其他很多重要的哲学家就可能会被忽略。比如说,古希腊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普罗泰戈拉,以及后来的斯多葛学派(Stoics)和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s)。还有,深受古希腊哲学影响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和中世纪逻辑学的集大成者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
如果在使用这台机器时航海,那么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你所有的经验感受都和真去航海完全一样。你能感受到涌动的海浪,看到遥远的荒岛,甚至还会有一点点晕船。当然,这种晕船的感觉也是你在使用机器前自己要求的。你能看到美丽的美人鱼或帅气的水手在岸边向你招手,甚至能看到有人在码头进行电视采访,等等。然而,在感受这一切时,你可能其实一直待在伦敦、纽约或新德里某个肮脏的地下室里使用经验机器。
迄今为止,科技还无法生产出这种机器,但万事皆有可能。我们可以假设存在这样一台机器,机器一端的电极接通你的大脑,再输入适量的电化学刺激,你就能够拥有相应的经验感受。在流行电影里,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假设,《黑客帝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讲述了虚幻的真实。那么,这个思想实验的哲学价值是什么呢?或许其中一个价值就是:它帮助我们了解是什么使人类生活与众不同,什么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设想一下,你能使用经验机器,通过这台机器,你能拥有任何你想要的经验感受,甚至无须下床。那么,开启经验机器之后,你是否就实现了自己的追求?经验感受是生命中唯一重要且有价值的事情吗?
对多数人而言,答案是“不”,上述背叛的例子亦能说明这一点。的确,人们渴望得到某些感受,比如快乐,而且无论这种感受是何种事物带来的,他们都会感到欢喜。有时,人们想要得到某种具体的感受,比如想听到演奏笛子的声音或闻到新鲜的花草香,而且他们不在乎这种感受是源自真实的笛子和花草,还是源自某种电子机器。然而,即便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仍然在意经验感受之外的内容:想要触摸真实的事物,希望经验源自真实的世界。
经验机器的失败之处就在于经验的源头:虽然该机器带来的经验感受足够真实,却并非来自真实的世界。是的,人们或许会渴望通过海洋环游世界的经验感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想体验在全球的海洋里航行。人们或许会幻想自己成为全球顶级钢琴家的经验感受,但实际上,他们想要的是成为真正的钢琴家,并能够在现实中获得赞扬和荣誉。
人们通常都渴望得到爱,渴望生儿育女,渴望自己支持的球队获得胜利,但实际上,他们渴望的并非爱、生儿育女和胜利的经验感受,他们追求的是真实的、不虚假的事物,即便他们无法分清“虚假的X”与“真实的X”带来的经验感受之间的差异。通常,人们追求的是真正的成功,而非机器带给他们的成功的幻觉。因为在这种幻觉中,他们并没有取得胜利,而仅仅是误以为自己取得了胜利。
上述背叛和经验机器的故事皆说明,对于人类而言,经验感受并非唯一具有价值的事物。当然,这些故事也会引起我们的困惑——如何才能确保自己的经验感受是真实可信的呢?换言之,我们如何确定自己并非正在使用经验机器呢?或许,我们此时正在经验机器里获得阅读哲学书籍的经验感受呢?这个思路其实与怀疑主义极具破坏力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质疑人能否获得关于“真实”的知识。这是一个属于认识论的问题,而“认识论的”(epistemic)这个词就源自古希腊的“知识”一词。至于怀疑论,我们到后面的章节中再讨论。现在,我们先来看看笛卡尔是如何利用怀疑主义揭示人类本质,以及他是如何进行论证的。
毋庸置疑,我们是有知觉意识的存在者,能够感受经验、坚守信念。但在这里,“我们”到底是什么,那个能够感受经验或坚守信念的“我们”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大脑和心脏,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本质上,“我们”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存在,应必须具备哪些符合逻辑的、必要的条件?
很多人相信肉体死亡,甚至肉体消失之后,人仍有活下去的可能性。但是,这种观念符合逻辑吗,它是否具有内在的矛盾呢?比如,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三角形在逻辑上不可能拥有四条边,假如不是三条边,它在逻辑上就不是三角形。那么,与之类似,假如没有身体,人是否在逻辑上就不能存在了呢?或许,人的本质是灵魂,无须身体人亦可存在?
经验机器的例子说明,事物或许并非它所彰显出来的样子。再来看一个比这一思想实验更极端的观点:笛卡尔认为,我们可以怀疑所有事物的存在,例如树木、蔬菜、土地、湖泊、果酱,等等,甚至可以怀疑机器的存在。或许我们只是梦见了这些事物的存在。
现代哲学之父
勒内·笛卡尔 (1596—1650):他之所以被视为现代哲学之父,是因为他最先开始尝试建立某种确定的、无法被质疑的知识,并且不诉诸古典的或宗教的权威。他鼓励人们也从事这样的研究,而他自己的发现则主要记录在《第一哲学沉思集》(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中。
生平: 笛卡尔年轻时喜欢旅行,为了旅行,他还参了军。1619年,在一个温暖的火炉旁,笛卡尔梦想着构建一种新的理解世界的方法。他创建了笛卡尔坐标,为解析几何学奠定了基础,他钻研光学和天文学,试图以数学和机械的方式解释自然世界和人类身体。同时,他把心灵或灵魂视为与身体截然不同的事物。
笛卡尔原本打算出版一本讨论自然世界的书,来说明地球围绕太阳转,但在听到伽利略因推广日心说而被教廷处罚之后,他就放弃了。虽然笛卡尔是一位天主教信徒,但他经常因为其机械论哲学而受到攻击。据说,这与他曾经发明的一个机械娃娃有关。
逝世: 笛卡尔声名远播,所以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希望他来教导自己。没有人能拒绝“皇家邀请”,尤其是喜欢被赞助的笛卡尔。在一个冬天,笛卡尔来到了斯德哥尔摩。由于体弱多病,笛卡尔通常会在下午起床,但在这里,他需要每天早上5点去给女王上课。不久之后,他就因感染肺炎而去世了。
就此而言,或许有一个全能的、邪恶的天才在欺骗我们。谁知道呢?或许是这个邪恶的天才让我们误以为自己拥有手指、器官和大脑。毕竟现实中也有人能感受到“幻肢”(phantom limbs)的存在:有些人在截肢手术后醒来,没什么感觉,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截肢了。只有掀开被单时,他们才会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腿。
但是,即便没有这种全能的、邪恶的天才,怀疑主义者仍然可以质疑客观世界是否真实存在。或许真的存在着一个外在的自然世界,并使我们产生了各种经验感受;或许我们的经验感受并非像我们想的那样来自外在世界,而是来自某种类似于经验机器的完全超乎我们想象的东西;又或许我们的经验感受根本就没有来源,它们就这么凭空出现了。尽管这些观点看上去不太现实,但它们在逻辑上确实是可以成立的。而实际上,我们似乎没有办法验证这些观点是真是假。
之前提及笛卡尔时,我一直使用“我们”这个词,但真正开始讨论时,却要使用第一人称“我”。因为,假如我怀疑外在物质世界的存在,那我也有可能怀疑他人的存在。这就是怀疑主义者提出的“他心知”(other minds)问题,即纵使我相信他人身体的存在,虽然这也是可以怀疑的,但我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人身体里面还存在着心灵呢?我们只能看到他人的身体,因此他人或许只有身体而没有心灵,这种情况同样存在着一定的可能性。或许,你就是这个宇宙中唯一有意识的存在,他人的言行其实只是由机器或僵尸之类的生物进行的复制或转述,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经验感受。你之所以觉得他人的言行有意义,不过是你自己赋予的。
通过这些怀疑主义的思考,笛卡尔最终得出结论:即便可以怀疑外在世界的存在,也不能怀疑“他”的存在。或许,他认为外在世界存在是因为他被一个邪恶的天才彻底欺骗了,但无论骗术多么高明,只有他这个人,即笛卡尔存在着,邪恶的天才才能欺骗到他。换言之,他可以否定全部的外在世界,但无法否定自己的经验感受。
由此,他得出了著名的观点“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拉丁语写作“ cogito ergo sum ”,亦常缩写为“ cogito ”。这里暗含着一个逻辑论证,即笛卡尔的欺骗论证(Feigning Argument),以第一人称表述如下:
前提1: 我被骗的时候,能够相信“我的身体(包括大脑)不存在”;
前提2: 我被骗的时候,不能相信“我(无论我是什么)不存在”;
结论: 因此,“我的身体”(my body)不等同于“我”(I)。
笛卡尔的结论说明了一种可能性,即在身体被毁灭之后,人仍有可能继续存在。当然,这仅仅只是一种可能性。同时他也曾简短地讨论过“不朽”。他声称,一个物体只能以两种方式被毁灭:要么被分割成细小的组成零件,要么全能的上帝让其灭绝。心灵,也就是“我”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它没有组成部分。幻想自己同时存在两个彼此分离的心灵是毫无意义的事。因此,只要上帝允许,心灵就可以永生。
笛卡尔的欺骗论证到底想说明什么呢?这里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理解:设想你听说过贝尔,也听说过廷克斯。如果你想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人,还是同一个人使用了两个名字,那么你可以尝试寻找贝尔拥有而廷克斯却没有的属性。比如,此刻贝尔在纽约,而廷克斯在加尔各答,那么他们俩就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既出现在这里,同时又出现在相隔千山万水的远方。
欺骗论证和有关贝尔与廷克斯的论证其实是相似的。就“我的身体”而言,被骗的时候,我可以相信我的身体不存在;就“我”而言,被骗的时候,我仍要相信我存在。因此,“我的身体”和“我”就不是同一个事物。除此之外,我存在,而他人不存在,这一假设符合逻辑上的可能性
 。同样,贝尔在一个地方,廷克斯在另一个地方,也符合逻辑上的可能性。换言之,从逻辑上来说,一个人存在而其他人不存在是有可能的。
。同样,贝尔在一个地方,廷克斯在另一个地方,也符合逻辑上的可能性。换言之,从逻辑上来说,一个人存在而其他人不存在是有可能的。
然而,某个事物具有逻辑上的可能性,并不能说明它具有物理或实践上的可能性。比如,在逻辑上,如果没有贝尔的存在,廷克斯仍然可以存在;但在实践上,如果没有贝尔的存在,廷克斯可能就无法存在,因为贝尔或许是廷克斯的母亲,又或许贝尔在多个方面对廷克斯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证(Arguments)
哲学家很少真的动手打架,但他们一定会进行论证:给出前提,进行推理,得出结论。如果根据前提必然能推出结论,这就是一个有效论证(valid argument)或演绎论证(deductive argument)。在有效论证中,如果前提全都为真,那么结论必然为真。如果一个论证是有效的,同时前提皆为真,它就可以被称为一个可靠论证(sound argument)。如果存在假的前提,论证仍然可以是有效的,只是不再是可靠的,比如:所有的女性都戴着帽子,贝特是一名女性,所以贝特戴着帽子。
以下是一个无效论证(invalid argument):如果下雨,那么客人就会浑身湿透;客人浑身湿透了;所以下雨了。在这个论证中,即便前提皆为真,结论仍然可能为假,毕竟,客人浑身湿透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打水仗,所以这是一个无效论证。当然,有一些非常好的论证不需要是演绎论证,也可以是归纳论证(inductive argument)。
我们可以再举几个关于逻辑可能性的例子。假如说一个人在两分钟之内跑完了一千米,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在实践中却是不可能的。经验机器在逻辑上是可能存在的,但这不意味着在实践中它可以被生产出来。
欺骗论证是一个好的论证吗?更具体地说,在该论证中,根据前提能推理得出其结论吗?换言之,假如该论证的前提是真的,那么结论就必然是真的吗?如果结论必然为真,那么该论证就是有效的,因为论证的有效性只与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有关。
即便论证是有效的,结论仍然可能是假的,因为有效论证可能是根据假的前提有效得出了假的结论。比如说,从“所有的哲学家都是美丽的”和“苏格拉底是哲学家”这两个前提出发,就会有效得出“苏格拉底是美丽的”这一结论。然而这个结论明显是假的,因为苏格拉底长得很丑。可见,此论证的前提,即“所有的哲学家都是美丽的”必然有误。

因此,在评价欺骗论证的时候,我们不但要评价该论证是否有效,还要评价该论证的前提是否为真。只有当前提为真,且论证有效时,我们才能说这是一个可靠论证,即一个结论必然为真的论证。
让我们直接回到欺骗论证中的前提1,巧舌如簧的笛卡尔确实表明了我们可以被欺骗,并相信自己的身体不存在。这里并没有说身体真的不存在,而是说我们可以先假装身体不存在,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前提1是真的。
前提2则是值得讨论的:的确,我可以假想一个我从未存在过的世界;但是,在我正在假想的这一瞬间,我不能假想我不存在。与之对应的是,在我正在假想的这一瞬间,我仍然可以假想我的身体不存在。然而,我们也不能过于相信笛卡尔视为理论根基的“我思故我在”,因为或许只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思维能力,我才不能假想我不存在。可以说,笛卡尔以某种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存在——由于笛卡尔在思考,所以他一定存在,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怀疑或质疑该论证的合理性。毕竟如果给笛卡尔灌上足够多的威士忌,他就可能会怀疑自己的存在,甚至可能开始怀疑“我思故我在”的合理性。
如果暂时先接受笛卡尔的怀疑主义,把前提1和前提2都视为真的,我们仍要追问,根据这两个前提是否必然能得出笛卡尔的结论。如果能,同时前提皆为真,那这就是一个可靠论证,结论必然为真。别忘了,这可是一个振奋人心的结论:假如人真的能与身体区分开来,那么从理论上来说,身体消亡之后,人仍然能够继续存在。以笛卡尔的视角来看,人的本质是心灵(mind)、自我(self)或灵魂(soul),而这三个术语在笛卡尔那里是被混用的;与之相比,人类以外的动物则缺乏心灵、自我或灵魂。不过,这一点也值得争论。难道仅仅因为猫、黑猩猩、海豚等动物不具有笛卡尔所说的理性,就认为它们缺乏心灵,也就是构成本质的那种东西了吗?
欺骗论证和有关贝尔与廷克斯的论证都是有效论证,它们具有相同的论证结构,且都依赖于莱布尼茨提出的一条原则。在笛卡尔之后不久,莱布尼茨开始写作,他是著名的数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首先提出了“不可分辨者的同一性原则”(Identity of Indiscernibles)
 ,具体是指,假如两个看似不同的事物拥有所有相同的属性,那么它们就不是两个事物,而是同一个事物。
,具体是指,假如两个看似不同的事物拥有所有相同的属性,那么它们就不是两个事物,而是同一个事物。
但是,不可分辨者的同一性原则也会受到质疑:能否假设宇宙中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铜球,而且完全无法对两者进行分辨?它们具有的所有属性都完全一样,但仍然是两个事物。于是,另一个被称为“同一者的不可分辨性”(Indiscernibility of Identicals)
 的原则,似乎看起来更加合理。以贝尔与廷克斯的情况为例,如果贝尔和廷克斯是同一或相同的人,那他们就具有完全相同的、无法分辨的属性。因此,如果贝尔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廷克斯也必然如此。
的原则,似乎看起来更加合理。以贝尔与廷克斯的情况为例,如果贝尔和廷克斯是同一或相同的人,那他们就具有完全相同的、无法分辨的属性。因此,如果贝尔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廷克斯也必然如此。
莱布尼茨的同一者的不可分辨性原则很好,但它并不适用于一些特定的属性,而上文提到的“欺骗”就属于这一类。换言之,当谈论心理状态及相关属性时,该原则就不正确了。以下就是该原则失效的一个例子。
从见到维丽蒂的第一眼起,卢克就爱上了善良的她。但卢克只在哲学研讨会上见过她:她从他身边娴静、温柔、端庄地走过。就这样,卢克爱上了维丽蒂。看报纸的时候,卢克偶然间看到一个恶棍有一个情妇叫玛克辛。玛克辛是一个妓女,她敲诈自己的客户,还参与了多起暴力犯罪事件。警方提供的玛克辛的人像素描比较模糊,卢克无法看清楚她的样貌。但显然,他不会爱上这样一个女人。然而,事情败露之后,卢克发现,维丽蒂和玛克辛其实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样子。于是,面对同一个人,卢克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两种完全冲突的心理情感。此时,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笛卡尔的欺骗论证。
在欺骗论证中,笛卡尔在描述“我的身体”和“我”时也涉及心理状态;“我的身体”和“我”可能是同一个事物,只不过呈现出来的样子不同。所以,从该论证的前提出发,并不能有效地推出该论证的结论,即便前提为真,结论仍然可能为假。如果仔细观察,我或许就能发现“我的身体”和“我”是同一的;正如卢克如果仔细观察,就能发现维丽蒂和玛克辛是同一个人。请注意,这里的类比只是一种修辞。
如果没有身体,我们究竟该如何观察身体呢?虽然笛卡尔的论证存在明显的问题,但他试图证明的结论似乎也有许多真知灼见。比如,假若我们在论证黑德维希比尼科莱特跑得快,即使理由很蹩脚,但也不足以说明黑德维希就跑得一定慢,比赛之时,自见分晓。同样,笛卡尔的论证虽然让人充满疑虑,但人是心灵和身体的结合体,这个看法或许是正确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方面的内容吧。
笛卡尔的二元论(dualism)区分了我的身体与我的本质,即自我。简而言之,我的本质即我的心灵,或者说,自我即心灵。笛卡尔把自我、心灵或灵魂视为实体,而非脑海中的空想,即便它们是非物质性的,不占据任何场所,不处于空间之中,即没有空间的广延。它们所占据的空间甚至不如数字7所占的空间大。
在笛卡尔看来,自我可以不依赖任何事物而独立存在,当然,除了上帝之外。但严格来说,笛卡尔理论中的实体其实只有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才是真正完全独立于其他所有事物而存在的。不过,宽泛地看,心灵与身体也可以被理解为实体。
在二元论的视域下,心灵和身体虽然可以区分,但在世俗世界中,它们却紧密交织在一起。世界通过人们的各种感知能力,如视觉、听觉、触觉等影响着人们;人们又通过各种行为,即由选择和欲望驱使着身体做出的行为影响着世界。比如说,当6点的铃声响起,铃声通过听觉和神经系统传达给我的心灵,导致我,也就是我的心灵认为是时候去喝一杯了,于是我的大脑做出决定——出发去酒馆。做决定是一个心理活动,它又使大脑开始控制我的肌肉,进而出现了走路的行为。
在笛卡尔的视域中,感知能力是对外在世界的被动反应,而后人们再根据获知的信息进行各种活动。但实际上,感知能力和活动都比笛卡尔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
先验VS后验
我们知道的许多知识都来源于经验,比如他人告诉的,自己看见的、听到的,以及对它们的记忆,等等;再比如,我们知道柏拉图是谁,或许知道委内瑞拉的总统是谁,还知道昨天下雨了。这些都是后验知识,不能仅凭理性就认识到。
与之相反,有些知识可以仅凭理性获得,它们被称为先验知识。比如说,只要掌握了相关概念,我们就可以知道29不能被3整除,双胞胎肯定不是独生子,单身汉一定没有结婚。但是,知道总统是什么意思,知道委内瑞拉是一个国家,却并不能让我们知道委内瑞拉的总统是谁。
偶然性VS必然性
偶然真理是真的,但它并不总是真的。比如“笛卡尔是一个哲学家”,但他未必一定会成为一个哲学家,他也有可能去农场养猪。同样,偶然谬误是假的,比如“你现在没有在读书”,但它也可能成为真的,因为或许你已经睡着了。
与之相对应,还存在必然真理与必然谬误。必然真理必然为真,比如不论在什么情况下,“2+2=4”都是真的。当然,“2”“+”等符号可以有其他用法,但假定不改变符号本身的含义,“2+2=4”就是一个必然真理。同样,“即使有一千个人,也不能给一个裸体之人脱掉衣服”是必然真理,也是先验的。
矛盾则是必然谬误,比如“这些字的颜色既是黑色的,又不是黑色的”,这个陈述就必然是错误的。
就感知能力而言,我们先来看下页图1-1中这幅鸭子或兔子的图画:相同的线条和绘画,没有任何差异,我们却既可以把它视为一只鸭子,也可以把它视为一只兔子。在感知过程中,人们通常要主动建构所看见的事物。毕竟人不是海绵,只能被动地感受外在世界,或吸收外在世界赋予的各种信息。
就活动而言,人们的所作所为部分地取决于外在世界。比如说,人们以为自己在给企鹅喂食,但或许正在不知不觉地毒害企鹅(见下页中的图1-2)。如果指示牌上写了禁止给企鹅喂食,你还会故意给它们喂食吗?如果还会喂的话,你是出于什么动机?或许,你根本没有打算给企鹅喂食,而只是在摆动手臂,但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的结果是撒了一地的花生。
根据笛卡尔所言,心灵,即笛卡尔认为的自我,在本质上是指一个有意识的实体,或者能思考全部有意识的经验感受的东西。心灵可以涵盖许多内容,比如心理素质、心理能力和心理倾向,以及思维、理智、欲望和情感,当然,情感或许也涉及身体方面。除此之外,笛卡尔似乎还认为,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充分利用自己的思维能力,而并不存在深层的无意识或潜意识。
心灵一定与身体或大脑不同,因为后者处于空间之中,具有形状、大小等物理属性。如果说物理实体,比如自行车、鹅卵石、海洋等只是人的思维或欲望的产物,这显然是荒谬的;但同样,如果说心灵长在下巴的上方,有100克重,这也是荒谬的。
人与外在世界的互动
感知能力:看见鸭子还是兔子
无论把这幅图看作鸭子还是兔子,它的线条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就是说,人们看到的内容并不仅仅取决于外界的信息。

图1-1
活动:喂养企鹅还是毒害企鹅
当把花生撒向企鹅的方向,是什么决定了我的行为?这个行为能被称作“喂养企鹅”吗?还是应该被称作“毒害企鹅”?又或者我只是在扔掉不想要的花生?严格地说,我只不过是摆动手臂,并且手指没有合拢而已。可见,人们行为的评价不仅取决于它对外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还取决于人们的意图、思虑、动机等。然而,这些心理状态是否像笛卡尔所说的那样,源自非物质性的心灵呢?

图1-2
因此,按照这个观点来看,心灵和身体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它们有着“真实的区别”,或者说,在现实之中可以将它们区分开来。
心灵不是可以在空间中存在的物体,鹅卵石也不是有意识的物体。按照笛卡尔的观点,鹅卵石没有意识并非偶然,因为所有的自然物体与心灵都是完全对立的。大脑也是一种自然物体,因此它也必然不同于心灵,不具有意识,即便它能够引发意识的产生。大脑与意识的关系就相当于“贝尔和廷克斯是同一个人”与“贝尔导致廷克斯产生了变化”的关系,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进一步说,笛卡尔认为心灵在本质上具有意识,这也就是说心灵不能脱离意识而独立存在。或许他相信,即便在熟睡或昏迷的时候,人们仍然具有意识,就像是在做梦,只不过人醒来后通常忘记了这些经验感受。
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是20世纪牛津大学的一位哲学家,他深受维特根斯坦影响,并提出了“范畴错误”(category mistake)的说法。他认为,笛卡尔在利用物理属性去理解心灵时就犯了范畴错误。他批评笛卡尔把心灵看作一个实体,抑或一个不具有任何物理属性的东西,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范畴错误。于是,赖尔戏谑地把笛卡尔眼中的心灵称作“机器中的幽灵”(ghost in the machine)。
按照赖尔的看法,心灵什么都不是。的确,我们常常把身体与心灵放在一起讨论,仿佛能够将二者区分开来。我们甚至更倾向于把心灵而非身体视作决定自身的关键因素,虽然只有拥有肉体才能拥有心灵。可见,语言的确能让我们产生误解。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语言能够蛊惑人心,而哲学是一场战斗,它反对将语言作为手段来使人们的理智入魔。
我们再以平均意义上的屠夫为例,说一下范畴错误的问题。假设屠夫平均每人养育了1.7个孩子,但每个真实屠夫养育孩子的数量显然不可能是1.7,要么他们的孩子的数量是整数,要么他们压根就没有生孩子。此时,平均意义上的屠夫具有的这个属性,即养育1.7个孩子,而真实屠夫并不具有,那我们能否因此就说平均意义上的屠夫是一种特殊的屠夫类型呢?这种结论显然是很荒谬的,因为与有血有肉的真实屠夫相比,平均意义上的屠夫不具有任何物质属性。或者说,平均意义上的屠夫不过是一种基于真实屠夫的“逻辑建构”(logical construction)。
同样,心灵具有一些属性,大脑和身体的确并不具备,那么,心灵是否可能也不过是一种逻辑建构呢,它是否只是人们用来描述身体和行为的另一种方式呢?这个问题,我们到第6章中再具体展开来讲。现在,继续正面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
在笛卡尔看来,心灵能够与身体联系起来不过是出于偶然,不过是出于上帝的恩赐。但如果心灵与身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实体能联结在一起的话,那么按照相同的理解方式,心灵和花朵也能联结在一起,心灵和计算机、沙发等都能联结在一起。当然,花朵、计算机和沙发都无法表现出它们与心灵相联之后的感觉和想法,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它们比较隐忍,不愿表现出自己的想法而已。
以上荒谬的假设都符合笛卡尔的思路,因此,若要接受笛卡尔的二元论,我们就不得不克服这些疑虑。但是,即便接受了笛卡尔所说的上帝的恩赐,即便不考虑这些荒谬的假设,笛卡尔的理论仍然存在问题。
现在,我们都是以科学的视角观察世界,看待所有自然物体,比如金属、果酱等。除此之外,神经学家已经能够告诉我们,当人们进行感知、想象或思考活动的时候,大脑中的哪块区域会被激活。这并不是说大脑发挥着和心灵同样的作用,而是说,正是因为有了大脑活动,才引发了人们的感知、想象和思考。到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太多讨论自然世界的知识,比如物理学、化学等,但我们仍然对心灵一无所知,即便去追问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师、临床治疗师等专家,他们也不能告诉我们任何相关的知识。
除此之外,即便我们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放在一边,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实体,即心灵与身体究竟是如何互动、如何沟通的呢?心灵这个不占据空间、没有形体的实体,究竟是如何引起大脑的电化学运动,并最终让人们竖起大拇指,抑或通过震动声带发出各种各样具有含义的声音的呢?
毫无疑问,心身互动问题给笛卡尔及其后续的哲学家带来了难题。牧师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深受笛卡尔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最终选择了以偶因论(Occasionalism)来对其进行解释。他认为,在你想抬起胳膊的时候,你的胳膊碰巧抬了起来,而这两者的协调一致则源于上帝的干预。因为既然上帝和心灵一样不占据物理空间,不会死亡,并且全知全能,那么他就可以让任何事情发生。
但是,这种理解又导致了新的道德难题:如果我想抬起手,并拿刀刺向恺撒,而只有上帝进行干预,刺杀动作才能完成,那么,上帝最起码也是刺杀恺撒的帮凶吧?不过,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框架之内,马勒伯朗士的观点或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荒谬。他只不过想要说明,心身互动问题的解决最终还要落脚于物理世界,而他个人则选择了一个神居住的物理世界。
如果两个物体能够互动,往往需要两者至少具有某些相同的属性才行,比如两者都要占据空间。虽然心灵和身体都具有时间属性,但在其他方面,这两者有太多本质性的差异。不过,我们也不能忘了,在物理世界中,地心引力和苹果也有很大的差异,但地心引力仍然可以成为苹果掉落到地上的原因;电流和轮子有很大的差异,但电流仍然可以成为轮子旋转的原因。趁此机会,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大卫·休谟(David Hume),他可是被博斯韦尔(Boswell)称为“伟大的异教徒”的一位思想家。
如他自己所述,休谟的第一本著作就像“在出版社死而复生”,不过如今,休谟已经在世界上拥有很高的声望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试图通过纯粹的理性推理,寻找世界的根基;与之不同,休谟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则试图根据对世界的经验感受,来寻求所有知识。那么,休谟是如何解决笛卡尔面对的难题的呢?
休谟的策略是,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经验感受这里。他认为,对于“一个事件是另一个事件的原因”,我们所有的经验感受不过是“先发生了一个事件,随后又发生了另一个事件”。比如,挤压牙膏管,牙膏冒了出来;按照休谟的分析,前者是后者的原因,不过是前者发生在先,后者发生在后。但不管怎么说,休谟的观点起码可以帮助我们开始质疑,原因与结果之间是否一定要有某些必要的相似性。
或许,心身互动问题不足以对笛卡尔的二元论构成根本性的威胁,但如何以二元论的视角来理解人们的行动,却依然是个难题。似乎人们的所有行动都涉及一定的心理事件;与之相反,身体变化,如肾功能的变化则不涉及任何心理事件,它并不受主体直接控制。二元论的观点是,我想吃早餐,于是我决定打开冰箱;做出这个决定是一个心理事件,是我的意志或意愿,它导致了相应的神经细胞运动,最终由我的身体肌肉带我走向冰箱。
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假如意志也被视为一个行动,那么按照这种逻辑,意志行动同样需要一个相关的心理事件;于是,我们只能再次诉诸决定这个意志行动的另一个意志行动,这就陷入了无穷倒退、没有尽头的困境。
或许你会质疑,为什么要认为人的每个行为背后都预设了一个在先的心理活动?反观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做早餐、躲雨、读书,它们都涉及意志行动吗?有多少行为涉及了意志行动?“嗯,”有人可能会答道,“意志行动通常都属于潜意识。”但这个答案可不是笛卡尔式的回答,因为根据上文可知,笛卡尔的理论体系里不能容忍潜意识。而且,如果无法解释清楚这些潜意识是如何产生的,这一回答就同样说服力不够。
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任意活动自己的脚趾,或者主动出门慢跑,甚至决定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等慢跑的念头慢慢消逝。因此,必然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心理活动,比如,“完全不受自己控制的腿抽筋”与“故意抖腿”背后的心理活动肯定就不尽相同。“故意”“决定”“意图”,这些都值得我们进行研究。但要注意,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陷入范畴错误。
假设某人的腿摔伤后打了石膏,现在拆了石膏,要重新学习走路。她尝试着挪动自己的腿,却不小心扭伤了。针对这个例子,有人就误以为“尝试”“不小心扭伤”等行为背后也存在着某种心理活动,认为无论何时,只要有行动的意图,这种心理活动就存在。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很好的理由作为支撑。
当我们故意地、有意地、有目的地做一件事情时,我们就要为这个行为负责,要给出如此行动的理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行动背后都有一个发生在先的心理活动。毋庸置疑,每个行动都会引起大脑里的神经活动,但我们绝对不能在“神经活动产生的感觉”和“神经活动”之间画上等号。下面,让我们再回过来看看笛卡尔的二元论。
近代的哲学家们
理性主义者
笛卡尔强调理性是获得知识的方式,我们拥有的理念是先验的。在大学的课程中,常把他称为“理性主义者”,与“经验主义者”形成对比。但实际上,这种区分是非常粗浅的,哲学家们并不能被轻易地分门别类。
斯宾诺莎 (1632—1677):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认为现实具有理性的必然性,幸福生活取决于理性。他认为上帝与自然同一,提倡容忍;也正因如此,他被逐出了犹太教的教会。后来,他一直以磨镜片为生,有人视他为上帝的忠实信徒,有人则视他为无神论者。
莱布尼茨 (1646—1716):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与斯宾诺莎不同,他曾参与外交事务,誉满世界。作为汉诺威皇家图书馆管理员,他在汉诺威市的黑水逗留了多年。他和牛顿分别独立发明了微积分,他热衷于实验,却认为世界由非物质性的单子组成。伏尔泰曾经嘲笑他竟然把这个世界视为“可能存在的最好的世界”。
经验主义者
与理性主义者不同,有些哲学家特别强调经验感受和经验观察。
弗兰西斯·培根 (1561—1626):持有经验主义的立场。他曾是英格兰的首席检察官,为了试验雪在肉类储存时起到的作用而受凉,最终因感染肺炎而去世。
约翰·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和 大卫·休谟 (1711—1776):在牛顿取得的科学成就的鼓舞下,这两位哲学家成了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洛克认为,自己的哲学研究根本无法与牛顿的相提并论;卓越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则是想在心理学方面模仿牛顿。
乔治·贝克莱 (1685—1753):他曾担任过克洛因教区的主教。他认为,现实世界由灵魂以及灵魂的“观念”构成。他的唯心主义(Idealism)观点可以被总结为“存在就是被感知”,值得一提的是,唯心主义的词源是观念(idea),而非理想的(ideal)。令人惊讶的是,贝克莱竟然赞成焦油水能够治愈很多疾病的观点。对此,心理分析师或许可以大显身手了。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综合
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可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比肩的伟大哲学家之一。通过阅读休谟的著作,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综合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理论。他还分析过笑话,但他的笑话和分析都说明他的幽默感实在是太差了。
虽然笛卡尔的二元论想要解释清楚,人类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但它还得面对一个至关重要的批评,矛盾的是,这个批评就来自笛卡尔本人。他说,考虑到我,即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我不仅住在我的身体里,就像一个舵手住在他的船上一样,我还和它非常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与其说这个观点属于二元论的立场,不如说它更强调了人类作为整体的统一性。我们总是能够不假思索地知道手指的位置(幻肢除外),知道我们想要喝水,知道我们的脚有没有被踩到。我们并不会刻意去了解这些,并不像舵手需要刻意了解自己的船。但要注意的是,“感觉到口渴”与“理性上知道自己处于脱水状态”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笛卡尔自己也认为,心灵与整个身体紧密关联在一起,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二元论立场。他解释说,心灵与身体的交互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地点,也就是大脑中的“松果腺”(pineal gland)。关于这一点,我们其实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而且即便他所言属实,这种解释也并没有起到任何帮助,心灵与身体的问题仍然是一个谜团。这种解释仍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独立的、不具有物质属性的心灵是究竟如何闯进了一个物质世界,但自然科学却可以把这个物质世界解释得十分清楚。
关于人的存在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了。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将转向自由意志的问题。对包括笛卡尔在内的许多哲学家而言,他们都想要相信:正是由于能够自由行动,人类才与众不同。那么,什么是自由的行动,什么是行动的自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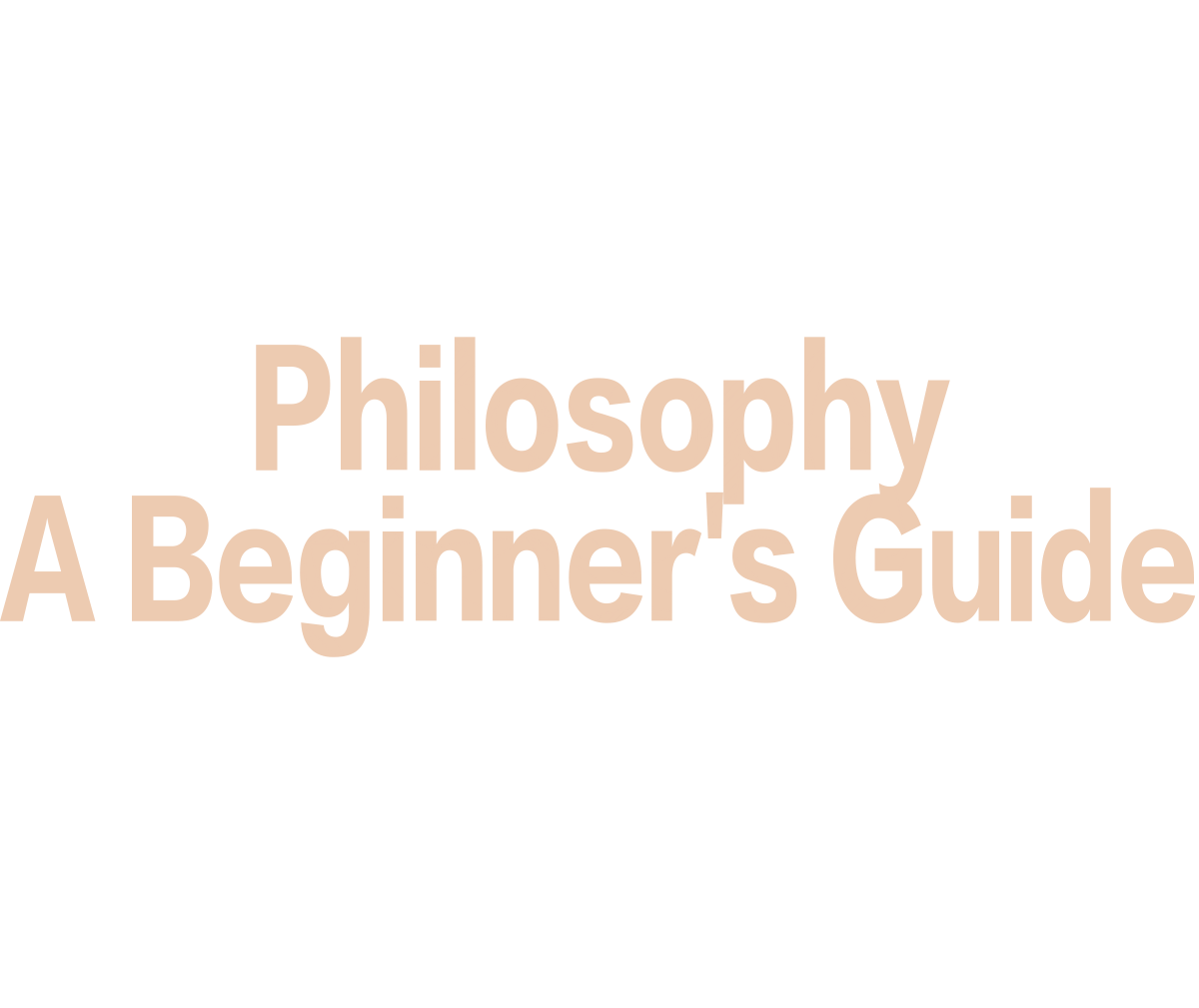
1. “他心知”问题: 即便可以相信他人的身体存在,虽然这也是可以怀疑的,但我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人的身体里还存在着心灵呢?
2. “我思故我在”: 即便可以怀疑外在世界的存在,但人也不能怀疑自己的存在。
3. “不可分辨者的同一性原则”: 假如两个看似不同的事物拥有所有相同的属性,那它们就是同一个事物。
4. “同一者的不可分辨性原则”: 如果两个事物是同一的,那它们就拥有无法分辨、完全相同的属性。
5. 二元论: 身体和心灵(自我)是相互独立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