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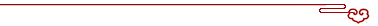
包拯对贪腐不仅有自己的认识和分析,更有严厉的反腐实践。宋代断案,在朝廷一级有大理寺、刑部、审刑院等机构的官员,地方主要有提点刑狱等官员,在州县,地方官全权负责行政、军政、司法。包拯长期担任地方州县官,还做过主管京城的开封府官,司法实践不会很少,但留下来的记载并不多,坊间流传的关于包公断案判狱的诸多故事,有很多文学加工、传说附会的因素。从现有可信的历史资料看,包拯反贪断案有以下特色。
在宋代官员反贪的上书中,包拯的上书最为典型,整部《包孝肃公奏议》,几乎都是揭露、举报、抨击贪官污吏,要求弹劾、惩治贪官的奏折。据统计,在这部奏议中,近一半是抨击贪赃枉法的,有55篇直言举报贪官污吏。其中,被指名道姓受检举弹劾的贪赃枉法官员有60余人,主要有王涣、闫士良、张可久、周景、胡可观、魏兼、范宗杰等。包拯反对这些贪官的主要办法就是不断地上书,不断地弹劾,历数其罪,要求朝廷严惩。比如,包拯曾先后7次上书弹劾王逵,6次上奏折怒责“国丈”张尧佐,被赞誉“举刺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鳞”。
包拯的上书反贪有一定的效果,出于各种原因,朝廷也能惩治一些贪官。但是,不是每次上书都能说服天庭,也不是每次指控都能服众。皇帝有自己的考量,他也必须庇护某些人,从正面看这是政治的多变性和灵活性所决定的;从负面看,政治实际上就是不同派系、力量的抗衡和博弈,为了自己的利益,最高层也难以时时刻刻做到一碗水端平,往往出现不同个案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同样的事由处理的结局却完全不同。所以,上书反贪、直达天庭的做法,在历朝历代基本上是悲剧多于喜剧,留下来的多是反贪者自己的悲愤抑郁,黎民百姓的唏嘘哀叹,文人骚客的呼号感怀……至于政治上的发展、制度上的改进,在封建时代仍然是原地踏步。
包拯认为,“励精治道”,在于“谨修人事”,“今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治乱之原,在求贤取士,得其人而已”。包拯认为反贪在于用人,必须用贤人,而不能用奸佞小人。
在选贤取士的同时,包拯还提出,必须推行监察和连坐法,以保证赏廉罚贪,廉者进用,贪夫黜退。包拯认为,只有实行严密的监察制,才能防范、制止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只有在用人上实施连坐法,才能防止贪赃枉法之徒进入官员队伍。因为治理天下,朝廷要倚重宰臣百官,“外则按察之官、刺史、县令而已”,这些人的职责非常重要,如能“辨狱讼之冤滥,财赋之出入”,或可防止贪官之胡作非为、贪赃枉法。但是,监察“事权至重,责任尤剧,设非其人,则一路受敝”。因此,他多次上书呼吁,“选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充职,不以资序深浅为限”。为了确保选用贤达之人,他还主张对州郡官吏的推荐实施连坐举主的办法,举荐有廉洁之誉的干敏之才者,予以奖赏,举荐庸才贪夫者应受到处罚。
传统儒家文化“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一直是人们追求政治清明、天下大治的思想来源。在这种思想逻辑中,官员道德水平的高低被看作是决定王朝统续的百年大计,选官用人就成为重中之重的大事,越是忠良之士就越是在用人选人上费尽心机,包拯的用人之道也是如此。当然,在包拯的时代,这种主张和措施对于澄清吏治,恐怕是最主要的手段。从用人的纯技术维度看,选官用人的重要性在今天也有它的积极意义。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德治文化必然导致人治政治,人是靠不住的,盼青天就是盼好人,就是人治思想的反映。正是在这种思想濡染下,包拯被人们一代一代企盼着、呼吁着;由于好人、青天在专制社会中是极为稀缺的资源,人们盼不到、呼不来,致使包拯和包拯现象似乎只能陷于梦想,延绵不断的民间包拯文化热就是明证。除去其对人事管理技术的重视外,选贤能的用人思想几乎就是乌托邦,所导致的政治劣势甚至是政治糟粕,在今天更有反思清除之必要。
首先,人治政治的性善论的人性假设就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得到证实或证伪的无头案,虽然性恶论在哲学上也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是,至少在性恶论的理论前提下,人们的基本利益欲望被平等地对待和正视。政治共同体的存在目的,就是平等地保护和对待每一个人,面对利益、思想之争,没有哪个特定人或组织更好或者更坏,所有人在性恶论的眼光中都是一样的。这样,就不会出现,至少不会长期出现把某个人(比如皇帝)的话当成法律的陋习,皇权也不可能毫无条件地凌驾于法律之上。
其次,贤人政治中的贤人标准是非常模糊的,这使选用贤能一是执行成本非常高,难以为继;二是被选出来的贤人“保质期”不稳定,贤人变贪官的故事不胜枚举;三是连坐法这样的问责制,虽然可以遏制荐举者的不负责任,但也能遏制荐举者的积极性,不推举将会是更多州郡官员的选择,造成呆政、懒政、庸政现象。任何政策都不仅是单方面的效应,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不考虑连锁效应的治贪政策必会得不偿失。
再次,被推崇的监察制的反腐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监察者以及监察机构本身并没有天生的防腐免疫力。凌驾于地方官员之上的监察者,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能暂时撇清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由于其还没有深陷腐败利益纠葛而获得更加中立、公正的超然地位,大力反腐。但是,这种作用只是暂时的、有限的,因为这仍然是建立在某些人具有“方正贤良”品质的假设之上的,一遇到现实环境与实际问题,这样的道德空想就会被打得粉碎,监察者与被监察者几乎没有不同,甚至更加腐败,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产生新的腐败。这也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贪腐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包拯廉洁的形象在民间流传甚广,其廉洁的故事也很多,本文只举一例,就是他42岁执政端州时,反对用当地的端砚贿赂官员的事例。
端州(今天的广东肇庆),出产著名的文房四宝之一——端砚。作为地方土特产,每年都要有端砚上贡给朝廷,当时叫土贡,即“任土作贡”,进献君主。在知端州任上,他了解到以前到端州做官的人,总是在每年端砚“贡额”之外,加征数十倍,用来贿赂其他达官贵人,作为升官的敲门砖。包拯上任后决心除掉这个弊端,就下令端砚只按“贡额”生产,不准额外出产。他本人也不接受任何馈送,包括端砚。由此革除了强加给砚工的额外负担,三年之后,包拯“一砚不持”地离任,这被传为包拯廉洁的佳话。《宋史·包拯传》记载:“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十分喜欢书法也喜欢砚台的包拯,在端砚产地任职,却不带走一方砚台,其廉洁亲民,可见一斑。
作为为官一任的个体,其高风亮节确实令人敬佩,其道德修为确实难能可贵,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这几层逻辑缺漏必须注意:一是只按“贡额”生产端砚的执行难度大,成本高,难以为继;二是不可能割除行贿受贿的官场之风,如果端砚被禁生产,只能使它变得更加稀缺,人们更是求之不得,就算是不送端砚,还有很多被认为是珍贵的东西可以用来行贿,腐败仍不可避免,没有一个官员或政府能够禁止生产所有的行贿品;三是对以此为业的百姓似乎也没有直接的帮助,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助益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