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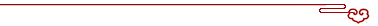
包拯生活在北宋仁宗年间,与宋太祖、宋太宗时期相比,仁宗在位的北宋王朝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像包拯这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有气节的士人和官员都忧心忡忡,竭力鼓之、呼之,试图遏制大宋王朝的颓势。可以说,包拯比较全面地痛斥了贪腐的各种病态现象。
包拯认为,“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擿发,无日无之”,“黩货暴政,十有六七”,特别是地方“州县长吏等,其间不才,贪猥之尤甚”。这表明,当时官吏的贪污腐败已经很普遍,无论大官还是小吏,无论京城显贵还是地方大员,几乎无一不贪。贪腐的形式也千奇百怪,包拯在奏议中就列举有贪污自肥、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违法经商、勒索“羡余”、馈送“苞苴”、监守自盗、恃强凌弱等,他们“旦方受署,夕已望迁,广纳苞苴,交结势要,市恩售进,唯恐不及,其财力丰耗,馈送欺隐,未尝校视,则建明利害,裁制出入,岂暇留心哉”?
作为当时的有识之士,包拯能痛陈贪腐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明白这种局势的人,也许并不在少数,但是,大声疾呼、敢于说出来的人,恐怕只有包拯这种耿直忠恕之人。他对儒家的忠恕文化虔信不移,这样的人,在任何时期、任何朝代,都是凤毛麟角,环境与文化只能让这种品行在有些人内心达到一般的嵌入程度,而达到像包拯这样的深度和高度,那基本上是可遇不可求了,其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上苍的恩赐。所以,把反贪腐的成效重点寄托于个人道德修为上,保障性较弱,成效性不可预期,风险性较大。
同时,我们也看到,包拯虽然对贪腐深恶痛绝,但是,他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除了泛道德主义的、民本主义的比如“贪者,民之贼也”的指责,是没有办法揭示腐败何以如此普遍、如此花样翻新的深层根源的。实际上,传统社会的专制所导致的对社会资源的专控垄断,是滋生腐败的主要根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也必然依赖专制。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被权力掌控,人们为了生存、生计、升迁……原本通过正常渠道和途径就可以实现的某种效用最大化,在专制体制下,只能通过对权力的行贿或赎买才能有机会得到,这样,腐败普遍化、多样化就成为必然。这是“包拯”们认识不到,而今天的我们在反腐过程中必须清醒认识与面对的问题。
首先,因为包拯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坚信民为邦本,所以,他对大大小小的官吏唯利是图、唯赃是求、枉法徇私致使百姓更加贫困的现象,忧心忡忡。他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贪于宠利者,惟务聚敛,掊克于下,前后刻暴,竟以相胜。前者增几十万遂用之,后者则又增几十万,以图优赏,日甚一日,何穷之有?而民力困且竭矣,所以疮痍天下,于今未息”。与此同时,包拯还尖锐地指出,贪官污吏“诛求于民,无纪极尔,输者已竭,取者未足,则大本安所固哉?臣以为,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官吏的贪污营私、损公肥私、侵占挪用、行贿受贿等行为,必然导致朝廷财政捉襟见肘,严重亏空。这样,贪腐就会下使百姓穷苦、上使朝廷空虚,大宋王朝的江山就会被葬送。
民本主义是传统社会最具有现代因子的政治思想之一。在维系政治统治的过程中,注重黎民百姓的感受或利益,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把统治者与百姓之间的舟水关系看作是王朝政治统续的重要变量,让统治者明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这些从一定程度上对统治者的专横、霸道起到了约束性作用,这也是子民百姓在传统社会无所不在的皇权迫压下,时刻盼望的清明政治。而这种相对清明的秩序似乎只有清官、青天大老爷才能够带给他们,除此之外,人们看不到任何出路与希望。所以,民本思想与青天诉求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包拯形象与文化之所以在中国民间历朝历代流布广泛、家喻户晓,各种传播形式大都关注并赞誉其清官形象、反贪政绩的主要原因。
但是,传统民本思想如果不经过宪政法治思想的改造,不把“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调整过来,不把保护公民的利益与反贪反腐建立在现代制度的法治治理之下,则其现代性因子将永远不会有新的生长点,就会仍然停留在传统民本思想的呼吁和倡导之中,就会使这种诉求要么因空洞无制度之凭、无实现手段而流于形式,要么无望地寄托于青天追求的泛道德主义的乌托邦幻想之中。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直存在着公私之争,在儒家正统思想看来,皇帝、皇权、国家、公共、天下为公……这其中有着万世一系、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关系,很多人直到今天还混乱、模糊在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认知误区中,理所当然地把它们等同起来。包拯对于贪官污吏的痛恨其实正是基于这种思想逻辑,其厉声批驳的“化公为私、损公肥私”之所谓公私关系,在今天也必须做进一步的现代性分析。否则,在当下的反腐浪潮中,经常被某些人高调倡导的所谓“公私”关系,依然会是“公=国-皇权”这种糊涂思想,并使人陷于认识误区难以自拔。
包拯说,当时幅员至广、官员至众,“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在这里,包拯深刻地揭示了贪腐对王朝法制的废弛和破坏的严重性,贪官执法不公,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而且自己肆意枉法贪赃,甚至以贿额钱财代法,败坏了整个吏治。所以,包拯大声疾呼,法律、诏令“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他规劝宋仁宗:“伏望陛下临决大政,信任正人。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虽近必黜,忠直者虽远必收。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
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中,纲纪、法度一直被看作是维护统治、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在这一点上,包拯比那些贪官、庸官的认识要高明得多,一个常态的社会,如果真能做到“法存划一、国有常格”,那也就意味着某种秩序的稳定性、可预期性,这也正是黎民百姓所期盼的“正大光明”。一个有常态秩序的社会比一个无政府状态的社会要好上千万倍,尽管有很多时候这种秩序本身并不完美,如公正性不强,正义性不够,尚需要反思改革。但是,仅从有无秩序这个角度讲,包拯的这一反腐思想在今天仍有其借鉴意义。
但是,到底什么是“法治”,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是不一样的,法制与法治是完全不同的。法治是多元民主的共同治理,强调公民的主动参与作用;而法制仅意味着按照某种规则治理,强调被规制对象的被动服从、顺从。法治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超越于法律之上;法制则认为法纪只是统治者手中的统治工具,法律不具有至上性,皇权就是法律的主要来源,权力者可以超越于法律之上,法律是用来管治老百姓的,而皇帝、皇权则永远高于法律。法制是一个简单的自上而下命令、规制的过程,法治则承认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公民,都应该有权利和机会参与社会规则的制定,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诉求与主张,只有在这种结构之中通过协商、谈判、博弈,形成的规则和法律,确立的权利框架,才真正是反映民意的,才是合法的,人们才会真心遵守法律。
虽然不能用这些现当代的法治思想苛求前人,但借助包拯的法制思想进行深刻的反思,则是当今反腐廉政建设、依法治腐的极为重要的一环,因为这种传统思想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现在还有不少人深陷于这种认识误区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