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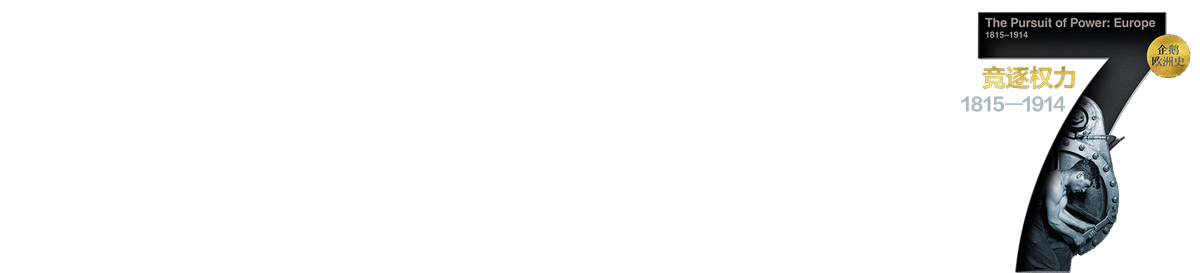
法国大革命改变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性质。这一点在法国看得最清楚。路易十八复位后,用以王室的鸢尾花徽为图案的国旗取代了三色旗,不承认拿破仑建立的荣誉勋位,同时正式宣布1814年是自己在位的第19年。这一切象征了他对旧制度的效忠。1814年,路易十八身边的一位近臣告诉他拿破仑退位的消息:“陛下,您现在是法国国王了。”路易十八回答:“什么时候我不是国王了?”旧制度下的种种宫廷礼仪、头衔和盛典浮华重现。路易十八拒绝接受拿破仑时期最后一届元老院废除皇帝后表决通过的宪法,因为他拒不承认王权源自国王与人民之间的契约。路易十八称,他的权力乃上天所授,载于复辟王朝下的法国宪法所依据的《圣图安宣言》中。他明确表示,他,路易,“蒙上帝恩典作为法国和纳瓦拉之君”,依照个人自由意志赐予法国人民各种权利。
路易十八对旧制度的合法性深信不疑。但他认识到,自己无法让历史倒退到1788年,尤其是在“百日王朝”造成的恐慌之后。路易十八同意不把大革命时期没收的土地退还给教会、贵族或王室。50万人已经购买了这些土地,有的买地后转手卖给他人。强迫这些人吐出自己购买的土地在政治上不现实。《拿破仑法典》继续适用。法国大革命废除了世袭贵族在军队和政府内任职的特权,实行“任人唯贤”政策。贵族这方面的特权没有恢复。宗教信仰自由依然有效,尽管政府把天主教定为国教。1790年把全国划分为行省、巴黎划分为区这一大革命时期的做法维持不变。国王路易十八把以上措施概括为自中世纪“胖子”路易(路易十八与他有很多相似之处)以来法国王室推行的一系列变革的一部分,宣布自己准备“重铸时间链条”。在威灵顿公爵的坚持下,路易十八任命拿破仑手下的两名重臣出任要职:塔列朗任外交大臣,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 1759—1820)任警察总监。夏多布里昂称之为“邪恶斜倚在罪行臂膊上”。路易十八还认识到,三级会议制度已无起死回生之可能。战胜法国的盟国对复辟的法国王室施加压力,警告它不要重蹈覆辙以至于引发大革命。为此有必要建立某种形式的立宪制。路易十八于是成立了一个两院制立法机构,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一切赋税的征收都必须得到议会同意,但路易十八继续握有立法动议权。
由于路易十八随时可以解散众议院,举行新的选举,不受每年改选1/5议员规定的限制,因此新的立宪政体被削弱了。只有国王一人有宣战权。国王任命大臣,大臣对国王而不是对议会负责。尤其重要的是,国王有权“为了国家安全发布敕令”,这实际上赋予了他废除宪法的权力。因此,路易十八统治下的法国其实不是什么立宪君主制,而是绝对君主制。任何时候,他都可以把限制他的宪法一脚踢开。不仅如此,贵族院的议员还由国王指定,众议院则由40岁以上、每年交纳赋税不少于300法郎的男子选举产生。因此,选民人数很有限。法国总人口2 800万,仅有9万名选民。而人口不及法国一半的英国,早在1832年的《改革法案》前,选民人数就已达到44万,《改革法案》通过后,选民又增加了21.6万人。选举法国新议会的选民资格受到严格限制,结果人们选出了一个由极端保王党人组成的议院。他们赶走了塔列朗,大肆迫害前革命党人和拿破仑分子。新产生的贵族院俨然以法院自居,处死了一些革命党人和波拿巴分子。还有些人被迫流亡海外,包括富歇和塔列朗。
埃利·德卡兹(Élie Decazes, 1780—1860)曾是拿破仑及其家族的助手。路易十八手下以德卡兹为首的大臣深知,鉴于对手不肯让步,若要保住君主制,新政权就必须扩大社会基础。卷土重来的贵族阶级一手操纵政治和政府机构,商人、律师和其他阶层的成员愤怒至极,开始转向1789年大革命早期阶段提出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了实现“王权国家化和法国王权化”,德卡兹说服路易十八解散了众议院,选举产生了一个新议院。新当选的议员大多是大地主和政府高官,很多人曾为拿破仑效过力。德卡兹没能走多远。1820年2月13日,路易十八的弟弟阿图瓦伯爵(Comte d’Artois, 1757—1836)的小儿子贝里公爵(Duc de Berry, 1778—1820)、王位的第三顺位继承人(因为路易十八没有子嗣)离开巴黎歌剧院时,被一个心怀不满的马具工人刺死。德卡兹绝望地说:“我们全被暗杀了!”
暗杀事件发生后,德卡兹被罢黜。他的前任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 1766—1822)官复原职。黎塞留是保守派分子,1815年前长年流亡海外,在沙皇手下供职。没过多久,黎塞留也遭罢免,换上了王室中意的极端保守分子维莱尔伯爵(Comte de Villèle, 1773—1854)。维莱尔试图完全恢复大革命前的君主制。1824年9月16日,路易十八死于肥胖症,阿图瓦伯爵继承了王位,成为查理十世(1757—1836)。阿图瓦当时已年近七旬,完全是旧制度的产物,思想顽固不化。这位新国王与极端保王党人结为同盟,连他的哥哥都对他的做法惊愕不已。查理十世授意维莱尔制定了关于渎圣罪法律条文,规定冒犯教会违法:亵渎圣杯者判无期徒刑,亵渎圣体则是死罪。此后他又颁布法律,向大革命时期丧失了土地的贵族提供经济赔偿。查理十世举行了场面宏大的传统加冕仪式,以此象征自己的强硬立场。他还强化了新闻检查制度,扩大教会权力。1824年,教会被授予指定所有小学老师的权力。
以上种种复辟举动延续了以维莱尔伯爵为首的极端保王党人以及他前任黎塞留推行的政策,仿佛是故意想激起自由派人士的反抗。自由派人士通过报章杂志和政治宣传活动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有两份报纸是作家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 1767—1830)在1817年到1818年间创办的。因为自由派人士发声,所以贡斯当在1819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此前一年,投身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 1757—1834)也入选众议院。雅克·拉菲特(Jacques Laffitte, 1767—1844)和卡西米尔·佩里耶(Casimir Perier, 1777—1832)等银行家被复辟后的贵族排斥,无法获得社会和政治权力,他们深感不满,也资助了自由派人士。1817年,时任法兰西银行行长的拉菲特因捍卫新闻自由而被解职。一些年轻记者和历史学家围绕大革命的遗产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就有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 1797—1877)。1823—1827年,梯也尔撰写的多卷本《法国大革命史》出版发行。他在书中为君主立宪制辩护,称该体制是人类渴望自由的必然结果,但“形形色色的过火行为”把大革命带入了歧途。25岁出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 1787—1874)同样认为,大革命的精髓是早期的宪政改良主义,而不是后来的大恐怖。他一度被政府禁止授课,在此期间(1822—1828),他在报纸上谨慎表达了自己的自由主义观点。此后几十年里,这两个人将在法国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
在反对派中,除了有一定身份的温和自由人士,还有形形色色的秘密社团组织。这些组织有的伪装成饮酒俱乐部(成员在那里唱政治歌曲),有的以做生意掩护,有的打着共济会分会的旗号,有的取了含义明确的名字,比如“自由骑士社”。这些秘密社团遍布欧洲各地,与拉丁美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某种超越政治界限的激进自由国际。为追求自己理想而四处游走的政治流亡者进一步推动了结社团体的发展。最激进、最活跃的是受意大利烧炭党启发、名为“烧炭党”的秘密小团体。该团体聚集了失业的拿破仑政府文官、失意的大学生以及靠一半薪酬勉强度日的帝国军队的军官和军士。后期的拿破仑宣扬自己是宪政自由的捍卫者,这一形象使共和党人和拿破仑分子团结在一起。密谋者试图煽动军营里的军人起义,挑起了1820年的巴黎起义、1821年的贝尔福和索米尔起义,以及1822年的斯特拉斯堡和拉罗谢尔起义,以上起义均以失败告终。拉罗谢尔起义失败后,四名下级军官被公开处决。当时还在上学的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 1805—1881)目睹了这次行刑。时人普遍认为,这些军人是“为自由事业献身的烈士”。在他们的感召下,布朗基投身革命运动。这段时期内,一共有12名秘密社团成员被处死。烧炭党人屡屡失败,内部产生了分裂,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时,该团体已名存实亡。布朗基本人于1827年在一次街头斗殴中受伤,暂停了活动。因此,19世纪20年代末,在法国掌权的极端保王党人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武装暴动,而是自由主义色彩的议会体制。在1827年举行的选举中,当选为众议员的自由派人士增加,维莱尔伯爵被迫辞职。他的继任者马蒂尼亚克子爵(Vicomte de Martignac, 1778—1832)试图与自由派议员谈判,结果也被解职。接替他的是朱尔·德·波利尼亚克(Jules de Polignac, 1780—1847)。波利尼亚克曾被拿破仑监禁12年,是国王绝对君主制信念的铁杆支持者。面对王室的顽固抵制,法国国内的革命和改良似乎毫无进展。19世纪20年代行将结束时,改良的前景显得遥不可及。
后拿破仑时代的德意志政治形势与法国很相似。德意志邦联的大多数邦国没有全面复辟旧制度。1815—1819年,一大批德意志南部邦国颁布了宪法,建立了代议制议会,意在给自己披上合法外衣,以便对和平协议确立的边界做出有利于自己、不利于竞争对手的修改。此类争端使德意志南部诸邦国无法有效联合起来对抗奥地利和普鲁士对邦联的控制。因此,梅特涅只要征得普鲁士政府的同意,就可以让邦联议会(成员国代表开会之地)批准他想采取的大部分措施。普鲁士的主要改革者陷入纷争,较保守的大臣掌握了权力,他们说服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 1770—1840)背弃自己颁布宪法的诺言。这样一来,梅特涅实现目标就更容易了。
志愿参加反拿破仑战争的人从战场返回家乡后,看到德意志邦联被一些君主玩弄于股掌之中,不禁大失所望。他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不只是为了把普鲁士、黑森或萨克森从法国统治下解放出来,也是为了解放全德意志,更有人认为,首先是为了解放全德意志。少数人认为,德意志邦联或许可以为更强大的国家体制奠定基础,1810年创立柏林大学的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就是其中之一,但其他人——尤其是1815年在耶拿发起了“学生协会”(Burschenschaft)运动的青年学生——却认为,只有彻底扫除德意志邦联中的专制邦国,用单一的国家体制取而代之,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团结。这些人深受作家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 1769—1860)的影响。阿恩特出生于瑞典属波美拉尼亚,先后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和耶拿攻读神学。1806年,拿破仑占领了他的家乡,阿恩特被迫流亡。流亡期间,阿恩特产生了基于语言的强烈德意志民族意识。他是一位杰出的政论家,在1814年号召用立宪君主制统一德意志,首都设在柏林(他认为维也纳的民族成分太杂)。阿恩特强调德意志人是一个整体,希望通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礼仪和象征符号,甚至共同的服饰风格来表达这一点。1812—1813年动员爱国者志愿投身反拿破仑战争的活动已经指明了方向。
阿恩特提出的观点激励了学生协会的学生。他们身穿昔日志愿军穿过的黑、红、金三色服装。1817年10月,学生在瓦尔特堡集会,纪念马丁·路德宗教改革300周年,倾听讴歌德意志民族特征的激昂慷慨的演说。当年路德就是在这座城堡里把《圣经》译成德语的。这次活动因焚烧了数十本书和杂志而臭名远扬,被烧的包括《拿破仑法典》、拿破仑时期宣扬与法国人合作的德语传单,还有抨击学生行为和目标的小册子。这些穷学生烧不起真书,改为把带有标签的废纸团投入火堆。年轻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痛斥这次活动,称它是中世纪愚昧的象征。不过他的那句名言“这不过是序幕:焚书的地方,最终也会焚人”,指的是1499年征服格拉纳达时西班牙宗教法庭焚烧《古兰经》,而不是指瓦尔特堡的那次焚书。
在瓦尔特堡被付之一炬的书中,有著名多产剧作家兼记者奥古斯特·冯·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 1761—1819)撰写的《德意志帝国史》。他在自办的杂志上大肆嘲讽学生协会成员的观点和举动,结果触怒了这些学生。此前科策布曾流亡俄国,加入了俄国外交部。拿破仑倒台后,他以俄国外交官的身份返回德意志,向沙皇呈送关于德意志情况的报告。有人认为他是间谍,但其实他根本不具备当间谍的条件。不过科策布确实支持亚历山大一世的保守理念。学生协会中的激进派成员卡尔·桑德(Karl Sand, 1795—1820)是个当时只有23岁的神学生,对科策布讥讽学生协会愤恨不已,认为他死有余辜。1819年3月23日,桑德登门拜访这位剧作家,用刀猛刺科策布,跑到街上高呼“德意志祖国万岁!”后拔刀刺入自己的胸膛。桑德活了下来,被送上法庭,翌年被当众砍头。很多评论员,甚至包括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者,都认为他所做的为人所不齿,但也有人把他视为英雄和烈士。行刑的刽子手内心同情民族主义者的理想,行刑后拆除了血迹斑斑的断头台,用拆下的木板在附近的葡萄园里建了一间秘密避暑小屋,用作学生协会成员的聚会场所。
同一时期,学生协会成员、药剂师卡尔·勒宁(Karl Löning, 1791—1819)暗杀拿骚一位政府官员卡尔·冯·伊贝尔(Karl von Ibell, 1780—1834)未遂。梅特涅以这两次暗杀为借口,不失时机地实施了一系列严厉镇压措施。1819年8月,来自10个德意志邦国的代表在度假城卡尔斯巴德制定了这些措施,措施于次月在位于法兰克福的德意志议会上获得通过。新措施规定各邦国有义务严密监视大学,开除宣传“敌视公共秩序或颠覆现政府机构”之有害学说的任何老师,确保他们不被其他高等学府再次聘用。大学一律不得录取参加学生协会等秘密社团的学生,政府机构也不得雇用这些人。一切刊物出版前都必须接受中央政府机构的审查。一个特别委员会也建立起来,专门负责调查和打击革命运动。此后学生协会四分五裂,成员最多时也不过500人左右。有组织的民族主义活动基本绝迹。各邦国的警察机构相互交换关于所谓颠覆分子的情报,严密监视俱乐部、咖啡馆及其他聚会场所。一切自愿性质的结社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廉价的传单和大幅广告受到严格审查,甚至被封杀。民间百姓很难彼此交流看法或了解政治时事。少数赞成宪政改革和民族团结的人仿效西班牙改革者的说法,称自己是“自由分子”。但他们无法就任何共同纲领达成一致。
德意志反动势力的得势体现在德意志邦联的宪法中。1820年7月,邦联对宪法做了修改,规定邦联内任何一个成员国为了维护秩序都可以干涉另一成员国的内部事务。原宪法中有关解放犹太人和实行宗教宽容的内容被删除。德意志邦联各成员国政府均采取措施,确保凡有议会的地方,议会都不会成为自由派抗议的工具。各邦国政府都禁止公开议会辩论的内容,迫使议员坐在事先分配好的席位上,免得他们结党。各地的选举都是间接的。新闻报刊检查制度严格限制竞选活动,因此几乎不可能举行公开辩论。一如法国,实际上一如19世纪20年代期间举行选举的任何一地,精心拟定的财产资格条款确保了只有富人才能当选议员。结果就是百姓对选举普遍漠不关心,即使有权投票的人也是如此。举例来说,1816年,只有5%的选民(本来选民人数就很少)在柯尼希山地方选举中投了票。在有些地区,代议制议会由昔日的社会等级组成,只有贵族能够参与。1823年普鲁士设立这类机构的目的是向政府提供咨询,而不是参与辩论,开会地点往往选在某处王宫内的一个房间。不过一个基本事实是,19世纪20年代,大多数德意志邦国确实有了代议制机构,尽管这类机构的权力极为有限,也受到种种限制。“开明专制”的观念已亡于法国大革命,无法复活。政府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德意志各邦国的治理靠的是官僚机构,而不是专制手段。人们普遍认为,一个遵照规则的行政体系可以比代议制议会更有效地限制君主独断专行。再说官员和议员通常是同一批人。正如青年时代的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在1838年所说(他早年的文官经历并不愉快),“一个人若想从政,就必须是领取薪俸、依附于国家的仆人,他必须完全成为官僚阶层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