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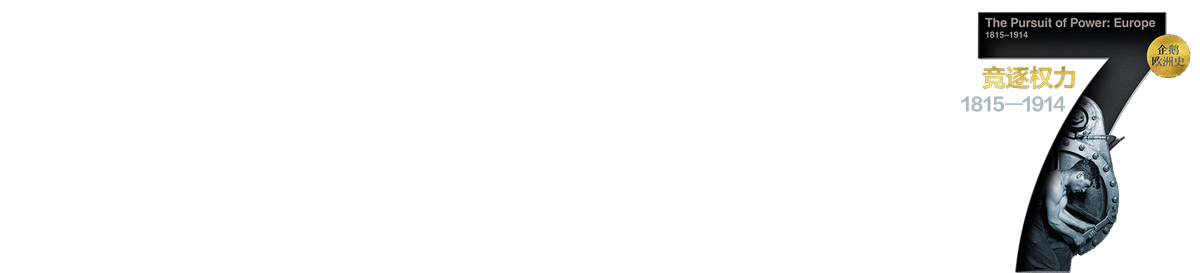
还没等得胜的欧洲诸大国给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这段历史画上句号,被流放到地中海厄尔巴岛的拿破仑就突然返回法国。此前,被处决的路易十六(1754—1793)的弟弟路易十八(1755—1824)在复辟王朝后马上陷入了困境,无力支付战争赔款。复辟的王朝保留了拿破仑时期不得人心的赋税,削减军费开支,还不顾之前几十年的激辩,恢复了新闻检查制度。好战的天主教被立为国教,疏远了大批法国知识分子。法国人普遍担心,国王会收回革命时期没收的土地,将其归还给教士和贵族。拿破仑重返法国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响,民众纷纷支持维护大革命的遗产。法国中部地区的一位地方官员报告说:“乡村农民对拿破仑的返回兴高采烈。每天傍晚,他们都在地势高的地方燃起篝火。各地村社的村民欢呼雀跃。”他得出的结论是:“普遍认为,假如不是皇帝返回,让贵族们摆正自己的位置的话,他们统统会被农民杀死。”
人民感情的迸发,加上巴黎工人的支持,疏远了很多资产阶级显达人士。教士阶层尤其仇视前皇帝。在通常同情保王党人的旺代、南部—比利牛斯区和布列塔尼等地,支持拿破仑的人也不多。只有他从前的部下依然积极拥戴他,这些人因被迫大批复员而气愤不已,对复辟王朝时期的经济措施也十分不满。拿破仑说:“只有人民和军队里上尉以下的官兵拥护我。其他人对我怕得要死。但这些人靠不住。”拿破仑重返法国,暴露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变革给法国社会造成的深刻裂痕。1815年3月1日,拿破仑在法国登陆,几周之内,他就召集了一支10万人的军队,因为大多数当年由他任命的法国各省官吏都一如往日征募士兵,法军老兵也聚集在帝国军旗下。盟国中断和平谈判,迅速行动起来。它们担心,如果拿破仑继续掌权,这位前皇帝很快就会再次走上征服和追求荣耀的老路。盟国也仅用了几周时间,就组建了一支由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 1769—1852)指挥的大军,军队由11.2万名英国、荷兰和德意志的士兵组成。1815年6月15日,这支军队在滑铁卢村阻击拿破仑军队。下午4点,老将冯·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 1742—1819)带着11.6万名普鲁士士兵赶到战场投入战斗。拿破仑误以为布吕歇尔将军在两天前的利尼战役中阵亡了。但布吕歇尔解救了英国人,之后两军合兵一处向法军发动进攻,最终打垮了法军。拿破仑再次被放逐。这一次他被流放到了大西洋上遥远的圣赫勒拿岛。1821年5月5日,拿破仑在该岛去世。
拿破仑留下的政治遗产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政治家、军官和学生中间很快演变成一个强大的神话。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前的“百日王朝”期间为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或真心或假意地)转向了自由主义思想,他们因此备受鼓舞。拿破仑深知自己地位虚弱,因此一方面努力让世界相信,他的征服梦已经结束了,另一方面又向法国人民保证,他将尊重公民的种种权利和自由,不会再像帝王那样独断专行。被流放期间,拿破仑在著述中继续表达这种观点,直到他去世。此后几十年,有关“开明皇帝”的传奇有增无减。作家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评论说:“在拿破仑还活着的时候,世界侥幸逃脱了他的控制;但拿破仑在死后占有了世界。”在法国,“波拿巴主义”象征着爱国主义、男子普选权、国家主权、平等对待所有公民的高效中央集权官僚机构,还代表政府会通过普选和公民投票定期与人民协商,法国人民与国家之间有默认的契约,而国家提供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此外,“波拿巴主义”也是民族自豪感和军事荣耀的象征。波拿巴主义与共和主义其实有相通之处,但波拿巴主义更强调强有力的领袖和军事实力。和共和主义思想一样,波拿巴主义在法国大批民众中有很深的根基。
1815年拿破仑最终战败后,他麾下的官兵解甲归田,回归战前的和平生活。此后几十年里,他们继续传播自己的观点。政治上对他们影响最深的是1799年拿破仑发动的雾月十八日(11月9日)政变。这场政变推翻了革命督政府,拿破仑作为第一执政执掌政权,并于1804年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19世纪20年代,欧洲各地有很多思想激进的军官认为,政变是摧毁王朝复辟时期各国专制政权、对政治制度进行开明改革的最有效捷径。同一时期,拿破仑的形象大受推崇,出现在数不胜数的民间故事里和廉价宣传小册子上,在民歌中得到传唱,表现在绘画和雕塑作品里,在昔日帝国硬币、香烟盒、小装饰物、围巾、帽子甚至儿童糖果上都能见到,有做成前皇帝模样的巧克力和甜食,还有糖纸上印有拿破仑时代各种徽记的便宜糖果。男人蓄起夸张的胡须,借此表达对拿破仑大军中蓄须的老近卫军的敬仰。人们在纽扣孔里别上紫罗兰花或红色康乃馨,以此对抗复辟的法国王朝严禁使用昔日帝国颜色的法令。法国以外的多地人民也认为,对拿破仑的崇拜是大革命成果的象征,具体体现为18世纪90年代初恐怖时期后推行的目标明确的改革。爱尔兰共和党人和波兰民族主义者开展政治斗争时,均以拿破仑为榜样。把南美大片地区从西班牙人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委内瑞拉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 1783—1830)对拿破仑钦佩至极,甚至跑到米兰去观看自己心目中英雄被加冕为意大利国王的仪式。在中国和马达加斯加,也有人把拿破仑奉为神明。
在法国本土,法国人回首往事,甚至觉得滑铁卢战役也不失为胜利,因其表现了面对绝境的勇气和献身“伟大国家”的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据说,皮埃尔·康布罗纳(Pierre Cambronne, 1770—1842)将军在滑铁卢说过一句话:“老近卫军的人只会阵亡,永远不会投降。”这句话很可能是后人杜撰出来的,而且康布罗纳最终也投降了,但这并不重要。他的不屈精神激励了后代人。司汤达[马里—亨利·贝勒(Marie-Henri Beyle, 1783—1842)的笔名]小说《帕尔马修道院》(1839)的主人公法布里斯纯粹出于理想主义而投身于拿破仑的事业。他的另一部小说《红与黑》(1830)把拿破仑后的法国描绘成一个虚伪、势利、不求上进的社会。另一位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在小说《悲惨世界》(1862)中用了40多页篇幅重述滑铁卢战役始末,并在多处推测这场战役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结局。拿破仑的作战计划“令人叫绝”。法军失利,是因为当时下雨(“下了几滴雨”),法军炮兵没能及时做好先期部署,地形不利,法军运气欠佳,威灵顿墨守成规的战术占了上风(“威灵顿是个战争匠人,拿破仑是战争中的米开朗琪罗……天才败给了经验法则……滑铁卢之战是一流的战役,获胜的却是二流的将军”)。如果拿破仑得胜的话,结果会极为不同。“滑铁卢不仅是一次战役,而且是世界走向的一次改变。”
真实情况是,拿破仑最终失败从来不存在任何悬念。即使布吕歇尔率领的普鲁士援军赶到之前威灵顿一度有可能被逐出战场,以盟国军队数量上的压倒优势,拿破仑最终也难逃一败。当时,一支庞大的奥地利军队已在滑铁卢以南的莱茵河东岸安营扎寨,另一支强大的俄国军队正向西欧挺进,滑铁卢战役打响时,俄军已经到了德意志境内。拿破仑连对付其中一支军队的兵力都没有,更不要说同时对付奥俄两支大军了。然而,拿破仑重返法国如同幽灵徘徊,令各国胆战心惊,担心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动荡会重演。因此,英、奥、普、俄以及众多欧洲小国的君主决定联合起来,干预另一个自主国家的事务。18世纪90年代初时也有过一次类似干涉,但当时至少有一个借口:法国的革命者威胁要处决国王和他的妻子——奥地利皇帝的妹妹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放言要把民主理念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1815年干涉行动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完全是预防性的,也为此后多年里类似的干涉行动敞开了大门。在那之后,一旦几个欧洲大国感到革命威胁迫在眉睫,就愿意联手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
把革命的精灵塞回历史的瓶子并不容易,因为自18世纪90年代以来,拿破仑以及在他之前的法国统治者发动的战争造成了许多破坏,而且不仅仅是生命财产方面的损失。拿破仑几次变更欧洲版图,兼并了北起汉莎同盟诸城市、经低地国家南抵意大利西北部的大片领土。他创立的法兰西帝国在巅峰时期面积达75万平方千米,人口达4 400万。拿破仑还在帝国四周建立了一圈卫星国,包括华沙大公国、意大利王国和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这些地方通常交给他的亲戚统治。1806年,起源于公元800年的查理大帝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土崩瓦解。1815年时,以上地区的归属大多又恢复了原状。但拿破仑让世人看到,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除了边界的变更,还发生了其他变革。教会势力被削弱,大片土地不再归教会所有,教会国家从地图上消失了。出生和婚丧登记改由世俗机构办理。修道院被解散。很多地区实现了宗教自由,结婚和离婚不再需要通过教会,世俗教育兴起,教士也由国家任命,这些都进一步削弱了教会势力。教会迫于压力,开始允许信仰自由,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非基督徒尤其是犹太人的平等权利。
在他统治的所有地方,拿破仑都用理性和整齐划一取代了僵硬的习俗和特权。拿破仑的大军在欧洲大陆驰骋的同时,他的文官悄然无声紧随其后,打破旧体制,组建新机构,统一标准。在法国兼并的地区和建立了卫星国的边陲地带,尤其是德意志西部、意大利北部和低地国家,出现了新一代职业行政官员,他们在拿破仑永无休止地南征北战之时,管理自己所在地区的地方事务。曾经,主宰地区和地方事务的是神圣罗马帝国那成百上千的帝国骑士,还有教会和领主法庭;如今,司法机构掌管的一套自上而下的统一体制取而代之。在以上各地,《拿破仑法典》取代了泥古不化的既有法律法规,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观念,尽管受拿破仑在妇女权利和义务等问题上的保守观点影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这一核心理念在某些方面被修改了。凡是实行《拿破仑法典》的地方,财产权一律受到保护,而此前,财产权在很多地区是得不到保障的。《拿破仑法典》体现了法国大革命的许多重要思想,包括个人自由,以及拿破仑本人在遗嘱中提出的机会均等、“任人唯贤”和“理性至上”。度量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标准化,境内关税取消,行会等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被废除,各地(包括波兰)还解放了农奴。拿破仑带来的变革遍及各地。1815年他动身前往最后的流放地圣赫勒拿岛时,以上很多变革显然已无法逆转。
拿破仑的遗产还有更深远的意义。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就波及范围而言,不仅是欧洲战争,也是全球性的战争。战争打碎了现有的一些全球帝国,为欧洲建立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新型关系铺平了道路。英国在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已被美国独立战争摧毁,但英国人也把法国残余势力赶出了加拿大,征服了印度,夺取了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吞并了毛里求斯、好望角、新加坡和锡兰。在法国革命的激励和英国的支持下,拉丁美洲各地的共和运动风起云涌,其领袖人物是西蒙·玻利瓦尔。他从混血和美洲原住民中招兵买马,组建了几支非正规军,打败了保王党人,在原西班牙省份建立了一批独立国家,包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拉丁美洲南部的独立运动也产生了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等几个独立或自治国家。1811—1824年,西班牙帝国在美洲地区的统治被摧毁了。西班牙因半岛战争(1807年到1814年)而元气大伤,无力集结足够的兵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在1811—1819年间,西班牙向美洲一共派遣了4.2万名士兵,但1820年年末时只剩下了2.3万人。其他人或死于疾病,或当了逃兵。西班牙本国舰队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覆亡,无力封锁起义者的港口,也无法打败英国激进的前海军军官托马斯·科克伦(Thomas Cochrane, 1775—1860)指挥的起义者舰队。强大的海军力量对南美洲的独立运动至关重要,而打破力量平衡的正是英国的海上力量。
英国政府一面假装中立,一面对科克伦这样的人听之任之,放手让他们从英国运送给养。打开拉丁美洲自由贸易的大门十分符合英国的利益。1823年,英国承认了新独立的几个国家。美国政府提出的反对欧洲国家对美洲地区进行任何干预的“门罗主义”遏制了英国进一步举动。1826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 1770—1827)阐述了英国多年来支持玻利瓦尔的理由:“我意已决。如果西班牙归属法国的话,也必须是一个不拥有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我催生新大陆是为了恢复旧大陆的均势。”当时巴西已脱离葡萄牙独立,这是拿破仑战争的又一结果。1807年法国征服葡萄牙后,“疯女王”玛丽亚(Maria the Mad, 1734—1816)的摄政王若昂(Dom João, 1767—1826)乘船去里约热内卢设立宫廷,宣布巴西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自主国家,享有一切相应的权益和特权。葡萄牙一下子沦为巴西的一个省,1816年玛丽亚去世后,若昂继位成为葡萄牙国王,但决定继续留在里约热内卢,这更体现了葡萄牙的降格地位。1820年,迫于葡萄牙国内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葡王若昂返回里斯本,被迫同意恢复限制与巴西贸易的重商主义政策。若昂留在里约摄政的儿子佩德罗(Dom Pedro, 1798—1834)迫于巴西商人的压力,于1822年称王,巴西成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葡萄牙出兵干预,但被海军将领科克伦的舰队打败。1825年,英国承认了巴西主权。
因此,欧洲国家在美洲帝国的覆亡与欧洲大陆的风云变幻密不可分:法国大革命孕育产生了种种新观念;英国凭借强大海军实力,打开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南美洲的大门,使其对自由贸易开放;美洲与欧洲殖民宗主国之间的联系因战争而断绝;在日益繁荣自治的北美殖民地,欧洲国家强行推行更严厉、更多的经济和税收措施。与此同时,美洲大陆的局势发展也对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欧洲的自由派人士、激进分子和革命者把拉丁美洲(不包括巴西,奴隶制在该国几乎原封不动又实行了几十年)视为解放运动的成功典范。玻利瓦尔的一系列解放战争展示了一种新型英雄主义。富有魅力的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后来又进一步发扬了这种英雄主义精神。他将从乌拉圭和巴西流放地返回祖国,领导统一意大利的人民斗争。
美洲殖民地的西班牙自由主义者与欧洲自由主义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拉丁美洲的革命者在欧洲积极宣传自己的事业,与形形色色的欧洲思想家保持书信往来。例如,危地马拉独立之父何塞·塞西略·德尔·巴列(Jose Cecilio del Valle, 1780—1834)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和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书信往来不断。洪堡本人也曾游历南美洲和中美洲的很多地方。与此同时,像朱塞佩·佩基奥(Giuseppe Pecchio, 1785—1835)这样的意大利流亡者也为德尔·巴列等拉美自由派人士出谋划策。1821年起义失败后,佩基奥被迫离开意大利流亡英国。一批意大利流亡者,包括克劳迪奥·利纳蒂(Claudio Linati, 1790—1832)在内,则积极参与了墨西哥革命运动时约克派(Yorkinos)与苏格兰派(Escoceses)之间的政治斗争——这两个派别得名于各自分属的共济会地方分会。拉美榜样对欧洲南部的影响尤其大。南欧与拉美的语言隔阂比较小,不像德意志、波兰和俄国。复辟王朝时期,为躲避反动政权流亡海外的自由派人士和革命者组建了某种形式的激进国际,其影响力遍及大西洋两岸。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发生的事情改变了全球各地区之间的力量对比。这并不是说,欧洲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在竞争力、宗教信仰和文化上逐渐胜过世界其他地区,然后出现了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17—18世纪期间,幅员辽阔的前工业化帝国并不鲜见,中国的疆土之大更是令欧洲诸帝国相形见绌。奥斯曼帝国1683年围困维也纳失败,其疆域在1700年前后达到巅峰,之后就不再大肆扩张,但奥斯曼帝国仍然幅员辽阔,起自东南欧,横贯西北非,直抵印度洋和中东。直到18世纪50年代,印度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一些伊斯兰国家的统治之下。奥约和贝宁等非洲大国控制了大片土地和大量人口。但是,拿破仑入侵埃及,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拿破仑占领开罗的教育中心爱资哈尔清真寺后,奥斯曼帝国对穆斯林世界的领导权也动摇了。一系列原教旨运动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新挑战。英国人逮捕了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皇帝,闯入了爪哇的王宫。1793年,马噶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率团出使中国,开启了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一段漫长艰难的交往史。1799年乾隆皇帝死后,清廷内部爆发了派系之争,全国各地反对腐朽清朝的起义此起彼伏,直接打击了清王朝的合法性。
1815年结束的一连串全球性战争不仅动摇了欧洲统治者的合法性,也动摇了世界各地统治者的合法性。战事结束后,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其他地区仍能发展经济,保持繁荣,经济发展的速度基本上与欧洲国家不相上下。然而到了1815年,这些国家就在与欧洲国家的竞争中落伍了。中国、俄国和美国因国内问题无暇他顾,在19世纪时虽有能力,却也无意扮演全球性的角色。法国战事连绵,国力耗尽,虽然其工业化进程从18世纪就已开始,但到1815年时,法国经济已接近崩溃。法国和西班牙、葡萄牙一样,丧失了帝国在海外的大部分殖民地。1815年末时,英国人没有可与之匹敌的对手。这一时期连年不断的战争促使欧洲各国推行彻底的改革,很多国家为了打败拿破仑不得不“师夷制夷”,采纳了法国人倡导的一些原则。
举例来说,普鲁士王国被迫减免一直压在本国农奴头上的苛税徭役,致力于实现军队现代化,改革国家官僚机构,提高其效率。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Mikhail Speransky, 1772—1839)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手下一位具有改革思想的大臣,出身寒微,精于治国。他改革了俄国原来摇摇欲坠的国家机器,加强了中央集权,大幅削弱贵族左右国家事务的权力。为了使行政管理更加合理,他还建立了一个由各部组成的体系,以国务会议为首,负责监理帝国的立法事务。斯佩兰斯基还想推行更广泛的改革,包括建立代议制机构,但没能成功,他自己也在1812年因此遭到罢黜。不过此前他已大刀阔斧改革了教育体制,建立了一个新的中级教育体系,在几个大城市增建了一批大学。受拿破仑影响,欧洲很多地区的行政机构提高了效率,学会了征兵和收税这两门至关重要的艺术。收税还与刺激经济生产的措施相辅相成,国家允许有进取心的人们为自己和家人聚富敛财,只要他们向国家缴纳赋税就行。这样,军事效率就与经济增长挂了钩。而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奉行的盘剥性国家经济政策却束缚了经济。
也许最重要的是,欧洲人的制海权,尤其是英国人通过一系列战争获得的绝对制海权,为1815年后欧洲称霸世界奠定了基础。欧洲人因此得以进一步在世界各地扩张,在澳大利亚和非洲大部分地区这样的地方建立殖民地。这些地方要么没有国家,要么国家虚弱,军事技术落后。欧洲人凭恃制海权控制了海上贸易,扼杀可与欧洲竞争的制造中心。推动欧洲国家海外扩张的那套观念,在法国大革命及此后的一连串国际战争中得到了具体体现。欧洲人于是愈加坚信,除了像美国这样欧洲观念和信仰已经扎根的地区外,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部分观念和信仰都比不上欧洲的。然而法国大革命所倡导、后来由拿破仑继承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没有马上惠及欧洲以外的地区。拿破仑甚至还在海地恢复了已被海地起义领袖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 约1743—1803)废除的奴隶制,而杜桑·卢维杜尔本人曾深受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早在1789年以前,认为欧洲在强权政治、经济和技术实力方面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观点就已经很流行了。1815年后的一百年里,这一观点首次有了现实依据。尤其重要的是,从更长远的观点看,对世袭原则的攻击始于美国,后来又从法国蔓延到欧洲各地,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君主制、贵族制、奴隶制和农奴制等体制的合法性。在19世纪的进程中,对世袭原则的冲击还将产生更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