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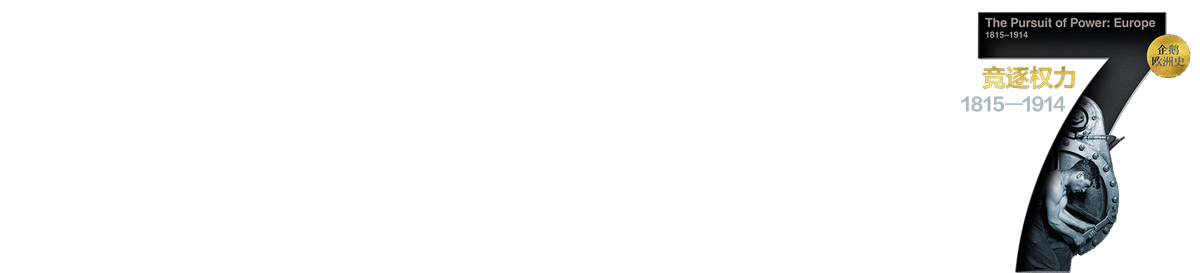
19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某个时候,在德意志西南部符腾堡的小镇埃尔旺根上,一个名叫雅各布·瓦尔特(Jakob Walter, 1788—1864)的石匠动笔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他被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的大军拉去当兵,随这支军队一直打到莫斯科,之后又一路败退回老家。瓦尔特用质朴无华的笔触讲述了1812年最后几个月他经历的千辛万苦:哥萨克人不间断地骚扰,他自己一身污垢,在饥寒交迫中到处寻觅食物,土匪沿途拦劫,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瓦尔特九死一生后,在一个波兰小镇把自己好好洗了一遍。他已经好多个星期没有洗过澡了:
我洗得很慢,慢慢地洗脸,慢慢地洗手,因为双手、耳朵和鼻子粗糙得像树皮,到处是裂开的口子,上面长了一层黑鳞屑。我的面庞看上去活似一脸大胡子的俄国农民。我照了照镜子,被自己古怪的样子吓了一跳。接着我花了一小时时间,用肥皂和热水搓洗自己。
瓦尔特竭力想除尽自己身上和衣服上的虱子(“我的主子”),最后还是失败了。他跟随部队继续向西撤退时,开始发烧,极有可能患上了斑疹伤寒。剩余的路途他是躺在一辆马车上行完的。他所在的马车队一共有175人,其中百十来人中途倒毙。一身虱子的瓦尔特回到家乡时,觉得亲人一定认不出自己了:“我身穿一件肮脏的俄国外套,头戴一顶老式圆帽子走进家门,衣服从里到外藏匿着无数个一路伴随我的伙伴,俄国的、波兰的、普鲁士的、萨克森的。”他终于能洗个像样的澡,处理掉爬满虱子的衣服,慢慢恢复健康了。本地人与他打招呼时开始叫他“俄国人”。当年凡是去过俄国的人都被人这样称呼。
瓦尔特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欧洲百姓一样,对政治不感兴趣,甚至根本不懂政治。1806年,他被法国的傀儡符腾堡王国征去当兵。1809年和1812年,他又两次被拉去服役。他和应征入伍的数十万名士兵一样,对此无能为力。从他的日记里,看不出他对法国乃至符腾堡王国的事业有丝毫的忠诚,对战争后果有丝毫的兴趣,对俄国人有丝毫的仇恨或杀死他们的意愿。身为普通一兵,他只知道上战场,对战役背后的战略考量全然不知。被卷入苦难的瓦尔特最关心的,是自己能不能活下来。18世纪90年代初,法军曾高唱马赛曲勇往直前,冲向反革命的奥地利军队。昔日法军的锐气早已消失殆尽。如今只有少数士兵依然对拿破仑的事业忠心耿耿,比如皇家卫队。瓦尔特在日记里自始至终流露出的厌战情绪也代表了整个欧洲的情绪,而且不无理由。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战争使所有人对苦难都已经麻木了,也对未来感到绝望。如果说瓦尔特有什么信念的话,他是靠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挺了过来。不过这没有妨碍他生动描述这场战争对亲历者人性的摧残。
瓦尔特返回家乡后重操石匠旧业,生活平淡无奇。1817年,他结婚成家,夫妻俩一共养育了10个孩子。1856年,他给移民到美国并定居堪萨斯城的儿子写了一封信,讲述家人的情况。当时他已经是一位殷实的建筑承包商和工头,子女尚有5个在世。第二年,这个小伙子回到德意志探望父母,娶了当地的一个姑娘,她是埃尔旺根邻镇镇长的女儿。依照家族习惯,他于1858年返回堪萨斯城时,也随身带回了父亲的回忆录手稿。此后,这份手稿一直由家族成员保存,直到20世纪30年代对学者公开。瓦尔特在埃尔旺根小镇又活了几年,于1864年去世。1873年,他的妻子病逝。如同19世纪千千万万的农民,瓦尔特的身世几乎无人知晓,我们只知道他在远征莫斯科的法军中的一段经历。瓦尔特不同于大多数参加了这场关系重大的远征的人,他活了下来,用笔记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因而不像绝大多数欧洲人那样,一辈子默默无闻。
在从莫斯科撤退的途中,瓦尔特偶然见到了拿破仑。瓦尔特在别列津纳河边坐下来,准备在野外吃顿饭。拿破仑留给他的印象很一般:
拿破仑看着自己那支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军队从面前走过。他内心是什么感受,无人知晓。他的面部表情让人觉得他对自己士兵的惨状无动于衷,也漠不关心。也许他内心想着的只有宏图和丧失的荣誉。尽管法军和同盟国士兵冲他大声喊叫咒骂,但拿破仑仍然面无表情。
从莫斯科悲惨地撤退后,大多数活下来的拿破仑士兵此时对他只有怨恨和蔑视。法兰西帝国那贪得无厌的征兵机器开动起来,迫使德意志、波兰、意大利和法国的68.5万人离开家庭,组成一支大军,向俄国行进。但回来的还不到7万人,40万人战死,10万余人当了俄国人的俘虏,还有部分掉队和开小差的士兵自己想办法逃回了家乡,具体人数不详。几次战役后,拿破仑军队伤亡惨重。英国人、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俄国人组成的欧洲联军穷追猛打,拿破仑军队向西节节败退。1814年,联军占领了巴黎,把拿破仑放逐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小岛上。
过去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同后来冲突造成的毁灭相比,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造成的危害较轻。然而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大陆各地的战争又持续了23年,大约500万人死于战火。就占欧洲总人口比例而言,人员伤亡之惨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790—1795年出生的法国男子,每5人中就有一个死于拿破仑战争。拿破仑军队的阵亡人数高达150万人。俄国人把莫斯科付之一炬,不给敌人留下任何过冬物资。一位观察者写道:“全城四处火光冲天,浓烟蔽日,炙热烤人,大火燃烧三日不熄。”在一片混乱中,法军士兵大肆抢劫,莫斯科周围村子的农民也趁机进城捞一把。大火熄灭后,满是残垣断壁的莫斯科没有留下任何房屋和食物可供拿破仑大军过冬。全城9 000栋房屋毁了将近7 000栋,8 000多个店铺和仓库被烧,329所教堂中的1/3彻底毁于大火。大约合2.7亿卢布的私人财产葬于火海,而且根本不可能得到赔偿。此前大批平民早已逃离莫斯科。留下的人后来也大多离城,过着流民般的困苦生活。只有2%的莫斯科居民留了下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包括不少士兵,都没能活下来。俄国人收复莫斯科后,不得不架起巨大柴堆焚烧1.2万具尸体。直到1814年,莫斯科才真正开始重建。昔日蛛网般的狭窄街道被一座座公园和花园取代,工匠还为沙皇建造了一个富丽堂皇的新皇宫。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莫斯科宛如一个大工地。迟至1842年,专为监督莫斯科重建工程而成立的委员会才结束工作。此后又过了很长时间,莫斯科才恢复了昔日的恢宏。
同一时期,西班牙无数城镇乡村毁于战火和围困。1810—1812年,法军围困加的斯,占领雷亚尔港。雷亚尔港全城6 000人中有一半死于战火,40%的房屋,3/4的橄榄树以及四周大片松树林被毁。西班牙的很多城镇此后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在法军蹂躏后的地区,牛、马、猪、羊的数量锐减。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丧失了战前人口的近15%。戈雅(Francisco de Goya,1746—1828)的版画《战争的灾难》( The Disasters of War )一共82幅,生动描画了战争的真实情况。这套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公开的版画表现了强奸、劫掠、断肢、屠杀等恐怖场面。在一幅版画中,一具尸体从棺材里露出半个身子,手上是一张纸,上面写着“虚空”。画家选择用这个词概括战争年代造成的后果。
莱茵兰地区连年遭受法军蹂躏,农田荒芜,牛羊猪马绝迹,城乡居民缺衣少粮。法国人对当地人民横征暴敛,助长了劫掠和贪婪。早在战争初期,战争造成的破坏就已显现,其影响持续多年。1792年,从莱茵兰地区返回的一个法国探子汇报说:“就连维持基本生存的物品也荡然无存,没有牲畜的粮草,没有种子,各村子里的其他东西也被盗窃一空。”成群结队的强盗鱼目混珠,装扮成法军士兵出没于乡间。这说明当地居民对占领军的强奸、劫掠和破坏行径早已习以为常。法军到达亚琛后,立即把该城和附近乡村洗劫一空。粮食、草料、衣服、牲畜,一切能够搬运的东西被悉数掠走。冬天降临后,饿死的当地居民数以百计。
不仅法军,其他军队同样一路抢劫,走到哪里,吃住在哪里。所有军队都竭力保证自己的后勤供应。至少在1812—1814年期间,盟国内爱国热忱日益高涨,贵族、商贾和普通农夫自愿为战争做出各种各样的贡献。然而战争规模巨大,仅靠他们的贡献是不够的。1813—1814年俄军一路西进时,依靠几乎已绷到极限的漫长交通线运输军粮,而所谓军粮不过是黑面包和稀粥。士兵若想吃得好点,就不得不去偷,有时还偷自己盟军的食品。骑兵需要马,拖拽野战炮、运送给养也得用马,于是,给成千上万匹马提供饲料就成了所有参战部队都面临的难题。征集粮秣的队伍四处搜寻燕麦和其他饲料。俄国人攻入法国后,大批村子毁于战火。农民如同当年躲避拿破仑派来征兵的官员一样,逃进了林子里,不时窜出来袭击沿线盟国军队的补给车。滑铁卢战役后,规模将近90万人的外国军队占领了法国,四处勒索,民不聊生。
在恢复经济方面,天公也不作美。1815年4月,位于今天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上的坦博拉火山大爆发,腾空而起的火山灰甚至飘到了43千米高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火山爆发。2 000多千米外的地方都可以听到火山喷发的巨响。大量硫黄被喷射到平流层,尘埃连续两年不散。黑云蔽日,出现了橘黄色落日的奇景。拜伦勋爵(Lord Byron, 1788—1824)写道:“早晨来了,又走了。早晨来了,却不见天日。”1816年1月,匈牙利下了一场褐色的雪,据说有大批房舍被雪掩埋。自1811年起,连续10年夏季低温,因为太阳能量输出和全球天气系统发生了变化,而且1808年时在哥伦比亚有一次火山爆发。1815年在印尼的这次火山爆发就发生在这10年的中间。1816年末,大片地区的农作物明显减产,产量仅及正常年景的1/4,收割季节也比以往迟到了一个多月。荷兰因夏季暴雨肆虐,庄稼严重歉收。1816年7月,一家英国报纸报道说:“我们不断收到坏消息,欧洲大陆各地都暴雨成灾。荷兰几个省的大片草地被水淹没,人们担心食品匮乏和物价上涨,人心惶惶。法国内地也饱受暴雨和洪涝之苦。”根据法国天文台的记录,那些年的夏季气温比1740—1870年夏季气温的平均值低3摄氏度。部分地区的葡萄甚至没能在入冬前成熟。
1817年在符腾堡编写的一本年鉴上记载:“去年夏天,每场暴雨过后,就会有严寒天气随之而来,仿佛已经11月了。”莱茵河下游连续5个月洪水泛滥。在伦巴第—威尼西亚地区,地上积雪直到5月都未融化。当年秋天早降的霜冻更是雪上加霜。卡林西亚地区的农民无法播种冬季作物,已经是第3年了。在位于西南部的德意志邦国巴登,1817年粮食产量据说是当时的人们记忆中最低的。据沙伦格拉方济各会修道院的记载,在东南欧一带,1815—1816年之交的严冬导致伏伊伏丁那地区的巴奇县损失了2.4万只羊,入春后又暴雨不断,“多瑙河水位上涨,造成严重涝灾”。“没有人,包括老人,记得以前有过这么严重的洪涝。多瑙河两岸的很多村庄、农田和草田都被水淹没了,河水水位上涨到一人多高。”克罗地亚一个村子的教区教士把1816称为“死亡年”:
大雨连连,天气恶劣,土地不出产,很多人的存粮都不够支撑半年,有些人甚至连两个月的存量也没有……3月刚至,“黑色饥荒”开始袭来。只要还有口饭吃,村民就相互接济……然而他们没能坚持多久……最后百姓们实在活不下去了,四处流浪,或倒毙家中,或死在路上,或葬身林中。
1816年和1817年是克罗地亚的大荒年,1817年尤其严重。粮食价格比5年后的粮价高出2~3倍。交通运输因战争中断,因此很难组织赈灾。这场全球性的气候灾难造成了欧洲一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歉收。欧洲遭受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破坏,正在艰难地恢复产业和贸易。英国实行封锁,拿破仑则用“大陆封锁”反制,重创了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商业。各地市场来往断绝,成千上万的人失业。截至1816年底,伦敦斯皮塔佛德区内有两三万名织工失业。萨克森、瑞士和低地国家的一些纺织城镇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战争结束后,数十万名像瓦尔特这样的士兵复员回乡,加入了规模已经相当庞大的失业大军。
百姓收入大幅缩水,又遇上1816年农作物灾难性歉收,粮价飙升。面包是大多数人的主食。1817年,巴黎的面包价格比前一年翻了一番。1817年,普鲁士军官兼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在莱茵兰地区旅行时写道:“德意志南部和西部几乎颗粒无收,‘真正的饥荒’要来了。”他看到“骨瘦如柴、几乎脱了人形的农民为了寻找吃的,在田间地头翻扒还没长好就已经烂了的马铃薯”。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伦巴第山区,穷人靠吃树根野菜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的东部省份,据计饿死的人有2万余人。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弗朗茨一世(Franz I, 1768—1835)抱怨说,在伦巴第某地,“灾情极其严重,当地人靠吃生菜、喝野菜汤果腹,很多时候什么都吃不到”。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穷人沦为乞丐和小偷,有的流入城镇寻找食物。1816年末,一位观察者写道:“慕尼黑的乞丐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仿佛是从地缝里爬出来似的。”据说,匈牙利各地“乞丐成群”,罗马和维也纳的警察也开始定期出动,把街上的乞丐圈起来送去参加公共事业工程劳动。1816年6月,有人到访瑞士阿彭策尔州,发现“乞丐大多是妇女儿童,数量之多令人震惊”。另一名观察者称乞丐“面如死灰”。大批穷人走投无路,只得离开欧洲。地方政府巴不得他们离开,因此提供了协助。1818年,2 000多人离开巴登,移居里约热内卢。1817年,据说有2万名德意志人和3万名法国人动身前往美国。听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许诺提供援助后,符腾堡的9 000多名穷人长途跋涉,迁徙到东面的俄罗斯帝国。大量人口尤其是军队士兵在广袤地域的流动传播了流行病。当年一无卫生预防措施,二无抗生素。在卫生状况恶劣的军队里,在成群结队的贫苦流民和乞丐中,疫情尤其严重。从1816年到1818年,巴黎死于天花的人数几乎翻了两番。与此同时,低地国家也暴发了一场严重流行病。人们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很容易患腹泻、痢疾和水肿。在意大利北部小镇布雷西亚(Brescia),仅1816年上半年,当地医院就收治了将近300名坏血病患者。人身上虱子携带的斑疹伤寒传播速度尤其快,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城镇几乎无一幸免。格拉斯哥全城人口13万,仅1818年一年,就有3.2万人染上了斑疹伤寒,其中3 500人死亡。赈灾措施反倒加快了斑疹伤寒的蔓延。一位爱尔兰医生说得相当准确:“大批流民为了活命流浪四方,加之各地政府为聚集成群的穷人提供热汤和其他食品,传染病迅速蔓延。”
鼠疫在巴尔干半岛迅速蔓延,于1815年传到意大利。意大利小镇诺哈位于亚得里亚海巴里城附近。镇上1/7居民死于鼠疫。鼠疫蔓延到巴利阿里群岛后,岛上居民大批死亡,1820年有1.2万余人被鼠疫夺去生命。波斯尼亚大批百姓死于鼠疫,死亡人数约占城镇人口的1/3和农村人口的1/4。食不果腹的人为了寻找食物,绕过隔离区和防疫警戒线,成群结队从农村涌入瘟疫流行的城市。在达尔马提亚地区,马卡尔斯卡全城人口因瘟疫而从1 575人减至1 025人。图彻皮村的806名村民中有363人死于瘟疫。面对灾难,当时仍然统治巴尔干大部分地区的奥斯曼政府束手无策。这是鼠疫最后一次在欧洲大规模暴发,也是后果极其严重的一次。研究这次鼠疫的一份历史资料得出结论,自黑死病流行的1347—1351年以来,“还没有其他欧洲国家经历过1815—1818年波斯尼亚经历的那种卫生和人口灾难”。在地中海西岸,各港口匆忙采取措施,隔离入港船只。哈布斯堡君主国与奥斯曼帝国接壤的省被称为“军政国境地带”(Military Frontier),素有重兵把守,交通不便。驻扎的重兵起了很大作用,阻止了鼠疫继续向北和向西蔓延。然而以上诸因素叠加,尤其是庄稼歉收和流行病,还是让欧洲各地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在西欧大部分地区,死亡率上升了8%~9%,部分地区受害尤其严重,同一时期瑞士东部地区的死亡率就翻了一番。
自1816年起,欧洲发生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波及范围最广、最暴力的一系列抢粮骚乱。东盎格利亚的大群饥民手持顶端装有尖铁头的短粗棍棒,高举“不见面包就见血”的旗帜,捣毁了可疑奸商的住宅,要求降低面包和肉类价格。在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人群夺取了粮库,袭击磨坊主、商贩和谷物商的住宅。法国各地成群结队的人阻止本地粮食运往外地。意大利的粮仓和面包坊被抢。奥格斯堡和慕尼黑均发生了粮食骚乱。1817年6月,低地国家的谷物价格飞涨,暴民袭击并洗劫了面包坊,借纪念滑铁卢战役二周年之机抗议面包价格上涨。法国东部的大批人袭击了农庄,人数之多,令有些人想起了1789年“大恐慌”时大规模出动的农民力量。骚乱通常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尤其是1817年发生在里昂的一次大规模起义,其起因是谣传拿破仑马上就要返回。1817年3月,曼彻斯特的数百名织工决定向伦敦进发,要求当局采取行动解决纺织业的危机。同年6月,诺丁汉爆发了一次不成功的起义,史称彭特里奇革命;8月23日,布雷斯劳又发生了起义,因为新兵不肯念普鲁士民兵誓词。两次起义均不无政治背景。若从全欧洲视角审视以上骚乱,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动荡主要不是当地或一国的政治因素造成的,而是源于生存危机、大规模失业、贫困,以及对未来的恐惧。在拿破仑之后的“白色恐怖”年代里,法国有2 280人受审,其中绝大多数人的罪名是强行压低粮价、阻止粮食外运、抗税或在私有森林砍伐树木。反革命派的反攻倒算只起了很小的作用。
1819年,危机开始消退,然而各地暴乱依然不断。当年8月,将近6万人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举行大规模抗议集会。军队开枪镇压,15名示威者被打死。民众借用滑铁卢这个名字,讥称这次事件是“彼得卢惨案”。同一年,一场因其战斗口号(Hep-Hep)得名的反犹太人骚乱波及西欧和中欧,各地的地方当局惊恐不安,将其归咎于秘密社团的阴谋。其实这场骚乱的起因,很可能是公众认为犹太商人借经济困难发财而心生妒恨。在大学城激进学生的鼓动下,愤怒的手工业者殴打犹太人,破坏他们的财物。很多犹太人被迫逃亡。排犹骚乱从维尔茨堡蔓延到卡尔斯鲁厄和海德堡,沿莱茵河往下波及法兰克福,并向北扩散至哥本哈根及附近村镇,那里的水手和当地居民一起向犹太人房舍投掷石块。骚乱还向东蔓延至克拉科夫、但泽、布拉格和里加,向西至莱茵河上游和下游的法国数省和摩泽尔。由于财物遭到破坏,地方当局均出面镇压。1820年年末,社会动荡终于平息。一些城镇中家境较好的居民和大学生也卷入其中,给骚乱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各地政府忧心忡忡。
就发生的次数和造成的后果而言,拿破仑战争后的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全欧洲动荡因地而异。迫于形势,各国政府均采取了福利和赈济措施,承认国家有义务改善最贫困人口的生活。然而在1815—1819年,欧洲各国在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时往往受到很大限制。此前几十年里,各国边界更易不定。新出现的国家仍在创建自己的行政机构,使其覆盖边远地区。当年还没有铁路,公路的状况很差,运河只有寥寥几条,河道难以通航,因此把粮食运送到受灾地区十分困难。以上种种因素意味着偏远地区的居民不得不忍饥挨饿,除非他们移居到政府机构所在的地区。社会精英阶层更是担心社会动荡会像1789年时那样引发革命,造成严重后果。有鉴于此,拿破仑战争后的解决方案既着眼于遏制法国任何可能的政治和军事图谋,又着眼于预防和镇压任何一地发生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