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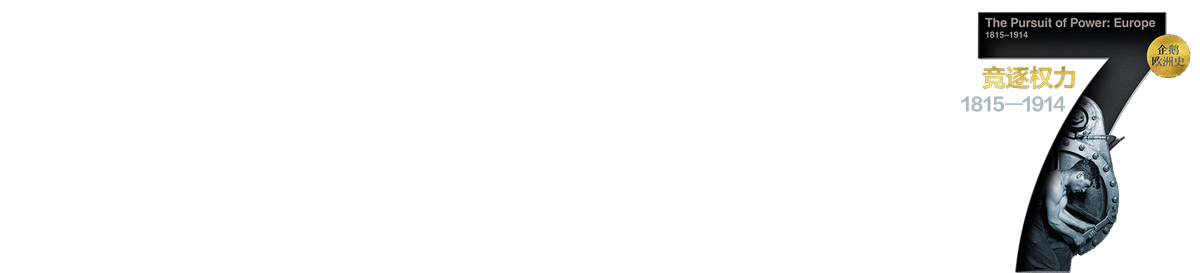
萨瓦·德米特里耶维奇·普尔列夫斯基(Savva Dmitrievich Purlevsky, 1800—1868)出生在俄国中部一个叫韦利科耶的村子里,从小在农奴制度下长大,对这一制度强加的种种义务和苛捐杂税深恶痛绝。普尔列夫斯基诉苦说:“农民人身依附制度无法忍受!”他的村子在一个中校军官不大的私人领地上,有大约1 200公顷可耕地、175公顷森林、656公顷的草地和牧场。这位中校平时住在圣彼得堡,整天花天酒地、寻花问柳,从不去自己的领地。一个管家为他照管领地,私吞了大部分收入。虽说领地上的农民大多是文盲,但普尔列夫斯基靠当地牧师送给他的一本扫盲课本学会了识字,开始用过生日或其他日子亲戚给他的一点点钱买书。普尔列夫斯基长大后,他的文化知识帮了他的大忙。
该村有大约1 300名村民,他们都必须向领主缴纳岁租。这不是太大的负担,因为农民除了为维持自己生活种植农作物外,还兼种亚麻及其他作物,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换其他产品。这个村子的村民知道,与大多数农民相比,他们的日子还算不错。普尔列夫斯基写道:“北部省份的平民几乎全靠吃黑麦面包、喝菜汤果腹。农民出于需要,不得不卖掉一切劳动所得,包括奶制品、牛羊肉、鸡蛋等,自己只能吃豆子、燕麦和芜菁块根。我们村比较特殊,村民靠集贸和做点手艺活有些收入,日子过得比其他村子的村民好一些。”但长住圣彼得堡的领主不时向村民提出额外要求。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从圣彼得堡发来指令,在村民大会上宣读。一次,他让管家“挑选4个适于站在马车后面踏板上的小伙子,年龄不超过20岁,身材要高大,另外再挑4个18岁的俊俏姑娘(他没交代让她们干什么,不过不难猜测),要亲自把这8个人送到圣彼得堡的领主家中”。
俄国的贵族地主通常不住在自己的领地上,他们大部分时间要么待在圣彼得堡,要么在法国度假胜地和中欧矿泉疗养浴场消磨时光,或在赌场挥金掷银以至于债台高筑。即便是没有因此负债累累的地主,也往往只把自己的领地看成维持在大城市生活方式的收入来源。韦利科耶村也不例外。1817年中校死后,他的女儿和女婿(女婿是俄国军队的将军)来到村里,要求村民立即预付今后10年的地租,数额高达20万卢布。遭到农民拒绝后,将军和他妻子跳上马车,返回圣彼得堡,但事情远没有完结。很快,村民大会又宣读了一道新指令。新领主将领地抵押,得到了一笔为期25年的贷款。他们要村民除了每年缴纳2万卢布外,再额外支付3万卢布的贷款年息。拒不付钱的人要么送去军队服役,要么遣送到西伯利亚领主的矿场做工。村民听到这道新指令后,惊愕万分,会场一片死寂。普尔列夫斯基后来写道:“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为自己的农奴身份感到悲哀。”农奴完全受人摆布。有些领地的领主肆意鞭打农奴,给不服从他们的农奴戴上铁项圈。普尔列夫斯基甚至听说,有一个领主因为一个农民孩子向他的猎犬扔石头,就把孩子的衣服剥下让狼狗嗅闻,随后把他带到原野,放群狗去追他(所幸孩子没有被狗咬伤。沙皇闻知此事后,下令把这个地主逮捕。即使是农奴制,也有一定之规,这个地主显然坏了规矩)。面对领主的索求,不仅普尔列夫斯基这样有文化的农奴感到无助,普通农奴也一样深感无力。
19世纪20年代,韦利科耶村的农奴境遇更糟了。来了个德意志人当他们的新管家,他开始干预村民的婚事,用鞭子抽打不服从命令的人,逼迫农奴在领主开办的纺织厂做工。农奴若是抱怨,他就马上派士兵进村。100余名农奴在领地全体农奴面前被鞭笞。这个德意志管家后来被一个不那么残暴的管家换了下来,但农民仍然怨声载道。最后,领主让全村唯一识文断字的普尔列夫斯基担任管家,试图以此消除村民的不满。普尔列夫斯基着手改善庄园的管理,说服领主在村里开设小学和诊所。普尔列夫斯基手下的人开始背着他侵吞财物,事发后领主怪罪到普尔列夫斯基头上,把他叫到圣彼得堡严加训斥。普尔列夫斯基害怕受到鞭打的惩罚,逃走了。他先潜逃到莫斯科,继而去了基辅,在当地用芦苇秆做了一个筏子,沿第聂伯河顺流而下,漂浮到了530千米以外的摩尔多瓦。他“在亚萨科(Yassakh)上岸时,精疲力竭,衣衫褴褛,腹中空空,身无分文”。当地的俄国流亡者收容了他,他们属于“旧礼仪派”下面的司科蒲奇派(又称“阉割派”)。1843年,德意志旅行家奥古斯特·冯·哈克斯特豪森(August von Haxthausen, 1792—1866)男爵在游历途中见过他们,描述了他们一般在夜晚举行的“怪异的秘密仪式”:“这些人尖利刺耳的声音,令人悚然的热忱和野性的狂热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痛苦印象。”这些人奉行独身主义,更可怕的是还践行自残。
司科蒲奇派成员靠赶大车为生。普尔列夫斯基很快通过诚实和勤劳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一天晚上,他偷听到两个成员议论自己:“他是个好人,我们应该让他改信我们的宗教。”正如哈克斯特豪森所说,司科蒲奇派成员“狂热追求让他人改信自己的教义,还阉割信徒”。普尔列夫斯基知道司科蒲奇派迫使他人改信十分普遍,他吓得魂不附体,再次逃跑。这一次,他往西跑了960多千米,一直逃到多瑙河沿岸,遇到一群世俗的俄国流亡者,和他们一起待了两年,靠捕鱼为生。1834年,普尔列夫斯基获知尼古拉一世豁免了逃亡农奴,于是动身前往东边1 290多千米外的敖德萨,在那里,农奴可以合法定居。普尔列夫斯基在一个酒吧找到了一份侍者的工作。没过多久,他升为经理,在一位酒吧常客的帮助下,他做起了糖生意,成了商人,还与在韦利科耶村的家人取得了联系。1856年时,他已经攒下足够的钱,为自己儿子买回了人身自由。普尔列夫斯基死于1868年。对一个农奴而言,普尔列夫斯基的一生很幸运,他的村子经济状况很好。像俄国中部地区很多农业不太发达的村子一样,韦利科耶正逐渐成为以纺织业和商业为主的工业城镇。这个村子经济的性质意味着村子里的农奴常常外出经商,有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而不是死水一潭,与外部世界隔绝。每当自己的权利受到威胁,农奴都敢于维权,虽然他们的抗争不是总以胜利告终。以上现象逐渐侵蚀了农奴制。在普尔列夫斯基眼里,农奴制是压在身上的沉重经济负担,是对农奴的敲诈勒索。最重要的是,他憎恨农奴制强加给他的屈辱和不公。最终他忍无可忍,逃离了这一制度。
在普尔列夫斯基生活的年代,俄国欧洲部分的农奴占欧洲大陆农奴人口的绝大多数。受1789年法国大革命平等思想的冲击,西欧和中欧的很多地区废除了农奴制,包括巴登、巴伐利亚、丹麦、法国、荷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瑞典属波美拉尼亚、瑞士。符腾堡、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于1817年废除了农奴制。但其他地区依然实行农奴制,包括汉诺威王国、萨克森王国、奥地利、克罗地亚、匈牙利、普鲁士、俄国、波兰、保加利亚、冰岛和波斯尼亚。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汉诺威和萨克森王国才废除了农奴制。1816年普鲁士推翻5年前推行的更激进的改革后,被削弱的农奴制一直延续到1848年或此后不久。俄国和波兰的农奴制终结于19世纪60年代。保加利亚的农奴制一直到1880年才真正废除。在偏僻的冰岛,四分之一的人口实际上都是农奴,直到1894年,冰岛才正式废除了强迫无地农奴为有地农民种地的法律。只有波斯尼亚的农奴制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结束。奥匈帝国于1878年从奥斯曼人手中攫取了波斯尼亚,在1908年正式将其吞并。波斯尼亚的农奴可以花钱赎身,但费用不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只有大约4.15万名农奴花钱赎了身。波斯尼亚农村的广大农民对农奴制没有被废愤恨不已。人民怨恨情绪日积月累,在1914年以戏剧化的方式宣泄出来。刺杀奥地利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1863—1914)的波斯尼亚塞族青年加夫里洛·普林齐普(Gavrilo Princip, 1894—1918)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时称:“我目睹民不聊生。我是农民的孩子,深知农村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要复仇。我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丝毫后悔。”农奴制的确给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
农奴不是奴隶。(欧洲也有奴隶,尤其是罗马尼亚的吉卜赛人,他们被当作奴隶在市场上公开买卖。直到19世纪40年代,教会和国家才解放了他们。他们在1848年彻底获得自由。)农奴既有义务,也有权利,但不是自由人。由于农奴制是历经几百年逐渐形成的,其存在方式取决于各地风俗习惯,因此它有许多表现形式,很难一概而论。但究其根本,都是强迫农民无偿服一些劳役,或是要他们每周几天在当地贵族地主的庄园里做一些具体杂务,比如协助领主狩猎、修缮领主房舍、为领主传递信函,以及各种杂七杂八的活计。农奴的妻子也许不得不为领主及其家人纺线,或做些轻体力活。农奴的孩子可能要为领主放羊放牛,或去领主宅第做家务。在有些地区,国家还强加了更多义务,比如派农奴去养护当地道路和桥梁,承担繁重赋税,为信使提供马匹,或派家里年轻人去军队服兵役。在有些地方,比如韦利科耶村,以上劳役改为缴纳年地租,但农奴的一些义务依然没有免除,比如去村纺织厂做工,在娶妻嫁女的事上顺从管家的意愿,在领主或管家认为农奴不听话时接受体罚。无论农奴承担什么性质的义务,他们的人身依附地位从来都清楚无误。
对大多数农奴而言,在领主庄园做工一般指提供拉犁耕地的牲畜,但也可能是体力活,比如为麦谷脱粒或帮助收割庄稼。服劳役时间的长短通常取决于农民耕地的大小。举例来说,在立陶宛,几十年来农民的土地都被分割为小块。一个耕种四分之一块耕地的农民一般需要每周三天向领主提供一男一女两个劳动力,一天从日出算起,到日落结束。因1797年沙皇帕维尔的一道敕令,一周三天的规定在俄国也很常见。农奴常常向领主提供农副产品,比如鸡蛋、牛奶、果仁、蔬菜等。西欧地区农民的耕地大多是祖上传下来的,而且劳役常常改用货币支付。农奴如果想将自己的地卖掉或遗赠给子孙,就必须以现金或实物的方式向领主支付一笔费用。此外,农民还必须向领主和当地牧师缴纳什一税,通常以农副产品形式缴纳。在东欧大部分地区,农民离开自己的村子都必须经过领主同意。农民如果迁居他处,就还要付领主一笔费用(如果不付费就迁走的话,这人就成了普尔列夫斯基这样的“在逃农奴”)。
所有捐税劳役加在一起,令农民不堪重负。例如,19世纪40年代,在奥地利统治的西里西亚,拥有大约17公顷土地的一户殷实农家每年最多要为领主出工144天,外带提供两头耕畜,此外还要干28天重体力活,花3天协助领主狩猎,再有两天放牛放羊。这户农民还要提供27.5立方米的木柴、大量纺线、60个鸡蛋、6只母鸡和一只鹅。农民一年耕地税略超过23弗罗林,还要缴纳15弗罗林的其他费用和什一税。在哈布斯堡君主国,据计一般农奴收入的17%要交给国家,24%以现金、劳役或实物方式交给领主,两者加在一起超过收入的40%。农奴劳动成果所剩无几,即使年景好时也只能勉强度日,根本谈不上改善自己的生活。农民及其家人每周好几天无法在赖以为生的自家土地上耕作。由于不能自由出售自己收获的农副产品,农民失去了很大一笔收入。领主享有诸多特权和垄断权力,农奴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在欧洲很多地区,农奴只能从领主那里购买盐、烟草、鲱鱼和烈酒。按照法律和习俗,农奴必须把自己打下的粮食拿到领主的磨粉厂去加工。只有领主有权打猎,这一特权不仅剥夺了农民获取衣食的一个重要来源,还毁坏了他们的庄稼。鹿和野猪在农民的耕地上肆意游荡。贵族狩猎追赶猎物时,有时会横穿耕地、践踏庄稼。在有些地方,为了防止木桩子伤到逃窜的猎物,妨碍狩猎,农民是不可以用篱笆把耕地围起来的。农民必须喂领主的猎狗,还得把自家的狗用链子拴起来,以免它们去追逐猎物。只有领主有权养鸽子,于是农民的庄稼又被鸽子糟蹋。领主往往还会垄断当地河渠的捕鱼权。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领主的种种特权和对农奴的限制都是靠领主法庭强制实施的。当地领主充当法官,审判不听话的农奴。领主法庭的权力是国家赋予的,其决定由领主警察强制执行,也就是由领主的私家仆人执行。农民若设陷阱捕捉猎物,开枪射杀飞禽,拖欠捐税,一经发现就会被扭送法庭,受到惩处。很多领主还私设牢房,他们有权对农奴进行体罚,通常是鞭打。更严重的罪行必须提交国家上级法院审理。大多数国家都对处罚方式做了限制,例如俄国。这类法庭的权力不是无边的,而是要受国家法律的限制。法庭开庭时,领主一般都请一位职业律师或法官主持庭审。由于需要依法行事,因此领主对农民的勒索若超过了允许的限度,农民也可以反告领主。国家法律对领主司法权的干预越来越多,因此许多不那么富有的小地主会把自己的司法权转让给邻近的大庄园主,或干脆建议废除领主裁判制度,他们在1833年的下奥地利三级会议上就是这么做的。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领主裁判制度都充斥着腐败和不平等。农民即使上法院打官司,也会处于不利的地位。19世纪40年代,一名富有的俄国大地主对一名旅行家说:“农民只给法官一个鸡蛋,我们给他一个银卢布。法官又怎么会为他伸张正义呢?”当然,农奴制有好坏两面。根据法律和习俗,年景不好时,领主有义务养活自己的农奴。病、老、残者若家人无力照管,也归领主照管。农奴带耕畜耕种领主土地时,领主管饭并提供耕畜饲料。很多地区的农奴有权在领主的牧场上放养自己的牲畜,在领主庄园收割后的地里拾散落的麦穗,在地主的私有森林里放猪觅食或砍柴。同样,领主通常也有权在村子的公共土地上放养牲畜或使用公共森林。
虽然一整套烦琐规则界定了农奴的权益和义务,但农奴以及他们租种或拥有的土地仍然可以被买卖。领主出售自己的庄园时,庄园上的农奴也会一并转售给新领主。国家常常默许只卖农奴不卖地的做法,这可以从法律规定中看出来。俄国有一条法律,禁止在公开拍卖农奴时使用锤子;1841年的一项法规规定,把农民及其未婚子女拆散出售违法。俄国的农奴必须耕种土地,还有越来越多的农奴被当作家庭用人、男仆、车夫、厨师等等。贵族出身、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 1842—1921)说,19世纪中,他父亲拥有1 200名农奴:“在莫斯科有50个仆人、在乡下还有60多个仆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地主最想要的,是手下的农奴可以满足自己的一切需求……客人若问:‘这架钢琴的音色好极了。是在席美尔店里调的音吗?’地主就会回答:‘我有自己的钢琴调音师。’”即使受过教育的农奴也可以买卖,有时他们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赌桌上就被转手卖给他人。像普尔列夫斯基这样的农奴虽然识文断字,做的是管理庄园的工作,但依然无时无刻不担心被鞭打。比他境况差得多的众多农奴就更不用说了,对这些农奴而言,人身依附给他们带来的屈辱是农奴制最可憎的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