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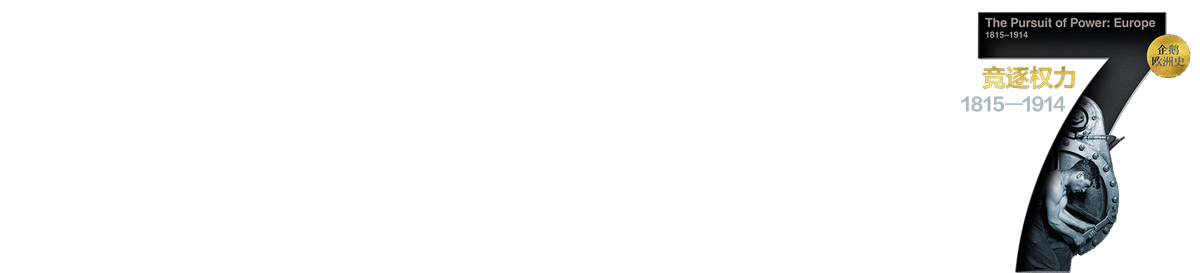
1829年,梅特涅写道:“我隐藏最深的想法是,旧欧洲的末日已经开始。我决心与它同归于尽。我知道该如何尽自己的职责。”1830年这一年似乎验证了他这句话,然而革命浪潮退去后,革命者和改革者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在很多大城市,最初的革命和改革成果都被推翻了。在莱茵河以东地区,除了波兰以外,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革命活动,现存国家体制的权力几乎没有受到触动。尽管“维也纳解决方案”安然度过了这场风暴,但梅特涅在青少年时代所熟悉的旧欧洲——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梅特涅年仅16岁——其实已不复存在。有人听到一个希腊强盗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打开了世人的眼界”,从此“统治人民就更难了”。19世纪20年代,都灵商会概括了这场变革:法国大革命“消除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人人穿戴相同,看不出谁是贵族,谁是平民,谁是商人,谁是官员,谁是业主,谁是工匠,谁是主人,谁是仆人。至少从表面看,引发革命的可悲原则令人遗憾地保留了下来”。魔鬼跑出了瓶子,想把它塞回去已经不可能了。
1815年重新执政的各国君主和政治家对此心知肚明。1815年复辟的王朝往往使用旧制度的各种符号和装饰。这些符号和装饰或许有意掩饰了一个事实,即这一时代的保守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事物。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把1815年看作一个新起点,认为它标志着理性极端化时代的终结。宗教信仰、人的本能和情感、传统、道德,以及有意识地对昔日怀有的新历史感将取代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成为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基础。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 1753—1821)等思想家继承了爱尔兰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提出只有人民普遍接受君主行使绝对权力是上帝的旨意,社会才会稳定。依照此论,人民要么服从,要么后果自负。迈斯特称:“君主的头号仆人应是刽子手。”根据这一保守观点,实行传统等级制度的社会才是秩序的唯一保障。理性是秩序的敌人,只有信仰和情感可以依赖。法国流亡者路易·德·博纳尔德(Louis de Bonald, 1754—1840)写道:“君主制和基督教同时遭到攻击之日,就是社会退回到野蛮时代之时。”文明不仅有赖于压制颠覆性思想,还有赖于压制一切思想。1819年,梅特涅的秘书弗里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Gentz, 1764—1832)写道:“我仍然捍卫以下论点:为了确保报纸不被滥用,今后几年什么也不该登。如果把这一条作为有约束力的规则加以应用的话,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到上帝和真理身边。”夏多布里昂等思想家认为,只有基督教带来的信仰才能保证人民安居乐业、顺从权威。夏多布里昂最初赞同启蒙运动的理性怀疑主义,后因革命年代的过火行为而重新归信天主教。
不过,博纳尔德和迈斯特这样的人只是处于边缘的极端分子。19世纪20年代期间,作家和思想家普遍开始倾向更自由的观点。1824年时,雨果还宣称,文学作品应当“反映一个信仰宗教的君主制社会”,但到了1830年,他就改为宣扬以下原则:“浪漫主义总的来说,就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艺术自由和社会自由是一切思维清楚的思想家都应该步调一致争取的双重目标。”1827年,法国艺术评论家奥古斯特·雅尔(Auguste Jal, 1795—1873)称浪漫主义为“1789年大炮轰鸣的回声”。仿佛为了证明他的观点,1830年欧仁·德拉克洛瓦创作了也许是最著名的表现革命的画作《自由引导人民》。在众多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眼中,希腊人民的起义是一个转折点,以拜伦病死在迈索隆吉翁为象征。1830年引发比利时革命的那场歌剧不过是新潮流的一个例子,这股潮流源于意大利,作家和作曲家描写古人争取自由的斗争,显然意在借古喻今。
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初期温和阶段响亮地提出了自由、人民主权、代议制政府和宪政等思想。自由主义观点在很多方面都受这些理念的影响,19世纪20年代时,自由主义观点多了一层新意,越来越与民族主义理想结合在一起。拿破仑在欧洲各地传播人民主权思想的同时,也带去了压迫、勒索和外族统治。受拿破仑影响,知识精英阶层认为,只有通过民族自决才能摆脱压迫。19世纪20年代时,从比利时到希腊的自由派就已经在宣扬这一很有说服力的思想了。在19世纪的进程中,这一思想的威力与日俱增。此前,自由派和革命者普遍认为,自己正投身于一场全欧洲的共同斗争,烧炭党人和共济会遍布各国的分支便是例证,但梅特涅及其政治警察机构无疑大大夸大了它们的能量。甚至希腊人民的起义也称得上是一次国际事件,至少就起义领导人而言。然而,从1830年起,各国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分道扬镳,其后果在19世纪中期的革命中显现出来。
以上革命,外加1830年横扫欧洲大陆的革命,都是1789年政治大地震的余震,不过两者是有差别的。在某些方面,造成1830年社会大动荡的社会力量也是推动法国大革命的力量:争取更多权利和更大自由的中产阶级知识阶层,以及渴求工作机会和面包的工匠和手工业者。然而,两方面力量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1793—1794年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在人们的记忆中还很鲜明,有时还会激励一些人采取激进行动,例如19世纪30年代初西班牙一些城市爆发的革命。雅各宾派采取的手法,比如在公共场所集会示威,引发骚动,构筑街垒阻止当局恢复秩序,仍然是城市群众表达自己观点的主要手段。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才会加入他们的行列,比利时就是一个重要例子。在欧洲其他地方,资产阶级几乎都对“暴民”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怕得要死。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要么组织市民成立民兵以恢复秩序,要么在旧政权调兵遣将镇压时,焦虑不安地被动观望。由于资产阶级抱有这种心态,因此在大多数地方,革命大动荡的结果仅限于温和的自由主义色彩宪政改革,君主制原则基本上没有受到触动。几乎在欧洲各地,被摧毁的都是绝对主义原则,中欧和东欧的几个帝国除外。
长达25年的战争以及拿破仑个人的榜样造就了一支新的社会力量——军官团,或者更准确地说,军官团里的中下级军官。1789年时还看不到这支社会力量的影子,但这一社会集团将在20世纪后半叶“第三世界”的一系列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年轻军官政治意识增强,感觉自己受到了1815年复辟封建王朝的冷落。在很多国家,他们率先发动革命,并得到了形形色色秘密组织的支持。有时他们还能争取到大批普通士兵为他们的事业而战,例如在波兰和西班牙。但总体来讲,在拿破仑战争刚结束的19世纪20年代初到20年代中期间,下级军官未能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他们发动的革命也都归于失败。有时他们得到人民群众支持,也是主要依靠中产阶级和手工业阶层的力量,但这支力量太弱小,无法取得革命胜利。一些受过教育的人昔日在拿破仑政府机构中任职,如今却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他们对现状不满,但也无力推动革命。再者,从19世纪20年代初到20年代中,神圣同盟和欧洲协调体系犹如惊弓之鸟,生怕革命年代时期的惨烈冲突死灰复燃,因此,它们不会袖手旁观,一旦觉得局势失去控制,就会联合各国进行国际干预。
1830年时,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新的社会变化逐渐把中下级军官排除在政治主流之外,中产阶级以及以工匠和手工业者组成的雅各宾力量为主的城市群众走向前台。欧洲协调体系依然在发挥作用,但主导这一体系的政治家——甚至连梅特涅也不例外——已不再对爆发革命大变动的危险疑神疑鬼,也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干预了。欧洲各地对希腊人民起义的踊跃支持是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希腊人民起义反抗的是一个老牌大国——奥斯曼帝国。该帝国与欧洲协调体系的关系并不密切,信奉的宗教也不是神圣同盟信奉的基督教。当然,总的来说,人们也清楚认识到绝对主义外加低效率绝非维持政治秩序的良方。1830年时,革命似乎已不再意味着天下大乱、暴力和战争。各地革命带来的是带有自由色彩的温和宪政改革。像梅特涅这样的保守政治家虽然不喜欢这些改革,但革命并没有把政权交给民众,因此他们尚能安心,觉得进行国际干预未免反应过度。
最重要的是,一股的重要社会力量几乎没有参与1830年的革命,那就是农民阶级。1789年法国大革命势不可当的原因之一就是革命在农村地区蔓延。生活困苦的农民和农村劳工加入了革命的洪流。革命扫除了长期以来控制农村社会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封建秩序根基,摧毁了贵族的政治权力。1830年,各地农村几乎普遍沉寂,而当时欧洲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下面我们要讲述的就是农村和农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