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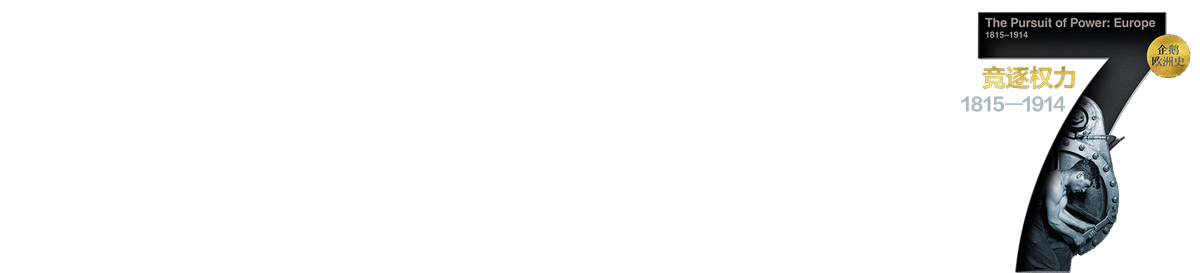
1830年法国革命令梅特涅心惊肉跳。但从长远看,这场革命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国际体系。查理十世曾雄心勃勃地制定并独自推行扩张法国海外帝国的政策,但该政策因革命而夭折了。现在法国对其海外利益采取了更审慎节制的态度。梅特涅试图煽动神圣同盟对抗路易—腓力。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马上附和,痛骂法国革命侵犯君主制合法性的神圣原则。但到1830年10月初时,所有欧洲大国,包括俄国,均接受了既成事实,正式承认路易—腓力政府。然而,问题并没有因此消失。18世纪90年代,法国人把大革命传播到欧洲各地。最初只有当地少数孤立的激进分子欢迎大革命。40年后,在西欧和中欧部分地区,同情温和立宪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理想的知识分子人数增加,以至于巴黎一起波澜,几乎马上就在其他地区激起类似震荡。
在梅特涅眼里,法国君主制的垮台意味着“欧洲大坝溃堤”,为革命洪流打开了闸门。8月23日,1830年法国革命不会限于法国一地的兆头初显。那一天,在布鲁塞尔上演了一场歌剧,表现的是17世纪意大利人反抗西班牙统治的那不勒斯起义。著名青年男高音阿道夫·努里(Adolphe Nourrit, 1802—1839)高歌《对祖国神圣的爱》一曲时,现场火爆。演出结束后,情绪高涨的观众涌上街头,因几个月前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而陷入贫困的手工业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当局害怕发生骚乱,马上取消了原定的焰火表演,结果这一决定反而把担心变成了现实。手工业者不满取消焰火表演,在街头构筑路障。布鲁塞尔外的源自中产阶级的民兵很快赶来支持起义。民怨沸腾的深层原因是,布鲁塞尔以说法语为主的居民憎恨维也纳会议把荷兰人强加在他们头上。当年外交家的初衷是让尼德兰王国与它南边的这块前奥地利领土连成一体,作为一个和平的缓冲国,与欧洲协调体系的大国一起遏制法国人再次扩张的任何企图。但尼德兰国王威廉一世(1772—1843)有自己的盘算。他想建立一个单一、中央集权式、中等规模的欧洲国家。为此他排挤占布鲁塞尔居民大多数的天主教徒,对他们横征暴敛,逼迫当地人负担新教学校的经费,剥夺他们在中央政府任职的权利。此前没有人问过布鲁塞尔人是否愿意接受荷兰人统治。现在他们开始明确表达自己观点:不愿意!
面对布鲁塞尔起义,威廉先是争取国际社会干预。但各国拖延不决,尤其是英国。于是,威廉召开议会,后者做出了一些次要让步,但未能平息人民的不满。看到起义没有要平息的样子,威廉派自己儿子弗雷德里克亲王(Prince Frederik, 1797—1881)带领一支1.4万人的军队开进布鲁塞尔。经过几天街头混战,经验不足的年轻荷兰士兵完全被城市街垒守卫者的气势压倒,斗志尽失。1830年9月27日,弗雷德里克的军队撤出布鲁塞尔。起义迅速蔓延到安特卫普,当地一支荷兰军队炮轰该城,把佛兰德人和新教徒为主的市民推入革命者的怀抱。9月26日,起义者成立了一个临时民族政府。10月4日,比利时宣布独立,之后召开了国民大会。国民大会体现了美国革命对欧洲政治思想的持久影响,发表声明痛斥尼德兰政府把比利时降格为殖民地,“把一种特权语言强加给比利时人民”,“向比利时人民征收赋税,不仅税额惊人,征税手法还强横霸道”。国民大会宣布,它将“在自由这一广泛和坚实的基础上建造新社会秩序的大厦,这是比利时人民长久幸福的起点和保障”。
面对比利时的纷乱局势,欧洲列强不知所措,反应不一。俄国人多次威胁动武并动员了军队,南德意志邦国则主张不干预。法国国内有很强的呼声,要求切割比利时,南部法语区归法国,但最终,法国因本国新成立的政府立足未稳,选择作壁上观。危急时刻,塔列朗再次现身,这一次,他的身份是法国驻英国大使。法国政府听从了他的意见,把本国稳定置于首位,这意味着对英国亦步亦趋。再者,同样是反法缓冲国,独立的比利时要比统一的强大尼德兰弱小得多。梅特涅认识到从长远讲是无法阻止比利时人的,于是派了一位大使参加伦敦会议,指示他动员欧洲协调体系接受一个温和、独立的比利时君主国。在新任命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 1784—1865)的主导下,伦敦会议于1830年11月4日召开,很快解决了主要问题,各方同意在比利时建立立宪君主制,成立两院制议会,对选民财产资格做了严格规定。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个新国家的王位让谁坐?
这个问题在会议上讨论了很久。很多候选人因这个或那个与会国不能接受而被否决。和19世纪此后年代里众多小国的情况一样,最后选出来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德意志亲王——萨克森—科堡—哥达的利奥波德(Leopold of Sachsen-Coburg-Gotha, 1790—1865)。他是当时各国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利奥波德亲王是沙俄帝国军队中的一名军官,在1813年的库尔姆战役中,他作战英勇,亲率骑兵猛攻拿破仑军队。两年后,他以中将军衔退役,年仅25岁。他是德意志人,但其实也是英国臣民,因为他于1816年迎娶了英国摄政王唯一合法后代夏洛特公主(Princess Charlotte, 1796—1817)。他因这桩婚姻获得英国公民身份,并被授予英军陆军元帅军衔,此后不久,他被赐予殿下称号,正式成为英国王室的一员。1817年,夏洛特公主死于分娩,孩子也没有活下来。为了迎合出席1830年比利时问题国际会议的各国,也为了安抚法国人,利奥波德表示,如果有合适人选的话,他愿意迎娶一位法国公主。不过尚有一个小障碍。1829年时,利奥波德娶了德意志演员卡罗琳·鲍尔(Caroline Bauer, 1807—1877),他们的关系只维持了两年。利奥波德解释说,这桩婚姻是私下安排的,从来不具有法律效力。各方被他说服了。1831年,排除了种种障碍的利奥波德成为比利时国王,并于翌年迎娶了路易—腓力的长女路易丝—玛丽。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尼德兰国王威廉仍不死心。1831年初,比利时入侵以威廉为名义国家元首的卢森堡大公国后,威廉极力拉德意志邦联出面干预。然而欧洲列强默许卢森堡并入比利时,德意志邦联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荷兰人气愤不已。1831年8月2日,威廉出兵比利时。利奥波德马上叫来法军支援,击退了荷军。但荷兰人依然据守安特卫普要塞。此后法国迟迟不肯撤兵,狐疑的欧洲大国转而对法国施加压力。1831年9月30日,法国人终于从比利时撤军。一项新条约略微调整了此前各方接受的边界和条款,把卢森堡一分为二,分别给了彼此争夺的比利时和荷兰。一年后,固执的荷兰人依然不肯撤离安特卫普。1832年11月,法国再次出兵,围困安特卫普。英国为了逼迫荷兰人投降,派海军封锁了斯海尔德河。1832年12月,荷兰人终于投降。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一直拖到1839年才最终得到解决。卢森堡,更准确地说是卢森堡东部德语区,继续归荷兰国王管辖。1890年荷兰威廉明娜女王(Queen Wilhelmina, 1880—1962)即位后,这块领土给了与女王血缘关系最近的男性子嗣,因为根据《萨利克法》,卢森堡大公国的王位不得传给女儿。由于比利时问题错综复杂,其对于法国、普鲁士和俄国的意义又非同小可,因此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三国都竭力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冲突。尽管欧洲大国之间分歧不断,俄国的尼古拉一世又因为解决方案公然违反神圣同盟原则而怒火中烧,但除了荷兰与比利时兵戎相见外,比利时问题最终还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了。欧洲各国普遍支持法国出兵比利时。正如1831年2月19日发表的伦敦会议议定书中所说,欧洲的权利源自维护国际秩序的义务,因此高于个别国家的权利。甚至连尼古拉一世也只愿意在欧洲诸国一致干预的前提下采取行动。1830年的革命之所以没有演变成重大冲突,也没有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威胁,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以上动荡及其在欧洲大陆的蔓延无疑意义重大。法国的局势不仅激发了邻国比利时的起义,还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起义。法语依然是上流社会使用的语言,也是欧洲外交场合的通用语言。旅行家、记者、外交家和商人把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时用的也是法语。1826年葡萄牙国王若昂去世后,巴西皇帝佩德罗与他弟弟米格尔(Miguel, 1802—1866)之间的长期争执终于结束。佩德罗放弃了继承葡萄牙王位的一切权利,改让他7岁的女儿玛丽亚·达·格洛丽亚(Maria de Glória, 1819—1853)继承。两年后米格尔篡位,导致这一安排破产。米格尔的支持者既有英国托利党人,又有葡萄牙站在绝对主义一边的显贵地主。前者想通过他恢复英国在葡萄牙的影响力,后者则憎恨1822年宪法和沿袭19世纪初拿破仑所定法律的做法。米格尔废除了大量拿破仑时期的法条,葡萄牙的自由派起义反抗,但被米格尔派镇压下去。在接下来的恐怖统治期间,大批人遭到逮捕、监禁甚至处决。1831年,革命浪潮席卷欧洲,佩德罗把巴西皇位传给了儿子,乘船返回欧洲,在英法支持下攻占了波尔图,此后被米格尔派军队围困在波尔图长达一年之久。据说,他手下的军官在英国酒商款待下日日宴饮,而普通士兵却营养不良,饱受霍乱之苦。佩德罗及其追随者得到了思想开明的英国海军上将查尔斯·内皮尔(Charles Napier, 1786—1860)爵士的帮助。内皮尔化名“卡洛斯·达·蓬扎”(Carlos da Ponza),指挥起义者船舰在圣维森特角大败米格尔派舰队。起义者乘胜占领了里斯本。大批兴高采烈的民众赶走了驻守兵营的米格尔派士兵,夺取军火库,释放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佩德罗为波尔图解围后移师首都。自由派宣布玛丽亚·达·格洛丽亚为女王,随后挥师南下,于1824年5月在阿赛西拉战役(Battle of Asseiceira)中打败了米格尔派的1.8万人大军。米格尔被迫同意流亡海外(根据当时达成的协议,他将得到一笔丰厚的津贴)。佩德罗重启自由派人士的改革,恢复了宪法,没收了米格尔派成员的财产。为了报复教会支持他弟弟的行为,佩德罗关闭了修道院,没收其房舍和资产。1834年9月,佩德罗去世。他的女儿、时年15岁的格洛丽亚继承王位,成为女王玛丽亚二世。她统治的这个国家因连年战争而负债累累,再次成了英国人的附庸。这一次是在经济上依附于英国。
在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专制政权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都没有丝毫改变,直到这位西班牙君主在1833年9月死于痛风。在他遗孀玛丽亚·克里斯蒂娜(Maria Cristina, 1806—1878)一手操纵下,费尔南多的幼女继承王位,成为女王伊莎贝尔二世(Queen Isabella II, 1830—1904)。1834年,自由派人士趁政府虚弱,推动通过了一部自由主义色彩的温和宪法,尊崇贵族寡头权力,重拾革命前的立宪主义,那种立宪主义有很大局限性,与昔日的社会等级代表制度也有象征性的联系。政府开会时,代表们必须身着中世纪服装,以显示他们不同于新体制下当选的议员。3年后,在更激进代表的不断鼓动下,又通过了一部基于人民主权原则的新宪法,但该原则也受到了限制,因为这部宪法授予女王广泛的权力。新宪法之所以能够通过,主要是因为西班牙各地城镇爆发了一系列革命。城市贫民纷纷上街游行,街头暴力冲突不断,小麦价格居高不下时更是如此。自由派人士控制的委员会做出让步,遏制了小麦价格的上涨。各地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的嗜血模仿者”——仿效18世纪90年代初法国雅各宾党人的做法,放火焚烧女修道院,杀害当地监狱里的囚犯,袭击顽固不化的贵族。后来,一位史学家说,一次冲突后,一位战败将军“被剁掉的手在‘新潮咖啡馆’各张桌子上传来传去”。法国大革命过去差不多40年后,从欧洲各地革命者和革命群众的举动中,仍然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
对法国大革命的记忆促使意大利烧炭党人起身反抗北部的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中部地区的教皇政权。19世纪20年代末,他们开始为起义做准备,意欲扩大自己领地的摩德纳公爵弗兰西斯四世(Francis IV, Duke of Modena, 1779—1846)也给予积极支持。在巴黎革命的激励下,烧炭党人发动了起义,但摩德纳公爵害怕再发生类似的社会大动荡,不再支持他们。烧炭党人在教皇国和帕尔马公国升起了意大利三色旗帜。年老的革命家菲利普·邦纳罗蒂(Filippo Buonarroti, 1761—1837)曾在18世纪90年代初追随罗伯斯庇尔,后来参与巴贝夫(Babeuf)为平等而密谋的活动,反对雅各宾派之后的督政府统治,还为此坐了牢。流亡期间,他极其活跃,积极组织秘密社团,比如“世界社”和“被诅咒的民兵”,还有名字不那么耸人听闻的“人民之友会”。邦纳罗蒂成立了一个解放意大利领导集团,协调各地起义。然而,集团成员为邦纳罗蒂奉行的雅各宾派原则争执不休,而且不无理由地怀疑,他坚持夺取政权后先实行一段“过渡”专制的主张别有用心。烧炭党人现在控制的意大利各城市依然不愿放弃它们之间几百年来的内斗,对在罗马召开一次团结大会的呼吁置之不理。博洛尼亚的起义者甚至不肯接受来自摩德纳、由前拿破仑将军卡洛·祖基(Carlo Zucchi, 1777—1863)率领的革命军队。起义者宣称:“公民们,请不要忘记,摩德纳的情况和我们的情况不一样!”起义者未能唤起农民加入他们的事业,却吸引了少数欧洲冒险家,包括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路易—拿破仑在意大利蛰居期间加入了烧炭党,参与密谋在罗马夺取政权,但预谋被当局轻而易举地破获了。在欧洲诸大国的默许下,奥地利人调集大军,很快将起义镇压了下去。祖基被人出卖,奥地利人给他戴上手铐脚镣打入大牢。他在狱中受尽折磨,直到1848年才被革命者救出。流亡的邦纳罗蒂继续从事他的毕生事业——组织密谋。1828年,他出版了讲述巴贝夫起义的书,该书成了革命者的实用手册,在19世纪后期深受无政府主义者推崇。
巴黎的事态对德意志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位于德意志邦联西北角的亚琛(艾克斯拉沙佩勒),当地人民以戴三色帽章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法国人民革命的支持。经济衰退不仅重创比利时手工业者,也促使其他城市的失业手工业者纷纷走向街头,出现这种情况的城市除了科隆、法兰克福和慕尼黑,还有维也纳和柏林。投身政治的工匠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 1808—1871)写道:“一夜之间,莱比锡人民成了这座城市及周边地区的主人。”人们摧毁了不得人心的商人、律师和官员的房子,但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不满转化为具体要求。自由派作家卡尔·冯·罗特克(Karl von Rotteck, 1775—1840)称他们的行为是“对社区的犯罪,罔顾祖国和宪法——驱使他们犯下这些罪行的,正是他们表现出的那种暴民式的狂热、野性、非理性和盗窃欲”。以上观点在中产阶级中间很有代表性,因此当局不费气力就把骚乱镇压下去了。2 000名装备精良的普鲁士士兵开抵亚琛恢复秩序,德意志多地的人群也被迅速驱散。
在德意志的一些中小邦国里,自由派人士利用政府惧怕“暴民”的心理,大胆迫使政府做出了一些重大改革。不伦瑞克邦国的官员威廉·博德(Wilhelm Bode, 1779—1854)领导当地人民赶走了废除1827年宪法的不得人心的卡尔公爵(1804—1873),换上了他比较开明的弟弟威廉(Wilhelm,1806—1884),从而摧毁了王朝复辟时期被封建卫道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原则。公爵城堡被付之一炬后,卡尔公爵魂飞魄散,仓皇逃亡海外。中产阶级一心关注以上事态发展,无暇他顾,由市民组成的民兵担负起了恢复秩序的职责。1832年,威廉被迫同意实行代议制体制。在黑森—卡塞尔,选侯威廉二世(Elector Wilhelm II, 1777—1847)试图把和他姘居的情妇封为贵族,结果疏远了中产阶级。骚乱者走向街头,抗议政府横征暴敛、警察粗暴执法,不满农民被迫向地主缴付封建捐税。在卡塞尔举行的中产阶级公民大会要求建立一个新体制,防止“穷人威胁对有产阶级开战”。威廉二世与其情妇先后逃离卡塞尔。他不在期间,自由派人士推动建立了一院制议会的新体制,放宽选民资格条件,甚至还包括了部分农民,他们赋予议会各种权力,包括起诉国王手下大臣的权力(但大臣依旧由国王而不是议会任命)。萨克森的手工业者和工人也掀起了抗议浪潮,波及乡村地区的纺织业中心。担忧时局的中产阶级公民开始组建民兵,一批高级官员迫使政府让步,于1831年颁布了一部新宪法。在仍处于英国君主统治下的汉诺威,哥廷根大学城的师生一起造反,矛头直指民愤极大的头号保守分子、大臣明斯特伯爵(Count Münster, 1766—1839),明斯特旋即被罢免。此后又经过一番斗争,1833年时,一部相对自由的宪法终于获得通过。
在德意志各地,王朝复辟时期的自由反对派受巴黎革命激励,也许更受波兰革命鼓舞,越发斗志昂扬。在巴登和巴伐利亚等邦国,自由派更换了政府官员,改革了新闻法。德意志各邦国内的自由主义改革运动汹涌澎湃,在普法尔茨汉巴赫城附近一座废弃城堡举办的一次规模盛大的节日庆典将其推向高潮。和此前的瓦尔特堡节一样,这次活动也模仿了18世纪90年代初法国大革命期间举办的盛大节日庆典。宣传新闻自由的记者约翰·格奥尔格·维尔特(Johann Georg Wirth, 1798—1848)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据计大约2万~3万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倾听所提出的各项改革要求。在场听众多是专业人员、商人、工匠和学生。群众热烈挥舞黑、红、金三色革命旗帜,很多人还头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红色弗里吉亚帽,聆听宣传德意志统一自由事业的演说。革命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聚集到了一起:革命走出了共济会员和密谋者烟雾缭绕的密室,从秘密转为公开,走上了合法的宪政改革道路,而不是造成剧烈社会动荡之路。在汉巴赫,主导事态发展的是演说家的讲坛和记者的书桌,而不是断头台和灯柱。之后,其他地方也举行了小型庆典。
在梅特涅眼中,以上事态发展就是镇压的信号。他宣称:“自由主义已经让位于激进主义。”梅特涅说服联邦议会颁布了一连串新法律(臭名昭著的“六条”和“十条”),强化书报检查制度,取缔政党,严禁举办节日活动或示威,禁止地区议会驳回政府预算或通过批评君主的动议案,还发布了很多其他禁令。军队开进德意志邦联各地城镇,驱散街头人群,几乎各地的自由改革措施都被废除。德意志大地上空,反动势力一时乌云压顶。1833年,德意志邦联成立了一个中央政治警察机构,专门负责协调各部门一起对付政治动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上层领导人聚在一起,讨论如何联手镇压革命。诗人海涅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被迫流亡,还有些人遭到逮捕和监禁,包括维尔特和在汉巴赫发表过演讲的其他人。时间将证明,德意志境内反动派这次得逞比1819年颁布《卡尔斯巴德决议》(Carlsbad Decrees)时的胜利更不堪一击,更加短命。
自16世纪以来,瑞士一批自治州组成的邦联就傲睨神圣罗马帝国,自由理念为它的傲立提供了合法性。拿破仑限制瑞士独立,强行征募瑞士青年去他的大军服役,瑞士人民加以抵制,通过斗争加深了自己的民族认同意识。一个带有半神秘色彩的人物威廉·退尔激励了瑞士人民。退尔是中世纪的瑞士弓箭手。据传,奥地利当局令他用箭射落放置在他儿子头顶上的一个苹果,他的箭穿苹果而过,显示了他的镇定自若和高超武艺。1804年,德意志诗人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写的剧本颂扬了这一传说。1829年,著名意大利作曲家焦阿基诺·罗西尼(1792—1868)在一部风靡一时的歌剧中讴歌了退尔。这部歌剧充满了那个时代的自由和浪漫情调。维也纳会议恢复了瑞士的独立地位和它传统上享有的种种自由。但1823年时,梅特涅和神圣同盟对瑞士享有的自由十分恼火,原因是瑞士的几个州利用自己的自由地位,向虽然失败但依然是潜在威胁的外国革命者提供庇护。维也纳会议列强迫使瑞士联邦压制流亡者的权利,同时限制新闻自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以及工匠、店主和大批农民对外国干预愤怒不已,结成同盟,呼应1830年法国革命,推动联邦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在10个州实行男子普选,保障言论自由。瑞士自由色彩最浓厚的城市苏黎世普及了6—16岁教育,免除穷人学费,同时大刀阔斧改革了市政府机构。
类似的和平改良也给英国的政治体制带来了巨大变化。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和以《六条法令》为代表的国家镇压措施开始显威,滑铁卢战役之后年代发生的骚乱和社会动荡逐渐消退。《六条法令》的内容包括严禁抗议集会,实行新闻检查,中止人身保护权,允许不经审讯就关押嫌疑人。然而,19世纪20年代末,一如欧洲其他地区,英国经济再次陷入低迷,让在1830年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手工业者日益不满。统治阶层惧怕后拿破仑时期社会动荡引发的那种革命,人民群众不满情绪滋蔓更令他们心惊肉跳。大批群众身披三色缎带、佩戴帽章,参加伦敦各处集会,聆听弗朗西斯·伯德特(Francis Burdett, 1770—1844)等激进政治家的演说。曼彻斯特的工人举行大规模集会,呼吁经济萧条期间不得削减工人工资。在远至东盎格利亚的南部各郡,农场工人焚烧干草垛和粮仓,捣毁机器,发泄对脱谷机的愤怒——大批工人因脱谷机的引入而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失业了。1830年,在英国首都伦敦,大批民众反对一年前新成立的制服警察机构大伦敦警察厅(Metropolitan Police)——成立这一机构本身就反映了当局对法律和秩序日益担忧。民众高呼:“不要警察!不要波利尼亚克!”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思想保守的首相威灵顿公爵抱怨道:“人们幻想,只要仿效巴黎和布鲁塞尔,就可以实现他们想象中的人民幸福繁荣的极乐世界。”他不满地说:“全国上下对改良丧失了理智。”
威灵顿政府因其顽固立场而倒台。1830年年底,一个由辉格党贵族领导的改革政府上台执政,决心在不断升级的危机爆发前化解危机。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当年震荡法国、比利时和瑞士政治体系的问题相似:中产阶级改革者、工匠和小农都渴望放宽法律限制,享受集会结社和新闻自由,更重要的是扩大政治参与。英国新一届政府提出了一项改革法案,旨在根除一些荒谬的现象,比如“腐败选区”(人口很少的村镇在下院也有一个甚至两个席位)和“口袋选区”(地方显贵提名本地议员),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等新兴工业城市在议会没有自己的代表,以及连续几日公开投票造成的大范围腐败。改革法案被上院的世袭贵族和高级教士否决后,革命的苗头很快显现。全国很多地区发生了骚乱。诺丁汉城堡被夷为平地,布里斯托尔的主教宫、45栋私宅和一座监狱毁于大火,12人丧生。一名议员感觉国家“正处在暴动前夜”。作家西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 1771—1845)称,政治精英吓得双手发抖,肚子抽筋。民众群情激昂,激进的演说家推波助澜。国王无可奈何,只得同意增加辉格党贵族人数,以压倒上院的抵制,威灵顿及其支持者也被迫让步。
1832年,《改革法案》在议会两院获得通过,成为法律。法案消除了不合理现象和欺诈行为,但在这次与法国和比利时政治体制变革相仿的改革中,选民人数仅增加了45%,还不到全国人口的5%。就扩大选举权问题展开的辩论产生了一个新概念,就是“中产阶级”。如首相格雷伯爵(Earl Grey, 1764—1845)所言,“无论是在财产上还是在知识上,中产阶级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构成了真正的公众舆论主体”,“没有中产阶级,乡绅权力就没有任何意义”。如同欧洲大陆的激进分子,主张给予所有成年男子选举权的英国激进分子强烈抨击改革的不彻底性。《贫民卫报》( Poor Man’s Guardian )称,这是“人们可能提出的最不自由、最专制、最糟糕的措施”。以上论调并没有很快消失。不过《改革法案》至少暂时平息了公众的愤怨。随着地方政府及行政方面的进一步改革,英国的政治体制在一个相对开明的新基础上稳定了下来。人们围绕改革展开激烈斗争,最终产生的宪法和政治体制与1830年实现成功过渡的几个欧洲国家的大同小异。英国与几个欧洲国家的区别在于,至少从中短期看,英国的改革更耐久,更能抵制改变现状的新尝试。《改革法案》的主要推动者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 1792—1878)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称,这次改革将“一劳永逸”。